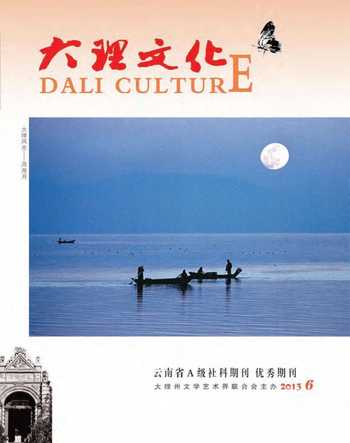煙站記事
吳安臣
熙來攘往皆是客。現在我躲在我屋里乏力地想。很久以來我把這間屋子當作一個無法搬動的固定的巢,這個巢似乎應該永遠屬于我,只要我想躲在這個巢里,似乎沒有人能把我拽出來。寂靜的巢包圍著我,在巢里看外面的風風雨雨。云卷云舒。這個巢雖然破舊,但有恒久的安全感,我的巢我做主,時至今日我發現其實我錯了。這巢終究要離我而去,現在我得自謀去處了。
我住的地方叫煙站,我寄宿好久了。六年前我就住進來了。時間一長我就產生了錯覺。以為自己是這兒的主人,潛意識覺得這個事實應鐵定無疑了。我在那片滿是瓦礫的地方挖了一塊菜地。我把那土弄得適合任何蔬菜生長,肥實、平整。但是那塊土地而今我無法搬走。我最多臨走時多望它幾眼,以示我的留戀。
我甚至想象著將來我要在這片茂盛的草地上養一大群羊。到那時白如雪般的羊在我們面前晃來晃去,那滋味一定不比一個美國的農場主差,同大院的老董也是這么想的,很可惜他也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雖然他的想象甚至超出我們的院落延伸到外面的荒地上,但他也是時至今日連羊毛都沒見到一根。這時主人來了,他們在我們的外面任意地挖,任意地改造,把一切弄得缺少章法,打亂了我們經營的秩序。但我們只能看著,表情再不能漠然,因為人家隨時可以說你們可以在某時搬走了,那時我們只能夾起尾巴走人。我們只是一些寄居蟹而已。我們的命運就是被驅逐。仿佛移民。
還清楚地記得我剛剛分進學校時,一卷行李和著一身臭汗。氣沒喘通,總務主任就例行公事地對我說:“小吳。學校沒房子給新來的老師住,委屈你一下,你去煙站住!”我才來就要委屈。這委屈的日子還要過多久?心里憋屈,但沒敢說出口,因為毛主席說過。干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揀瘦。年輕人不去住。難道叫那些老教師住?但是煙站在哪?剛要問總務主任,卻見他已經丟下話走遠了。他全不把我當回事。我大聲問,他遠遠地回答,“出校門一直往下400米左右,見到右邊的鐵大門就是。”
八月了。太陽仍然賊毒。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長。毒日頭似乎要把我曬成干巴才會罷休。孤獨的我又是一身臭汗蹣跚到煙站。大門倒是敞開的。不算冷漠。但我心里總感覺怎么像剛進門的新媳婦就給打入冷宮一樣的凄落。孤獨的我面對著一個空曠的大院,除了一棟陳舊的住宿樓,其他的都是墻面斑駁的倉庫,倉庫上依稀可以看到背陰的地方有不斷向上蔓延的青苔。真可謂“苔痕上階綠”了。悵然若失地找了一塊地方坐下來,卻看到那瘋長的雜草好像一下就會蔓延到自己腳下,幾棵樹在火辣的太陽下雕塑般靜默著。遠離了霓虹閃爍,遠離了書聲瑯瑯。再加上青燈古佛,看來在這兒若要修煉成仙的話倒也不失為一個好所在。一陣苦笑。我看到有些房間的門已經不在了。看來盜賊連門都沒放過。沒有入住感覺這神經就進入了戒備狀態。果然我們住進來后光摩托車就丟了三輛。當然這是后話。看來,學校想讓這已經廢棄的院落來點人氣熏染,除了那些野貓,野狗,我是第一個正式入住這荒蕪院落的成員。
找到寫有我的名字的那扇門。心中算有了著落。推開門,感覺頭被什么給纏住了,細看是蛛網,蜘蛛在這扇還沒被偷走的門口設置了一個大大的陷阱。想不到今天網到的居然是我這樣一個它吃不動的大獵物。一地的老鼠屎,看來老鼠也沒少光顧這兒。再看看擋在門下方的木板條,那上面已經被鍥而不舍的老鼠啃了一個很大的洞,不知它在這洞里出出進進多少個來回了,這荒蕪的房間在前肯定是它休憩的大廳。荒蕪的院落,荒蕪的房子,加上一個懷著荒蕪心情的我。蒼涼感就鋪天蓋地地傾瀉了下來。也罷!不要給我晚上在床上抬頭還要數星星就行了。推開蒼蠅屎密布的窗子,直撲眼簾的卻是窗外的一丘荒冢。頭稍微伸出去點,甚至還可以看到碑心上的字。是什么老孺人,還是什么老先生之類。至今沒心情仔細去看明白,總之一晃時間已經過去了六年。
一扇窗子隔開的仿佛就是陰陽兩界,他(她)擁有窗外天地,我擁有窗內人生,各自相安無事。記得入住進來的第二年一朋友來訪。夜宿我處,我說叫你一個人睡這,你敢嗎?他說這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時窗簾還拉著,那夜月色如水,我呼一下把窗簾給拉開了,把他拉到窗子跟前,月色下那荒冢上的草在夜風里不停地擺動著。兀自增添了幾分陰森氣象。這一看他說,你這家伙明天說給我不行啊?于是那晚上他一直纏著我吹牛,直到我眼皮再也無力抬起。他說了些什么已然記不清楚,但很清楚地記得他第二天眼皮發泡,印堂發暗,我啞然失笑。多大膽的人。居然就被那似乎游蕩在外面的魂兒給弄得失了眠。從此我的朋友大多不會在晚上來找我,都戲稱晚上來你這一會,保不準帶著個青面獠牙的什么精回去。也好,晚上正是我的寫作時間,我說。不來的話倒也合適。
之后我搬進了很多的書,睡著看,站著看,走著看,全在斗室之內,接著滿腦子的亂想。想到昏昏然。想到不明所以。寫下了滿紙荒唐言,四處投稿但石沉大海。時至今日寫作上已有些許收獲,感覺沾了點這地方的“仙氣”,還暗自竊笑呢!那時關起門來獨自咀嚼痛苦的滋味,慢慢的療傷之后覺得陋室還是太小。所以緊閉了心門,方覺還是出去到外面呼吸一下空氣為好。于是約三五同事在大樹濃蔭之下殺上幾盤軍棋,這要不了多少智力的游戲。也倒幫我們打發了不少時間,為一盤棋幾個人吵得面紅耳赤。甚至為此迷到把煮飯的炒鍋也給燒爛了,但過后依然要殺棋,仍然不亦樂乎,初入煙站的樂趣或許就這些吧。跟高雅似乎沾邊,但又都是些俗人的玩法。但畢竟是快樂的。
但好景都是難以持久的,不久就聞到外面的惡臭。去查訪了一下發現原來是外面有一個酒廠,又喂了許多被酒糟催肥的大豬,這些豬制造垃圾可是一流的。可害苦了我們的鼻子。不過還好!這惡臭是過一段時間才會飄來一回,開始我覺得作為這兒的主人。我們有權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空氣問題不可小視,但是交涉幾次沒人理我。這個時候我就躲回斗室內苦讀,要么寫點阿貓、阿狗的文章。繼續懷揣著它們能變成鉛字的愿望,不斷地希冀。編織自己夢想的美麗霓裳。你別說真有一些文章見報了。那份欣喜真的讓人忘卻了豬糞的惡臭。仿佛修煉已臻無色無味之境界。
至此我堅定地把自己視為煙站的主人了,于是后來進駐院落的我似乎都可以把他們當成敵對者,可以發自己的滿腹牢騷,可以對他們說我的意見,他們還只得聽著。第一撥人是一伙架高壓線的,外地人。他們是我入住后的第一批“侵略者”。他們似乎忘卻了他們外來者的身份,開始就肆無忌憚的談笑。南腔北調的聲音回蕩在我耳邊。很不受聽,于是我沉著臉去表達我的不快,他們呢,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于是就有一個主管跑過來趕快遞給我一支煙,我擺擺手,他把手尷尬地縮了回去。不好意思的笑著說。以后一定不會影響你們了,我們這些工人不知道這些,請你們原諒之類,果然以后清凈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漠然地看著他們。覺得自己的空間已經被局部侵犯了,他們不止于礙眼,簡直要把我憤怒的火焰點燃了。
第二撥人來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的干預有點乏力了,因為他們是來收煙的,儼然房東一樣的高傲。不斷進出的騾馬和車子,各色人等,把這個煙站弄得像個熱鬧的集貿市場。不斷飄揚的粉塵和煙葉的味道充斥著我脆弱的腦袋,我茫然地看著外面。好像我的殼已經成為外面這個喧嚷世界的殖民地了,我的眼里飽含屈辱的冷光。后來收煙的不斷壓級終于引發了一場“戰爭”,那時騾馬奔走。煙農們拿著扁擔怒視著收煙的。我的心里不知是該快意呢。還是該惱怒。總之這件事弄得我感覺自己像個清末的中國公民。就好像日本和俄國在我的國土上打仗一樣,我已經不能保持領土完整,但是我也只是敢站在幕后冷眼看這一切。并且很清楚即使自己站出來了。沒人會認我這根“蔥”。或許人家還嫌我礙事呢。后來政府出面把爭端平息了。但告誡收煙的不管什么等級的煙都要收。那些收煙的迫于壓力強忍怒氣收了一些垃圾煙。收來后也不拉走,大火一把燒在外面的曠野里。于是整個煙站彌漫著尼古丁和焦油的味道。出門很遠感覺那股味道還在追尋著我。幾乎窒息的我到外面大口地喘氣。在自己的住處我幾乎被尼古丁和噪音害死了。卻沒有向任何地方申訴的權力。更無人說這不公正。那段時間我的神經向著崩潰的邊緣滑行,我無心再把腦袋扎在書里了。那些人終于丟下一些爛煙葉走了,人走了,但是氣味仍殘留著,我愈加感到這個領地的非真實性。
第三撥人是收亞麻的,因為他們看中了我們這兒閑置的倉庫,和收煙的差不多一樣的忙亂。仍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糾結和矛盾。誕生著新的噪音。新的煙塵,那些帶著鋸齒狀的亞麻隨時追隨在我褲腳上。我小心翼翼的讓著它們。但是最終我還是被它們包圍著,無辜而無奈。照樣沒人理會我,仿佛我也是外面來的一員。學校也不出面干涉,于是我只有忍耐。我想養一群羊來占據草地的愿望不斷地建立起又被毀滅掉,因為草地總是有很多人去踐踏。把一塊甚至可以做高爾夫球場的草地弄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那些亞麻堆在倉庫里后,他們還特別叮囑我要注意火燭,不然亞麻著火了我似乎脫不了干系。仿佛已經提前告誡過我這個“縱火犯”,我再次感到窩囊和憋屈。看來一切都是虛假的。我也只有住在這里的權力。屋子漏水了。我剛剛想修補下。學校領導就說我只有看守權。沒有改造權,于是大雨天我在屋內看小雨嘀噠。心痛得仿佛陳子昂登上幽州臺,獨愴然而涕下。想哭。但是覺得雨水就夠多了。再加上淚水這陳舊的房子怕支撐不了這巨大的哀愁,省了眼淚,心里卻梗了一樣硬物樣的不暢。
再后來就來了煙站原來的主人。他們一來就財大氣粗的動動這,動動那,對哪兒不滿意就敲下。打下,隨自己的意愿,我看到的不再是些所謂的“侵略者”,而是房東,房東對我還算客氣,于是我開始變得誠惶誠恐,仿佛這些年來貪了他們很多便宜,撈了很多好處,那位經理對我說,他要把外面我們原先下棋的石桌敲爛。改成花臺。我說行,你家的東西嘛!他說你幫我參謀下,我說我不懂。逃開,看,他給我了多大的面子啊!
愚鈍至今方悟到:其實進進出出的都是過客,看來只有那些隨意改造自己的巢的人才是主人,其他的最終都只得選擇離開,我的巢不在這里。我仿佛第一次從巢里走出來。這時我發現陽光太刺目,我有點眩暈了,老窩好像就這樣給人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