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清供
陳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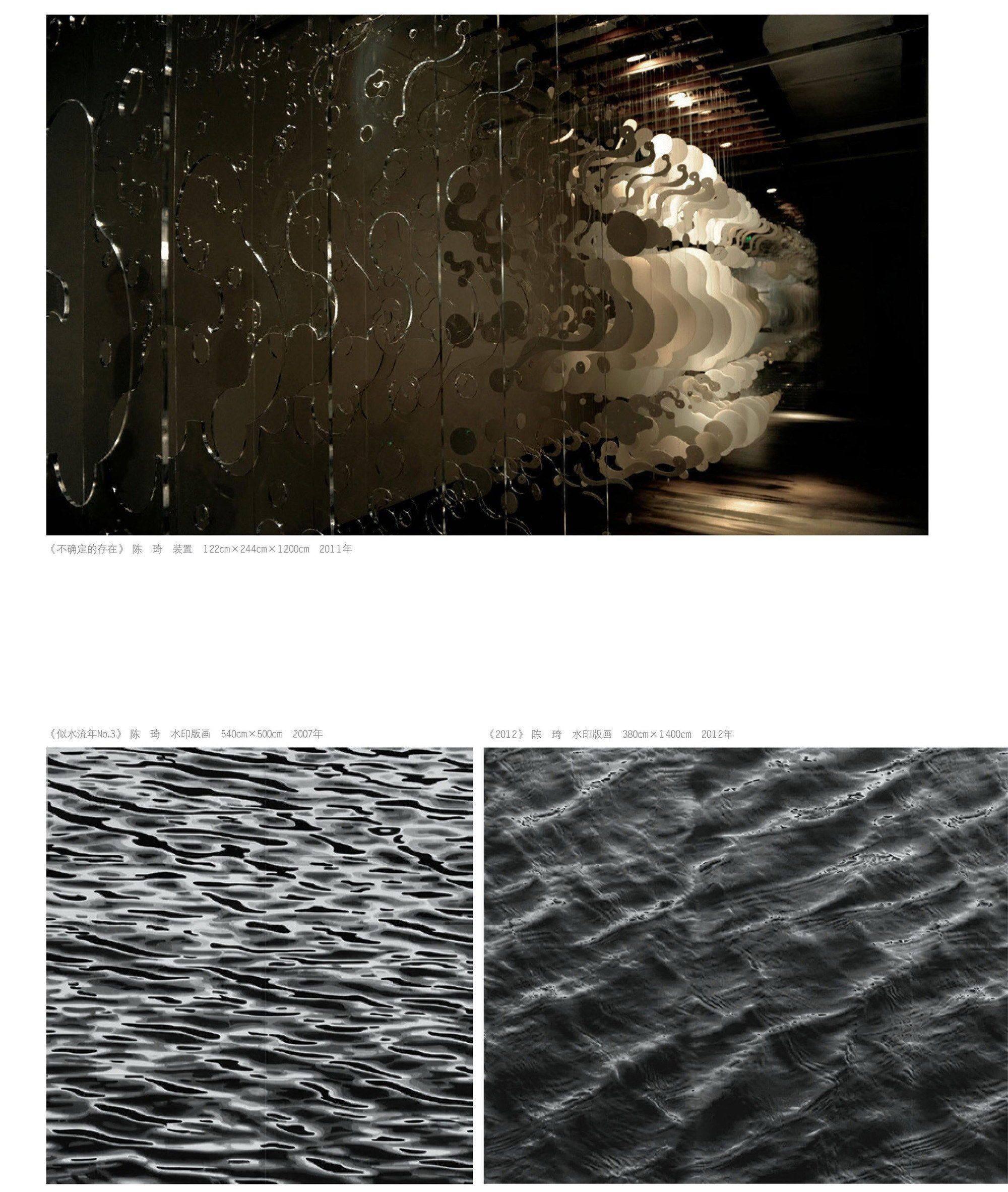


1982年我上大學時,正值改革開放前期,禁錮已久的國門洞開,西方各種藝術思潮狂飆涌入,此消彼長,光怪陸離,令我們這些初習繪事的少年目不暇接。當時雖看不懂那些新奇古怪的畫面,心中卻有一種莫名的激情在涌動,于是瘋了般畫了許多很“現代”的油畫。日子久了反覺空蕩蕩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這樣做的意義。于是,心中慢慢萌生出一個疑團:繪畫是什么?我為什么繪畫?
繪畫是什么?繪畫的意義何在?似乎是個不著邊際的話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也許沒有人能說得清。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必須厘清的問題。否則,我畫畫便毫無意義。帶著這個疑慮,我請教過許多人,也試圖通過閱讀藝術史找到答案,結果都很失望。后來明白,這個問題別人無法幫你,必須由自己來解答。此后我便不再盲從于新潮的藝術流派,也不被新奇眩目的藝術形式所誘惑,而沉靜下來傾聽自己的心聲,并將這種心聲幻化為胸中的意象,再通過畫面呈現出來。
從1986年至今,我的繪畫活動基本在這種狀態下持續進行。許多作品隨著我生活的旅途遷徙自然而成,盡管存有缺陷,卻是內心最真實的鏡像反映,它們經大腦醞釀、剪裁、編織而成,其基礎是流動的意識與凝固的情感,是心靈深處抽象意識的外化。那些在我作品中出現的人與物或場景,如南京城外郊縣的風景、兒子的蝴蝶模型、書桌上的水晶煙灰缸、朋友的古樂器、池塘的荷花等等,都是我親臨而熟悉且在心間反復觸摸成型的。它們見證了我的生命過程,記錄了內心大千世界的起伏和情感的脈動。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繪畫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有著不同的功能。比如中國文人畫和同時期西洋宗教畫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完全不同。在我看來,谷溪的《六柿圖》遠比倫勃朗的自畫像更能使人感動。正因如此,美術史的記錄或評價角度也各不相同。同時繪畫對每個人來說意義也不相同,有以繪畫為謀生、有以繪畫悅心、有以繪畫娛樂等,作為一個畫家對此須有清醒的認識,否則便難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目標。
繪畫對我而言是一種探究人生意義的途徑。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在于人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以及人對生命意義的思考。所有的宗教或哲學命題都跳不出這個范疇。參悟生命意義的形式有多種,苦行、打坐、面壁、靜思、祈禱、游歷、寫作等等。我將繪畫當作自己參悟的必修課程,繪畫便是參悟,繪畫的過程就是對自己內心的探幽、對生命的追問、對人生的解讀。我曾說過:“我作品中的空靈與幽深其實來源于我年少時對繪畫的困惑和人生的迷茫。因此一直在繪畫中找答案,希望找尋一種能把自己完全安放進去的畫面世界,使自己的人生、精神上的擔負得到解放 ……”
或許正是這種人生迷茫與困惑和找尋答案的堅定信念,每每使我在一幅畫稿上長久地流連,介乎于理想與現實、真實與夢幻之間徘徊。對生與死的體味,使我對萬物世界保有距離的優雅審視,但好奇心似乎總是抑制不住地將我瞭望的目光延伸到風景背后的精神花園,這種審視帶有一絲超然、欣賞與贊美,但更多是主客體間的喃喃低語。我希望在我的作品里能以可見的第一自然洞見不可見的第二自然。當繪畫不再承載圖像紀錄或再現淺表的生活情境并同時擺脫功利目的時,便獲得了極大的自由空間和更寬闊的文化意義。
一次偶然淘書,我翻到朱良志先生新近出版的小書《生命清供》,立刻被書中的清新優美的文字、深厚的文化底蘊、敏銳的洞察力、脫俗的見識和邏輯森嚴的論述吸引,一氣讀完后,竟有闊別已久老友相逢之喜悅,也因此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藝術信念,對我而言,繪畫不正是一朵伴隨自己生命歷程,永不凋謝的幽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