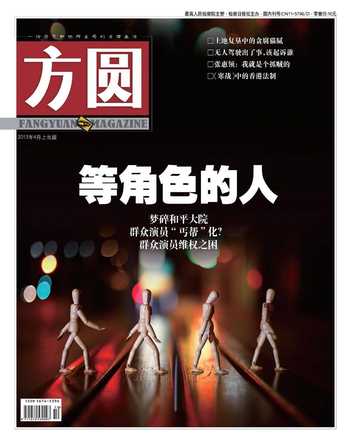多種了五畝三分田
朱建中 徐建強


【√】五畝三分地的荒廢得失,牽動著一個典型農夫的所有情感,觸碰著兩個宗姓的敏感神經。在那偏遠鄉間,當制定法秩序遭遇風俗宗法時,包鑲著國家強制力外殼的冰冷法條,其內核該閃爍著怎樣的人性之美、理性之光才能點亮世道人心
我的老家在陸莊,只是蘇北宿遷農村一個普通村莊。在那里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后來考上大學、進入檢察機關,成為一名檢察官。
盡管跳出農門多年,但城市生活并沒有讓我“脫胎換骨”,忘卻農村生活的印記。“中國鄉村法治調查”給了我一個回望故鄉時代變遷的法治視角,讓我憶起老家六爺因為“多種了五畝三分地”而陷入的一場官司。
同源同宗的陸莊
案件起因是土地原主人唐守東向實際耕種者——六爺討要五畝三分耕地,用法律術語說其實就是土地用益物權(指依法對一定的土地占有,并加以利用取得收益的權利,包括土地承包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糾紛。
案情簡單但背景極為復雜,理清其中關系,需要從陸莊的歷史說起。陸莊區域面積僅4.5平方公里,耕地1812畝,最鼎盛時期總共也不過40戶人家。除了張、唐兩家,是與陸姓沾親帶故的外姓,清一色姓陸。據說往上追溯幾代,都源于從外地逃難而來的一家9兄弟。
同源同種的陸姓宗族向來睦鄰團結,雖然鄰里間因家長里短、雞飛狗跳等引發打罵的事件偶有發生,但矛盾自有解決辦法:小事自行了斷,時間自然消弭恩怨;疑難復雜事件則由德高望重的長者出面做主。“法律”對于陸莊人來說是個遙遠的詞匯,“打官司”更是前所未聞。
傳聞早年間,兩個堂兄弟因宅基地邊界問題爭執不休、大打出手,連共同的祖父都未能勸解,生產隊長便請出輩分最高的五老太。聽聞事件原委后,五老太先是不慌不忙地給祖墳燒罷紙,然后就劈頭蓋臉地將雙方三代輪流罵了一通,罵畢,五老太下令各家讓出半米地方留作公共通道,一場干戈就這么化了玉帛。
所以一直以來,陸莊別說嚴重刑事案件,就是一般民事糾紛也少有發生。然而小村的平靜終被打破,外姓村民唐守東竟因幾畝薄田起訴六爺,大姓竟然被小姓人家告了,這種“撕破幾輩子老臉式”的打官司方式,讓陸姓人家驚詫,更讓作為被告的六爺心里無法接受。
覺得面子上受了奇恥大辱的六爺采取的第一個應對措施是進城找我,見面就要聘我替他打官司,并且“不問花多少錢也要把案子扳回”。
“官二代”六爺
六爺與我是“未出五服”的本家,六爺的品行家境我都比較清楚。他是我二老爹的小兒子,爺和老爹是家鄉的俚語,按照標準的稱呼應該是叔叔和爺爺。二老爹是抗日老革命,解放后一直擔任村支部書記。
村支書雖算不上官職,但在陸莊,有此出身的六爺用現在流行語來講也算是“官二代”。但二老爹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的人,一生公而忘私,據說當年大集體分田到戶的時候,他也沒利用職權給家里多分一畝地,只給六爺留下了一筆“忠厚傳家”的精神財富。
因此,六爺這個“官二代”當得可沒有城里的那些舒服。六爺也是屬于老黃牛般埋頭種地的典型農民,一輩子含辛茹苦地在田里耕作。但早年種地是靠天吃飯,遇到收成不好,“繳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所剩只有一點口糧和籽種,因此六爺家的生活光景一直在溫飽階段徘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于糧價低賤而“四糧七錢”賦稅沉重,不少頭腦靈光的農村人紛紛拋荒土地,離開村莊另謀出路,但六爺依然孜孜不倦地耕耘家鄉的田野。
其實,原告唐守東原先也陸莊人,屬于村里少有的外姓人家。1996年,唐守東為了“認祖歸宗”,把家從陸莊搬到了2里外的唐莊,并且本人也進城務工。人不在,家也不在,唐守東之前在村子里分的五畝三分田,就逐漸荒廢了。在陸莊人看來,唐守東從陸莊搬走,不過問位于陸莊的五畝三分責任田,就等于說他已經不是陸莊人了。可是,因為種地不掙錢,當時陸莊也沒人愿多種這幾畝田,導致這地一度拋荒。
此時,陸莊生產隊的隊長看六爺“侍弄莊稼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便找上門來讓他耕種唐守東放棄的那五畝三分田。因心疼良田荒廢,六爺沒有猶豫就應承下來,這種行為甚至被村里人笑話為“犯傻之舉”。
誰料,從2006年起,國家全面取消了農業稅,種地不但不要錢,還發種糧補貼,一畝地一年就補一百多!六爺家占有“生產資料”——土地多這個優勢開始逐漸凸顯出來,加上勤勞肯干,他家逐步富裕。
本莊有人總結他家致富經,除了打工積攢、副業收入以外,會特別提出讓他增產增收的五畝三分田。嘖嘖咂嘴羨慕他時來運轉,以往誰都不愿多種的拋荒地,結果他一種國家就免了農業稅,
五畝三分田的官司
五畝三分田,是讓六爺陷入糾紛的開始。而唐守東則覺得,自己狀告六爺也有苦衷。
由于農村現代化發展提速和城市化浪潮擴張裹挾,陸莊已漸漸成為臨城的近郊,環境宜居,交通便捷。看到新農村開發,土地附加價值不斷提高,當初在唐莊賣房讓地給唐守東的那戶人家在2007年竟然“非轉農”逆流返鄉,并反悔原先的賣房贈地行為。唐守東一打聽原來農村宅基地是集體土地的小產權房不能轉讓,也就是說他的購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無奈之下,只好盤算再要回陸莊的五畝三分地。
自知無法從陸莊獲得支持,唐守東咨詢法律人士了解到土地承包年限是30年,他的承包還未到期。有了這點底氣,他試探著找六爺協商要地事宜,卻遭到拒絕。
在六爺看來,唐守東1996年搬走時隔12年又回過頭來索要原屬他家但目前被六爺耕種的五畝三分田,簡直是“倒打一耙”。2006年,六爺找到隊長要求長期耕種,當時隊長答應這五畝三分地讓他免費種到“大動地”——新一輪土地承包期開始為止。因此,六爺判斷是唐守東搬離陸莊,以拋荒的方式把這五畝三分責任田退給了陸莊生產隊。而六爺恰巧又從生產隊承包了五畝三分地,但此地和唐守東退出的地毫無關聯。所以,唐守東就是想要地,也應向生產隊要,六爺和他是沒有任何瓜葛的。
而陸莊人也都認為,唐守東早不要,晚不要,偏偏在種地不要錢、給補貼有利可圖時要,完全是財迷心竅。六爺氣憤地說唐守東純粹是惡人先告狀。況且,這五畝三分地中還有一畝多是唐守東家“私吞”的集體社屋地。六爺回憶到,當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個叫張矮子的南京知青下放在陸莊,就住在村莊東首的社屋。文革結束后,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張矮子過了很久才得以回城。張矮子走后,他居住的社屋無人問津,幾年后茅舍坍塌夷為平地。這一畝多的空地被緊鄰的唐家不斷蠶食,據為己有。
但唐守東仍不死心,又找村委負責發放種糧補貼的會計,希望取得補償款。會計是唐姓族人,一開始還提出個方案想從中調解,沒想到被六爺頂了回去,發誓再不過問。
后來兩家動靜鬧大,“驚動了官府”,鎮政府便派干部下來處理,但村鎮干部工作方法失當,導致雙方矛盾激化,陸、唐兩姓差點“揭竿而起”,事情最終不了了之。
庶出的唐守東
六爺說:“這事要怪也只能怪唐守東自己,通過搬家就能洗刷‘庶出的命運?”
說到庶出,就不得不提一下唐守東的身世。原來唐守東1950年在陸莊出生時,他的父親已在老家唐莊先有家室。由于 “重婚”是發生在解放前,雖然一夫二妻,家庭內部矛盾不斷,但政府對此“不告不理”。幾十年里,他父親“走婚”于陸、唐兩莊。
應該說在集體時期,作為第三者和外來戶,唐守東的母親遭到各種輿論非議,那時正值二老爹當政,多虧了他的寬容和收留,他們母子才能在陸莊分得田地棲身度日。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六爺恨極了唐守東的忘恩負義,認為他是惡人先告狀!
背負“二房庶出”名分,唐守東自強不息,計劃經濟年代先在村部當了七八年會計,“政治上有了些資本”。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又搞禽蛋養殖,夯實了“經濟基礎”。不像其他農民有錢就翻蓋房屋,1996年唐守東聽聞唐莊有人進城想賣房,便一舉買下他的田地房舍,全家搬遷唐莊,此舉曾轟動一時。
但在陸莊人看來,搬遷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無非是想通過搬家表明他已正式被唐姓家族接納。加上他把陸莊的舊屋半賣半送給了他的二弟。稅費不繳、田地拋荒不種,更不再向陸莊繳納各種用于灌溉、鋪路等公攤費用。據此六爺堅定地認為既然唐守東當初如此決絕地搬離陸莊,十來年都未對這個組織盡過義務;而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集體——陸莊村委會,就有權與他徹底了斷,無任何牽連。
平心而論,唐守東也不是非要種這地不可,更不是特別注重一年幾百塊錢的種地補償款,已然有了法律意識的他更看重的是確認權利,以便將來獲得更大利益。
這個更大的利益是什么呢?原來陸莊所屬城市的開發區已經擴展到村門口,征地拆遷指日可待,土地利益豈容他人窺視?
不算復雜的法律糾紛
我告訴六爺,作為一名檢察干警,不能以律師身份代理案件,但我仍會向他提供法律服務。如今法治社會,不存在花錢扳回案件,當被告也不用驚慌,更不是恥辱,依法應訴便可。
站在法律的角度看,這是一起并不算復雜的訴訟糾紛。
因為根據規定,農村集體組織的成員只要沒有農轉非、遷入市區,在土地承包期限內,不論什么理由,承包地都不能被收回。也就是說唐守東雖然12年前就從陸莊搬走,將土地拋荒,不繳納“四糧七錢”,但因為仍在30年的土地承包期內,所以唐守東仍然享有在陸莊的五畝三分地的承包權經營權。
可是內心預判官司必贏的六爺,在我搬出土地承包法向他詳細解釋說明之后,神情變得沮喪。
法律雖然如此規定,我還是分析了案情發展存在的不同可能:如果唐守東對政府不能為其確認土地承包權不滿,狀告政府,六爺可作為共同被告。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會判決讓政府確認五畝三分地的承包權的所有人。
而如果唐守東以六爺為被告,訴求六爺歸還土地的用益物權——經營種植權,如果六爺能夠拿出證據證明唐守東在承包期間自愿放棄承包地的權利,而他本人包地又獲得全莊2/3以上的成員同意,并依據有關程序和陸莊簽訂了承包合同,就有可能依法享有耕種這土地的權利。無論怎樣,考慮到六爺實際耕種土地并在土地上施加肥料精耕細作而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就憑這一點他也有權獲得相應的補償。
事實上,唐守東與六爺的訴訟還有一個關鍵點:主要證人——當時和六爺達成協議的時任隊長,后來不知什么原因竟中風失憶,失去作證能力。六爺認為隊長是有權決定陸莊土地的人,即使要2/3村民同意也沒問題,畢竟整個村莊幾乎是陸姓一家。只是后悔當初沒有與隊長簽下正式的協議,埋下今日口說無憑、承諾成空的隱患。
我安慰六爺,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國家基于集體組織成員的身份,給予農民的一種權益。別人搶不走,自己也不能隨便放棄。從六爺本身來說,辛勤耕種這本不屬于他的五畝三分地已經給他帶來過不小的收益,盡管前期也繳納“四糧七錢”,最終這土地還是要歸還給有關組織和個人。
我空洞無力的法律語言最終沒能說服六爺。后來,因為不能提供有效的證據,五畝三分地被判給了唐守東,但判決仍然沒能“擺平”糾紛。六爺依然不愿放棄已經固守多年的田地,雙方爭執不下,這片曾長滿莊稼的土地便再次荒蕪。
》》觀察員手記
失靈的鄉村矛盾解決機制
用唯物主義眼光判斷這起訴訟爭端,其實質無非是當下基于土地而獲得的現實或可預期的經濟利益,但交織著農民對土地感情、農村的宗族矛盾的案件絕非“多收三五斗”這么簡單。
這起案件讓我重溫農民與土地血脈相連的天然感情、再陷法理、情理形同水火的現實糾結。五畝三分地的荒廢得失,牽動著一個典型農夫的所有情感,觸碰著兩個宗姓的敏感神經。
在六爺的夾敘夾議中,我了解到村委會和鎮干部兩次斡旋失敗,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原因:由于外出打工人員多、參軍考學人員多、留守老人兒童多,經濟待遇少,如今的陸莊從2007年以后再也沒有選出過生產隊長,雖然名義上陸莊由村部“直轄”,但這種無序的村民自治已非過去的鄉村自治。
在陸莊過去的鄉村自治體系中,年齡、輩分等因素促成了村莊里必然有“說一不二”的人存在,例如五老太。他們在糾紛出現時最重要的作用是:先各打五十大板,再居中調停。而村民基于對調停者個人的尊重,以及對宗族禮法的發自內心的遵從,于是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而村莊城市化進程里,最明顯的變化是禮崩樂壞、一代不如一代,導致一直頗為有效的矛盾解決機制失靈。而在當農村歷史遺留問題引發矛盾紛爭時,現代法律對于村莊糾紛的調整雖然合法,但“情理不通”。
六爺不能理解法律為什么不能尊重土地已被他耕種12年的事實。表面上六爺對我的分析不置可否,但我隱約感到他內心已經拿起了準備戰斗的武器:作為陸莊人,他維護的顯然已非五畝三分地的種植權,而是沒有隊長的村莊的共同利益,甚至還有宗族的顏面。
末了他有點堂吉訶德般地宣示:不論官司輸贏,結果只有一個,這地只能留給陸姓子孫,外人誰也搶不去,肥水豈能流到外人田?相反,如果他把地給了唐守東,必遭本莊人怒罵、外姓人嘲笑。
去年,六爺帶著對法律的不解,或者還夾雜些許失落離開了人世。
當下,農業經濟發展帶來格局調整、農民法治意識不斷覺醒。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來的法律工作者,我時常叩問內心:在那偏遠鄉間,當制定法秩序遭遇風俗宗法時,包鑲著國家強制力外殼的冰冷法條,其內核該閃爍著怎樣的人性之美、理性之光才能點亮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