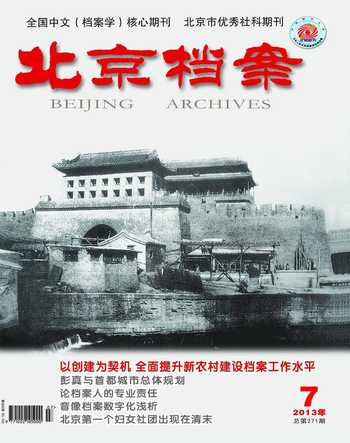給北京帶來嶺南文化的廣東會館(三)
張衛東
在北京盛行的廣東音樂
北京素來有喜好廣東音樂的民間組織,其實這種組織最初也是經廣東會館傳播開的。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李君盤、劉樹楠為翔千學堂和實踐女子學校籌款,在天樂園(大眾劇場)舉行義演,2月14日晚,上演的節目中就有廣東音樂以及管弦合奏、簫笛合奏、喇叭單奏等。
揚琴也是經過廣東會館的舉子們傳來,最初叫“洋琴”,后改稱“揚琴”。這種樂器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愛,早年在口語上還叫“蝴蝶琴”、“打琴”。后來被廣泛地用在北方曲藝中,不但在梅花大鼓中使用,還能獨奏。民國年間翟青山使用揚琴主奏,逐漸發展成一個獨立曲種“單琴大鼓”,后經關學曾繼承改稱“北京琴書”。揚琴已經是北京俗曲演唱中的主奏樂器,卻少有人知道它是經廣東會館傳來的。
民國后的廣東音樂在北京更是盛行,多是居住在廣東會館的學生帶到學校中。后來的匯文、崇實、育英等中學也都有廣東音樂社團,中國大學還有獨立的音樂藝術團。參加這一時期的演奏者多數已經是地道的北京人參與了,現年90多歲的滿族老畫家穆家麒就是當年匯文中學的樂手。廣東音樂在北京發展至今,卻成為幾乎沒有幾個廣東籍的群體,這種藝術在北京可謂是南花北移。因廣東省是孫中山先生的家鄉,所以民國以來把廣東音樂稱為“國樂”。現在喜好廣東音樂的民間組織在北京還有一兩家,至于在公園演奏的愛好者就更多了。
北京松風國樂社成立于1944年9月,由當時北大學生楊雨金、馮葆富、王貽炬等發起創辦,還有社員崔文治、羅廉、臧爾忠、倪寶恕、羅作新、李淳、裴新生、席福盛、白祥麟、鄧振瀛、翟峻岑、藍寶年、孫寶正、劉實、鄺宇忠、雷慶文、吳川、周璞、白子潔、馬殿騶等。該社每周六晚和周日下午及晚上活動,在王貽炬的父親家里。
這個樂社有近10年的活動經歷,是北京民間的公益性組織,為社會上義務培養了不少民樂人才,其中一些成員步入了專業音樂團體及音樂院校。松風國樂社如同北京推廣廣東民間音樂的一所學校,他們還不斷研究印制學習資料,曾經編印了《粵樂彙粹》、《絲竹樂曲集》等4冊。李凌著的《廣東小曲》曾引用《粵樂彙粹》部分素材,廣東音樂家甘尚時與天津音樂學院趙硯臣,以及余其偉所著的一些有關廣東音樂書籍中,都對“松風”資料做了引用。松風廣東音樂社經過近10年的積累,樂曲達數百首之多;還曾在北平電臺、勝利電臺、華聲電臺、聯合電臺等直播演奏節目。
解放后,松風國樂社以吹打樂《聞勝起舞》、《拿天鵝》,以及合奏《翠湖春曉》等曲目,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演出,由北京師范大學楊大鈞教授指導排練。新華電臺當即為這幾段樂曲錄音,播送后,聽眾反響強烈,因為這個電臺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傳播覆蓋面很廣。后來電臺還吸收了樂社的王貽炬為文藝科成員,自1949年8月1日起正式錄制批量節目,以“北京業余國樂研究社”的名字取代原來的“松風”。從此這個樂社的演奏水平日益提高,還錄制了廣東音樂《秋水龍吟》,以及絲竹樂合奏《萬年歡》等唱片出版發行。“松風”于1954年夏停止活動,但原來錄制的廣東音樂以及絲竹音樂仍不時繼續播放。
1984年10月14日,在北京舉行了紀念“松風”國樂建社40周年座談會,后來在北京的一些“松風”老社員們又開始恢復了活動,還在中央電視臺《夕陽紅》、《怡情雅趣》、《長壽天地》等欄目中,展示過他們的演奏。
現在北京還有喜好廣東音樂的民間絲竹社團,多半是經原來松風老人們傳承。廣東音樂能在北京有民間愛好組織與嶺南音樂文化分不開,但最重要的是有“松風”這個民間樂社薪火相傳。
廣東傳來的昆弋鑼鼓“廣家伙”
北京的廣東會館目前只存中山會館戲臺,原來南橫街粵東新館、韓家潭廣東會館等處也都有固定戲臺,其他會館一般可以臨時搭臺演出,所以當年在會館演戲是常見的事。廣東省自明代就傳入昆腔和弋陽腔,后來結合當地語音風格逐漸演變成如今廣東地方戲特色。
弋陽腔傳入北京應是明代中期,曾經與昆腔合流逐漸形成北京弋腔特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有“高腔”、“京腔”以及“京高腔”等名稱。它只用鑼鼓擊節,眾人幫腔的形式演唱,沒有絲竹相伴。雖說弋腔出自江西,但鑼鼓卻來自廣東,弋腔很可能不是直接來自江西,或許是經杭州、廣東傳到北京,所以就與會館的關系密不可分,因此北京戲曲界便稱高腔鑼鼓為“廣家伙”。
目前多數劇種的打擊樂器多以金、木為主體,總體上按照五行分類,故將打擊樂稱之為“武樂”。“金”是指銅制的鑼、鈸類,“木”是指以鼓師手中的指揮樂器檀板和鼓楗子。戲曲的重要打擊樂器——單皮,亦稱板鼓;是以木做胎外包豬革加白銅釘制成,當屬木金合成。通常以板鼓指揮其他鑼鼓為演唱打擊節奏,雖然中國各類劇種豐富,但在使用打擊樂方面是共同的。
“廣家伙”是高腔戲的節奏支柱,它在配合身段、上下出場時,都要按照不同行當的人物身份和感情加以鑼鼓點子配合,如同劇中人心臟跳動的節奏一般,用以表現劇中的矛盾沖突和武打類技術表演。
舊時,北京的戲班演出開始必有“打通兒”的程式,就是以打擊樂作開場鑼鼓演奏。這種形式共分為三通兒鑼鼓。第一為“高通兒”,就是用“廣家伙”打擊的高腔鑼鼓。第二為“蘇通兒”,是從蘇州傳來的昆曲鑼鼓,梨園行習稱為打“蘇家伙”;也就是后世繼承的京劇鑼鼓。
第三為“吹通兒”,是以昆曲吹奏的曲牌夾雜打擊樂等混牌子。
這些演奏形式,一來是為招攬生意,二來是使觀眾和演員們進入戲劇氛圍。京劇的打擊樂極為復雜,首先就是它的來源眾多。
北京高腔鑼鼓用的這種“廣家伙”是為演唱作為擊節的主奏打擊樂器,樂隊的鼓師和其他樂師邊打擊鑼鼓邊幫腔演唱,使唱腔和打擊樂完美結合。這種形式現已不見于北京舞臺,只能在傳世的部分錄音和一些老藝人口中才能了解大概。掌握打擊樂的鑼鼓技能一般不能看譜演奏,一定要將各種鑼鼓點子以口頭形式背誦,如誦念經文一般,所以舊時戲班稱打擊樂的鑼鼓點子為“鑼鼓經”。
北京舊時梨園行中素有“鑼鼓經要是不會背,這輩子打不對。心里有鑼鼓經,巧練準能成!”的口頭禪。其實即便能背會鑼鼓經也未必能打好鑼鼓,還要在打擊樂的基本功上下工夫。作為演員也需要會背誦鑼鼓經,它是統治整出戲的靈根。每個鑼鼓點子都是震撼觀眾和劇中人物內心的標點符號,而每個符號都要由演員控制強弱起伏。打擊樂在劇中還有烘托氣氛和人物情緒,以及時間、情景、環境等技術功能,有時還要夾雜管弦類文樂來表現。戲中表現時間多用“起更”鑼鼓,幾下更鼓就是一夜,這種時空轉換是利用中國傳統寫意法,就是“斗轉星移”。用鑼鼓打擊組合表現江、河、湖、海的水流湍急,是為演員在舞臺虛擬表演提供鋪墊,而另一部分的真實環境則由觀眾配合劇情想象而成。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通過打擊樂亦能表現,這種借助手段是傳統戲劇中的經典,比當今利用聲、光、電等舞美手段高明得多。
不同劇種的打擊樂有不同主奏鑼鼓,昆曲一般由板鼓、大鑼、小鑼、鐃鈸以及堂鼓組成。京劇繼承昆曲打擊樂程式,另有河北梆子、評劇、豫劇等劇種亦略相同。“廣家伙”由板鼓、大篩、大鐃、大鈸、小鈸、小鑼、大堂鼓等組成。它的鑼鼓經很是豐富,念出來與“蘇家伙”有所不同。同樣是“五擊頭”,蘇家伙是:哐、切、哐、切、哐;而廣家伙的鑼鼓經則是:嗟、咚、嗟、咚、嗟。高腔“廣家伙”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劇種,它是演唱中的主奏樂器。
在北京類似這種廣家伙的鑼鼓在民間還有一種打擊樂,就是為獅子、五虎棍、少林拳等香會社火伴奏的“文場”。這是一個由7個人組成的游行式樂隊,有單皮、镲鍋、小堂鼓、兩對大鐃、兩對大鈸組成。這種打擊樂也是屬于廣家伙范疇,有些鑼鼓經與高腔鼓點如出一轍。
北京高腔早已不見于舞臺,但在部分的昆腔中還有保留。在河北絲弦中也使用“廣家伙”,目前受京劇影響已經改用京劇鑼鼓。現在廣東的傳統粵劇、正字戲、白字戲、潮劇等還保留有部分高腔鑼鼓,但“廣家伙”的演奏形式在其他劇種中已經難得一見了。
廣東會館在北京的終結
廣東會館多數是為科舉服務,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后便驟然蕭條。雖然,民國初年暫時繁榮,但隨著民國十七年(1928)的國都南遷,在京的廣東籍政治人物隨國民政府搬到南京,導致北京的廣東會館管理失控,甚至違背制度將空房租賃給外鄉人。特別是在日偽統治時期,官府惡霸們相互勾結瓜分會館公產,以致后來在京的廣東會館竟沒有細致賬目記錄資產。1949年,幾乎所有會館都成為多戶人家居住的大雜院,全然沒有當年的那種幽雅氣度。
根據現存資料記載,1956年時,北京的廣東會館共有大小房產2908間半,除原崇文區袁崇煥墓堂以及祠堂由文物部門接管,其他多是由房管局接收作為居民住房。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強烈地震,波及北京,自此居民在院里搭建地震棚,而后誰也不會回拆,因此本來就已成為大雜院的會館文化幾乎淹沒得無影無形。2000年3月,隨著北京城市改造的藍圖展開,經歷明清兩朝數百年的會館建筑最終被無奈地拆除。廣東會館只剩下一座中山會館,龍潭湖畔依然屹立著康有為為袁督師撰寫的碑記和祠堂,廣渠門內的袁崇煥墓堂尚在,但在此看守了三百年的佘氏家族已被遷出。
現在的北京依然飄灑著嶺南文化,但多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圳、香港風情。舊時會館傳來的科舉文風東流一去,衣食住行等也隨著新時代的推移改變成更為便捷的方式。
(作者系國家一級昆曲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