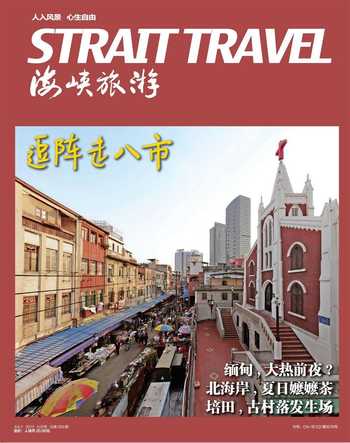永安變奏
劉君

相對于閩中其他小城,永安變化的節奏感更加明顯。帝國時代,以貢川為核心,這里是文化重鎮,有讀書致仕的傳統,同時,山歌和隱士的琴聲合鳴,雅俗共賞。抗戰時期,永安是福建的臨時省會,愛國氛圍空前熱烈。新中國建立,永安進入小城市的市井節奏,并不富裕但自得其樂。計劃經濟解體了,永安意識到危機,以及自身的巨大潛力。林竹、紡織與新興的化工、建材等產業齊頭并進,共同譜寫新時代的樂章。這種變化的速度令人驚訝,背后隱藏一個巨大的問號: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斷重組小城的形象?
突如其來的雨水讓永安更加安詳。“降坡”已略顯破舊,盡管它曾經是小城最熱鬧的街道,如今也只蕩漾出絲絲懷舊的氣息,注視著城市圍繞著那顆古老的大榕樹重獲新生——這里便是永安的“下城”(downtown)。從北門到南門,步行不過半小時的距離,參差不齊的建筑群圍攏在幾個繁華街區。兩條主干道燕江中路和解放路的交叉口,車水馬龍的光景已今非昔比。人們穿梭于商場、服裝專賣店等寬敞明亮的空間,或者在街角的冷飲店買杯飲料。在夜晚燈光的照耀下,核心地段更加璀璨,與一線城市比也不遑多讓——這是永安市政府大力投入的結果,就在去年,夜景改造和亮化工程上耗費了近6000萬資金。
走在永安市區,你會覺得這座城市既清晰又模糊,清晰是因為它井然有序的城區結構,模糊感則來自它歷史上不斷變幻的形象——宋明時期,這里是著名理學家陳瓘、陳淵的故鄉,還誕生了琴學大師楊表正,文化源遠流長;盡管相對封閉,在廊橋上對歌的山民們長期過著詩意的生活——這是屬于永安的風雅小調;民國時期中國本土第一架飛機的制造者李寶浚為永安涂抹上驚艷的一筆。抗戰時期,永安因為地理位置而成為了福建省的臨時省會,長達七年半的時間熏染出強烈的愛國氣氛,野火春風斗古城,演繹的是激越飛揚的苦斗篇章;如今,工業上的飛躍讓小城變得繁華起來,在三明首屈一指——通常,它被定位為“新興工業小城”,但真的就蛻變得如此徹底嗎?
從書聲、琴聲、山歌聲,到今日2600多家工廠的轟鳴聲,這些反差強烈的節奏都屬于永安。路易斯·芒福德說,城市是一個劇場,上演著過去、現在與未來。永安的劇情上演得過于蒙太奇,人們幾乎找不到各幕之間的聯系——除非,將過去一一回溯。
溪聲如訴
永安古名浮流。九龍溪與巴溪在城區西門匯合,形似燕尾,流經城區的那段河道被稱作燕江,因而它又叫“燕城”。建制是出于這里是“險要之地”,時間在明景泰三年(1452年),沙縣與尤溪之間的幾塊區域組合成為一個新的縣城,名字中寄托著統治者的理想。此前,這里為人熟知的,是其下轄的貢川。貢川距離城區只有十五公里之遙,歷史甚至比永安更為古老。至今流傳的俗語說:“先有貢川后有永安。”由于讀書致仕者眾多,宋欽宗賜予它現在的名字。
進入貢川,遍地都是回憶。追憶,就是古鎮現在的表情。會清橋記錄著過去幾百年的風雨,這座純卯榫結構的橋梁,橫跨于九龍溪與沙溪的匯合之處。據說,每到六、七月份的雨季,九龍溪水變得渾濁,而沙溪水依然清晰。對比十分鮮明。在橋梁建成后,一位叫羅明祖的進士寫了一幅對聯:會極環瞻星北拱,清波永奠水東流。希望它永遠能夠見到清流,當然,這種愿景不切實際,溪水如時代本身,而風雨總是不可預期。現在,會清橋已被歲月侵蝕成青黑色。橋中央,關二爺依然威武地享受著供奉,只是不知溪水清濁夾雜了多少回。
在貢川,十多年前還保存著不少石屋,讀書致仕的人家還建造了許多三進式的院落。但現在,只有進入街巷深處,才能發現一兩座石屋,墻上階下的青苔已經密密麻麻了,顯然是許久無人居住。鎮上養老院的一位老人說,新一屆的鎮政府與上屆不同,喜歡新容新貌,拆掉了那些老屋,然后繼續木然地面向電視屏幕。從外面看,貢川保持著整體劃一的建筑高度,三層的新式板房,上住下商。剝筍的女人們聚集在廊下,等待收貨的皮卡車。這天正逢鎮上的“趕墟”(定期趕集),人們提著購買的雜貨,尚未返家。那些年邁的老人或臥或坐,輪流交換一只破舊的話筒,從咿呀的山歌里追尋從前的時光。
正順廟里的煙火不絕如縷,與感恩寺內的神祗一起守護這個變幻的“古堡”。在青石小巷內行走,曲曲折折,遠離了喧囂的集鎮中心,隱約之間,楊表正的琴聲在耳邊繞起來。它追隨著你,轉過延成路,穿過竹林,踏進嚴九岳破敗的三進式院落,依然緊隨,甩也甩不掉,仿佛你的耳朵一定要你聆聽著它,才能打破回憶與現實之間的壁壘。有人這樣形容楊表正的琴聲:“其音之清,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如金石相宜,絲竹并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在山腳下,溪水畔,屋檐下,陽光和雨水共同醞釀的迷霧里,琴聲一直飄蕩。這琴聲有一半的蠱惑力來自九龍溪水和漫山遍野的竹林,清風明月溪橋,在這樣的背景和伴奏中,迷思緩緩流淌而出,即便漫不經心,也帶有高士的趣味。它隔著漫長的時空,像蠶絲那樣緊緊纏繞你。
這個古鎮不只有楊表正,還有許多進士們從這里走出。他們衣錦還鄉,短暫的慶賀之后甚至一去不歸。昔日營造的宅邸早已成灰或者只有一片石墻,如訴的溪水反襯著寂寥。在這些人中間,有兩位理學家:陳瓘與陳淵。雖然人數并不算多,卻代表了貢川的理學傳統。
陳瓘在23歲時中了探花,后來還成為了理學大師“二程”的弟子,但在此后的仕途中一直是一名剛直不阿的言官,既彈劾力主變法的王安石,也貶斥蔡京等佞臣。盡管屢遭打壓,在他內心世界深處,依然存在一個光風霽月的逍遙世界。他在《卜算子》里寫道:“身如一葉舟,萬事潮頭起。水長船高一任伊,來往洪濤里。潮落又潮生,今古長如此。處夜開尊獨酌時,月滿人千里。”他渴望結廬人境,看鳥倦云飛,兩得無心。或許恰因為有著這樣的心境,他能夠始終淡然守在廟堂。他的書法與詞風一樣清麗——紙墨里滲透著他的理學觀:理本氣末,體用一源。這些感悟或許小時候觀看竹林和聆聽溪聲時就已產生,只是命運后來將他拋向了一個更為復雜的世界。
琴、理學的遙遠世界,與支離破碎的現實之間,不僅僅隔著一道爬滿青苔的高墻。這些風雅的隱士與文人已很少在貢川還魂。這并不奇怪。在中國,許多小鎮像貢川這樣,曾經有過優雅的過去,而今又同化于面目全非的時代。急管繁弦的變奏中,傳統的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復返——農耕時代,貢川是古意昂然的城堡,不僅走出了許多讀書人,有許多隱士渴望在這里隱居;尋常百姓也家家戶戶養雞、挖竹筍、打糍粑、編草席,悠閑的時光里則在會清橋上對山歌。如今,山歌已很少能聽聞,隨琴聲渺渺而去,如散去的精魂。
尤其是編織草席的古老手工藝,鎮上已很少有人掌握——70多歲的鄧麗娣老人是鎮上的傳承人,她坐在編織木樁前,認真地壓實每一根稻草,感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夠貼補家用。她的兒子說:“現在政府不重視老房子,更不重視民間工藝,重點放在工廠上面,搞活經濟嘛。我們搞這些東西又不賺錢,但是扔掉了又有些可惜。”
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機車從大街上轟鳴而過,旁邊則是剝竹筍的噼啪聲,偶爾傳來幾聲躁動的雞鳴,很快又被化工與管材工廠的機器聲淹沒。
園林城市
快速崛起的化工、建材等新工業,與傳統的紡織、林竹業結合起來,讓永安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現在進入了風馳電掣的城市化節奏中。高樓如當地盛產的竹筍那樣節節冒出來,越來越細的行政區、日益增多的商店以及不斷拓寬的馬路,都在強調密度和速度。在南門賣了二十年粿條的老板說,許多新地名他也不認識了,長期不出門,偶然轉悠一圈竟然會迷路。
工業的發展似乎并未影響永安的生態。自然環境與工業發展,兩個貌似悖反的條件共同塑造了今日永安的格局。在2002年建設部批準的福建省城鎮體系規劃中,永安被確定為省域二級中心城市。這標志著永安地位的飛躍,同時激發了“把永安做大”的想法。2007年,永安被評為“國家級園林城市”,80.7%的森林覆蓋率是其躋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政府順勢制定了《永安市城市總體規劃》,里面寫到:“永安市區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資源和旅游景觀資源,森林型山水旅游城市的功能要求永安城市的未來是:環境優美的綠園、居民安居樂業的家園、旅游者的樂園”。
不久前,福建省城市文明指數評定小組來到永安。小組內的一位官員說:“我們這次主要考察永安的經濟重點工作、公共環境、公共秩序、社會活動和公共關系等。這幾項永安得分都不低。”那幾天,永安的電視臺和廣播都在反復提醒市民注意日常文明細節,比如過馬路要看紅綠燈、不隨意在街上吐痰等。一位出租車司機聽到這些提醒時啞然失笑:“這些提醒對永安人有點過時啦,他們應該提醒人排隊打車、優先照顧老人和小孩這些東西。”他強調說,永安人應該按照大城市的文明指數來要求自己,“畢竟已經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了。”
不管文明指數如何,單從總體自然環境來看,永安至少無愧于“園林城市”的名號。它的現狀,接近德國的工業小鎮在20世紀初期,狂熱的工業化浪潮之后,人們開始顧及對綠色的經營。對于永安良好的生態條件而言,這一動作仍不算晚。市民們也漸漸適應了新的城市面貌和生活節奏,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住在距離中心稍遠的新安小區、建設小區、五洲小區居住,社區的層次跟隨樓下底商的增多而豐富。如果說社區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標尺,那么永安除了規模上仍稍遜一籌,已然躋身二線城市的行列了。
除了“宜居”,“宜游”也是園林城市的應有之義。相對于工業,永安的旅游業發展的步伐慢了半拍。但可觀的旅游資源中潛藏著巨大潛力。桃源洞-鱗隱石林風景區是主打的名片,其中的“一線天”景觀尤其值得一看。徐霞客曾經記述道:“上辟山巔,遠透山北,中不能容肩,蓋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余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夷、黃山、浮蓋,未曾見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在正午陽光的照耀下,天光一線灑落,異常神奇。這條地殼運動擠壓形成的縫隙,每年旅游旺季都招徠大批游客欣賞。游客們欣賞完這一自然景區,往往還會前往槐南鄉洋頭村的安貞堡——建于清光緒年間的圍龍屋式民居,它的結構與功能多出于軍事防御的需要,建筑隨地勢起伏而逐次升高,有人將其稱為航行海上的戰艦,這無疑是變亂年代人們出于安全感和想象力創造出的產物,傳統的夯土建造法,斗拱、門扇、窗間、雀替、柱礎上精雕細鑿的浮雕、壁畫與泥塑,展現的是永安古人非凡的想象力。這些自然與人文景觀仍處在開發的階段,很快將成為推動永安發展的“綠色產業”。
但在永安旅行,有時游人會產生倦怠感,然后是疑惑——這座城市的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實、工業與自然似乎割裂得過于徹底,沒有一個核心的基調將其統籌為一體。這多少是因為潛意識在作怪:“園林”更容易誘發人們向鄉村想象;反過來,真正的園林城市需要高度的現代化作為支撐,同時抱有鄉村般和諧的生態與傳統。
永安的精魂隱藏在九龍溪的溪水中,還是在古堡與竹林之間,抑或是漸行漸遠的琴聲與山歌里?從前,大多數永安人在這里孑然獨立地書寫農事詩,在變奏了數次之后,如今卻是機器與流水合鳴。當然,從時間上看,這也只是城市進行曲中的一個篇章而已。
工業的發展似乎并未影響永安的生態。自然環境與工業發展,兩個貌似悖反的條件共同塑造了今日永安的格局。這座城市的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實、工業與自然似乎割裂得過于徹底,沒有一個核心的基調將其統籌為一體。永安的精魂隱藏在九龍溪的溪水中,還是在古堡與竹林之間,抑或是漸行漸遠的琴聲與山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