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勇:大三聯的“小”編輯
何志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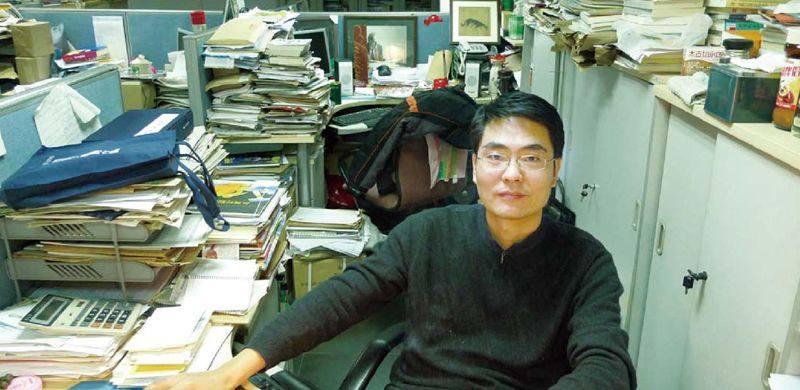


鄭勇說他早年有兩個理想:一是做《讀書》雜志的編輯;另一個是在工作之余開一家書店。都與書有關。
1996年,鄭勇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便奔著《讀書》雜志去了三聯。去三聯做編輯是他的不二之選。可惜,分配崗位時,鄭勇被分配到了圖書編輯室。當年《讀書》雜志的前輩覺得他的性格太活泛,擔心留不住。鄭勇笑說其實自己只是愛跟作者打交道而已,骨子里是個坐得住冷板凳的文靜書生。后來這些前輩也后悔當年沒把鄭勇留在《讀書》雜志。當然這是后話。而他最終也繞了一圈,仍舊回到最初的原點來。當初的“可惜”又另當別論。
開書店的理想倒是出乎意料地變成現實。1996年年底,鄭勇被派往南京三聯商務文化中心擔任經理,主理了半年的書店業務。
看起來,鄭勇的不少經歷都是在繞彎路。比如當年在去北大讀研之前,本科其實是在浙江大學念的機械設計與制造專業,之后又在蘇州醫學院工作了一段時間,都是與文學和出版毫無干系;最初進入三聯,做《讀書》雜志的編輯的愿望也未能實現,做了十七年的圖書編輯之后,今年“回到”《讀書》雜志,擔任主編。回頭看這些回形經歷,鄭勇在坦然中倒多了些感恩,“現在回頭看,理工科的讀書經歷,對思維訓練蠻有好處的,那就是在激情之外,更趨于理性;做出版之前先做書店的經歷,等于是做完下游之后回頭再做上游,對出版的全流程有更多的認知,對市場和讀者有一個更感性的認識。”我想,鄭勇后來策劃、編輯的“三聯精選”、“三聯講壇”、“Home書系”等等圖書,或許最先得益于這樣的“彎路”。
“三聯講壇”“HOME書系”,開拓三聯出版的新傳統
《北大舊事》是鄭勇1997年從南京回到編輯部編的第一本書,書的編者是北大中文系的陳平原和夏曉虹兩位教授。當年鄭勇因為未能遂愿去《讀書》雜志,幾欲另謀出路,虧得導師陳平原先生的開導,才在圖書編輯部做下來,做的第一本書竟也是陳平原編的書。
《北大舊事》是陳平原夫婦為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編訂出版的,但對于鄭勇個人而言,此中除了與陳平原的師生情分,也飽含著一份對北大的情緣,后來的“三聯講壇”叢書亦是如此。
“三聯講壇”這套書,集聚了錢理群、葛兆光、陳平原、洪子誠、王德威、吳曉東等學術名家,其中不少都是北大的優秀文史學者,而書稿的內容是他們的代表性課程的講稿,比如錢理群的《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鄧曉芒的《康德<判斷力批判>釋義》。“‘三聯講壇最主要的思路是做學術普及的出版工作。當時我覺得高校和社會之間有一道藩籬,而這套書希望把名校名師的名課,轉化為紙上的學苑風景,使無緣身臨其境的普通讀者,也能借助閱讀,分享當代校園知識、思想與學術的進展和前沿問題。最初的創意和出發點后來也成功實現了。”從這個角度來做書,“三聯講壇”算是開了“課堂書”的先河,且與此后的跟風之作相比,這近二十種書絕非泛泛之作。很值得一提的是,鄭勇在這套書的策劃、編輯過程中,將講堂的味道原汁原味地保留到了紙頁上。“這些書稿的風格不是后加工的,否則就變成了專著。所以,我當時設計并堅持的原則就是,以課堂錄音為底本,整理成書時秉持實錄精神,不避口語色彩,保留即興發揮成分,力求呈現原汁原味的現場氛圍。作者如有增刪修訂或審閱校樣時有觀點變異、材料補充,則置于專辟的邊欄留白處,權作批注;編者認為值得細味深究或留意探討的精要表述,則抽提并現于當頁的天頭或地腳。著名書裝設計家陸智昌也喜歡這套書的創意,幫著設計版式,很好地實現了那種歷時性的意圖和多文本疊加的效果。”
“三聯講壇”和自2003年策劃的“HOME書系”,其實可算作三聯出版傳統的創新。三聯幾十年積累的品牌和形象,一直是偏重學術和文化面向的出版,如“Home書系”這一類相對通俗的生活類圖書是三聯先前較少觸碰的。當然這跟2002年前后三聯內部從原先一個編輯部分化為生活、讀書、新知三個編輯部有關,鄭勇當時擔綱生活編輯部。“當時剛剛成立了生活編輯部,三聯之前很少出生活類圖書,可說既無經驗,也無資源,真是白手起家。而且當時市場也發生了變化,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所以覺得做生活類圖書有市場壓力。當時想策劃一套適合都市讀者,偏于生活和時尚的書,就找到了香港的歐陽應霽先生,對內地讀者來說,當時他還是新面孔。”《設計私生活》、《兩個人住》、《回家真好》、《半飽》、《尋常放蕩》,包括持續到近年出版的《香港味道》、《快煮慢食》、《天真本色》,這套書一直受到都市年輕讀者熱捧,而對于三聯來說,這套書吸引到的群體是全新的,與以往三聯那些關注學術與文化的讀者群不同,“出版社的功能不僅要滿足老讀者,也應該在堅守中有所調適,創意選題和圖書會培養新讀者,成功地策劃、引進一套書,會為出版社帶來一批增量的讀者群。”鄭勇說。
同樣的,鄭勇同1217俱樂部合作策劃“年度書系”,從2005年起始每年出版的《話題》,也看似與三聯的出版傳統有所出入,但鄭勇說,“三聯為什么這么多年特別受讀者或者知識分子的支持,大家對三聯有好感和認同?我的一個判斷,是因為三聯很關注中國思想界進程,同時引領著時代的風潮。三聯圖書的內容是大家精神生活和生活領域的話題,能引發大家的討論。”八九十年代持續出版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學術前沿”等即是最好的例證,“這些書都給中國當代的思想討論或者時代風潮提供了閱讀資源,是三聯關注社會現實的體現”。而鄭勇當初也正是看中了楊早、薩支山、施愛東等青年學者定期組織年輕學人,對影響到當代國人精神生活的熱點話題進行討論的活動,試圖為這個倉皇的時代留下記憶年輪,把個性化的思考留給后人,這一理念是與三聯關注當下現實的精神相契合的。雖然這套書并沒有創造經濟利潤,編輯團隊每年卻要為此付出許多精力,但是鄭勇說,“只要他們堅持做這件事,有耐心有恒心做下去,我作為出版人,作為編輯會全力支持,三聯也會全力支持,不計賠賺地支持。因為這是一批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者在做著的有價值的文化工作。”
追隨“溫暖的腳印”
除這些叢書之外,鄭勇編輯的不少作品,是更有“三聯味”的,同時也是跟他個人的喜好和品位貼近的。陳從周《梓室余墨》、曹聚仁《萬里行記》、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周有光《百歲新稿》、金安平《合肥四姊妹》……文史類作品是鄭勇偏愛的,尤其鐘愛那些帶著些許民國風骨的老人的作品,比如金克木、黃裳、董橋、范用諸位的小書。鄭勇說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想將自己的書齋叫作“黃金齋”,因為喜愛黃裳和金克木的文字。鄭勇也做了不少他們的小書,黃裳的《珠還記幸》、《來燕榭少作五種》,董橋第一次在大陸出的自選集:《從前》、《品位歷程》、《舊情解構》,而范用編著的《文人飲食譚》等六七冊書也都出自鄭勇之手。
范用是鄭勇的前輩,鄭勇自進入出版圈時便結識了范用。2010年,范用去世之后第四日,鄭勇寫了一篇《“溫暖的腳印”》,憶敘了他與范用先生的這段情誼。
當年鄭勇進入三聯,最初就住在方莊的集體宿舍,離范用先生的家很近,所以時常去范用家里看書借書,對他的藏書印象頗深,“像所有愛書人第一次進入范先生書房的感受一樣,我也只能用如入寶山、流連忘返、驚嘆羨慕一類詞語形容。像我借閱過的董橋、黃裳的作品,就包括大陸版之外的港臺版、平裝本之外的毛邊本、精裝本,一應俱全,而且大都是作者的贈本。”后來,鄭勇與黃裳、董橋的結緣,都算是范用先生的牽線搭橋。文中還提到《懶尋舊夢錄》的再版、劉再復父女兩地書結集《共悟人間》、車輻《川菜雜談》等書的出版,也都得到了范用的引薦。
范用一生為人做書做嫁衣,從未有自己的作品出版,自退休之后才編了《文人飲食譚》、《買書瑣記》、《買書瑣記(續編)》,寫了《我愛穆源》、《泥土 腳印》、《泥土 腳印(續編)》等幾冊書。其中《文人飲食譚》和《買書瑣記》也是較早收入“閑趣坊”書系的作品。“閑趣坊”的作品,都是很有性靈的文化散文,也做得素雅靈巧,一直被很多人認為頗具“范用味道”,我想這是對鄭勇做這套書的肯定。
鄭勇說他在范用身邊的那些年,就像是他的小學徒,踏踏實實從字體、字號、書眉等等微小的細節學起。有人稱道鄭勇的書做得好,范用先生開心;遇到工作疏漏,鄭勇也領受他的批評。比如《回家》出版時,鄭勇“就收到范用先生一封附帶著勘誤表的‘吼叫信:‘看到樣書,心里十分不安,里面的錯字,錯得太不像話。讀者看了會笑話范用。……對三聯的信譽亦有損害。”比起很多私淑范用的編輯,鄭勇與范用這樣兩代出版人的交情,是讓人羨慕的。
從陳原、范用到沈昌文、董秀玉,到鄭勇,甚至更年輕的三聯人,幾代三聯人之間的薪火相傳,是在三聯之外其他出版社難見到的。鄭勇常借用宋代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的說法,將鄒韜奮、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稱為三聯的“一祖三宗”,而他就是在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這“三宗”的身邊,從他們所做編輯的作品中,觸摸到三聯的體溫和氣息,三聯的精神得以熏陶化人也在此。鄭勇編輯生涯最早的成名作“三聯精選”,能夠看出他對三聯出版傳統的繼承、對三聯傳統資源的整合。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連續出版了五輯共50種的“三聯精選”,多為大家小書,朱自清、聞一多、葉圣陶、唐弢、朱光潛、浦江清,《經典常談》、《詩論》、《沉思錄》、《道德箴言錄》都在其中,很能體現出三聯圖書的人文精神取向和注重文化積累與學術普及的努力,尤其映照出三聯在目下出版社日趨商業化的環境中,仍舊抱持著的當年的理想。那份純粹和摯誠,不知溫熱了多少代讀者。
“三聯不只是三聯人的三聯”
5月,鄭勇去常州參加“周有光與中國語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赴會之前,他將前些年周有光在三聯出版的書重又找出來翻看。周有光退休之后在三聯出版的七八套書,不少也是經由鄭勇編輯出版的。“通過這七八套書,能看出來周老從一個專家學者轉向獨立知識分子的過程,他的這種人生轉型,剛好在三聯書店的出版中得到完整的體現和記錄,見出一個作者和一家出版社很好的精神氣質的契合。”
三聯和《讀書》雜志的這種明顯的精神氣質和特點,就像許紀霖曾經說過的,“確立了在金錢和權利之外的第三種尊嚴——知識的尊嚴、思想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尊嚴”,這與楊絳先生對三聯“不官不商有書香”的贊譽正相契合。很多時候,用鄭勇的話說,三聯不再是三聯人的三聯,而是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知識界的公器。2004年的“三聯風波”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2004年2月,孫曉林、吳彬、葉芳、舒煒、鄭勇等十四位三聯人向上級主管單位實名舉報總經理人事、經營等一系列嚴重違規事件。最初被媒體稱為“《讀書》公務員版風波”的事件,最后成了“三聯保衛戰”,因為此間,楊絳、陳樂民、資中筠、葛兆光、陳平原、許紀霖等作家學者紛紛也提起筆來撰文回憶與三聯的過往,表達對此事的關注和焦慮,聲援“三聯十四志士”;范用、袁信之等京滬兩地參加過三聯工作離退休前輩通過各種方式向上級領導機關呼吁盡快解決三聯問題,據言兩地的20位老出版家年齡加起來超過1600歲,82歲的范用在里面是最年輕的;全國42家民營書店發表聯合聲明,以示支持,一并參與到“三聯保衛戰”中。這一場三聯風波持續到當年9月,才以時任總經理被免職調離而宣告平息,三聯重新回到正軌。鄭勇說,如果沒有那么多熱愛三聯的作者、讀者、媒體人和書店等出版界的道友的大聲疾呼和全力支援,光靠三聯人怕是難以恢復正軌的。
這實在是一份難得的道義,對三聯人是莫大的鼓舞。鄭勇說,有三聯氣質的出版人、作者和讀者形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在三聯做事,你能感覺到吾道不孤,因此不能放棄文化理想和精神堅守,否則,如何對得住公眾對你的期望?‘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這樣的稱譽太高了,辜負了這一期許,三聯就只是一家普通出版社,一家平常的企業。因此,《讀書》也好,三聯也好,都是一個公共平臺,屬于全體知識人的公器,而絕不只是三聯人的三聯。我們在里面工作,感受特別具體,就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讓你為之工作不敢懈怠,不敢造次。”
今年2月,《讀書》雜志繼2007年人事大調動后再一次更換主帥,執行主編賈寶蘭轉調藝術研究院,王焱即將退休離任,部分《讀書》編輯轉任圖書分社崗位,一時間又引發不小的風波。
“新三聯的歷史,可說是先有《讀書》,后有三聯。因為《讀書》雜志1979年創刊時,三聯書店還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三聯書店在恢復獨立建制后,能夠那么快速地成長、定型,獲得那么多支持,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其實都離不開《讀書》雜志,離不開《讀書》的作者和讀者、品牌和影響。”而對于更多數的讀者來說,尤其是對知識分子,《讀書》的存在和價值更為深遠。所以《讀書》近年來的每一次風吹草動也都引發著讀者的關注和回應,所謂“《讀書》無小事”,一次次得到驗證。這一次鄭勇接任《讀書》主編,自然也受到關注。鄭勇說,“我們今天接手主持《讀書》,要做的只是順勢而為。幾代前輩《讀書》人的接棒努力,已經使《讀書》成長為根深葉茂的大樹,我們享受著她的蔭庇,是榮耀和福分。她的深厚傳統,也是《讀書》人和讀書人共同攜手培植出來的,所以我們只能順勢而為。今天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生態,和大家懷念的陳原、范用、沈昌文時代當然變化太大,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堅守中加以調適,在延續中有提升,我們固然有諸多想象、選擇和設計,但我想,最根本的還是依賴作者的參與形塑,傾聽讀者的意見,或者說是大家一起合力打造以后的《讀書》新面目。” 鄭勇調任之后,計劃走訪全國各地的部分一線城市,舉辦座談會,聽取作者和讀者的意見。“我的定位很清晰,我是為《讀書》打工、跑腿兒的小伙計。我是帶著臨深履薄的敬畏之心來上崗的,是為這個心愛的刊物服務的。5月我們去上海‘拜碼頭,每一場座談會上都能聽到老、中、青各個年齡段的作者、讀者對《讀書》的深厚感情、對《讀書》的殷切期待,許多人收藏著從創刊號以來的全套《讀書》,即使有段時期《讀書》讓他們感覺失望,甚至不讀了,也還在堅持訂閱或購買《讀書》。這種不離不棄的支持,讓我們在感動之余,也更增添了信心。”
鄭勇說,作為職業編輯那么多年,最大的體會是,“大三聯,小編輯。我很認同業界的說法:讀者是上帝,作者也是上帝,而編輯呢,很簡單,就是在兩個上帝之間穿梭往返著跑跑腿。這個定位在我從業十七年來從沒改變過。而且‘竭誠為讀者服務,這是三聯的祖訓,三聯編輯入職教育的第一定律。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希望自己跳出來,為自己博出位,那是我們最忌諱的。我就希望隱身在作者和圖書后面,作為他們的推手。為人做嫁也很幸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