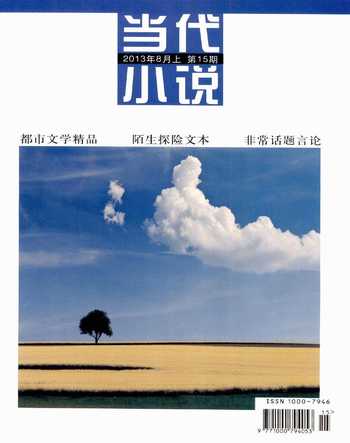一對核桃
郝煒
在別人的眼里,老古是一個比較古怪的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把所有的閑錢都花在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上,比如買一些奇形怪狀的石頭啦,各種各樣的手串啦。我這么一說你就明白了,老古其實是一個有更高生活情趣的人。
不過,老古最近喜歡上了核桃,他自然不是喜歡那種吃的核桃,而是喜歡那種拿在手里把玩的核桃。現在生活好了,你經常可以看到許多老年人拿著一對核桃在手里搓得咯咯響——其實這是普通老百姓的玩法,真正玩核桃可不是這么玩的。你要是問老古,老古就會告訴你,核桃是要輕輕地搓,核桃與核桃之間是不能觸碰的,因為核桃本身就被稱作“文玩”。這些知識老古也是剛剛學到的。老古還知道,好的核桃大都產自河北、天津、山西和北京部分山區,而且叫法也是有名堂的,什么獅子頭、虎頭、官帽、公子帽、雞心、羅漢等等,不一而足。如何養護也是一門學問:去除灰塵要預備兩把牙刷,一個長毛的一個短的;過夜時,核桃要用塑料袋封上。反正你要是專業研究,哪一行學問都不少,都能讓你感到“學無止境”。
老古生活在一個小城市里,這樣,老古的愛好就和這個城市不對等,也就是說,他很難買到像樣的核桃。這里生長的核桃,大多是那種楸子核桃,就是北方的大山里自己生長的核桃——當然,楸子核桃也是一種很好的核桃,諸如鴨子嘴兒、雞嘴兒、子彈頭兒、棗核、雙聯體、三棱兒、四棱兒。但正如遠地方來的和尚會念經一樣,終歸不比外地核桃上手快,起色好。于是,老古只好到那些專門的商店里去買,比如花鳥魚市,比如古玩店,而且大都是玩過的。老古買了好幾對核桃,都不滿意。
好在老古的兒子在北京,這樣,老古就有經常去北京的可能。北京可是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城市了,那里什么東西都有,特別是玩的,好像這個城市就是為老古這樣的人預備的,老古一到北京就如魚得水,專往那些旮旯胡同鉆。前些年老古喜歡奇石,每次去自然都是大鐘寺啦、十里河啦、弘燕奇石城啦的逛一逛,雖然那里的奇石貴得嚇人,老古還是愿意坐著公交車或者地鐵,每天去看一看,大多是過過眼癮,偶爾價錢老古覺得能夠承受,也買個一塊兩塊的。
最近,他又去了兒子家,兒子的家已經搬到了通州。老古比兒子知道通州的歷史,他知道通州就是以前的通縣,是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的最北端,也堪稱是大運河的“龍頭”。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古去市里淘寶的路程要遠了。
現在因為喜歡上了核桃,老古逛街的首選目的地就改了,改成潘家園和十里河文化城。老古這個人熟悉環境很快,他問明了如何到達市里的公交路線,這一天就去了潘家園。老古是熟知詳情的,這一天正是周六,潘家園大集。潘家園這地方我不用說,去過北京的人都知道,它是北京最大的舊物市場,也是所有人“淘寶”的地方。中國人、外國人都愿意到那里去,淘到的東西真假不知道,全憑你的眼力。老古坐上門前的667次公交車,到大北窯下車(實際上就是國貿),又急匆匆換乘地鐵十號線,坐到潘家園。走出地鐵站一打聽,沒有多遠,就是潘家園了。
潘家園老古其實也是挺熟悉的,以前也多次來過。這次來,覺得變化很大,地攤變成了“百姓跳蚤市場”,另一面也扣上了大棚,面積無形中擴大了。那天潘家園的熱鬧和擁擠,老古用什么形容詞都不為過,擺攤的一個挨著一個,賣啥的都有,只要是玩的東西,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東西,新的舊的都有。買貨的呢?我這么說吧,如果你不是有把子力氣,根本就擠不到跟前兒。
老古倒是不疾不徐的,他背著手東瞅瞅,西瞧瞧,這回他比較專一,專瞅核桃。那些核桃有的包裝精致,放在塑料袋里,有的裸露在外面,也是放置在一個個的格子里,它們端莊地坐在那里,顯得很高貴。老古把地攤上那些賣核桃的大致看了個遍(你要說全看遍那是瞎扯,因為根本不可能),也大體就有了點了解,好一點的核桃大都在300元到600元之間,就是稍差一點的都在百元以上。這大大出乎老古的預料,他原來想,花個百十來元買一對好一點的核桃,他不想投入太大,他只是個初級玩家,他知道,玩核桃的路很長呢。
這么貴?老古有些憤憤。他想,都是全國人民(不知道外國人玩不玩核桃?)把這價抬起來了的。
老古立刻就對核桃失去了興趣,他轉而到那些賣手串的地攤。要不說北京就是北京,玩的東西就是漂亮,那些手串也令你眼花繚亂,木制的千種萬種,瑪瑙的千種萬種,玉石的千種萬種,嗨嗨,哪里是一個“多”字了得?老古總算擠了一個地方,蹲在那里看手串。其實,老古對瑪瑙手串還是心中有點數的,他不喜歡那些花里胡哨的瑪瑙珠子做成的手串,那些大多是染色的,盡管鮮艷,還是有作假的成分。他喜歡的是那種原石做成的手串,市場上有內蒙的,外蒙的,新疆的,他獨獨喜歡內蒙阿拉善的。老古在這方面很內行,只要一搭眼,他就能分清哪個是內蒙的,哪個是外蒙的,哪個是新疆的。阿拉善的石頭珠子看著沉實,顏色艷而不麗;新疆的就鮮艷多了,大多是透明的,像糖豆一樣;而外蒙的,就更多了一層華麗,有眼睛石,有筋脈石,那種手串都是價格不菲,眼睛石也被稱為“天眼石”,稍好一點的手串都得五六千以上,甚至上萬。當然,好一點的什么樣的手串都得上萬,這是圈外理解不了的。總之,這種在別人眼中看不出來的細微差別,老古是駕輕就熟,一眼就能看出。
那些手串和手鏈擺了一地,老古拿起一條問問價格,還真不貴,一百到三百不等。老古算計了一下,這種手串光是打眼就得30到50,再加上珠子本身,這幾乎是賠錢在賣。
這就是市場,市場是最殘酷的啊!
老古挑了一條黑黢黢的手串,這條手串雖然一打眼看上去不怎么舒服,但它是阿拉善的珠子,只要在腕上戴上一段時間,它就會變得圓潤起來,發出沉實的亮光。再說,這么圓的珠子在店里已經很少能找到,就是找到,一個珠子至少也得五十六十的。
問價,答曰五百,老古砍價,二百行不?攤主是小兩口,正忙得滿頭大汗,不可開交。女的說:“不賣!這價都賠了,還砍價?”男的說:“拿去拿去。”女的說,“那條手串昨天給300都沒賣。”男的一瞪眼睛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說賣就賣!”老古感覺小兩口好像在鬧別扭,這機會難得,所以連忙掏錢。
接過手串,老古立刻就把手串戴在腕上,他腕上原來戴著一條手串,這也是剛才那個男的賣給他的理由,“瞅著這位大哥就懂行,賣給他我愿意。”兩條手串相比較,他當然還是喜歡自己原來的那個,那是幾年前老古精心地從大鐘寺、弘燕奇石城、十里河奇石城等處一個珠子一個珠子地挑來的,那時候許多玩石頭的還沒有醒悟到,有一天這些珠子會價值連城,老古并不是有什么預感,而是他自己喜歡手串罷了,不過是這種愛好幫助了他,成全了他。
“淘”到這樣一個手串,老古感覺很滿意,其實淘東西的過程,就是一個自我滿足的過程。他又幾個地方轉了轉,諸如看看舊書市場,看看那些琳瑯滿目的章料,最后覺得應該回家了,便走出了潘家園。
潘家園外,已是微微細雨,剛才轉悠的時候,老古根本沒有注意到,居然下雨了。老古沒有帶傘,他用手護著腦袋,走到地鐵站前。
地鐵站前圍著一堆人,有站著的,有蹲著的,都不怕雨澆似的。一個人正在大聲喊著:“核桃!核桃!潘家園賣三四百的,我這里就三四十啊。咱是自家的核桃,大家隨便挑啊。”
核桃?三四十?老古有些不相信地湊過去,一看,嚯,還是帶皮的核桃,好像剛剛被扒開,上面殘留著一些黑乎乎的核桃皮,在雨里變得濕乎乎的,眼看著只剩下幾對了。老古立刻擠進去,管他三七二十一,迅速地抓一對在手上。老古端詳著,這核桃形狀還真不錯,他認識這種核桃,叫“公主帽”,在潘家園的確得三四百。
眼瞅著核桃被眾人瓜分完畢,已無挑選余地。這么好的核桃,誰不想搶到一對啊?搶到手里的,有的匆匆付錢而去,有的還在那里細致欣賞、端詳。倒是那些沒搶到核桃的,圍在那里起哄,他們可能希望那些核桃是假的。他們問,那些核桃上的黑皮能刷下去嗎?那個戴草帽的老農(誰知道是不是老農)早有準備,拿起手頭的刷子(看來就是用來解答這些疑問的),在雨水中唰唰幾下子,核桃的黑皮就被蹭掉了,但那人并不刷凈,已使人相信。
老古等到所有人的疑問都問完,聽到了那個人的答案,他的疑問自然也消失了,他幾乎是最后一個掏錢的。老古付錢后,那個老農形象的人一臉喜悅,沖他眨了眨眼,拾起地上那個破草袋子,抖了抖,夾在腋下,說了聲:“拜拜了,伙計。”
走了很遠,他突然把破草袋子和草帽一扔,喊了一句:“你們都他媽的揀著了!”然后,跑了起來,他奔跑的速度很快,轉眼就消失在大街上的人群中。
老古不知道他何意,他以為這個老農是高興的,他可能沒想到這核桃賣得這樣快,他指定是跑到哪個小酒館喝酒去了,農民不容易啊!
天上依然下著雨,老古的心里一片陽光燦爛。四十元錢買一對上好的核桃,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這世上的道理誰能說得清呢?偏偏就讓我老古趕上了,幸運,幸運啊!
他幾乎是哼哼著歌回到家里的。到了家,老伴在看電視,問他,又買了什么寶貝?他沒敢說手串,因為他家里的手串太多了。他舉著那對黑乎乎的核桃說:“買了對核桃。”
老伴沒看他,繼續看電視。他躲進衛生間里刷起核桃來。核桃很快被刷了出來,油光光的,這讓他很奇怪,新核桃怎么會有油呢?他立刻懷疑起來,這核桃是不是假的?
很快,他的懷疑被證實,雖然老古玩核桃的時間短,但他還是從核桃的屁股那兒看出了眉目,怎么看怎么別扭,那明明是堵上去的,和真核桃就是不一樣。
他立刻像泄了氣的皮球,他把核桃扔在水池子里,拖著濕淋淋的兩只手回到屋里,頹然地坐到了沙發上。
老伴立刻驚叫起來:“老古,手!手!”
老古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黑乎乎的,油乎乎的,還淋著水。他順手拿起茶幾上的一張《體壇周報》,嘁里喀喳地擦起來。這再次惹起老伴的驚叫,那是兒子買的,兒子的東西在老伴的眼里向來是神圣的,哪容老古動,而且是損壞。老伴大聲嚷道:“衛生間不是有手巾嗎?”
老古沒好氣地說:“我不愿意用,咋了?”
“你眼瞎啊,你沒看出那是兒子的報紙嗎?兒子興許還沒看呢!”
“我眼睛可不是瞎咋的,”這句話好像一下子捅到了老古的肺管子上,老古氣哼哼地說,他只說半句話,就不往下說了。
老伴覺出了老古的古怪,沒再理他,繼續看電視,電視里在演《上陣父子兵》,老太太很愿意看范偉的表演。他們是在等兒子和兒子的女朋友下班回家吃飯,他們的單位都在市里,開車回來也得半個多小時,這還不算堵車。兒子剛才來電話,再過十分鐘就到家了。
飯菜已經做好了,她充分地估計到了老古今天在外面可能遇到了什么不順心的事情,這讓她很高興。他們來這里有好幾天了,她一直惦記著家里的事情,家里那邊要說有事情就是好多事情,他們住在一樓,種了好多蔬菜,爬秧爬蔓的需要經管,就是那一缸大醬也讓她不放心,生怕大弟弟(他們臨來的時候,把這些都交給了大弟弟伺侯)一不小心給落進雨水,那可就糟了。她曾私下跟老古商量想早些回去,可老古執執拗拗的,看老古那樣子,不回去才好呢。什么潘家園,李家園的,一走就是大半天,花著錢不說,還經常慪氣。
老古一直等著老伴問,可是老伴專注電視根本沒問,這下子沒了轍,想來想去還是主動坦白吧。
老古說,“今天我買了一對假核桃。”
老伴眼睛盯著電視,沒吭聲。她其實聽到了,不想接茬。
老古大聲地說:“我買了一對假核桃。”
老伴看了他一眼,說:“啥好事咋的,還這么大張旗鼓的?”
老古說:“我知道不是啥好事,但是我得找人說道說道。”
老伴說:“你甭說了,我就知道你那貪小便宜的樣兒,人家不騙你騙誰?”
以往老古總炫耀自己有眼力,在這里淘到了什么東西,那里淘到了什么寶貝,都是別人吃虧,他撿了大便宜似的。老伴就一直頗不以為然,說他凈想著撿便宜,早晚有上大當的時候。
老伴說:“你也別凈埋怨人家北京人,興許都是像你這樣的外地人呢,敗壞人家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
老古想,老伴說得也許是對的,但他沒心思去辯駁這件事兒,眼前的事兒是,這倆核桃他怎么處置呢?扔了吧,有點可惜,留著吧,還添堵。
過了幾天,老古去十里河文化城,在路邊上,他看見那里的流動商販挺多,都是賣古董和雜七雜八的。想想在兒子家也積攢了不少東西,干脆也擺個地攤得了,一是試試自己買的那些東西能不能增值,二是借此機會倒一倒錢(錢讓他花得差不多了,而要買的東西依然很多)。再者,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是想借機把那對核桃賣出去。
一聽說老古要去練攤,老伴立刻投了贊成票。她對老古買的那些破爛東西早已深惡痛絕,要不是年齡大了,她早就叫老古把它們都扔了。她特別不喜歡那些古人的東西,在她看來,那就是死人用過的東西,可每當看著老古如獲至寶的樣子,她又不忍心說他。所以,當老古表示有這個意愿的時候,她立刻大力支持,不僅是口頭支持,還付諸行動。她為老古買來帶轱轆的小車,買來折疊椅,買來礦泉水,還買了許多木糖醇的食品(老古有糖尿病),以備老古中午用餐。她還千叮嚀萬囑咐地告誡老古,一定不要生氣,不要和人家干仗。這一切,他們都是瞞著兒子進行的。
老古上街的那一天,有些陰,天上就像扯起了棉花套子。在老古的感覺中,北京的天氣大多是這樣,就是被稱為“霧霾”的那種,老古不懂得氣象和污染方面的問題,他認為這樣的天氣挺好的,既沒有太陽,還不下雨。
他拉著包,走出地鐵,雄心勃勃地出現在那條街上。那些賣貨的人都用很陌生的眼光看著老古,老古并不在乎,反正是你賣你的貨,我賣我的貨,誰也不影響誰。老古找了個地方,把自己的東西一樣一樣地掏出來,立刻就有人圍觀過來。老古留了個心眼,他沒敢把那對核桃擺出來,畢竟是假的,有些心虛。他擺上了幾個手串,那是戈壁瑪瑙的,擺上了幾塊馬達加斯加的水沖石,那些石頭真漂亮,滿身花紋;他還擺了幾個瑪瑙的小物件,比如他收藏的一個類似小豬的內蒙阿拉善的瑪瑙,那個小豬像景泰藍一樣呈現著藍色,渾身還布滿了白色的斑點;還比如他自己戴在身上的一個項墜,也是個蒙古的眼石瑪瑙,整個墜子呈現著一個桃型,桃身竟是黃色的,而周邊還有一圈一圈的葉子,葉子卷曲著,煞是好看。
一個女的走過來,她伸手拿起了那個項墜,問多少錢?老古想了想說,二百。那女的在自己胸前比了比,說,這個我要了。老古當時就后悔起來,他沒想到生意居然這樣好做。盡管這個項墜是老古幾年前買的,沒花了多少錢,好像就二十塊錢吧?但那畢竟是老古從一大堆石頭里千挑萬選出來的,老古戴在自己脖子上都有兩年了。要是現在,這么好的戈壁石在石店里咋也得上千元,關鍵是,他沒想到這個女人會要。后悔也是白搭了,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他老古可不能不講信譽。那女的旋即又拿起一塊馬達加斯加水沖瑪瑙,問多少錢,這回老古尋思,往高了抬點,他說,三百。他實際上起初打算要二百的。那個水沖瑪瑙在女人的手里攥著,女人的手很好看,是那種蔥白似的樣子。她握了握放下了,這一放下,老古的心也跟著沉了一下。是不是自己要高了?不過這些石頭來價就高,都是一百到二百來價不等,三百也不算高。這一下讓老古又后悔,那么貪心干啥,掙個三十二十的不就行了。那個女人接著又拿起了那個小豬問:“這個多少錢?”老古吸取了剛才的教訓,想了想說:“一百。”女人站起身來,從小包里邊掏錢邊說,“這兩個我要了。”
她指的當然是項墜和小豬。
女人丟在老古面前三百塊錢,倏地走了,仿佛沒來過一樣。老古望著丟在地上的三百塊錢,心里這個叫苦啊,這兩件東西都是自己最喜歡的,要不能上北京都帶著嗎?雖然當時沒花什么大價錢,可那是老古千辛萬苦淘來的東西啊!都說收藏玩的是眼力,可老古不缺乏眼力,缺乏的是對自己收藏東西的正確評價和估量它們在市場上的價值的能力。
老古感覺這個女人是很有心計的,她先是果斷地買下了吊墜,給你的印象是她出手大方,儼然是一個真正的買主。然后,又把目光投向馬達加斯加的水沖瑪瑙,而這個在他的攤位上是最多的,也是價格比較高的,她心中并不想買,而是通過終止交易打擊老古的自信心。最后,她拿起那個真正想買的小豬,在你心理處于低谷的時候,急于成交的你還敢要高價嗎?她根本不用跟你砍價,就實現了她的目的。
這個女人,真是高明。老古在贊嘆這個女人的同時,也沮喪地想,我真不是一個做買賣的人。
又一個男人過來,蹲在地攤前,比較著兩個瑪瑙的手把件,他心思不定地比較著,比較得老古老鬧心了。男人先是砍價,那瑪瑙把件倒不是什么值錢的玩意兒,老古是二十進來的,他才要五十,不打算賣高,三十就行。男人砍到四十,老古同意了。
要是擱別人,可能早就拿起其中的一個走了,可是那個人還是反復比較,最后居然還仰著臉問起老古:“你說,哪一個好呢?”
老古心中當然有自己的判斷,當初老古本來只相中了一個,他是要帶給一個朋友的。后來,在講價的時候,那個賣貨的小姑娘說,你要是買倆就四十,他所以買了倆。他把自己相中的那個指給了男人。男人高興地站起身來,拿著那個手把件心滿意足地走了。
老古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刮子,你說你是什么賣貨的啊?人家讓你幫著挑,你把不好的那件告訴人家不就得了?老古啊老古,你說你能賣貨么?
老古就這樣苦惱著熬了一上午,中午吃過飯,人漸稀少,老古有些倦意,正待回家。這時,老伴來短信,問:賣得怎么樣?老古炫耀地回短信,說,“賣了三百四,”他迅速地在心里盤算了一下,項墜成本20,小豬成本50,手把件成本20,“純利二百五”,他發出短信后,老伴立刻發來短信:你純粹是個二百五啊。
這一句不幸被老伴言中了,真是純粹的二百五,他一想起那個小豬和桃子吊墜他就心疼,心疼也是白搭了。
第二天,老古還要去,不知怎么讓兒子知道了,兒子說,老爸,你加小心點,人家城管要管的,我從電視里看到,前幾天報道過了,那里特別地亂,有人舉報,這幾天要嚴加整頓呢,你別趕著上。
老古說,沒有啊,我昨天中午在那兒,根本沒有什么城管啊。
“還是加小心為好。”兒子說。
老古不以為然,說:“我又不和他們爭,到時候就跑唄。”
老伴一聽,害怕地說:“你還是別去了吧?這是北京,咱人生地不熟的。”
老古倔強地說:“他們橫是不能打人吧?”
兒子說:“你還真說對了,北京的城管還真就不打人。”
“那就行,”老古拉起小轱轆車,砰的一聲甩門而去。
老古的倔強是有名的,家人都有領教,所以也就由他去了。
這一天,天還是不錯的,不說是陽光燦爛,也可以認為是天氣晴朗,這樣的天氣是有助于人的心情的。由于老古已經出過一天攤,也算是老人了。那個叫老汪的,一副刀條子臉,有點自來熟,昨天就主動和老古搭訕,老古沒怎么理他,老古比較討厭這種人。此刻,老汪手上、脖子上都掛著物件,長長短短,好像他自身就是一個古董架。他看了看老古的東西,搖了搖頭,隔行如隔山啊,明顯對老古的東西看不懂。
這個人很愛說,他對老古吹噓說,這條路沒有的時候,他就在這兒出攤了。老古感覺他明顯在吹牛,這條路瞅著起碼也有幾十年了,他并且自相矛盾地說,幾年前他還是個外地人。這種人,老古見怪不怪,不過是愛吹個牛而已。老古就應付著,又正好問了一些問題,那個姓汪的果然快嘴快舌,介紹了這個地方的情況。老汪說,這地方是個自發的市場,原來根本沒人管,因為高峰時占道,影響交通,不久前讓記者曝了光,這一下市里區里都重視了,重兵把守,派城管死看死守,他說:“你昨天是趕巧了,他們不知白天為什么沒上班,晚上可是搞了一下突襲,收走不少人的東西呢。”
老古有些后怕,就問:“那今天沒事吧?”
老汪說:“還不清楚,誰知道呢。盯著那邊城管的車吧。”
他往那邊一指,老古根本沒看見有什么城管的車。
“現在當然還沒有,”老汪一臉不在乎地說,“是一輛白色的執法車。等看見車來了你再跑,趕趟。”
老古忐忑地擺下地攤,這次他決定把那對核桃擺上,因為對他來說,機會已經不多,過兩天他就要回家了。剛一擺上,就有人過來打聽那對核桃的價錢,也難怪,那對核桃擺在一堆石頭中,實在是太顯眼了。老古不斷地回答著別人的問價,四十四十四十,他想得很簡單,這是個假東西,便宜點賣出去。即便人家上當了,也不會當回事,也就不會回來找他算賬。自己呢,收回被騙的本錢就行。讓他意外的是,幾乎所有人聽了他說的價碼,都用懷疑或者詭秘的眼光望著老古,有的拿起來,立即燙手似的放回去,也有的特意拿起來,掉過去看看屁股,笑了笑,那笑是別有意味和充滿洞察的,甚至很像是嘲笑。
老古身上立刻像爬了一百個螞蟻,奇癢難忍,但他不知道為什么這些人聽了他的報價,就會有這樣的不屑。
后來,老汪走過來,努著嘴問他:“你這對核桃多少錢?”
老古說:“四十。”
老汪笑著說:“假的吧?”
老古很窘地答道:“是。”
老古于是把這對核桃的來龍去脈說了,老汪咂著嘴說:“你這個老先生,咋還上這個當?”
老古無言以對,坦誠道:“我剛玩核桃,不知道這玩意兒水這么深。”
老汪說:“我擺弄核桃許多年了,核桃造假很早,現在就更像了,你如果晃晃,還能聽到聲音。這么說吧,玩核桃的只要聽說你這個價格,就知道你核桃是假的,這么好的核桃怎么會是這個價格?我給你支個招,你喊三百看看。”
老古老實是不敢喊價格,他想,明明是假的東西,怎么能按真的去賣呢?
這時,又有一個人過來,盯著那對核桃問:“這對核桃多少錢?”
老古使了使勁,說:“三百。”
說完了,他心就開始打鼓。可是,事情完全向著老汪預測的方向發展,那個人蹲下身,反復地看了看,就要掏錢。
這時,有人突然壓低聲喊道:“城管來了!”
老古立刻不好意思起來,他假借城管來這件事兒,連忙說:“不賣了,不賣了。城管來了。”
他邊說邊把那對核桃從那個人的手上要了下來。
那個人有些不高興,不依不饒地說:“你看你這個人怎么這樣,城管來了能咋的,我都掏錢了,你咋還反悔了?”
老古邊收拾東西邊說:“我就是不賣了,我就是反悔了。城管來了,沒收我的東西你賠啊?”
老汪也掐著他那些長長短短的東西,過來催促說:“老哥,還磨嘰啥呢?趕緊走啊。”
那邊,果然見城管人員穿著制服排著隊,巡視過來。買核桃的那個人見狀,顯出無奈,趕緊走了。老古這邊,連忙把所有東西包作一團,匆忙地逃走。在逃走那一刻,老古分明聽到啪嗒一聲有什么掉了,但他實在是顧不上回頭,倉惶離去。
逃到地鐵站口,他才喘了一口氣,沉穩地通過檢票口。
到了家里,老古才發現,丟掉的居然是那對假核桃。
“這真是天意啊!”老古嘆了一口氣,對老伴說。
“什么天意?”老伴說,“還不是你心里一直有鬼。”
老古想想也是,嗨,人啥時也不能心里有鬼啊!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