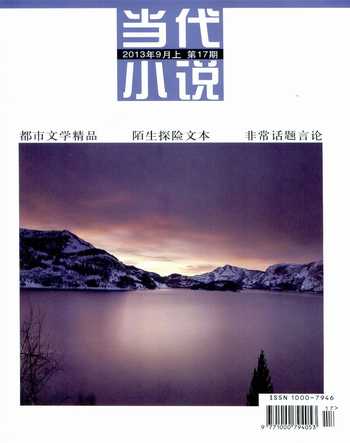秘密
劉劍波
隔床的那位昨天走了,走得平心靜氣,了無掛礙。當載著那位的鐵床從他身旁滑過時,他歪頭看了一眼。映入他眼簾的,是兩只露在白床單外面的僵硬的腳。一個人,來到這個世上時,最先露出來的也是腳。他苦笑了笑。下面,該輪到你了。以前,前頭都有很多人,他只是跟隨著,往前慢慢移動。在班會課上,老師會說,下面,該輪到你發言了。在運動會賽場上,裁判會說,下面,該輪到你起跳了。在排著長隊的食堂里,掄著長勺的師傅會說,下面,該輪到你打飯了。現在,他終于被推到最頂端了,他眼前猶若史前世界一片空曠虛渺,往后,再也不會有個聲音對他說,下面,該輪到你了。重癥監護室死一般的寂靜。這是他的看法。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誰也別指望圍繞他身邊的冰冷的監護儀、多功能呼吸治療機、麻醉機、心電圖機、起搏器、輸液泵、B超機、微量注射器會發出什么聲音來。誰置身在這些死一般的儀器中間,誰都會覺得隨時都會死去。可是這些冰冷的儀器不會讓你隨時去死。它們會將你殘留的生命像拉彈簧那樣扯到最長,直到最后發出“嘎嘣”一聲斷響。每次,迷迷糊糊醒過來時,他都會艱難地喘一口氣,我怎么還沒死?他覺得他已經死了,早在前幾天就死了,其實他應該走在那位的前頭。他知道,之所以茍延殘喘著沒走,是在等待。可是,究竟在等待著什么,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他已經沒有什么可等待的了。該交代的都交代了,藏書,日記,古玩,銀行卡和證券的密碼。該見的都見了,同學,朋友,親戚,甚或街坊,被判給前妻的女兒,及不遠萬里從歐洲趕回來的兒子。可是,他還在等待。在這個世上,做很多事都是需要理由的,惟獨等待不需要理由。
我在等待死亡?
你今天覺得怎么樣?她一進來就俯身病床,貼在他耳邊問他。她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她不想驚擾了病室的寧靜。還有,就是他的聽覺幾近于無——除了自己的綿弱的心跳,他已經什么都聽不清了。
還好。他這樣說。其實,他什么也沒說。他只是嘴唇翕動了一下。病魔已經剝奪了他使用語言的能力。可是,她能聽懂。誰叫她是他耳鬢廝磨的妻子呢?
醫生數次告訴她,她丈夫真是個奇跡。醫生這么說,是因為他幾乎所有的生命體征都消失了,可是他還頑強地活著。顯然,這種活比死亡還要痛苦,不僅他本人痛苦,他親人也痛苦,甚或比他更痛苦。所以,她內心里希望他割斷紅塵,早些上路。
你還記掛著什么呢?她貼在他耳朵上輕聲問他。他雙目緊閉,眉頭皺得像一把鎖。他在積蓄著力量。等待也是要力量的。
她想不出他還記掛著什么。應該沒有什么再讓他記掛的了。既然不記掛,那么他是不是在等待?如果真的是在等待,那么,他在等待什么?難道他……一想到這個,她不禁心頭一凜,整個人都顫抖了一下。
要說等待,其實這幾天她也在等待。她在等待一個時機,將囚禁心頭多年的秘密和盤托出。可是,有很多個時機她都錯過了,準確地說,是放棄了。在他進入重癥監護室的頭一天,她就決定告訴他事情的真相。她不想再隱瞞,不想再欺騙他了。無論他是不是原諒她,她都想說出來。她不想讓他帶著她對他的欺騙走到另一個世界去。然而,每當話到嘴邊,她又猶豫了。到底該不該告訴他?告訴他,我是解脫了,得到了救贖。可是,他呢?他會是怎樣的感受?本來,他也許能輕輕松松上路,可是,如果他得知了她的秘密,他就會突然背上沉重的負荷,這讓他怎么上路?如果是這樣,她就是落井下石,未免太殘忍了。
本來,她已經改變了主意。她不想告訴他了,就讓它在她心里爛掉,變成塵埃,隨風飄逝。可是,今天,當她再次握著他瘦骨嶙峋的手,她突然產生了告訴他的強烈愿望。這些年來,她一直生活在一種罪過之中,她不想再受這種罪過折磨了。
她再次湊近他耳朵。她想這樣告訴他:幾年前,差不多有八年吧,我背叛過你,他是我在出差的火車上遇到的一個南方男人。后來,每次我去南方出差,我都去找他。我們甚至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如果他不是在一次出行時罹難車禍,我可能已經改嫁他了。
然而,她欲言又止。因為她發現,他的嘴唇再次翕動起來。于是,她變傾訴為聆聽。他想盡量發出聲音出來。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是,這種努力是徒勞的。他的喉嚨已經被一種無形之手掐住了,再無可能發出丁點聲響,哪怕是一聲微弱的咳嗽。他只能將他想表達的東西呈現在嘴唇上。好在,她能讀懂他的唇語,盡管是斷斷續續的——
幾年前……我,我有過一次……外遇……我和她……一直保持著……性愛關系……我告訴你……是因為我……不想背負……這個秘密上路……它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
她的眼淚奔涌而出。整個世界都擋在她的淚簾之外。她替他合上了睜著的眼皮。她不知道他為什么還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