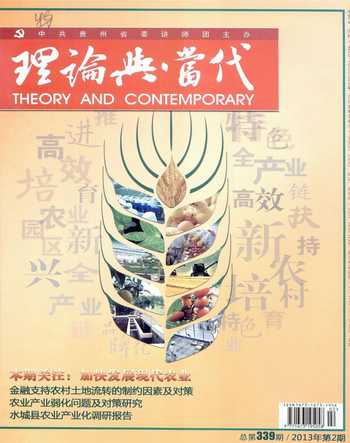碑刻與黔西南鄉村治理
李曉蘭
碑刻是前人記載時人時事的手段之一,是前代保存下來的具有較大史料價值的歷史文物,是研究近現代歷史發展狀況、社會風俗演變的寶貴資料。黔西南地區現存的近代碑刻由鄉規民約碑、禁革碑和曉諭碑、界碑、修路建橋碑、少數民族文字碑、記事碑等六類組成,廣泛分布在興仁、興義、安龍、冊亨、貞豐、普安、晴隆各縣。碑刻記事的年代從道光四年(1824年)至民國年間,超過一個世紀,主要以道光、成豐、同治、光緒四朝為主。從立碑者看,有寨老或頭人獨立、寨民合立、眾寨合立、地方知縣所立等。碑刻記載了近代以來黔西南地區鄉民在世風日下的背景下,“齊心眾議,挽此頹風,禁此不良”,進行鄉村治理、開展鄉村自救的狀況。
現存的大多數碑刻,均記載了黔西南人民遭受盜賊、窩贓嚴重侵擾的情景。位于興義縣興化鄉的水淹凼四楞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立)記載了盜賊猖獗的情形,輕者或“被賊挖墻入室”,或“被賊盜竊牛馬”,甚至“禾苗成熟之時,三五成群結交,偷割田谷”的現象屢有發生。重者更是“勾內入黨,成群入戶,劫掠財帛牛馬等件”,使得鄉民屢被“惡匪擄掠”,敢怒而不敢言。如恰逢“年歲荒歉”,再經歷偷盜、劫掠,鄉民們“田谷無幾”,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維系。長此下去,良善之民將無安身立命之所。
清朝明文規定禁賭,從《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條目眾多、懲罰嚴厲的禁賭例文即可窺知。普通民人如“將自己銀錢開場誘引賭博、經旬累月聚集無賴放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徙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禁令嚴厲反襯著清朝的賭風之盛。地處僻遠的黔西南地區也深受影響,世風日下。從現有的碑刻記載來看,黔西南地區近代以來的許多賊盜現象均起于賭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所立冊亨縣馬黑“永垂千古”碑記載:“士農工商,是君王之正民,奸詐淫惡,及鄉里之匪類,所口奸情賊盜,起于賭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立安龍縣阿能寨公議碑描述了嗜賭之徒的日常生活,“日則搖錢賭博,夜則偷盜口生”,“從不務農”。賭博使人們事業荒廢,精神沉淪,禮儀喪失,道德淪喪,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由賭博引發的偷盜等行為破壞了當地傳統的民約鄉俗,造成社會風俗敗壞,社會秩序混亂。
針對偷盜、窩贓、賭博、亂砍濫伐、不講公共衛生等現象,淳樸的鄉民為保衛家園,采取了多樣化的整治手段,安良緝盜,保護生存環境。以寨老、頭人為首的鄉寨領袖肩負起維持村寨安全、寨民生活有序的重任。他們以宗族宗法制度、重義輕利、倡導和諧的傳統儒家思想為主導,進行鄉村治理。治理的方式包括精神動員、嚴厲處罰和議定處罰條款立碑公示等。鄉內眾寨老屢次集體商議,提出了改變盜匪、窩贓、賭博、亂砍濫伐、不講公共衛生等現狀的相應對策,不僅把上述處罰方式詳列在案,而且把公議的約定俗成的處罰內容和條款鐫刻下來,采取立碑的方式,告示鄉民,自覺遵守。治理過程中,寨老、頭人等扮演著議定治理條款內容、審訊仲裁人等重要角色,同時重視鄉民的參與,在由寨老、頭人等對違反鄉規民約的鄉民直接進行審訊制裁的過程中,無論是處以行刑或誅戮,均需“聚眾”或“約眾”。通過鄉民的廣泛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治理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同時也可威懾鄉民,起到規諫、勸誡作用。
除鄉民自己采取措施挽救頹風外,當時的地方政府為維持地方的正常秩序,亦以官方名義立碑,刻下所議條款和約法,威懾地方。如位于興仁縣大橋河鄉海河寨的“奉示勒石齊心捕盜”碑,即由安義鎮府右營副府劉德達、興義縣知縣楊光輝、普安縣知縣李培基、興義府知府陳熙、安南縣知縣袁汝相、新城縣丞趙履增等六位地方官聯名所立,“守望相助,聲氣相通”。偷盜、窩贓之人,如果改過自新,“聊開一面之網”,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則“擒送官究治,活少,死多”。以官府的名義來威懾四方,安民緝盜,一方面說明黔西南地區的確存在較為嚴重的匪患,一方面也說明地方官員同樣希望社會安定,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而以地方官員名義豎立的石碑,較之鄉民所立者更有號召力與威懾力。
近代以來,黔西南地區面臨世風日下、違法犯罪日漸猖獗局面。當政的清政府自身正面臨嚴峻的內憂外患,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能力對地處偏遠的黔西南地區給予較為有效的政府行為控制。地方政府希望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在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的情況下,他們一方面制定政策措施加強官方控制,一方面寄希望于寨老、頭人等鄉寨威望較高的宗族領袖,希望他們能夠以宗法制度為本,以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維護鄉寨正常的秩序,以延伸和擴展政府對邊遠地帶的控制。此種治理方式把官治與民治結合起來,是維持邊遠地帶鄉村安全和鄉民生活有序的必然舉措和必要行為,是近代以來黔西南人民試圖營造和諧鄉村的樸素體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一。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愿望。碑刻記載的大量保護山林、禁止開挖、禁止亂砍濫伐、禁止縱火燒山的措施,就是他們對于人與自然和諧意識的樸素體現,有利于鄉民們逐漸形成良好的環境意識。當然,鄉民的環境保護意識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有的碑刻稱栽蓄樹木是為了“培風水,光前代興裕后人”,但以立碑公示的方式約束民眾不“妄砍樹木”,卻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偏僻落后、民眾文化素質低、缺乏環保意識的黔西南地區,此種方式可以廣泛號召民眾自覺參與保護森林、不亂砍濫伐,可以為后人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功德無量。
其二,體現了人與社會和諧的要求。以地方官或寨老、頭人等有威望、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人的名義,聯合寨民以及周邊村寨合立告示碑的方式,通過公認的鄉規民約、嚴厲的懲罰措施,約束和警示民眾遵規守法。正是這些大家公認的鄉規民約一定程度上約束著民眾的行為,即使世風日下,大多數鄉民仍能保持淳樸的民風,自覺抵制偷盜、窩贓、賭博等非法行為,有力地遏制了犯罪的蔓延,從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鄉民們與其所生活的鄉村社會以及鄉民之間的正常秩序,恢復鄉寨舊有的寧靜生活,回復鄉民舊有的良善品行。
其三,體現了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愿望。協調鄉民之間的關系、和諧鄉鄰、淳樸民風是碑刻記載的重要內容之一。針對“調戲人家妻女”,“估淫人妻”,鄉寨中富貴之人“恃尊凌卑,兇行磕索”,甚至僅因“口角細故”而對簿公堂的現象,碑文明確規定“不許調戲人家妻女”,“不準估淫人妻”,不準鄉寨中富貴之人“恃尊凌卑,兇行磕索”。鄉鄰之間“禁有口角細故”,如出現糾紛,應“經頭人”秉公處理,“不可枉控”。鄰里之間如有何矛盾,要先在本寨頭人處進行協調,不可意氣用事而隨意告官,以免傷了和氣。為避免因信仰、習俗上的差異導致的民教沖突再發生,冊亨州正堂特立曉諭碑,規定“所有迎神賽會,不準攀教民,倘有等情,致干查究不貸”。在西方宗教已經深入中國社會,已經成為普通鄉民必須面對的現實時,此種處理方式開始正視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現實,客觀上有利于協調民教沖突,化解矛盾。
其四。體現了人自身和諧的要求。為改變不衛生的用水方式,碑文明確規定,公共用水的井渠邊,“將雞、豬崽、口水,在此井邊合息禁止:凡不洗菜、布、衣,污穢水井”。實行居民飲水和畜養家禽、日常洗刷用水分開,保持飲水的清潔。如有違者,“豬、雞、酒加培(倍)賠完”。這些條款,說明了黔西南鄉民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開始認識到不衛生的飲水方式導致病從口入,身體各部分有機協調功能下降,從而又導致身體素質下降,疾病纏身。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注意日常衛生,才能強身健體,使身體各部分處于良性循環。
黔西南地區現存碑刻記載了鄉民們應對巨變、開展鄉村治理、以期恢復和諧鄉村的具體舉措。不可否認,他們仍然以儒家思想作為鄉村治理的主導思想,以公認的鄉規民約作為治理的基準,他們想要維護和實現的仍然是男耕女織、世外桃源般的小農生活。他們一心向善、純潔無瑕的心靈,是鑄造和諧社會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社會安定的基礎,有利于人民樹立正確的善惡觀,培育和保持樸實、善良的民風。通過對普通民眾生活處世觀念的向善誘導,引導民眾自覺樹立良好的品德,從而有利于民眾的長期安居樂業,國家的長治久安。
責任編輯:郭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