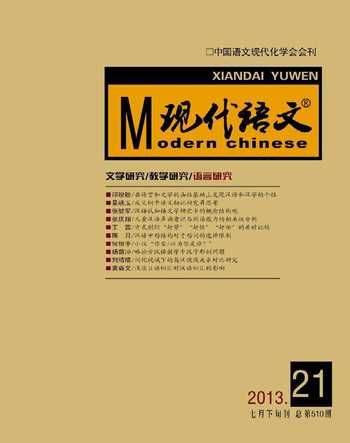漢語認知語義學研究中的概念結構觀
摘 要:本文系統回顧了新世紀以來漢語認知語義學中的概念結構研究,集中探討了詞義研究中的概念結構觀和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問題,揭示了其中蘊含的語言學思想,從中可以看到概念結構理論完全適用于漢語語言事實,可以對漢語的諸多語言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認知語義學 概念結構 概念成分 注意力強度 概念域
一、引言
新世紀以來,漢語認知語言學界的研究志趣發生了明顯的轉向,由此前的標記理論、隱喻理論轉向了概念化、主觀性和主觀化、元語理論、構式語法,近些年尤以概念結構研究為重。國外的認知語言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目前隱喻研究的熱潮已過,取而代之的必將是概念結構和構式語法。這種潮流的轉型,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本土的語言學者同國際語言學界研究興趣的不謀而合。
認知語義學同傳統語義學的首要區別就在于對語言意義本質的看法。傳統語義學關注詞語的意義及其變化歷程,而認知語義學則有所不同。Langacker一再強調,意義就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語言的意義與人類的一般認知能力和認知方式間關系密切。[1](P105-106)具體地說,詞語的意義就是語言使用者大腦中被激活的概念結構、概念網絡。這業已成為認知語義學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研究方法上,認知語義學采用概念路線,通過概念的形成過程透視詞語的意義,在特定的背景中建構相關概念間的關聯模型。由此可見,概念結構觀實質上已居于認知語義學理論體系的中心地位。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漢語學界就已經開始嘗試運用認知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具體分析漢語中一系列相關的語法、語義現象,如對“有界”和“無界”的概念區分就屬于構形結構(schematic category)中的界態(boundedness)的研究[2](P2-29),隱喻和轉喻作為一種重要的認知手段,更是認知語義學的中心話題之一[2](P30-52)。而近些年來,漢語認知語義學的研究視野更聚焦在概念結構上,體現出顯著的概念結構觀。本文擬就漢語認知語義研究中的概念結構觀展開討論,同時考察相關論著中所體現出的概念結構與語義結構的關系問題。
二、詞義研究中的概念結構觀
沈家煊[2](P71-81)曾列舉了動詞“偷”和“搶”在句法上的一系列不對稱的表現。如:
(1)*張三偷了李四。→張三搶了李四。
(2)他偷人錢了。→?他搶人錢了。
(3)張三偷了李家100塊錢。→?張三搶了李家100塊錢。
沈先生指出這一現象與動詞語義角色的“凸現(prominence)”情況有關,可以將“偷”和“搶”的語義角色構成概括如下:
“偷” [偷竊者 遭偷者 失竊物]
“搶” [搶劫者 遭搶者 搶劫物]
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搶”與“偷”相比有明確的人身攻擊意味,遭搶者所受到的損害一般要大于遭偷者,故遭搶者是搶劫事件的注意中心,受到凸現,是語義上的凸現角色(用黑體字表示),搶劫物相對成了非凸現角色;相形之下,偷竊事件的注意中心則是失竊物,失竊物是“偷”語義上的凸現角色(用黑體字表示),遭偷者不被凸現。這種經驗投射到語言形式上,凸現角色就具有了如下表現特征:
①不可隱去。通常要有句法表現形式,不能隱含。例(1)中“偷”的凸現角色“失竊物”沒有出現,這導致了該句的不合語法。
②指稱的具體性。如果用泛指形式指稱受害人,會降低凸現程度,所以例(2)中“他搶人錢了”的合格度就受到了泛指形式“人”的影響。
③較高的生命度。人比事物更能感覺到所受的損害,反過來說,事物也不像人那樣易受損害。例(3)的后一句中生命度較低的處所成分“李家”充當了遭搶者,卻并不具備相應的凸現度,因而可接受性較差,而前一句的凸現角色是失竊物“100塊錢”,故合法性不受“李家”生命度的影響。
認知語義學用概念化的視角重新解析詞語的意義結構。就動詞而言,其概念結構不僅包括所支配的語義角色的數量和類別,而且涵蓋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strength of attention)”情況。注意力強度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前景化(foregrounding)”“背景化(backgrounding)”“突出(salience)”等,上文多次提及的“凸現(prominence)”也是其中之一。注意力強度存在著級別上的差異,也就是說,在某個動詞的概念結構中,有的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要強一些,而有的則相對較弱。在動詞“偷”和“搶”的概念結構中,“失竊物”和“遭搶者”分別是受到凸現的概念成分,因而注意力強度最強,“遭偷者”和“搶劫物”是非凸現成分,注意力強度最弱。“偷竊者”和“搶劫者”也成為凸現成分,就是基于施動者在概念結構中的地位:作為偷搶行為的發出者和偷搶事件的起因,“偷竊者”和“搶劫者”理應受到關注。這一處理方式就是一種建立在廣義行為事件基礎上的公設性的一般化結論,只是具體到“偷”和“搶”的概念結構中,施動者(“偷竊者”和“搶劫者”)的注意力強度恐怕就要弱于“失竊物”和“遭搶者”,但仍強于非凸現的“遭偷者”和“搶劫物”,處于中間地位。現將“偷”和“搶”的概念成分的注意力等級表示如下(“>”讀作“強于”):
“偷” [失竊物>偷竊者>遭偷者]
“搶” [遭搶者>搶劫者>搶劫物]
如將這些成分置于抽象化的事件關系中考量,上述等級序列式就得到了進一步的提煉:
“偷” [受事>施事>奪事]
“搶” [奪事>施事>受事]
而這種概念成分的等級模式顯然對于“偷”類動詞、“搶”類動詞等動詞小類內部的其他成員也同樣具有解釋力。
上述詞義結構中概念成分和注意力強度的選擇和映現實質上是受到了“理想認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簡稱ICM)”的內在驅動與規約,Lakoff認為這一模型的提出可以較好地解釋語義范疇和概念結構,進而說明普遍的人類范疇化問題,根據Lakoff的表述,ICM至少可以從如下兩方面加以理解[3](P206-208):
1)在一般性質上,ICM體現了話語主體對特定經驗知識所作出的理解,這種理解往往是統一的、抽象的、理想化的。
2)在構成機制上,ICM是一種具有格式塔(gestalt)性質的復雜認知模型,作為完形結構,通常應建立在多個“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簡稱CM)”的基礎上。
第二點表明ICM實際上是由多個CM集合而成的集束模型(Cluster Model)。仍以動詞“偷”為例,作為一個ICM,可被分解為如下一組CM:
(CM1)一種違法犯罪行為。
(CM2)通常涉及遭偷者、偷竊者、失竊物三類對象。
(CM3)偷竊事件發生后,失竊物一般會成為關注中心。
(CM4)遭偷者遭受暴力傷害的可能性較小。
……
“偷”的理想化認知模型就可以記為:
ICM[偷]=CM1+CM2+CM3+CM4+…+CMn
單從結論上看,“偷”概念成分的構成情況似乎與三價動詞“偷”的價語形成了一致,但二者間其實存在著方法論上的不同。配價語法雖然也具有完形心理基礎,但總體上仍是基于語義層同句法層的互動關系,而以概念結構視角看待“偷”的語義結構則完全是出于語言使用者一般性的認知心理,是處于既定文化背景下的說話人對認識對象的判定、分析、理解,在此過程中,說話人的百科知識(encyclopaedia)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這也就是不少學者在論述相關問題時經常使用“常識”“生活經驗”等提法的原因。
三、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
根據語言的象似性(iconicity)原則,語義結構同句法結構間應該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對應關系,上一節提及的“偷”和“搶”概念結構中的非凸現成分可以隱去,凸現成分則不一定可以隱去[2](P76),這說明同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相對應,非凸現成分可以相對自由地脫離句法表現形式的約束,而凸現成分在部分場合下必須出現,要有句法表現形式,其中蘊含的象似性就是能看見的事物比看不見的事物更顯著、更引人注意。
如果將句法和語義視為既相對獨立又密切相關的兩個認知域(domain),上述對應關系實際上就反映了形式域同意義域之間的映射(project),構成了典型的語法隱喻。但是這種隱喻性映射卻并非表現為整齊規則的對應關系,而是一種不對當的扭曲關系(skewed relation),如下例:
(4)a.張三偷了100塊錢。
b.*張三偷了李四。
c.張三搶了100塊錢。
d.張三搶了李四。
例(4)的a、b兩句表明凸現成分“失竊物”的出現具有強制性,一旦隱去會導致句子不合法,而c、d兩句則無疑代表一類違背對應原則的例外情況,凸現成分“遭搶者”無論出現與否都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針對這類形式和意義之間部分的、不完全的對應情況,沈家煊先生[2](P220-238)認為對語法現象只能作出部分的、不完全的預測,因為形式和意義間的關系是一種有理據的約定俗成(motivated conventions)。
我們認為可以引入王寅[3](P238-251)所提出的“事件域認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簡稱ECM)”對上述例外加以解釋。事件域認知模型是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抽象概括而得出的概念結構,事件域通常包含兩類成素:行為(Action)和事體(Being)。一個行為由多個個體構成,而一個事體也是由很多個體構成的,其模型結構可以圖示如下:
如果認為例(4)a表達了一個事件域,核心行為要素就是“偷”,而事體則包括失竊物、偷竊者、遭偷者、工具等(如圖中的B1、B2……Bn)多個實體(entity)。個體數目雖多,但受到結構容量的限制,不可能都取得句法表現形式,例(4)a中就只出現了偷竊者和失竊物,遭偷者、工具等其他個體缺失,正因為這類缺省信息的存在,語言結構傳達的信息往往要少于實際事件場景含有的信息,可以用下列關系式表示這三類信息間的關系[3](P246):
實際場景信息=言語信息+缺省信息
上面的公式和圖解都清楚地顯示句子的事體表達同所對應的現實事件間存在著“部分—整體”的轉喻關系,在轉喻機制的促動下,某一語句僅用部分要素就完全可以表達整個事件,例(4)c和例(4)d就分別用[搶劫者 搶劫物]和[搶劫者 遭搶者]轉喻搶劫事件整體,而ICM框架下的凸現成分“遭搶者”在ECM框架內同其他事體個體一樣,既可以用于轉喻整體事件,也可以缺省,這就是例(4)c和例(4)d都成立的原因。不過考慮到事件性質的差異性,尤其是(4)b的不合法,我們認為也應該對概念成分的注意力強度對于ECM的影響予以充分的重視,現將上述轉喻規則表述如下:
構成某一事件的各事體要素具有同樣的轉喻功能(出現或缺省),但是注意力強度高的凸現成分相對于其他個體而言擁有實現轉喻功能的優先權。受事件性質的影響,這種優先權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
這一規則體現了原則性與或然性的統一,可以對例 (4)所代表的各種形、義間的復雜對應關系作出統一的解釋。
四、結語
現代認知心理學將人自身看成一個信息加工系統,人類作為認知主體同外部世界間始終處于動態的信息交流過程中,而概念結構正是信息加工的一類主要模式。漢語學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充分證明了概念結構理論同樣也適用于漢語的客觀事實。認知心理學還認為表象實質上體現為一種類比性,同外部實體間并不是簡單直接的一一對應關系,其間存在著認知加工過程,而對概念成分及其交互關系、組織結構的研究無疑為這一加工過程作出了很好的注解。
認知心理學的概念結構觀中的經典理論認為,一個樣例(token)或者明確地屬于某個概念或者明確地不屬于某個概念,Smith和Medin[4]則對此進行了批判,認為概念的邊界應是模糊、不明確的。這一觀念同時也為今后的概念結構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問題,比如怎樣才能更加客觀精確地給概念成分劃界或歸類等。類似課題都留待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加以解決。
注 釋:
[1]束定芳.認知語義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2]沈家煊.認知與漢語語法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3]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4]韓勱.認知心理學中概念結構觀的演變[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張健軍 遼寧大連 東北財經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 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