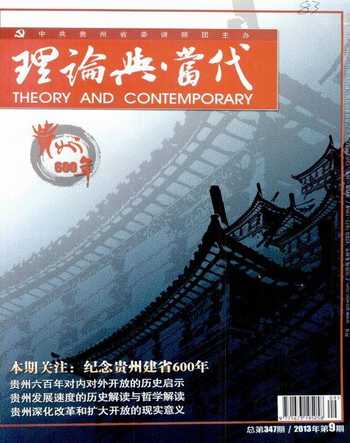貴州發展速度的歷史解讀與哲學解讀
李發耀
一、貴州發展速度的歷史解讀
在貴州的發展過程中,貧困一直伴隨著貴州的歷史進程,從速度的視角看,貴州經濟社會的歷史發展始終圍繞零上下小幅度徘徊。貴州之窮,自古以來,已成定論。《貴州通志·財賦》(嘉靖)中說:“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貴州為最后,故貴州財賦所出,不能當中原一大部,諸所應用大半仰給于川湖。”郭子章<黔記·止榷>中說:“貴州崎嶇……國家以滇南門戶而郡縣之,兵倚協川、湖征解,愆期動欲脫中,商苦賤盜,卻往來稀少,天下最為苦之地,不宜驚擾”。
明代全國十三布政司中,貴州田賦最少,十五年(1502年),全國共征夏稅大小麥462.559萬石、秋糧2216.6665萬石、平均數為夏稅35.5814萬石,秋糧170.5128萬石,而貴州征夏稅玫蕎255石、秋糧4.7442萬石,分別為全國平均數的0.7‰和2.78‰。當年,夏稅以陜西布政司72.5796萬石為最高,秋糧以江西布政司的252.8269萬石為最高,它們分別是貴州布政司的2846.26倍和53.29倍。與鄰省相比,貴州也顯得很少,當年,四川夏稅39.9594萬石、秋糧71.7078萬石:湖廣夏稅13.14萬石、秋糧203.6102萬石;廣西夏稅3390石、秋糧42.6636萬石,云南夏稅3.3708萬石、秋糧16.6913萬石。
到了清代,清政府推行地丁制,將丁賦攤入地畝的納稅人丁額為3.7731萬。這是全國定額最少的,當時除云南14萬,其他省都在三四十萬以上,最多的是四川,額定丁數為380萬。但由于貴州戶籍無定,直至乾隆十二年后,貴州始行地丁制,到了道光時期,貴州的人口及生產達到了高峰,但同全國其他省比,貴州的賦稅收入仍是最少的。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為例,各直省地丁銀收入是:直隸262萬,江蘇356萬,安徽187萬,江西229萬,浙江188萬,福建145萬,湖北52萬,湖南87萬,河南292萬,山東303萬,山西314萬,陜西169萬,甘肅33萬,四川108萬,廣東113萬,廣西96萬云南86萬,貴州12萬。上述各省的地丁銀收入中,除貴州而外,最高的江蘇356萬和最低的甘肅33萬分別是貴州的29.7倍和2.75倍。與貴州相鄰的省份都全部在7倍以上。總計清代的丁銀雜賦,在政黨景每年僅為18萬兩至20萬之間,年支出卻是90萬兩(包括兵餉55萬兩)。整個財政處在困難境地。
貴州的發展速度在歷史上經常性地以負數存在,自開省以來,糧荒、銀荒始終是頭疼的大事。解決的辦法,就是朝廷對貴州實行“協濟”。協濟有三種情況:一是命湖廣、四川兩省每年固定將銀糧解納貴州以保證日常開支;二是因云南過往貴州驛道頻繁而給予驛道補貼;三是遇有戰事則令有關省區協濟錢糧以作軍費。明代每年對貴州的協濟大約是:糧5萬余石,布6萬匹,銀5萬余兩,外加云南協濟驛站銀1500兩,其數約占貴州財政收入的60%嘲。清沿明制,從清初起貴州也一直是靠外省的協濟度日,正常年份,各協濟省一般都按時撥解,但在荒年或遇有大的戰事發生時,則往往拖欠協款,這時只有受協省自己另請中央設法解決。
貴州的發展速度長期受原生性貧困制約,歷史上經常性地出現基本生存問題無法解決,經濟社會發展是一部輸血的歷史,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包袱,這種貧困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期。一方面是人均耕地僅0.8畝,其中保證灌溉的基本農田僅0.3畝,全省每年均需從外省調進7.5億公斤以上的糧食,另一方面是鄰省發展速度加快,貴州與之相比差距逐漸擴大。進入90年代,全省各級財政每年投入大量資金興修水利,實施環境改造工程,大力科技興農,糧食生產在連續6年豐收之后,到1998年產量達到110億公斤,貴州才歷史性地突破糧食自給。
在這樣的背景下,“貴州發展速度”的提出和實現既是對貴州歷史的總結判斷,也是對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改變的要求。
二、貴州發展速度的哲學解讀
“貴州發展速度”是貴州歷史面貌改變的要求,是貴州經濟社會大發展的總結,只有加快發展,調整發展。才會走出歷史貧困的邏輯循環。這就是“穩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則快、又好又快”。
在哲學上,速度是一個統籌時間和空間相對變化的運動狀態描述,決定速度快慢的因素包括:矢量、大小、方向,速度的運動軌跡有直線運動和曲線運動,速度的運動方式有勻速運動和變速運動,速度的特殊表達是加速度,包括勻變速運動和變加速運動,加速度是“貴州發展速度”的核心和關鍵。
“貴州發展速度”是對貴州貧困形成與發展的全面詮釋,是針對貴州貧困的問題追問,貴州貧困有著特殊性的“源”。貴州的貧困,屬于原生型貧困,具有先天性,貧困的積累程度深,覆蓋范圍廣,跨度時間長,這是歷史貴州的特點,是今天的現實存在。首先,貴州的貧困條件決定了貴州貧困的形成。貴州位于云貴高原東部的滇東高原湘西丘陵之間的過渡地區,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廣西丘陵之間的亞熱帶巖溶化的高原山區,地形破碎,地面崎嶇,地形的水平切割密度和垂直切割嘗試均居全國的前列。高原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97%,盆地及河谷壩子僅占3%,全省70%以上的地區均是石灰巖等碳酸巖發育活躍的巖溶地區。喀斯特面積13萬平方公里,喀斯特分布的縣市達83個,占全省總縣市的95%。由于喀斯特廣布,山高坡陡,加上成土緩慢,風土層瘠薄而不易存留,石漠化是這些地區耕地的普遍特征。大自然賦予貴州的是:封閉、貧瘠、饑荒、災害,這樣的物質生產環境,生存首先是第一大挑戰,在農耕時代,自然的貧困是貧困的第一要素,地理的貧困直接導致了物質的貧困,注定了貴州社會發展的歷史滯后。其次,貴州在全國政治板塊、經濟板塊、文化板塊的大格局中,處于邊緣位置。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自我被動地偏離主流位置。秦漢之際,中原地主經濟已相當發達,而此時貴州夜郎侯還不知道“漢孰與我大”。如果說漢代貴州還與中原和巴蜀有一定聯系,到了魏晉南北朝則進入了400年之久的封閉期。唐代有過轉機,但處于大唐與南詔戰爭的前沿。歷史的發展進程并沒有得到加快。南宋時期朝廷在南方開馬市,貴州地方一度卷入并受惠于全國市場但也維持100多年,時局的變化迅速中斷了這種短暫的發展。進入明代,貴州獲得了發展加速的外來動力,大規模地開驛道、屯田、養馬、移民。然而,這樣的結果卻同時伴隨著頻繁的戰爭。歷史本身并沒有超越原來的起點,貴州地方仍處于“畬山為田,不以牛耕,第歲易”的落后的農耕狀態,自然經濟普遍存在,各地大量保留原始經濟成分,殘存著許多古老的制度經濟的痕跡。明清時期,在貴州“改土歸流”一直是重點,作為一種強力的進步變革,其歷史意義是重大的,然而實施的過程只是為了制夷,變革并沒有給貴州引出新的動力機制,反而使原來的社會基礎在外力作用下出現畸變,加劇內部發展的不平衡。
“貴州發展速度”是對貴州改變發展的真切要求。縱觀貴州歷史進程,一方面,是沿著單一的邏輯自身發展:另外一方面,歷史生態長期遭到破壞,社會進步緩慢。從秦漢至明清時期的兩千多年間,歷代中央王朝均采取“不邊不內”的羈縻和“懷柔”政策治理。治理的目標和結果,只要該地不禍及中原,作為化外之地,符合中央的政治、軍事一統即可。即便是建省,也是從軍事戰略的需要出發。貴州曾宣布政使司的行政版圖,是以黔中為核心,包括湖廣、四川、云南等3個布政使司相鄰邊區,整個區域實際上是地理特征相同的山區邊角組合,這些地方人煙稀少,山川阻隔,難于聯系交往。自然條件又使得民族地理分布格局明顯,各民族之間以及同一民族內部,構成一個個封閉的有地域特色的“溪峒”或“山原”,這些獨立的自然群體在歷史進程中很少受到外界沖擊力和吸引力的影響,也使得貴州整體發展呈現出封閉軌跡的現象。
“貴州發展速度”運用發展哲學總結貴州歷史。貴州遠離全國發展的中心,先進的文化、生產力對貴州的影響極其微弱。歷史上全國每一次發展浪潮的出現,貴州均失之交臂。貴州與鄰省相比,經濟的發展程度差異甚大。零星的發展支離破碎,歷史進程難以獲得連續的、統一的、有效的整體性開發,始終處于一種低水平的徘徊發展階段。貧困的歷史造成貴州發展的內在不足。發展的內在不足又造成歷史發展的貧困,每一次在回應時代主題的時候,發展的方式都不自覺地是被迫式的、反映式的、階段式的。于是,貧困在貴州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永恒話題。“貴州發展速度”從變的視角提出了貴州發展的主題和發展目標。
三、貴州發展速度的實現與保障
“貴州發展速度”的主體是“人”,是“貴州人”求變的發展意志與發展決心。
“貴州發展速度”的第一要素是貴州人。人構成歷史,人是歷史的主體。貴州歷史發展的貧困,也即是貴州人的貧困。貴州的貧困體現出來的主要有兩方面:制度貧困與發展貧困,這兩個貧困長期互動,貴州始終沒有走出貧困的歷史循環。從地理特征看,貴州是以溪峒和山原構成人的生存環境。與周邊鄰省相比,貴州的生態板塊自成一體。這種板塊先天具有封閉性,再加上貴州緩慢的歷史進程,人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文化積累與外部相比有很強的自生性。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點上發展,在人或社會的形態方面,大多數世居民族仍處于自然發生的人的依賴關系的血緣群體和血緣與地緣相伴生的群體本位的生活方式,姻親—血緣一地緣,這是表現出來的重要特征。貴州是多元民族地區,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區長期固守著自己特有組織方式,如:黔南“瑤山”的瑤族的“油鍋”制和“石牌”制,黔東南苗族的‘‘議榔”制和侗族的“峒款”制,黔西南布依族的“亭目”制,黔南布依族水族的“奉”制,黔西北和黔西彝族的“則溪”制,黔中安平(平壩)—廣順—歸化(紫云)等地多民族的“枝”制,這些制度維系了民族地區的碰撞,阻礙了外來文化的輸入傳遞。制度是歷史生存的選擇,制度也是生產力,貴州的貧困正是因為缺少了一種適應時代發展的機制,使得社會發展的內動力沒有得到充分挖掘。
貴州發展速度是貴州發展貧困的轉身。發展貧困是貴州貧困的歷史延續,歷史的發展貧困是貴州人對發展缺乏意志和失去信心的綜合反映,這比現實的物質貧困更深重、更可怕、更難以擺脫,因為它容易形成“物質貧困——精神貧困——物質貧困——精神更貧困”的惡性循環模式。事實上,貴州的這一方面早已形成并存在。由于惡劣的環境和長期貧困的折磨,使得許多人形成了強烈的宿命感,聽天由命,消極無為。他們把自己的貧困歸于老天的安排和命運所定,面對貧困,他們不是窮窮則思變,而是無可奈何地忍受貧困,即使產生某種想法,也是信天、信視野、修碑、建廟、求神。群體性地老守田園,安樂現狀。對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著本能的隔膜和心理抵拒,正如魯迅筆下的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樣,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從而駐足貧困。更為重要的是,整個貴州從上到下,不自覺得有著“等、靠、要”的依賴心理,一種貧困歷史的長期心靈積存,身在貧困不知貧,沒有挑戰貧困、創新生活的任何精神動力,在某種程度上,這又是一種價值貧困、精神貧困,也是更難治愈的貧困,其他貧困只是外相,發展貧困是貴州歷史真正走不出貧困的深層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判斷,“貴州發展速度”的提出明確了消除發展意志的惰性,堅定發展現狀改變的決心,以高于全國平均發展的“貴州發展速度”創造和實現歷史。
(作者單位:貴州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