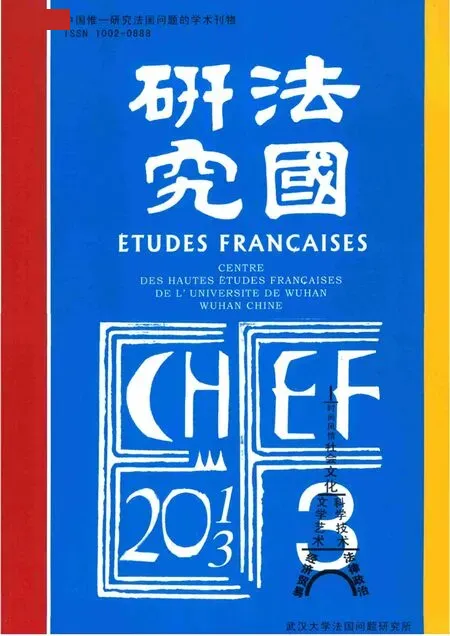芻議中世紀教權與法國王權之關系
王首貞
1209年至1229年的阿爾比十字軍作為天主教會發展史上臭名昭著的事件永久載入西歐史冊。回顧這場持續二十年之久的所謂“圣戰”,倘若不是法國王室在戰爭后期的鼎力參與,其結果將會完全不同①有關法國王室對阿爾比戰爭的支持,詳見:王首貞,《中世紀卡塔爾教派研究——以圖盧茲地區為中心(1145-1234年)》,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1月,第144-149頁。另見:W. A. Sibly, M. D. Sibly,The Chronicle of William of Puylaurens, Woodbridge, The Boy dell Press, 2003, p. 130.。從戰后《巴黎和約》的簽署與交戰雙方對南部領土的安排加以判斷②W. A. Sibly, M. D. Sibly, 2003, p.138。,教皇與法國王室之間的關系在當時似乎是融洽和友好的。據《巴黎和約》條款,在確保和平的名義下對南部法國奧克西坦各項事務作出的安排都有教皇與法國國王的共同見證。就此而論,在阿爾比戰爭結束后的 13世紀上半葉,羅馬教廷與法國王室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平衡和妥協。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歐洲局勢的變動,這種貌合神離的關系很快證明是極其脆弱的。由于海峽對岸的安哲文帝國(Angevin empire)對法蘭西國家的戰爭威脅日益迫近,法蘭西王室的各項戰爭準備已迫在眉睫。戰事頻仍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王室的財政負擔。為了緩解王室的財政壓力,法國國王把矛頭對準一向享有稅收豁免權的西多會修道院。沖突迅即在腓力四世(Philip IV the Fair)國王與時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之間爆發。盡管14世紀初法國籍教皇克萊蒙特五世(Clement V)的繼任曾令雙方之間的矛盾得以短暫平息,但這終究未能阻止沖突愈演愈烈的態勢。不久,腓力四世在關于圣殿騎士團的問題上給予教廷當頭棒喝。教皇在這次事件中飽受凌辱,從此一蹶不振。對于羅馬教廷而言,繼之而來的是 14世紀漫長的“阿維農之囚”階段。總之,關于中世紀盛期法國王權與羅馬教廷教權之間的關系演變,美國中世紀史家威廉·喬丹(William C. Jordan)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他認為在現實層面兩者處于“永恒的紛爭”狀態①William C. Jordan, Unceasing Strife, Unending Fear,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筆者通過剖析14世紀前后法國王權與教廷教權之間的關系,主張正是這一階段的政教關系為未來數世紀天主教會的歷史發展定下了基調,并由此深刻影響著西歐社會整體的歷史進程。
一、歷史性的妥協
1198年當博學多才的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繼任教皇職位時,擺在他面前的基督教歐洲絕非是一個平靜的世界。這位中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教皇在推行教會改革這一宏偉藍圖時,不得不尋求與世俗國王之間的妥協。此時,無論法國王室還是羅馬教廷都面臨著更為棘手的問題亟待處理。一方面,法國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Augustus)的壓力主要來自海峽對岸正在崛起的安哲文帝國,因為自 1160年代末法國國王路易七世第二任妻子卡斯提爾的康斯坦茨去世后,卡佩王朝與安哲文帝國之間由于領地紛爭導致矛盾不斷。“盡管卡佩王朝路易七世對和平的熱愛給所有同時代人留下銘心的記憶”,但面對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于 12世紀后半葉起在大陸諾曼底、阿奎丹等地奉行的擴張主義政策頻頻施壓②有關金雀花王朝國王亨利二世的擴張政策,詳見:John Gillingham, The Angevin Empire, New York, Holmes& Meier Publisher, 1984, pp.27-30.,路易七世只能疲于奔命。另一方面,12世紀末的羅馬天主教會亦是危機重重。盡管格雷戈里七世(Gregory VII)的教會改革計劃已基本完成,但是嚴重的世俗化現象向天主教會各個角落的廣泛滲透已然使其積重難返。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對西歐各地新千禧年到來后出現的大眾異議思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別是以卡塔爾教派(Cathars)為代表的天主教異議教派在南部法國等地強勁的傳播勢頭③這一時期天主教異議思想在西歐各地的廣泛傳播,詳見:王首貞,《12世紀西歐大眾異端起源探析》,《法國研究》2011(4);王首貞,《中世紀卡塔爾教派研究》,第45-67頁。,正在撼動羅馬天主教會的統治權威。因此當英諾森三世在 12世紀末繼任教皇職位時,消除天主教異議思潮的影響并重振天主教會昔日的聲望,成為這位法學家教皇必須擔負的當務之急的使命④英諾森三世改革教會的藍圖主要記載于其任期內召開的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的相關文件中。此外,為了消除天主教異議思潮的影響,英諾森三世任期內羅馬教廷發起了阿爾比十字軍。詳見:王首貞,《神圣光環:1209-1229年阿爾比十字軍考察》,《歷史教學》2011(14);Norman P. Tanner S. J. ed.,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30-271。。
由此可見,在 12、13世紀之交的西歐,無論是羅馬教廷還是卡佩王朝的法國都因更加迫切的其他事務之牽制而自顧不暇。特別是羅馬教廷更加岌岌可危,由于在授職權問題上的爭議(Investiture Controversy)⑤這是一場自11世紀末至12世紀前期發生于帝國皇帝、法國國王、英國國王等世俗君主與教皇之間的、在主教授任權問題上的爭議。1122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的簽署,標志著這場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紛爭落下帷幕。詳見: William C. Jordan, 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1, pp.85-9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它已與帝國皇帝之間結下宿怨。于是當面對遍及歐陸的天主教異議思潮不斷向天主教會權威發起挑戰時,卡佩王朝的法國無疑成為教皇在大陸地區僅有的潛在援助者。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天主教異議思想在南部法國阿奎丹、圖盧茲等地的傳播勢頭更為強勁不無關聯,這里傳統上屬于法國王室領轄。因此,13世紀初法國王權與教廷教權之間能夠保持一種表面的妥協與平靜便不足為奇。不過13世紀上半葉的阿爾比戰爭徹底打破了兩者之間的權力平衡,14世紀起羅馬教廷已是日暮途窮。阿爾比戰爭期間羅馬教廷在處理宗教紛爭問題上對法國王室的依賴,為羅馬教廷教權的衰落埋下了禍根。法國則漁翁得利,戰后通過《巴黎和約》很快兼并了南部幅員遼闊、文化昌明的廣大地區,奠定了法蘭西民族國家在 14世紀甚至更長時段擴張的基本版圖。
二、權力平衡的打破
法國王室與羅馬教廷之間勢力平衡的打破根本上應當追溯至 13世紀初的阿爾比“圣戰”。在阿爾比戰爭中,羅馬教廷主要憑借的是北部法國天主教貴族的力量,法國國王也在道義上對這場所謂的圣戰表示支持,并在戰爭后一階段當“圣戰”隊伍遭遇重創后積極參與其中。這場基督教世界內部的大屠殺以對法蘭西王室絕對有利的戰后安排宣告結束。根據 1229年簽署的《巴黎和約》,法國南部重要市鎮圖盧茲城的雷蒙德七世伯爵同意將“羅納河以外屬于法蘭西王國的領地以及隸屬于或者可能屬于伯爵的所有權利,現在都絕對地并永久性地以羅馬教會的名義讓渡給教廷使節監管……同時根據教廷使節的授意,同意把圖盧茲的城墻夷為平地”①W. A. Sibly, M. D. Sibly, 2003, p.142。。此外,對于圖盧茲伯爵管轄范圍內的其他三十個市鎮和城堡——凡耀(Fanjeaux), 卡斯特納達里(Castelnaudary)、阿維農(Avignonet)、 皮洛朗(Puylaurens)、阿讓(Agen)等——也作出同樣安排。這些安排意味著南部法國的自治城市將很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與此同時,《巴黎和約》規定雷蒙德七世繼續享有圖盧茲伯爵的稱號,撤銷戰爭中羅馬教廷對其一切指控,但重申他必須保證效忠于未滿15歲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根據和約中的聯姻與繼承條款,1249年9月法國如約吞并了圖盧茲伯爵領,加龍河畔(Garonne River)這塊是非之地最終成為“奧克語”區(Tongue of Oc),亦即現在的法國朗格多克省②有關Tongue在此處的翻譯,這里取其字面意義。詳見:Mark G. Pegg, A Most Holy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1。。總之,從阿爾比戰爭后的各項事務安排看,法國王室力量在戰后乘機得以擴張,它實際控制了南部的廣大地區。伴隨著法國王室對奧克西坦事務的干預,其在圖盧茲地區的影響日益擴大,從而為統一的法蘭西國家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卡佩王朝對奧克西坦事務的干預卻成為羅馬教廷在該地區鞏固教權的一大隱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爾比戰爭的結束恰恰預示著教權的式微。盡管羅馬教廷與法國王室曾經在同一陣營中并肩作戰且共同參與 1229年《巴黎和約》的簽署。但是條約的具體條款已經表明,法國王室才是戰后事務安排的主導力量。這里需要提及的是,為了能在未來順理成章地吞并圖盧茲伯爵領地(注:此處指上文 1249年的事件),法國國王蓄意安排了雷蒙德七世是年年僅九歲的女兒的婚姻③Mark G. Pegg, 2008, pp. 180-181; Dom CL. Devic & Dom J. Vaisset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nguedoc,Toulouse, M. Edouard Dulaurier, 1790, p.649。。對于王室力量的鞏固至關重要的是,對于《巴黎和約》中的任何一項條款——即使在對“異端”問題的處置上——雷蒙德七世都必須向法國王室做出承諾。至此,法國王室以捍衛信仰之名參與戰爭的真實意圖已昭然若揭。實際上,從戰爭前路易八世寫給教皇洪諾留三世(Honorius III)的信件亦可得知,法國王室的參戰與其說是在協助教廷處置教會“異端”問題,勿寧說更多是在謀求王室在南部地區的戰略利益④W. A. Sibly, M. D. Sibly, 2003, pp.132-13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阿爾比戰爭的“雙刃劍”最終扼殺了羅馬教廷在南部鞏固權威的最后一線希望。戰前路易八世就把參與這場“圣戰”視為一次與教皇討價還價的契機,戰爭的結局已經表明它實際為法國在南部地區擴大影響掃清了障礙——因為就連這里勢力最大的領主圖盧茲伯爵也不得不向法國王室表示臣服。正如現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分析的那樣,通過阿爾比戰爭,“教廷雖然仍能取得一些顯赫的勝利,但其日后衰落的景象卻已可預見于此了”⑤【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39頁。。
關于法國王室和羅馬教廷在阿爾比戰爭中的多重關系及其對羅馬教廷帶來的影響,美國學者約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分析稱:
“如果宗教異議群體能夠通過刀劍得以粉碎的話,那么政治上的異義群體——對于教皇的反抗——亦可通過這把刀劍得以征服……如果法國王室家族應當對阿爾比十字軍的最終勝利負責,那么他們同樣需要對教皇發動的其他戰爭負責。只要他們能夠從中獲得報償,法國王室又何樂而不為呢。這樣一來,教會在依賴法國支持方面就會變得愈加危險。當 13世紀末法國國王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間產生糾紛時,教皇愕然發現自己竟是如此孤立無援。即使他遭遇法國人領導的陰謀者團伙劫持并蒙受奇恥大辱①此處指1303年9月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遭遇法國貴族的綁架,詳見下文。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教皇與法國國王之間因征稅等一系列問題所導致的沖突不斷升級,雙方之間的矛盾在法國國王腓力四世(1285-1314)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時期最為激烈。教皇與法國王室之間的持續沖突最終導致中世紀教權日漸式微。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Papacy 詞條。(Jordan,2005:3、7),也沒有人能施以援助之手。卜尼法斯的繼任者根本不敢在意大利生活,他們只能避難于法國邊境的阿維農小城。盡管教皇在此 70多年的駐足使教會管理機構得以改善,然而它卻失去了大部分精神權威。他們鏟除了異端、打敗了政敵,但這時卻只能從朋友那里獲得不溫不火的幫助。14世紀的神圣羅馬教會要比13世紀更加虛弱,并且影響力劇減。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宗教改革時期”②Joseph R. Strayer,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reface,p.3。。
此外,阿爾比戰爭后教廷與王室之間頻發的沖突也使其在處理 14世紀的社會危機時陷于困境。據美國中世紀史家威廉·喬丹研究,
“教皇與國王之間關系中的多重束縛使其在面臨大饑荒時難以協調并給予救濟……教會與王室沖突使其在面對民眾的宗教熱忱時幾乎不可能做出機敏而有效的回應……對于那些遭受因黑死病帶來的各種社會、經濟的‘脫臼’的人們,從來不存在真正的和充分的救助”③William C. Jordan, 2001, p.314。。
總之,阿爾比戰爭中法國王室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戰后卡佩王朝對南部地區的實際控制,從客觀上削弱了教權和天主教會在該地區的影響。13世紀上半葉卡佩王朝王權與羅馬教廷教權之間權力平衡的打破,注定教廷在 14世紀遭遇更加悲慘的命運,這鮮明地體現在“阿維農之囚”④在法國國王頻頻施壓下,1309年身為阿奎丹人的克萊蒙特五世教皇不得不把教宗座(Curia) 遷至羅納河畔的阿維農,由此開始了天主教會歷史上長達七十年之久的“阿維農之囚”(1309-1377年)。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Papacy。(Jordan,2005:18)的劇情中。
三、教權與王權的正面交鋒
伴隨法國王權與羅馬教廷之間權力平衡的打破,卡佩王朝法國開始奉行擴張主義政策⑤當阿爾比戰爭激烈進行之時,法蘭西王室已經開啟了其擴張政策。詳見:John Gillingham , pp. 82-5.,這使得法王與教皇之間在14世紀遭遇多次正面沖突。沖突最初由限制教廷在法國境內的征稅權引發,在關于圣殿騎士團問題的爭議中達于頂峰,最終以教會的“阿維農之囚”宣告結束。
教廷與法國王室之間的緊張關系至少應追溯至 13世紀末。當時,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與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因阿奎丹公爵領——位于南部法國,但英王愛德華一世從法王腓力四世那里作為采邑而取得——的統治權問題發生了戰爭。兩位國王都期望其臣民在戰爭中給予財政支持。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雙方都沒有征得教皇的正式許可便開始向領地上的牧師征稅。但是依據 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教規,向教皇的請示是不可缺少的⑥Norman P. Tanner S. J. ed., pp.259-260。。對教廷更大的挑釁是關于西多會修道院的征稅問題。西多會修道院是一個具有稅收豁免權的修道院,通常情況下它即使對十字軍國王也不承擔財政支持義務。戰爭前期西多會修道院對英王的慷慨解囊已經讓修道院處于一貧如洗的境地①西多會修道院此時亦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因為新修道團體的興起已經使其失去許多信眾,此時的王室征稅無疑于雪上加霜。(Jordan,2005:4),但這次仍未能幸免于難(Jordan,2005:3)。為了維護教會權利,時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2月發布教皇通榆,禁止修道院向國王支付款項并以開除教籍相威脅。腓力四世對此的回應是禁止向羅馬出口貴金屬,這些舉動令雙方關系雪上加霜,因為教廷的財政福利主要依賴位于高盧地區的教會作出的貢獻。頑固的卜尼法斯八世以維護教會自由為借口而不甘示弱。作為當時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王,腓力四世亦不會善罷甘休。他派遣使臣彼得·福洛特(Pierre Flote)親臨羅馬城并以支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反對者、意大利紅衣主教相威脅,教皇無可奈何只好作出讓步。1297年教皇在新發布的諭令中解釋稱,盡管國王在向西多會征稅前取得教皇許可是適當的,但某些情況下——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時——國王在履行上帝賦予其的捍衛領土的義務時,并不能坐等教會許可。至于什么情況屬于危機時刻則完全由世俗君主進行確認。至此,13世紀末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修道院征稅問題上的矛盾暫時得以平息。
然而,14世紀教權與法國王權之間的沖突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紀初一位南部法國主教、帕米爾的伯納德·賽斯特(Bernard Saisset)對腓力四世國王進行惡意誹謗②該主教聲稱腓力四世像一只貓頭鷹,盡管溫文爾雅但卻呆若木雞,并把他謔稱為惡棍,有朝一日其王國將會被剝奪。(Jordan,2005:5);加之因法國國王對宗教裁判機構——為根除教會“異端”于 1234年設立——某種程度上的支持,南部民眾已經對法國王室表現出不滿和抗議。此時帕米爾主教賽斯特散布有關國王的流言蜚語,在腓力四世看來無異于玩火自焚。接下來對這位主教的逮捕和司法審判——更多的是激情而非清醒思考——在某些方面觸犯了教會法,例如首先將賽斯特主教囚禁于世俗監獄。這一舉動在教皇看來無疑是對教會自由的一種挑釁。卜尼法斯八世一反之前迫于教廷財政壓力而表現出的溫和態度,他于1301年12月發布諭令,以激烈言辭譴責腓力四世。這一做法嚴重冒犯到法國國王和國王法庭上的臣屬。形勢急轉直下,一場新的沖突在所難免。據威廉·喬丹教授研究,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戲劇性的場景不斷在法國國王與教廷之間上演。為了支持腓力四世,那些“艷羨其高貴血統并極盡諂媚之事”的法國貴族、教會人士和市民集合起來共同為國王出謀劃策。他們甚至直接向教皇寫信以抗議紅衣主教,并三番五次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本人發起控訴。巴黎大學的一些追隨者甚至于1303年6月指控教皇犯下“異常、巨大、恐怖和可惡的罪行——其中某些顯然有異端的意味”(Jordan,2005:7)。對于這種“大逆不道”的控訴,教皇試圖通過廢除法國王位予以反擊。然而,腓力四世在其臣民的積極響應下先發制人,在卜尼法斯八世尚未發布諭令前,王室間諜就在其寓所將其逮捕。此后不久卜尼法斯八世在郁郁寡歡中結束了生命,繼任者是那位短命的教皇本篤十一世。經歷近一年的教皇空位后,1305年6月一位來自南部的法國人克萊蒙特五世當選教皇。與之前桀驁不馴的卜尼法斯八世相比,這位法國籍教皇與國王之間的關系較為融洽。綜上所述,腓力四世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關于西多會修道院的征稅問題上引發的爭執,已經為 14世紀法國王權與教權之間的關系譜寫下不和諧的音符,這種局面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對法國王權的影響。
四、14世紀法國王權的勝利
盡管早在 1305年克萊蒙特五世就已繼任教皇職,然而迫于法國王室的壓力他遲遲未能移居羅馬,并最終于 1309年將其寓所確定在羅納河畔(Rhone River)的南部法國城市阿維農,開始了教會歷史上的“阿維農之囚”。阿維農教廷延續至 1378年教會大分裂前,在這期間所有的七位教皇都由法國人擔任①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Avignon Papacy.。美國中世紀史學家威廉·喬丹曾意味深長地指出,“至 1306年秋天——在克萊蒙特五世繼任教皇一年之久后——許多人都在尋思著圣彼得的精神繼任人為何不離開波爾多前往圣彼得的教區,他們對此表示了憂慮”(Jordan,2005:18)。當然,作為一名阿奎丹人,克萊蒙特五世對南部法國的語言和文化更有一種親切感,這固然是他長久駐足阿奎丹的波爾多城的原因之一。不過從當時法國王室與教廷之間的關系來看,更多也許是受到法國王室的施壓。但是,克萊蒙特五世這位法國籍教皇的繼任并沒能最終阻止王室與教廷之間沖突的不斷升級。如上文所述,由于與金雀花王朝之間在爭奪領土方面的綿延戰事,法國國王在整個 14世紀都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為形勢所迫,圣殿騎士團問題成為法國國王緩解財政困境的權宜之策,這一軍事修道團因長期的稅收豁免權而在法國擁有龐大地產和財富。通過在圣殿騎士團問題上的新一輪較量,羅馬教廷最終屈服于野心勃勃的法國國王美男子腓力。
其實,1305年新任教皇克萊蒙德五世繼位后,對法國國王與教皇卜尼法斯之間的沖突一度表現出寬容姿態,這在一定程度上令卜尼法斯八世在位期間教廷與法國王室之間火藥味十足的局面有所緩和。然而,很快 1307年左右在關于圣殿騎士團豁免權問題上的爭議,最終使得先前的各種努力付諸東流。圣殿騎士團(Knight Templar)是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保護前往圣地朝拜的基督徒成立的——時間大約在 11世紀末,它成為這一時期其他軍事修道團的模范。由于其肩負的特殊使命,圣殿騎士團不僅享有許多特權——例如 1139年教皇英諾森二世發布諭令給予其免交十一稅、免受教區法庭審判并直接隸屬于教皇個人等一系列權利——而且有不少貴族慷慨解囊予以捐贈。至 14世紀圣殿騎士團已經聚斂大量財富,這不能不引起長期被戰爭拖累的法國王室的注意。與此同時,在一個天主教會內部關于“異端”的指控甚囂塵上的時代,圣殿騎士團秘密宣誓的行為也讓其備受猜疑。甚至有人指控這種保密的方式掩飾著“許多不譽行為”(Jordan,2005:26)。而圣殿騎士團成員又必須宣誓恪守規章要求,絕對服從騎士團的最高長官。這使得宣誓的內容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唯一可以得知的是教皇克萊蒙特繼位時,這個軍事修道團體已是流言四起、聲名狼藉。
1305年11月克萊蒙特五世繼位不久,法國國王腓力四世針對外界對圣殿騎士團的各種指控很快與教皇進行了磋商。教皇明確表示要發起一次正式調查,腓力四世隨后不斷向教皇施壓。正如威廉·喬丹教授指出的,“可以確定的是國王此時關注的不是圣地問題,而是阿科(Acre)陷落后其在歐洲的國內與外交事務”(Jordan,2005:27)②詳見:Alan V. Murra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Oxford, ABC&CLIO, 2006, p. 952.。面對各界對于圣殿騎士團形形色色的指控罪名,教皇的處理方式本身表明他對待法國王室的立場。克萊蒙特五世含沙射影地告誡腓力四世國王,稱圣殿騎士團特別地把這種誹謗與法國國王聯系在一起。他同時表示愿意再次對該事件發起調查——圣殿騎士團也希望以這種方式為其洗脫罪名。然而,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腓力四世竟然于1307年9月14日單方面秘密采取行動逮捕了圣殿騎士團的成員,緊接著又發生10月13日法蘭西王國內對圣殿騎士團的襲擊。顯然腓力四世的這一草率之舉并未得到歷史學家的認可。美國中世紀史家威廉·喬丹不無批評地指出,“王室清楚誰應當對圣地失陷承擔責任,而且這一激烈態度已經讓事情清楚明了”(Jordan,2005:27)。不過更富戲劇性的是圣殿騎士團遭逮捕后的表現。由于外界對圣殿騎士團的各種指控很快傳到巴黎大學的神學家那里,這令“無論該修道團的支持者或誹謗者都對這些控訴的嚴重程度和性質感到震驚”。因為被逮捕的修道團的高級領袖(grand master)竟然承認某些指控的罪行,特別是承認公開放棄耶穌·基督和褻瀆其肖像的罪行。盡管他們很快矢口否認這樣的懺悔,但到目前為止事態的發展足以置教皇克萊蒙特五世于進退維谷的境地。雖然巴黎大學的神學家們此后也沒有表現出對腓力四世的支持,但關于圣殿騎士團的爭議最終在 1310年召開的維也納公會議上以對法王絕對有利的安排而告終①維也納公會議上關于圣殿騎士團問題的聲明,詳見:Norman P. Tanner S. J. ed., pp. 333-340,相關研究另見:包來軍,《法國卡佩王朝王權崛起與圣殿騎士團的滅亡》,河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4月。。教皇克萊蒙特五世在處理整個事件時的態度恰恰表明了他所承受的政治壓力,這也是促使他在 1309年將教皇寓所遷至法國南部小城阿維農的重要因素。
結語
綜合文中考察,在中世紀盛期特別是13至14世紀,法國王室與羅馬教廷之間在征稅和圣殿騎士團問題上的矛盾,致使雙方沖突迭起、紛爭不斷。這場與教廷之間的權力博弈,對于法蘭西民族國家的發展來說也許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很顯然此時法國擴張面臨的更大障礙來自海峽對岸金雀花王朝的英國,百年戰爭的陰霾已經在英吉利海峽上空盤旋。但是對于這一時期的羅馬教廷而言,這種延綿不絕的矛盾帶來了無可爭議的深遠影響。因地緣因素加之在授職權問題上教廷與帝國皇帝積怨已久②14世紀上半葉教皇與帝國境內巴伐利亞路德維希之間因關于帝國王位選舉問題仍發生著激烈沖突。(Jordan,2005:74),因此對于捍衛和鞏固教皇權力來講,教廷與法國王室之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14世紀的法國人尚且對阿爾比戰爭記憶猶新。如果不是法國王室鼎力支持,很難設想羅馬教廷面對圖盧茲地區民眾的浴血奮戰仍能夠“大獲全勝”。由此可見,在事態發展的當前階段,教廷與法國王室在 14世紀頻發的正面沖突無疑會給天主教會帶來立竿見影的致命影響。“阿維農之囚”后教廷的一蹶不振正是這種影響的顯現。對此,英國史學家戈登·勒夫(Gordon Leff)指出,“1305年教皇被流放至阿維農降低了其行動自由——它寄人籬下于法蘭西土地上以及接踵而至的法國人教皇必然賦予其更加受限的特征”③Leff Gordon, Heresy,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 Medieval West,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2002, Chap II, p. 38.。14世紀法國王權對于羅馬教廷教權的勝利也將對西歐天主教世界的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緊隨教會“阿維農之囚”而來的是 1378年開始的教會大分裂和議會至上運動。教會內部正在醞釀著的變革很快撼動了昔日位高權重的教皇所享有的專制權威和精神領袖地位,若干世紀后宗教改革的紛亂景象從中已隱約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