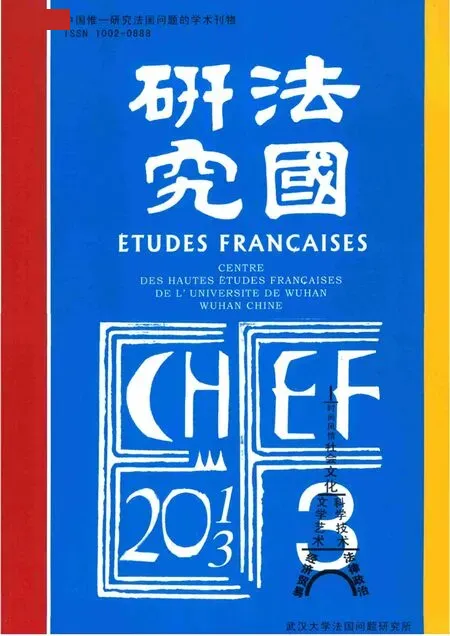法國文學史的建立
——從圣伯夫到朗松
錢 翰
法國文學史的建立
——從圣伯夫到朗松
錢 翰
文學史研究在今天我們眼中是理所當然的一門學問,然而它真正的確立實際上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其建立的條件是西方近代以來的人本主義和現代化以來新的知識體系和大學機制。在法國文學史知識體系的建立過程中,圣伯夫、丹納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完成了文學批評從個人經驗的審美向知識體系的轉化過程。
文學史 圣伯夫 丹納 朗松
[Résumé]L’histoire littéraire est maintenan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discipline qui va de soi, pourtant elle n’a qu’une centaine d’années d’histoire. Son établissement a été conditionné par l’humanisme européen et le système de savoirs universitaires depuis le modernisme. Sainte-Beuve, Taine et Lanson sont les trois porte-drapeaux marquant le tournant de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qui la ramènent de l’expression personnelle à un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s.
文學有歷史。按照現代的文學概念所劃分的文類,中國的文學史上溯至《詩經》,西方的文學史上溯至荷馬史詩。然而,把文學作品的沿革當作歷史加以研究卻是非常晚近的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法國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在大學建立并得到學術的承認,成為大學文科教育的基本知識系統之一。可以說,這是文學批評和研究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們今天已經把文學史當成一門理所當然的學問,但是在經歷了“文學理論”對文學史的沖擊之后,回望文學史的建立過程,也許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文學史,無論是其局限性還是價值。
經過十八世紀 “啟蒙時期”的洗禮,歐洲觀察世界的視點從神逐漸走向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思想,推動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他從普遍的懷疑出發尋找理性的基礎,認定只有那個正在懷疑的我是無法否認的:“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什么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呢?那就是說,一個在懷疑,在領會: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覺的東西。①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頁。”雖然笛卡爾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理性思想卻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動搖了上帝的地位。從此,大寫的理性逐漸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人開始成為世界的主體,開始站在自然和世界的對面發現和認識世界。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錄》中的一段話表達了對人的理性思維的崇尚:“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他;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②帕斯卡爾:《思想錄——論宗教和其他主題的思想》,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57—158頁。”。人,作為思維的主體逐漸與作為思維客體的世界相分離。與認識論轉向相對應的是向人類學的轉向。康德哲學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后,世界之秩序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認識對象。人的理性和意志成為整個世界的出發點。福柯在《詞與物》中總結了康德的三個問題:“當康德在自己的傳統三部曲上添加了最后一個問題:于是三個批判問題(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須作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與第四個問題聯系在一起,并以某種方式歸于‘它的說明’:人是什么?”①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為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44頁。歐洲思想開始向人自身聚焦,由此產生了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一系列人文學科,它們將與文學史產生緊密的聯系。而文學史自身的焦點也是人的問題:作品的造就者——作家。
直到法國大革命,歐洲的歷史觀與中國古代的歷史觀是比較接近的,類似“進步”或者“發展”的概念對于歐洲人的精神來說也是陌生的。在當時人們的意識中,人類的根本境遇是完全相同而不變的,歷史事件被看成孤立的不連續的特殊事件,人類的秩序主要是空間性的,而不是時間性的。19世紀以前,描寫歷史故事則一直被當作一門藝術,屬于文學的一部分,歷史小說(roman historique)和歷史著作被看作相類似的文學作品。貢巴尼翁在談到史學與文學分離的過程的時候,說:“直到 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最后25年,歷史才真正成為一門科學,與文學分道揚鑣,立身于科學之中……”②AntoineCompagon, la troisièmeRépublique des lettres, Paris, Seuil, 第24頁。歷史從逐漸敘述話語轉向實證知識,丹納與米什萊爭論的時候說到:“確實,歷史是一門藝術,然而它同時也是一門科學。”③Taine,?Michelet ?, Essais de critique et d’histoire, Paris, Hachette, 1904, 10eéd. P. 95.新建立的歷史學所具有的博學和實證的特性很快使它在人文學科中建立了強大的權威,而且成為解釋人類社會變化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歷史學為社會的變遷確立了時間上的軸線,并建立了從古到今的連續體;另一方面,它也能為現實世界提供“我們從何處而來”的說明,并且對未來提出種種構想。對“永恒秩序“的思考讓位于對人類變化歷程的解釋,19世紀成為“歷史”的世紀: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從米什萊到丹納,歷史成為人類反觀自身的關鍵詞。
對文學的思考同樣也與上述的制度和思想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圣伯夫④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法國著名文論和批評家,1804年 12月 24日生于布洛涅(Boulogne-sur-mer),1869年辭世于巴黎。、丹納⑤Hippolyte Adolphe Taine, 法國著名哲學家和史學家,1828年4月21日生于福紫葉(Vouziers),1893年3月5日辭世于巴黎。和朗松⑥Gustave Lanson, 法國著名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家。1857年8月5日生于奧爾良,1934年12月15日辭世于巴黎。三位大師的貢獻,文學史作為研究文學的專業逐漸建立起來,直到當今還是大學文學系的知識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史被當做實證主義的文學理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過對作家背景和身世的研究,包括作家的家庭、社會、教育、生活背景以及生活圈子,來解釋作家的作品和創作,這是一種發生學的研究,文學史家們希望以自然科學中的因果律方式來回答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因果規律。19世紀中后期的法國出現了三位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圣伯夫、丹納和朗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的關系之上,創立了法國的文學史批評。
一、 傳記批評理論
19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和批評發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的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要么是詩人和劇作家,如雪萊、華茲華斯、席勒和歌德等等,他們在創作之余,在一些零星的文章或者作品的序言中,表達自己的文學觀念,或者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要么是哲學家,如柏拉圖、康德、謝林等人,他們從各自的哲學體系出發,討論美的問題,并就文學問題提出他們的觀點,像布瓦洛這樣的專門的文學批評家為數甚少。19世紀,伴隨著文學史的奠基,出現了一批專門的研究專家,他們把文學批評、史學和社會學相互結合,創立了文學史研究方法。文學史以前的文學批評所關注和提出的問題是:戲劇和詩歌應當怎樣寫?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而文學史則提出了全新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詩?荷馬或者高乃依這樣的詩人是如何產生的?這些問題在今天看起來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然而它們的提出標志著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新時代的來臨,并延續至今。
從社會條件上說,文學史的建立與現代大學制度息息相關,19世紀后期,因為普法戰爭的失利,法國開始全面學習普魯士的大學體制,使大學成為新知識的工廠①參見:Antoine Compagnon,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Paris, Seuil, 1983.。在新建的文學系中,教授們既不是傳統的作家也不是哲學家,而是專門的文學研究者,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探究有關文學的種種知識。從思想史的角度上說,文學史的基礎是十九世紀得以充分發展的三大主題:人、科學和歷史。
19世紀是自然科學突飛猛進的時代,新的知識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極其深刻地影響了人類關于世界和自身的認識。“認識你自己”,實現這一任務不再完全依賴冥想和哲學的思辨,也不依賴上帝。實證主義成為主流思潮,人們相信只要采用正確的方法,就可以最終認識世界的真理。對社會現象的分析也開始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并卓有成效,在人類的精神領域,科學知識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人文學科也開始向科學看齊,普遍吸納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長期以來,文學被當作個人的教養和美學修辭,但是在 19世紀的大學中,它作為一個學科,必須提供知識,貢巴尼翁先生認為文學批評有兩大主要的動力,一種是求知,一種是美學的判斷②參見:Antoine Compagnon, art. ? Littéraire (Critique) ?,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96.,19世紀后期,在“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的大潮中,文學走向了求知之路。
圣伯夫(1804-1869),法國著名批評家,是法國現代批評的先驅之一,他的批評關注于作者的生活,通過分析作家來理解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保爾-羅亞爾修道院》、《周一雜談》、《文學肖像》等。
作為一位偉大的批評家,圣伯夫認為批評自身并不具有獨立的價值,它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文學作品:“批評并不創造什么,并不出產什么完全屬于它自身的東西,它邀請甚至強迫他人參加一場盛宴。當所有人都徹底地享受了它最先發現的東西之后,它自己就悄然隱匿。它的職責是教育讀者大眾,就像豐特列爾等優秀的教育者所說的那樣,他的工作就是要讓自己顯得毫無作用……”③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 Victor Hugo. Les Feuilles d’automne ?,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 décembre 1831, repris dans Pour la critique, édité par Annie Prassoloff et José-Luis Diaz, coll. Folio/essai, Gallimard, 1992, p. 126.對他而言,文學批評既非權威的審判官,也不是自娛自樂的獨語者,面對偉大的文學作品,批評必須總是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
圣伯夫的文學評論主要是為同時代的作家所勾畫的肖像,在他的主要作品文集《星期一》中,他觀察和描寫同時代作家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他們的生活瑣事,梳理他們的心路歷程,從而對作家的性格特點、生活方式和思想加以評判,力圖在作品和作家的人生之間建立起確切而真實的聯系,從人到作品,從作品到人,“知人論世”的傳記批評是圣伯夫批評的主要方法。他這樣總結自己的文學觀:“對我而言,文學和文學創作與人的整體是密不可分的。我可以品味一部作品,但是缺少對這位作家的知識,我很難做出判斷。我想說的是:什么樹結什么果。因此文學研究很自然地會走向對精神的研究。”④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 Chateaubriand jugé par un ami intime en 1803 ?, Le constitutionnel, 21 et 22 juillet 1862. Repris dans Pour la critique, édité par Annie Prassoloff et José-Luis Diaz, coll. Folio/essai,Gallimard, 1992, p. 147.在圣伯夫眼中,文學作品就是作家個人的性格、氣質和精神狀態的反映,并表現作者的意圖,因此對文學作品的研究,也就意味著對作家個人的研究。那么,我們如何才能把握一個人呢?圣伯夫提出的方法是從一個人出生的地方、種族開始,然后是他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他的孩子,從這些人身上可以觀察作家可能具有的遺傳的性格特征,最后應當研究偉大的作家所處的團體,而他所說的團體,“并非偶然形成的一群為完成某項目標所構成的群體,而是一個時代的杰出青年才俊,他們也許并不類似也不屬于同一家族,然而卻像是在某一個春天同時起飛的鳥群,他們在同一片星空下孵育出殼。雖然他們的職業和志趣并不完全相同,卻好像是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誕生在這個世間。例如開啟了一個偉大的世紀的團體:布瓦洛、拉辛,拉封丹和莫里哀。”①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 Chateaubriand jugé par un ami intime en 1803 ?, Le constitutionnel, p. 152-153.圣伯夫設想過,我們將可以像研究植物和動物一樣研究人的精神和性格,探尋人的心理規律,解釋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創作心理活動。
圣伯夫認為,為了徹底了解一位作家,應當盡可能收集有關作家的一切資料,許多過去看上去與文學毫無關系的問題在他那事無巨細的觀察之下都成為解釋文學問題的鑰匙,他說:“關于一位作家,必須涉及一些問題,它們好像跟研究他的作品毫不相干。例如對宗教的看法如何?對婦女的事情怎樣處理?在金錢問題上又是怎樣?他是富有還是貧窮……每一答案,都和評價一本書或它的作者分不開。”②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195頁。圣伯夫的研究雖然歷經種種批評,但是至今依然是文學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二、文學發展的“三要素”
伊波利特·丹納(1828-1893),是法國19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他是法國文學史批評的先驅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批評與歷史文集》、《藝術哲學》、《英國文學史》。
與圣伯夫知人論世的常識不同,丹納所設想的文學藝術史具有更強烈的科學基礎,他的哲學思想與科學,尤其與博物學息息相關。丹納的一生都在建構某種科學的觀念,把自然看成有機組織起來的整體秩序,在他眼里,整體和多樣性,變化和連續性是結合在一起的。丹納像一位博物學家觀察自然史那樣來觀察文學和藝術的歷史,藝術家和作家就像森林中所生長出來的花朵,他所提出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些花朵,它們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個地方?他提出解釋藝術特征成因的步驟和方法,把作品和作家都置入更為宏觀的背景中加以解釋。在《藝術哲學》中,他這樣來說明他的三個研究步驟:藝術品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從屬于藝術品的總體。首先,藝術品屬于一個藝術家的全部作品。其次,藝術家本身和他的全部作品還屬于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最后,“這個藝術家庭本身還包括在一個更廣大的總體之內,就是在它周圍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會。因為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對于群眾和對于藝術家是相同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我們隔了幾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復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一樣,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③[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頁。
傳統觀念把藝術家視作無法解釋的天才,然而丹納試圖給藝術家的產生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在《〈英國文學史〉?導言》中,丹納把種族、環境和時代當作對作家起決定作用的三種力量。種族指的是“天生的和遺傳的那些傾向,而且根據規律,與在性格和身體結構上的明顯區別聯系在成一個整體。”種族的自然因素是最初的決定因素,在此之上就是包圍著他的環境,“人不是孤立生活在世界上;自然環境圍繞著他,人類圍繞著他,偶然的和第二性的傾向疊加在他的最初傾向之上,物質和社會環境會干擾或強化他的性格。”而第三個因素就是時代,因為“民族的性格和周圍的環境發生作用的時候,并不是作用在一塊白板之上,”那塊土地已經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同樣都是法國戲劇,高乃依時代的戲劇迥異于伏爾泰,埃斯庫羅斯異于歐里庇得斯。種族是內因、環境是外力,時代則是后繼的推動力,只要認真地研究了這三個方面,就“不僅僅窮盡了當前的全部原因,而且窮盡了所有可能的動力之源。①Taine, ? Introducti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Hachette, 2eéd. t. I, 1866, p. XXXIV.”丹納對作家的研究效仿了生物學的方法,把作家置入一個同心圓結構,認識的范圍一層一層從外圈到圓心。生物學從界、綱、目、類、種、屬的方式對生物分類,并解釋生物的形態如何被其環境決定。而丹納試圖以類似的方法解釋藝術品的相似和不同之處,并以這個同心圓模式來加以解釋:作品由作家決定,作家由作家的群體決定,作家的群體由風俗和精神狀態決定,精神狀態受種族、環境和時代決定。丹納的研究第一次把作家納入到一個更大的范圍之內研究其創作的動力學和因果關系,作家和藝術家的特色不再僅僅歸之于神秘難以言說的天才,而屬于自然和社會總體結構之一部分。藝術家特性的源頭不再是神或者繆斯,也不是難以言表的靈感或特殊的心靈,而是可以觀察、研究和說明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在丹納眼里,之所以在古希臘出現了那樣完美絕倫的雕塑,是因為希臘民族的特性:聰明而早熟,熱愛科學和抽象思維能力的發達。其次是希臘的地形狹小,然而外形明確,空氣明凈。這是一個快樂的民族,多神教并不嚴格,城邦政治使人性獲得全面的發展。這一切都把希臘人造就成最好的藝術家,善于辨別微妙的關系,意境明確,中庸有度,使他們創造出細膩而富于表現力的雕塑,還有比例和諧、莊嚴而寧靜的神廟建筑。
在解釋藝術的特征的時候,丹納已經具有明確的系統論思想。他最為重視的概念是“時代精神”,也就是某個國家或者文化圈在某一時期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哲學、宗教和文化特征,它們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體,“無論在任何地方,藝術都是哲學變成可感知的形式,而宗教則是被視為真實的詩歌,哲學是一種藝術和抽象為純粹觀念的宗教。”②Taine, ? Introducti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Hachette, 2eéd. t. I, 1866, p. XXXVI.人類的精神是相互依賴和聯系的系統。因此,我們既可以知微見著,也可以從整體來觀察局部的特征,在宏觀和微觀之間建立起解釋的循環。“在一種文明中,宗教、哲學、家庭形式、文學、藝術構成了一個系統,任何局部的變化都會導致整體的變化,因此一個有經驗的歷史學家只要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大致明了并預知其他的部分。”③Taine, ? Introducti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Hachette, 2eéd. t. I, 1866, p. XL.例如,我們可以一方面從十九世紀法國的文化現實來總結和抽取出巴爾扎克小說的特征,并解釋其成因;同樣也可以從他的小說的細節描寫出推論出當時法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丹納這種文化系統觀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二十世紀中后期的文化研究的思路中也可以看到丹納的影子。
三、文學史的建構
朗松(1857-1934),是法國文學史研究的奠基者,其主要作品有《法國文學史》、《文學史與社會學》等。他在法國大學體制大改革的時期,走上了學術生涯的高峰。他不僅是一位學者,而且是一位文學教育家,把文學史方法推廣到大學和中學的教學中。他繼承了圣伯夫的傳記批評和丹納的科學精神,并加以取舍,奠定了文學史的主要方法。
在朗松看來,丹納過分機械地理解了作家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畢竟,人不是植物,尤其對于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來說,總有光憑環境所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譬如,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為什么還是會有不同類型的作家,表現出不盡相同的風格,體現出高低不一的價值?朗松對丹納過分機械的決定論加以修正,對作家的研究既考慮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又承認作家的個性和天才的部分。
與丹納一樣,朗松認為文學研究要參考歷史學的方法,像歷史學解釋社會變遷一樣來探索文學的規律,一位文學史家應當如一位真正的史學家一樣博學,才能進行客觀的批評。他強調社會的因素,因為這是作家的精神狀態得以形成的基礎,同時也重視對作家個人生活史的考察。朗松認為可以通過社會學和傳記的方法說明作家的部分特點的來源,他要用科學精神來對作家加以研究,這樣的話,批評家才不會陷入主觀的陷阱。他說:“我們要加入科學的生活,唯一不會欺騙人的,這就是要發展我們身上的科學精神。我們與(自然科學)都有自然的工作工具,蒙田把它們稱為理性和經驗。我們也有相同的對象,就是事實,就是現實……”①Gustave Lanson, Méthodes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25, p. 24.他認為,實證的知識對于我們了解作家來說不可或缺。然而,畢竟作家還有一部分是不能說明的,社會學和傳記研究只能考察作家的外部條件,即所謂作家與社會和他的生活圈子的共性,但是作品的獨特之處難以解釋其發生的因果關系,這就是作家的天才,而只有通過閱讀作品,才能通過感受來體會作家的靈感,這個部分是留給審美的。在朗松所著的《法國文學史》中,他比較了皮埃爾·高乃依和托馬斯·高乃依兩兄弟,他們屬于相同的家庭、接受類似的教育,受到同一個時代的影響,然后前者的戲劇是法國古典主義的巔峰之作,而后者則相對平庸,朗松說托馬斯“屬于這樣一些人,他們雖與眾不同但還是平庸,樣樣都能,但是卻做不出超于常人的成就。②Gustave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remaniée et complétée pour la période 1850-1950 par Paul Tuffrau, Paris, Hachette, 1952. p. 535.”對于這樣的差別,只能歸之于不可知的個人因素。然而,朗松要求我們需要盡可能收集客觀的資料,只有在客觀的資料和邏輯推理無法應用之處,才能歸之于神秘的個人因素。
另一方面,朗松批評圣伯夫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身上,把作品當作了研究人的工具。在《人與書》的導言中,他寫到:
在令人佩服的心理直覺和對生活不容置疑的感覺的帶領之下,圣伯夫把傳記變成了批評的全部工作。……實際上,當他構建這些精神解剖學的檔案的時候,就已經放棄了文學批評的工作;……他在應用其方法的時候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為他不是用傳記來解釋作品,而是用作品來建構傳記。在他的傳記方法中,文學杰作與一位將軍急就而成的回憶錄和一位婦女的信件沒有什么不同,所有的文字都被他用于同一個目的,就是理解人的靈魂或心靈,這樣的話,他就取消了文學的價值。③Gustave Lanson,? introduction ?, Hommes et livres, Paris, Lecène Oudin, 1895, p. VII et VIII.
朗松的文學研究一方面重視社會學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也重視文學自身的審美價值。在《法蘭西文學史》的《前言》中,他就對僅僅聚焦于前一種傾向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如果這樣……人們就會通向沒有文學品質的知識本身。文學簡化為事實和規則的干巴巴的合集,其結果就是讓年輕的心靈對作品感到厭惡。”④Gustave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VI.文學研究與科學研究不同,是個人心靈的相互接觸,其結果一定是不確定的,因此文學研究既具有客觀性,同時又與自然科學有區別。人們探索高乃依或雨果的心靈,“并不是通過可以被任何人重復的經驗和方法,也不能得出普遍不變的答案,而是因人而異,只能是相對的和不完全確定的。”①Gustave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VIII.朗松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把丹納的科學精神、圣伯夫的知人論世的傳記批評和傳統的審美感受融合在一起,調合其間的矛盾,對作者進行全方位研究。然而,后來有些研究者把文學研究完全歸結為考證和社會學考察,試圖在作家的生活經歷和文學作品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聯系,把朗松的文學史研究歸結為實證主義,這其實是對朗松文學史研究的庸俗化和簡單化。沒有把握他博采眾長,中庸調合的特質。
與丹納強調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不同,朗松格外強調文學的社會學影響,一方面是作家受到時代的影響,例如自然科學對文學的影響,并對此深感憂慮②參見:朗松:《文學與科學》,載于《朗松文論選》,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第84-127頁。;另一方面是時代與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法國外省文學生活研究計劃》中,他就提出了對法國外省的閱讀史和閱讀生活進行研究,“讀書的是怎樣的人?他們讀些什么?這是兩個首要的問題,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就可以把文學移置于生活之中。”③【法】朗松:《法國外省文學生活研究計劃》,載于《朗松文論選》,同上書,第71頁。例如我們應當研究某地的文學愛好者如何組織讀書俱樂部,如何出版內部刊物,這些活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對于文學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有什么意義。如果說在 20世紀初,他的這些設想還僅僅是計劃,那么在今天,就已經在文學閱讀史研究中取得了豐碩成果,并且對于文學本身的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朗松是法國文學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確定了對文學批評的“科學要求”。文學史使文學批評從審美轉向了認識,把文學評論從文學家的事轉向了文學研究者的學術工作,使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在大學體系內占據了自己的地位,并且成為現代文學領域內知識生產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史研究是現代文學批評的奠基之作。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張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