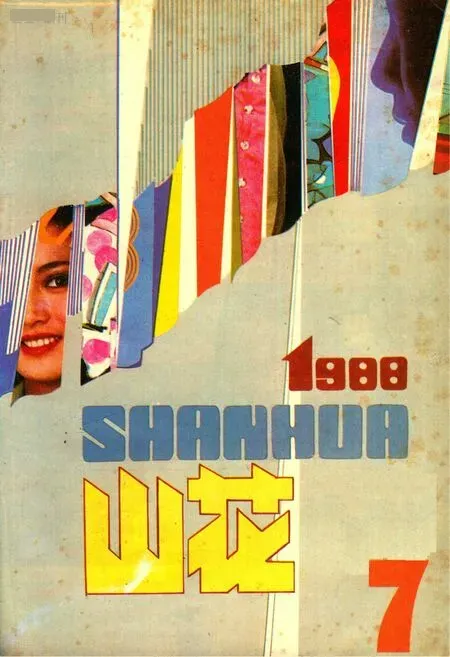當下詩歌:騎著木馬趕“現實”——新世紀詩歌精神的考察
霍俊明
在當下的詩歌批評語境談論一首詩歌并不難,甚至更多的時候會顯得非常容易。但是平心而論認認真真地讀一首詩,負責任地評價一首好詩卻是有難度的。這種難度不僅與整個當下的詩歌生態相關,而且也與每個生存個體的困窘有關,更與如此廣闊的差異性的“現實”有關。在我看來當下眾多詩人的文本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一個詩人的一首孤立的詩作,而是會牽涉到很多當下中國具有“特色”的詩歌現象、詩歌問題和“現實”境遇。在一個看起來加速“前進”的高鐵時代我們詩人離現實不是越來越近,而是恰恰相反。我們的詩人仍然在自我沉溺的木馬上原地打轉,而他們口口聲聲地說是在追趕“現實”。由此我們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一首首詩歌中的“中國”離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實”究竟有多遠。是的,在一個如此詭譎的時代我們進入一個“現實的內部”是如何不易。在一個“新鄉土”寫作已經成為熱潮的今天,真正的詩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時候是更好的語言。在很多近期的詩人那里我強烈感受到了一個個所謂的“旁觀者”的無邊無際的沉默。這“沉默”和那扇同樣無聲的“拒絕之門”一樣成為這個時代罕有的隱秘聲部。詩人試圖一次次張嘴,但是最后只有一次次無聲的沉默。這種“沉默的力量”也是對當下那些在痛苦和淚水中“消費苦難”的倫理化寫作同行們的有力提醒。
這是一個飛奔“向前”的時代,但是同時那一塊塊鋼化玻璃窗也模糊了我們內心之間的界限,模糊了我們與窗外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時代之間的關系。在一個城市化的時代,我們正在經受著去地方化的命運。那墻壁上一個個出自強壯的拆遷隊之手的粗糙甚至拙劣的巨大的白色的“拆”字也在一同拆毀著族群的方言和地方的根系。而曖昧的時代“敵人”盡管不如極權年代那樣如此具體和直接,但是更為龐大的無處不在的幽靈一樣的規訓和對手卻讓人不知所措。而吊詭的則是在一個“鄉土”和“地方性”不斷喪失的時代我們的文化產業和各個省份的文化造勢(比如名人故里之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甚至連縣鄉的草臺班子都在爭搶所謂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如火如荼過。仍有那么多不為我們所知的“地方”和“現實”存在,而我們似乎又無力通過詩歌對此作出應有的“回應”。當我們坦陳我們曾經一次次面對了那些“拒絕之門”,我們是否該側身進去面對那撲面而來的寒冷與沉暗的刺痛?盡管在一個如此龐大而寓言化的現實面前,我們更多的時候只能無奈地充當“旁觀者”和“無知者”的角色!
當我們的詩歌中近年來頻頻出現祖國、時代、現實和人民的時候,我們會形成一個集體性的錯覺和幻覺,即詩人和詩歌離現實越來越近了。而事實真是如此嗎?顯然不是。更多的關涉所謂“現實”的詩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樣的仿寫與套用,詩歌的精神重量已經遠遠抵不上新媒體時代的一個新聞報道。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一個寓言化的時代,現實的可能性已經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極限。而在此現實和寫作情勢之下,我們如何能夠讓寫作有更為遼闊的可能?而在一個“非虛構寫作”漸益流行的年代,詩歌能夠為我們再次發現“現實”和“精神”的新的空間嗎?作為一種文本性的“中國現實”,這不能不讓我們重新面對當下詩人寫作的境遇和困難。也許,詩歌的題材問題很多時候都成了偽問題,但是令人感到吊詭的卻是在中國詩歌(文學)的題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問題。顯然,這個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學自身的問題,而是會牽涉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構造與文學想象。新世紀以降詩歌的題材問題尤其是農村、底層、打工、弱勢群體作為一種主導性的道德優勢題材已經成為了公共現象。實際上我們也不必對一種寫作現象抱著道德化的評判,回到詩歌美學自身,我想追問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當它涉及到“中國現實”時作為一種文學和想象化的現實離真正的“現實”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顯然在一個分層愈益明顯和激化的時代,“中國現實”的分層和差異已經相當顯豁,甚至驚訝到超出了每個人對現實的想象能力。在這種情境之下,由詩歌中的“現實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實我們可以通過一種特殊化的方式來觀察和反觀中國現實的歷史和當下的諸多關聯。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寫作者和批評者們已經喪失了同時關注歷史和現實的能力。換言之在他們進化論的論調里歷史早已經遠離了現實,或者它們早已經死去。顯然,在一個多層次化的“現實”場域中,鄉村題材顯然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寫作的虛構和想象中都構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重要現實”。而當下處理這一“重要現實”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僅詩歌在介入,而且小說、散文甚至時下最為流行的“非虛構”文本也在輪番上演著“鄉村”敘事。那么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眾多的相關文本就為寫作者們設置了極大的難度。換言之,一首詩歌如何能夠與龐雜的類似題材的詩歌文本區別開來?區別的動因和機制以及標準是什么?這顯然是一個必須探究的問題,而且非常有必要。
實際上,我們的詩歌界這些年來一直都在強調和“憂慮”甚至“質疑”的就是指認當下的詩歌寫作已經遠離了“社會”和“現實”。里爾克的名言“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著某種古老的敵意”在今天的中國是否仍然適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對著當下的帶有“重要現實”層面的詩歌寫作而言,詩歌和詩人與“現實”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呢?或者說當詩人作為一個社會的生存個體,甚至是各個階層的象征符號,當他們的寫作不能不具有倫理道德甚至社會學的色彩,那么他們所呈現的那些詩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因為任何企圖回答這個問題的人都必須具備綜合的能力,顯然詩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這也是為什么出現了抗震詩、高鐵詩,但是真正能夠留下和被記憶的卻幾乎成了空白的原因。在現實和寫作面前,詩人應該用什么“材料”和“能力”來構建起的詩歌的“現實”?進一步需要追問的是這些與“現實”相關的詩歌具有“現實感”或“現實想象力”嗎?曾記得2009年,著名藝術家徐冰用廢棄的鋼鐵、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兩只巨大的鳳凰。這本身更像是一場詩歌行動,時代這只巨大“鳳凰”的絢爛、飛升、涅槃卻是由這些被廢棄、被拋棄、被擱置的“無用”、“剩余”事物構成的。這就是詩歌的真實、藝術的真實。

陳紅旗作品-人像局部4
在時代匆促轉換人們都不去看前方的時候,詩人該如何面對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內心?在一個極權時代遠去的當下,我們的生活和詩歌似乎失去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生活和詩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我們的媒體和社會倫理一再關注那些日益聳起的高樓和城中村,一再關注所謂的農村和鄉土乃至西部,但是我們的詩人是否足以能夠呈現撼動人心的具有膂力的“原鄉”和“在場”的詩句?我認為經歷了中國先鋒詩歌集體的理想主義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詩人的“遠方”(理想和精神的遠方)情結和抒寫已經在新世紀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時代宣告終結。尤其是在當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時代,我們已經沒有“遠方”。順著鐵路、高速路、國道、公路和水泥路我們只是從一個點搬運到另一個點。一切都是在重復,一切地方和相應的記憶都已經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變,一切都快煙消云散了。在一個如此詭譎的時代我們進入一個時代“內部”是如何的不易,而進入一個無比真實的“現實”是如何艱難。真正的寫作者應該是冷峻的“旁觀者”和“水深火熱”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給我們的無邊無際的沉默、自語和詰問。與此相應,我們每天與那些看起來無比真實和接近現實的詩歌相遇,但是他們幾乎同時走在一條荒廢的老路上。我們的當下有那么多的艱難情勢被我們的詩人可怕地忽略,與此還有那些更為斑駁不自知的靈魂淵藪。我們的詩歌都成了自我的關注者,個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體驗從來沒有在詩歌中變得如此高調和普遍。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倫理化的底層和民生抒寫熱潮中,詩人普遍喪失了個人化的歷史想象能力。換言之他們讓我們看到了新聞一樣的社會現場的一層浮土,讓我們看不到任何真正關涉歷史和情懷以及生存的體溫。
在我看來,當下諷喻性的詩歌寫作已經逐漸成為帶有倫理化傾向的一種潮流和趨勢。面對當下中國轟轟烈烈的在各種媒體上呈現的離奇的、荒誕的、難以置信的社會事件和熱點現象,我覺得似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真正“寓言化”的時代。換言之中國正在成為“寓言國”。首先應該注意到目前社會的分層化和各個階層的現實和生存圖景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具有多層次性,越來越具有差異性。甚至這種復雜和差異已經遠遠超過了一般詩歌寫作者的想象和虛構能力。也就是說,現實生活和個體命運的復雜程度早已經遠遠超過了詩人的虛構的限閾與想象的極限。詩人們所想象不到的空間、結構和切入點在日常生活中頻頻發生,詩人和作家的“虛構”和“想象”的能力受到空前挑戰。由此,面對各種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會“奇觀”和現場事件的媒體直播,我們的詩歌和文學還留下什么能夠撼動受眾的特異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寫那些“現實”性的詩歌其難度是巨大的。相反,我們涉及到屬于更小范圍內的詩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圖景時,其可能性的空間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所以,我們也據此應該重新認識以往的一個怪論——詩人只對自己負責,不要寫什么重大題材和現實題材。
從整體上而言與社會熱點焦點話題、熱議現象、重大活動和民生問題有著密切關聯的詩歌數量是相當龐大甚至是驚人的。由此,我們必須正視每年各種紙質刊物發表的詩歌數量已經可觀,但是我們發現這些發表的詩歌在譜系學或光譜學上來看具有很強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復和生產性。加之各個地區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軟實力的角力和宣傳活動也需要文學和詩歌的鼓吹,詩人們似乎與“現實”的膠著關系似乎從來都沒有如此貼近和激烈過。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機。但是是否如一位詩人所偏激地強調的“足不出戶的詩歌是可恥的?”實際上,詩人和現實的關系有時候往往不是拳擊比賽一樣直來直去,而更多的時候是間接、含蓄和迂回的。顯然,中國當下的詩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層的、低級的對所謂現實的回應。
而當我試圖從“主題學”或者“同質性”的視野來進當代的詩歌寫作,我們最終會發現大量詩歌(數量絕不在少數)與“鄉村”、“鄉土”以及“鄉愁”、“還鄉”(更多以城市和城鄉結合部為背景,回溯的視角,時間的感懷,鄉土的追憶)有著主題學上的密切聯系。而這么多在譜系學上相近的詩歌文本的出現說明了什么問題?顯然當下的詩人所面對的一個難以規避的“現實”——閱讀的同質化、趣味的同質化、寫作的同質化。無論是政治極權年代還是新世紀以來的“倫理學”性質的新一輪的“題材化”寫作,我們一再強調詩人和“現實”的關系,詩人要介入、承擔云云。但是我們卻一直是在浮泛的意義上談論“現實”,甚至更為忽略了詩歌所處理的“現實”的特殊性。但是當新世紀以來詩歌中不斷出現黑色的“離鄉”意識和尷尬的“異鄉人”的鄉愁,不斷出現那些在城鄉結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與不斷疏離和遠去的“鄉村”、“鄉土”時的焦慮、尷尬和分裂的“集體性”的面影,我們不能不正視這作為一種分層激烈社會的顯豁“現實”以及這種“現實”對這些作為生存個體的詩人們的影響。由這些詩歌我愈益感受到“現實感”或“現實想象力”之于詩人和寫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個加速度前進的“新寓言”化時代,各種層出不窮的“現實”實則對寫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試圖貼近和呈現“現實”的詩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應的具有提升度的來自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具有理想、熱度、冷度和情懷的詩歌卻真的是越來越稀有了。更多詩人浮于現實表層,用類似于新聞播報體和現場直播體的方式復制事件。而這些詩歌顯然是在借用“非虛構”的力量引起受眾的注意,而這些詩歌從本體考量卻恰恰是劣詩、偽詩和反詩歌的。詩人們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過詩歌的方式感受現象、反思現實、超越現實的想象能力。換言之,詩人試圖反映現實和熱點問題以及重大事件時,無論從詩歌的材料、構架、肌質還是詩人的眼光、態度和情懷都是有問題的。
確實在當下詩壇甚至小說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虛假的鄉村寫作和底層寫作。當詩人開始消費淚水和痛苦,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視野再推進一步,在一個愈益復雜、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鄉村化”的時代,詩人該如何以詩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擔當?正如一位異域小說家所說,“認識故鄉的辦法就是離開它;尋找故鄉的辦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記憶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個異鄉去尋找它。”這是必然,也是悖論。詩歌是通往現實的入口。這個入口需要你擠進身去,需要你面對迎面而來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緊牙關在狹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許你必將心存恐慌。但是當你終于戰戰兢兢地走完了這段短暫卻漫長的通道,當你經歷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壓抑的時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義上懂得你頭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顏色,你腳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語言的現實和發現性的“現實”空間里真正掂量你所處的社會現實。
由此我想到了很多詩人文本中的“城市”、“小鎮”、“鄉村”和一個個陌生的“地方”。以這些“地方”為圓點,我們在多大的范圍內看到了一種普遍化而又被我們反復忽略不計的陌生性“現實”的沉默性部分。這一個個地方,除了路過的“旁觀性”的詩人和當地的居民知道這個地方外,這幾乎成了一個時代的陌生的角落——一再被擱置和忽略的日常。而我們早已經目睹了個體、自由和寫作的個人化、差異性和地方性在這個新的“集體化”“全球化”時代的推土機面前的脆弱和消弭。“異鄉”和“外省”讓詩人無路可走。據此,詩歌中的“現實”已經不再只是真實的生存場景,而是更多作為一種精神地理學場域攜帶了大量的精神積淀層面的戲劇性、寓言性、想象性和挽歌性。在這些蒼茫的“黑色”場景中紛紛登場的人、物和事都承載了巨大的心理能量。這也更為有力地揭示了最為尷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視的深山褶皺的真實內里。實際上這個經過語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運之痛所一起“虛擬”“再生”的“現實”景象實則比現實中的那些景觀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實的力量和可以不斷拓殖的創造性空間。而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城鎮和曾經的農耕歷史被不斷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時代,一個詩人卻試圖拭去巨大浮塵和粉灰顯得多么艱難。而放眼當下詩壇,越來越多的寫作者們毫無精神依托,寫作毫無“來路”。似乎詩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體時代個體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戲。在一個迅速拆遷的時代,一個黑色精神“鄉愁”的見證者和命名者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尷尬莫名的。因為通往圣潔的“鄉愁”之路的靈魂安棲之旅被一個個淵藪之上的獨木橋所取代。當我們膽戰心驚終于下定決心要踏上獨木橋的一刻,卻有一種我們難以控制的力量將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遠的寒風勁吹的黑暗。語言的溫暖和堅執的力量能夠給詩人以安慰嗎?過多的時候仍然是無物之陣中的虛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溫暖,現實的吊詭勝于卑微的渴念。當然我所說的這種“鄉愁”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對“故鄉出生地”的留戀和反觀,而是更為本源意義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業時代景觀中一個本真的詩人、文化操持者,一個知識分子,一個隱憂者的人文情懷和酷烈甚至慘痛的擔當精神面對逝去之物和即將消逝的景觀的挽留與創傷性的命名和記憶。一種面對迷茫而沉暗的工業粉塵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與堅定相摻雜的駁雜內心。由此,我更愿意將當下的后社會主義時代看作是一個“冷時代”,因為更多的詩人沉溺于個人化的空間而自作主張,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現實感”的詩歌寫作的缺席則成了顯豁的事實。

陳紅旗作品-人像局部5
然而,更為令人驚懼的是我們所經歷的正是我們永遠失去的。多少個年代已經在風雨中遠逝,甚至在一個拆遷的城市化時代這些年代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一切都被掃蕩得干干凈凈。而那些當年的車馬早已經銷聲匿跡。幸運的馬牛們走進了墳墓之中,不幸的那些牛馬們則被扔進了滾沸的烹鍋之中。那些木質的輪車也早已經朽爛得沒了蹤跡。我們已經很難在中國的土地上看到這些已逝之物,我們只能在灰蒙蒙的清晨在各個大城市的角落里偶爾看到那些從鄉下來的車馬,上面是廉價的蔬菜和瓜果。而我們卻再也沒有人能夠聽到這些鄉間牲畜們吃草料的聲音,還有它們溫暖的帶有青草味的糞便的氣息。說到此處,我也不由有了疑問。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懷鄉者并不難,這甚至成了當代中國寫作的慣性氣質。但這體現在詩歌寫作中卻會使得“懷鄉者”的身影又過于單薄。“歷史”和“現實”更多的時候被健忘的人們拋在了灰煙四起的城市街道上。我們會發現,在強大的“中國現實”面前歷史并未遠去,歷史也并非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相反歷史卻如此活生生地出現在被我們反復路過卻一再忽視的現實生活里。這多像是一杯撒了鹽花的清水!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了這杯水的顏色——與一般的清水無異——但是很少有人去喝一口。顏色的清和苦澀的重之間我們的人們更愿意選擇前者。而詩人卻選擇的是喝下那一口苦澀,現實的苦澀,也是當下的苦澀。當然,還有歷史的苦澀!而詩歌只有苦澀也還遠遠不夠!
“一無所知”的“過客”性存在,實際上是每個生命的共同宿命性體驗,同時人的認識和世界是如此的有限而不值一提。而在當下的時代,這種遺忘性的“一無所知”還不能不沾染上這個時代的尷尬宿命。我們自認為每天都生活在現實之中,但是我們仍然對一切都所知甚少,甚至有些地方是我們窮盡一生都無法最終到達的。有的地方我們也許一生只能經歷一次。“單行道”成了每一個人的生命進程。詩歌的最后部分提升了整首詩的空間高度和視閾廣度,從而避開了類同題材的粘滯和表象化處理。
“中國的一天”應該是短暫的,但是我們走得卻是如此艱難和漫長。因為它所牽涉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觀感,而是牽涉到整個中國的現實,還有詩人的精神現實。我們所見太多,遺忘也太多。我們在隔著車窗高速度前進的同時,我們的雙腳和內心都同時遠離了大地的心跳聲。我們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墻里只看到同樣灰蒙蒙的天空,我們最終離那些“遠逝之物”越來越遠,直至最終遺忘。是的,多少年代,多少車馬,都已經遠去了!還有那沉默的巨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