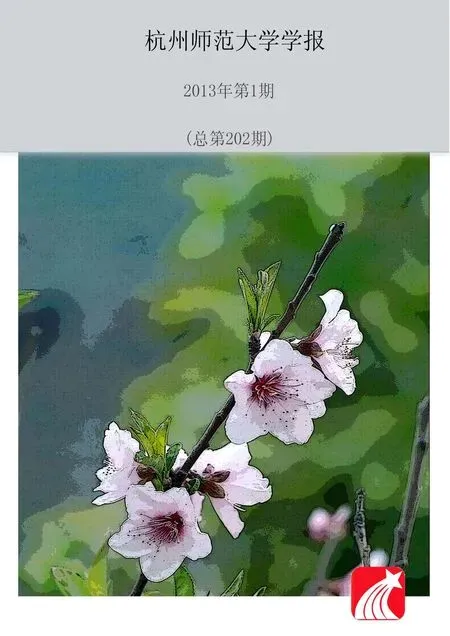恐怖倫理學
[美]雅克·萊茲拉著,王 欽譯
(紐約大學 比較文學系,美國 紐約 10003)
恐怖倫理學
[美]雅克·萊茲拉著,王 欽譯
(紐約大學 比較文學系,美國 紐約 10003)
“恐怖”作為倫理學基礎預設了共同體邊界的確定和普遍性主張的適用范圍的不確定性。在考察索福克勒斯和塞涅卡對于同一個故事的不同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將索福克勒斯設置的僵局從政治本體論領域轉化到審美領域,并在審美的層面上處理它們。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城邦的持存前提是政治的喪失——被轉化為塞涅卡的喜劇。由此,“恐怖倫理學”的命題導向政治概念的缺陷性問題和主權問題。
恐怖;倫理學;主權;俄狄浦斯王
讓我們把故事設定在1982年。哲學家列文(Michael Levin)提出一個假設:一座城市的存在岌岌可危,而它的存亡取決于我們的決斷。列文說的是一座具體的城市,但它代表任何城市。他著名的寓言令人感到恐怖,但這卻是他所意在達到的啟發經驗,或者更好地說是公民經驗——如果我們真的感到恐怖,那我們就會行動起來保衛這座城市。他所講述的故事涉及倫理判斷和政治利益的關系,并且將全球化與民族利益之間的沖突問題放置在一個大都市想象的形式之中。列文寫道:
設想一個恐怖分子在曼哈頓安置了一枚核炸彈,它將于7月4日正午爆炸,除非……(這里列舉了一連串常見的要求,例如金錢、釋放同伙等。)然后,設想他在災難降臨的那天上午10點被捕,但是他寧死不屈,不愿透露炸彈安放的位置。我們該怎么做?如果我們按部就班——等候他的律師、進行進一步審訊——數百萬人將會死去。如果解救這些生命的唯一辦法在于施加極其殘暴的折磨在這個恐怖分子身上,有什么理由拒絕這么做?我認為沒有理由。無論如何,我請你們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這個問題。
嚴刑逼供恐怖分子違憲嗎?很可能。但數百萬人的性命當然要遠遠勝過合憲性問題。嚴刑逼供的手段野蠻嗎?大規模殺傷性襲擊遠遠比這野蠻。事實上,為尊重某個藐視自己罪責的人而讓數百萬無辜者白白送死,這是道德懦弱的表現,也是政治上不愿意有損自己清白的表現。如果你抓住了恐怖分子,如果你知道數百萬人因為你不愿使用電刑而死去,你還能睡好覺嗎?*Michael Levin, “The Case for Torture”, Newsweek, June 7,1982.這篇文章被收入很多文集,網上可見http://www.coc.cc.ca.us/departments/philosophy/levin.html。也見Linda H. Peterson和John C. Brereton編的The Norton Reader: An Anthology of Expository Pros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3),694-696。
與之相反的論辯從未占過上風,至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美國媒體或政治辭令中沒有,“9·11”事件以后就更沒有了。甚至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和關塔那摩監獄受到曝光的囚犯待遇和“強化審訊”等種種丑聞,都沒有對上述論辯產生沖擊——無論是在法理上、法律上,還是文化上。在學界內部,列文提出的爭議場景的影響力也絲毫不弱。這篇文章在各類寫作課或修辭課的課程大綱上出現,與其說證明了它論證的自洽,不如說證明了它在論題、意象和技巧方面的出色,以及與令人難過的時事之間的切合。*雖然從原則上講,“恐怖”威脅或行為的真實例子要比假設性的場景更能闡明對于酷刑的功利主義式運用,但真實例子有很多實際的和概念的約束。首先,臭名昭著的一點是,由于嚴刑逼供而來的信息常常不準確,能夠證明酷刑對于調查或法理程序起幫助作用的實際例子少得可憐。其次,拿酷刑在真實情況下“奏效”——阻止某起恐怖行動——作為例證,馬上就遇到我們或可稱為“道聽途說”的麻煩。因為沒有任何政府或組織希望被人看到運用嚴刑逼供的手段,政府或組織就很難以第一人稱斷言,在阻止某起具體的恐怖襲擊時,他們確曾運用過這種手段。相反,人們可以說自己曾聽到某個政府或組織曾利用過從酷刑中得到的信息——比如,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堅稱,菲律賓政府曾于1995年利用嚴刑逼供套得的信息以“挫敗暗殺教皇和使11架商務客機墜落太平洋的計劃”(Alan M. Dershowitz, Why Terrorism Works: Understanding the Threat,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137)。人們甚至可以說:“我們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或美國政府曾利用過我們聽來的菲律賓通過酷刑獲得的信息,以挫敗某項恐怖計劃。”反過來,菲律賓政府可以訴諸某種相同的“道聽途說”:“為了挫敗某項恐怖計劃,我們菲律賓政府將我們聽到的信息——據說是某個政治組織利用酷刑得來的——傳達給美國中央情報局或美國政府。”為酷刑負責的總是他者,而任何以第一人稱說出類似“我因為原因X或Y而動用了酷刑,為的是達到效果A或B,取得信息L或M”的話,從表面上看都是自我挫敗的:承認對他人施以酷刑的主體,由于這一事實本身,就沒有資格對于已經做出的酷刑給出任何理由。真實例子(如果確實存在的話)還有進一步的邏輯約束和實際約束。人們可以這樣分析嚴刑逼供的“真實例子”:比如這樣一個陳述——“這個信息是通過明令禁止的審訊手段收集來的,作用是阻止某項襲擊或犯罪行為”——結合了兩類陳述。一方面,對于事態的描述做出了事實論斷或指涉性論斷。“在此我們擁有或曾經掌握著某個信息”是個可以被證實(更可能的是被證偽)的陳述,而“某個恐怖行動并未發生在這個或那個時刻、這一天、這個地點”看上去也是個事實陳述,某種意義上看上去是真的和可證實的(盡管我們首先要對什么是這里的“事實性”或“真”進行相當狹隘的理解)。另一方面,有一些陳述的基礎是,將貌似事實性的陳述以關鍵的、虛詞性的(syncategorematic)形式組合起來。比如這樣一個論斷——“某個恐怖行動沒有發生在某天,因為我們掌握了某個信息”,這個假設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成立,但它并不在任何條件下都成立,而且它從來不是必然成立的。我們總是可以設想其他理由來解釋為什么某個行動(包括恐怖行動)不會或不曾在某天發生——從意外事故、內部故障到世界末日。關于酷刑的文獻多得讓人束手無策,最近的文獻列表可見Sanford Levinson編的Torture: A Coll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基于“定時炸彈”場景的功利主義論述相當刻板,并且,如電視劇《24小時》所表明的那樣,“更多人的更大數量的善超過任何特殊利益,也超過某些普遍利益(例如體現于保存法律與‘合憲性’之中的抽象社會利益)”——這一論題具有不可否認的商品特征(commercial cachet)。反對列文場景的最有效方式是從實際性的反對出發(例如,論證嚴刑逼供的手段并不奏效,因為它并不產生所需要的效果,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應;或者論證說,嚴刑逼供的手段會縱容他人用同樣的方式對待美國士兵;或者論證此類折磨有損美國的國際聲譽,等等)。義務論、價值倫理、宗教道德——當想象這座城市危在旦夕之時,一切反對酷刑和國家恐怖的倫理學論辯都倒塌了。城市的圍墻保護我們不受敵人的襲擊,抵擋恐懼,形成我們彼此的交際圈,界定了一系列實踐、習慣和語言,正是它們規定了我們的身份。在城市的圍墻內,我們都是人文主義者;權利得到平等保護,政治自主性的標準得到確定。當我們允許那些實踐逾越城墻,并運用于那些并不接受這座城市的語言和習俗的(域外的)人們身上時,我們就被扣上“道德懦弱”的帽子。
我們繼續在這一點上停留片刻。更仔細地解讀列文的立場,我們會發現它取決于一種要么是不自洽的、要么是不切實際的價值論述。首先,在列文的描述中,之所以嚴刑逼供被允許,是出于其“求真”的作用,但這一作用或許無法與其他次級的、更次級的作用分開,而這些其他作用則無法因同樣原因被允許(因此也就需要與首要目標進行權衡,假設這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舉兩個例子:產生“真相”(如果確實如此的話)的折磨行為也必定產生對這些手段的自返性證成(reflexive justification)。如果我們成功拯救了這座城市,那么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得到了證成;如果我們失敗了,那么我們至少不必有“道德懦弱”的愧疚,即便我們對其他事情感到愧疚:我們的英雄主義屬于悲劇英雄一類。下述原則——嚴刑逼供因其奏效而可被允許——并沒有因此被反駁;恰恰相反: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審錯了恐怖分子(可能是其他人知道炸彈安放在哪里),也可能是我們沒有對那個知道真相的人施加足夠的酷刑。這第二種自我正當化的、英雄主義式的作用,并不作為折磨行為的目標而在道德上被允許,但它無法與第一種作用區分開。而且,折磨行為也具有人們或許可以稱為詞序上的(lexical)次級的后果:如果我可以允許自己運用電刑,那么我就不再是在此之前的那個我了(例如,我或許由這一姿態而獲得了某種憲法之外的英雄主義),而我所拯救的城市如今被籠罩在一圈域外的、法理之外的圍墻內,這些逾越的圍墻不同于之前那些界定并守護這座城市的圍墻。正如不存在一種單一而謹慎的折磨行為——相反,存在的是行為的“復數性”,包括各種姿態、決斷、不同勢力運用的各種工具、在時空上的延伸,等等——因而也就不存在折磨行為的簡單結果(例如,吐露真相也是一種報復行為)。
第二,考慮到嚴刑逼供下的陳述行為,上面這種行為的雜多性,以及它跨越空間、行為者、時間的分化和滲透,同樣成立。懺悔,或者是有關地點、計劃、姓名的坦白,在證實條件滿足以前,將不會算數。坦白與事實相符嗎?要是所陳述的信息是真的卻不完整,那怎么辦?換句話說,可能炸彈確實在X位置,可我還沒有告訴你如何拆除它(恐怖分子都聰明得可怕)。例如:告訴我炸彈安放在哪里;炸彈在X位置,比如說在法航售票窗口,但這一陳述即便證明為真,也不足以阻止炸彈爆炸。還需要進一步的答案,以及更進一步的其他問題。(如何拆除炸彈?)從法學角度出發則又預設了另一類問題和答案,由種種問題而確認這個人確實是我們需要套其口供的恐怖分子(而不僅僅是個漫步于城市的游客)。一些問題滋生出其他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的問題。這里的困難既是概念上的,也是實際上的:在開始提出問題之前,我們需要設想非常多的情況,不存在單一的問題足以應對列文所設想的場景。問題本身也是雜多的。
認為存在一個單一的、主導性的問題,這個幻想也與時序幻想密不可分。思考一個古代的故事:這次場景是在忒拜群山間,兩條道路在城市附近交叉,那里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懸而未決的犯罪,以及一起私下的、被人遺忘的犯罪(拋棄一個孩子),這兩起犯罪仍然在困擾這座城市。牧人說出了那個當初把孩子交給他的人的名字,由此瘟疫消失了,或者不如說,他同時命名了這個瘟疫并通過命名而終結了瘟疫。像索福克勒斯的寓言那樣,列文的寓言具有神話的視野:當恐怖分子因酷刑帶來的痛苦而說話的時候,威脅消失了。事實上,我們意識到威脅已經消失的時候(只有到這個時候),才知道他的話是真的。或者是因為,答案已經提前知道了(正如在列文的例子里,大家都知道日期是“注定的”。就像“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而他的信息著實會幫助拯救這座城市等等事實那樣,俄狄浦斯的出身也預先就被諸神、斯芬克斯、先知提瑞西阿斯[Teiresias]、俄狄浦斯、觀眾們知道了)。我們會說:“當然啦,我們始終都知道炸彈裝置就在那里”,并且現在炸彈不在那里了,或者已經失靈了。如果沒有這種神話式的意識結果,折磨行為就無法在產生真理和拯救城市的層面上展開——這種行為是我利用信息時所產生的間接后果(雖然我或許是有意為之)。相反,如果沒有上述意識結果,產生的就會是這樣一種言語,其真假有待在最后一刻揭曉:亞里士多德學派的邏輯學家或許會稱之為“未來偶然事件(future contingent)”。(這類事件是在真理上保持中立或有待確定的陳述,無法適用亞里士多德的排中律原則——即要求命題必須或為真或為假。最著名的例子是亞里士多德說的“一場海戰會在明天爆發”。如亞里士多德的例子那樣,“安放在曼哈頓的炸彈將在‘7月4日中午’爆炸”尚不為真或為假:它僅僅會變成真的或假的陳述。)在未決的時期,介乎陳述和證實之間、行為及其結果之間的時期,我的判斷同樣是中立的、懸而未決的、懸置的。說到底,如果不是把一種行為、一個決定、一種事態與其預期的或推斷的結果相聯系,或與某些確實是內在的、公認的、清晰的、構成共同體紐帶的標準和準則相聯系,我(或者我所在的共同體)又將如何進行評判呢?*我強調算計或推測的一面,以闡明這一政治共同體觀念與韋伯(繼滕尼斯之后)所謂的“結合性社會關系(Vergesellschaftung)”相關,在這個群體中“社會行為的導向依賴于理性驅使的利益調整,或受到類似推動而達成的一致,無論理性判斷的基礎是絕對價值還是暫時的理由”。見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1968; r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40-41。
人們無法同時依照結果主義和真理上中立的偶然性來證成某個行為(或一組行為:嚴刑逼供);人們無法假定哪些行為后果將從屬于倫理判斷、而哪些僅僅是偶然事故;或者不如說,人們可以這么假定,但僅僅能夠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這么做。舉個文學的例子或許有幫助:考慮另一個故事。這次是《煉獄篇》,維吉爾正指導朝圣者但丁如何理解出現在他眼前的折磨和懲罰場景:
我的眼睛正專心致志地望著,
要看極愿意看到的新鮮事物,
但掉過去觀望他時并不遲緩。
讀者,我不愿意你因為聽到了
上帝如何命定罪人償清債務,
就嚇得拋棄了你的善良意圖。
且不要注意那折磨的形式;
要想一想那隨著來的,想一想
這痛苦最多也不會超過末日審判。*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X, ll. 103-111, trans. W. S. Merwi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00),99;行數根據原文略有調整。(譯者按:引文翻譯根據朱維基譯但丁《神曲:煉獄篇》,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80頁。)
這里的場景引人走神,以至于詩人但丁轉而(站在旅程終點的高度而回溯性地)指導他的讀者如何理解他在維吉爾幫助下所目睹的折磨。他告訴讀者:想一想那隨著來的,想一想“末日審判”。專注于折磨的種種形式,便犯下了濫施同情或“道德懦弱”的過錯。只有從結果或事件(event,對于“succession[隨之而來]”一詞的程度很強的佳譯)的角度來看,從奧林匹亞的位置來看(這個位置是保留給那些人的:他們不僅知道時日和行為有其結果,并且知道行為的賞罰;他們拯救了城邦或靈魂),人們才能真正做出判斷。但丁用了兩遍動詞以示強調:不是目見或想象,而是思想,il pensier,幫助我們從我們看到或想象的折磨中找到用以證成這些折磨行為的結果。結果主義思想能夠防止一個例子變成反面教訓,也能防止(比如)從他人的受苦場景中感到太多的興趣、快樂或滿足,也能防止我們的所見或所想從附屬位置反過來壓倒一切“善良意圖”,像美杜莎那樣麻痹我們的判斷并攝住朝圣者。列文的寓言既要求讀者具備關于事件的神話視角,也將這個視角作為城市賴以建立的基礎,以及判定共同體成員身份的基礎。公民的判斷被放在末日審判的角度來思考,從屬于主權的完整性。主權思想將我們僅僅看見和想象的事物排除在城墻之外。這座城市是一種末世論。是否存在另一種方式來想象恐怖、判斷和城市之間的關系?
讓我們換一種方式開始故事。仍然是古代的場景,古老的悲劇:女性、枯萎、瘟疫;它們的原因不得而知。這座城市,城邦(polis),支撐它的制度和共同體實踐,使這些制度和實踐得以可能的牢固的城墻,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一切都處在危難中。兩個故事交錯于這個古代場景中:城市的受難故事及其統治者的起源故事。在這兩個故事交會的地方,主權者正向仆人說話;這個仆人(他起初保持沉默——出于什么呢,克制?禮儀?忠誠?)被迫開口說話:出于暴力(violently)。對于總是在旁的公民歌隊而言,這一場景有著索福克勒斯或塞涅卡的現代讀者所不熟悉的形式。例如:我們作為這些古代悲劇的現代讀者或觀眾,相信出現于歌隊面前的故事與出現于我們面前的故事應相互區分,因為一者涉及到公共事務,而另一者涉及私人事務。并且我們相信,將主權(既有鎮定自若[self-possession]的意思,即能夠自主決定采取何種行為方式,也有政治主權的意思)置于一個職務或一個個體身上,或是將主權分配到各個團體身上,其背后的道德基礎取決于一項區分:城市的利益與生活在城市中的個體的利益。我們或許要再次詢問,對于以城市為名實施的行為而言,判斷其是否允許的基礎,是否可能是世俗的、非末世論的?最后,我們相信,即便我們承認如果仆人不說出那個故事,城邦就不能繼續持存;進一步,即便我們承認為了達到持存的目的,仆人(或恐怖分子)按照列文的話說可以“被施以最為嚴酷的折磨”——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會下結論說,此后這個城邦將不再是它之前那個樣子了,當它以暴力的方式獲得那個將會使它得救的故事時,它的種種自我理解也就不復存在了——例如,它將不再是一個“合憲”的社會,它的價值將不再具有普遍性或得到普遍應用。
當這個古老的故事開始的時候,這四種反對都不相關: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尚未采取其現代的、差異性的、相互關聯的、對立的形式,而且它們之間的區別也不具有規范性價值。仆人的故事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屬于這個城邦,而它在公共事務中的位置則是暴力的結果——當代的眼光可能會覺得這種暴力根本無效,甚至是自我挫敗的;巨大的、低效的、精微的世俗化裝置在那時還沒有立足點。*關于奴隸的“對體性”歷史,見Page DuBois, Slaves and Other O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在索福克勒斯那里、甚或在塞涅卡那里,并不存在這樣一個世俗立場,借此某個角色、歌隊的某個成員,或事實上是某個觀眾能夠:第一,詢問這個城邦在牧人說出故事后、在探得這個故事所需的暴力被實施后,還能否繼續持存;第二,判斷集體利益是否確保了個體的犧牲(仆人或主權者)。沒有一個單獨的概念——比如“城邦”、“個體”,或其關聯,“公民權”——能夠脫離那場威脅著這個城邦及其居民的瘟疫,不存在這樣一個中立而無涉的概念,借此人們可以判斷是否(或要求)某種行為應當被實施,由誰實施,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實施,然后描述并制定規則以“按流程實施”。不存在任何穩固的立場,借以做出哪怕是最簡單的倫理判斷或政治判斷——也不存在借以任何評判它們關系的立場。不存在任何一個這樣的位置,由此出發可以確定,決定接受城邦法律的行為,發生在法律存在之前還是之后;或試圖確認這一行為究竟是不是一項決定: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闡述的關于國家的理論將會探討這個空缺。*對于倫理言語和政治言語之間的“縫隙”(尤其涉及列維納斯的著作)的細致論述,可見Simon Critchley’s “Five Problems in Levinas’s View of Politics and the Sketch of a Solution to Them”, Political Theory 32,no.2(2004):172-185。
因此,這就是我想提到的古代場景。這個場景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公共的或政治的故事與私人故事交匯的場景之一,也絕不是最具有暴力性的一個。或者,不如說它的暴力性不同于提瑞西阿斯盛怒下的質詢,也不同于俄狄浦斯與克瑞翁的對峙,也不同于以下兩種極端的、卻是幕后的具體敘述: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雙眼,這個姿勢將一個故事永遠與另一個故事縫合起來,他瞎了的眼窩標志著兩個點,城邦的故事,主權者的故事,以及每個公民對它們的了解,都在那里匯集到一起;盲目的點,十字路口,絕境。城邦的利益、城邦的健康、城邦的持存:這些因素在戲劇開始時就顯然處在關鍵地位(俄狄浦斯對乞援人和歌隊說:“你們每人只為自己悲哀,不為旁人;我的悲痛卻同時是為城邦,為自己,也為你們。”11.60ff),但在這高潮性的一幕中卻不是如此。俄狄浦斯并未以政治理由詢問仆人,這里存在著另一種邏輯:
報信人:喂,告訴我,還記得那時候你給了我一個嬰兒,叫我當自己的兒子養著嗎?
牧人:你是什么意思?干嗎問這句話?
報信人:好朋友,這就是他,那時候是個嬰兒。
牧人:該死的家伙!還不快住嘴!
俄狄浦斯:啊,老頭兒,不要罵他,你說這話倒是更該挨罵!
牧人:好主上啊,我有什么錯呢?
俄狄浦斯:因為你不回答他問你的關于那個孩子的事。
牧人:他什么都不曉得,卻要多嘴,簡直是白搭。
俄狄浦斯:你不痛痛快快回答,要挨了打哭才回答!
牧人:看在天神面上,不要拷打一個老頭子。
俄狄浦斯:(向侍從)快來人,立刻把他的手反綁起來!
牧人:可憐呀,為什么呢?*Sophocles, OedipusRex, ed. R. D. Rawe,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70-71。對這幾行的闡釋歷史,見Jean Bollack, L’Oediperoi de Sophocle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1990),v.3,753:“因為‘把手反綁起來’并不是開始一系列審問性酷刑的姿勢,apostrepsei幾乎總是被譯成‘連起來(bind)’……至于‘扭’,譯者們依賴的是《奧德賽》中有關墨蘭托(Melanthio)的懲罰的描述……因此,威脅是被明確指出、但未被執行的。”(dustēnosantitou)
關于上述詩行存在一些編輯上的細微分歧。牧人的呼告——dustēnos,“可憐的,災難性的,悲慘的”——普遍被讀作自指,雖然有些編者指出這一形容詞也可能用于俄狄浦斯:這個詞在仆人和主權者之間滑動,對兩者都有意義。關于俄狄浦斯的“快來人,立刻把他的手反綁起來!”一句也存在分歧:這句話既可以理解為威脅(把牧人的手綁起來,準備其他未明言的酷刑),也可以理解為牧人的苦難已經由此開始了(被扳住雙手就是牧人所受折磨的一部分)。
由此,這一對話產生了兩種舞臺布置:一種認為僅僅對于苦難的懼怕就足以使牧人說出故事,而另一種則將角色的受苦展現出來:第一種理解符合這出戲自始至終對于暴力場景的處理,即將其置于想象性的、幕后的領域中(謀殺拉伊俄斯[Laius]、伊俄卡斯忒[Jocasta]的自殺、俄狄浦斯刺瞎雙眼);第二種理解則威脅要將暴力場景搬上舞臺。塞涅卡的版本青睞于第二種理解。他筆下的俄狄浦斯質問福波斯(Phorbas)——負責照看忒拜城皇家羊群的牧人:
俄狄浦斯:(旁白)為何還到遠處尋找?如今命運已近了。(向福波斯)完完整整告訴我,那個嬰兒是誰?
福波斯:我的忠誠禁止我這么做。(Prohibetfides.)
俄狄浦斯:你們誰,拿火來!火焰馬上會燒盡忠誠。(Hucaliquisignem!Flammaiamexcutietfidem.)
福波斯:真理是靠這種血腥手段尋得的嗎?我懇求您原諒我。(Pertamcruentasveraquaerenturvias?)
俄狄浦斯:如果你認為我殘酷無情,你馬上可以找到報復手段:告訴我真相!(Siferusvideortibi/Etimpotens,paratavindictainmanuest:/Dicvera.)[1]
無論是索福克勒斯筆下的命令(“說出故事”或“把他的手反綁起來!”),還是塞涅卡的(“告訴我真相!”),都不是基于城邦利益與公民利益的嚴格區分。兩個版本的《俄狄浦斯王》在這一點上都不可能自洽地在主權者表達的欲望(作為兒子、丈夫、有謀殺嫌疑者、被背叛者;作為可以為所欲為的人;作為盲目追隨他人安排的命運的人)與城邦利益之間做出區分。盡管種種區分在這出戲將兩者進行比較的領域內具有決定意義(確定家族或世代的區分;區別陌生人和親屬,奴隸和公民,主權者和臣民,或現在與過去;確定表面上看是自由的行為是否確實是自由的,抑或其實遵循了某個更古老的邏輯),但在政治判斷甚或倫理判斷的領域內,這些區分都既是根本的,也是不可能做出的。*不可能做出區分——更好地說是毫無意義。比如,維特根斯坦在其“倫理學講演”結尾說(Ludwig Wittgenstein, “A Lecture on Ethic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4(1965):3-12):“現在當這種異議出現時,我便立刻清楚地看到,不僅我能想到的一切描述都不能描述我所謂的絕對價值,而且我反對任何人從一開始就根據其重大意義而提出的一切意味深長的描述。這就是說我現在明白了,這些荒謬的表達并非沒有意義,而是因為我還沒有找到正確的表達,但它們的荒謬性卻正是其本質。因為我對它們要做的一切就是去超越這個世界,即超越意味深長的語言之外。我整個的傾向和我相信所有試圖撰寫或談論倫理學或宗教的人的傾向,都碰到了語言的邊界,像這樣在我們囚籠的墻壁上碰撞是完全地、絕對地沒有希望的。倫理學淵源于希望談論某種關于生活之終極意義、絕對善、絕對價值的欲望,就這點來看它不能成為科學。倫理學談論的事情,在任何意義上都對我們的知識無所補益。但它是人類思想中一種傾向的紀實,對此,我個人不得不對它深表敬重,而且,說什么我也不會對它妄加奚落。”(譯者按:中譯根據萬俊人譯文,見《維特根斯坦的倫理學演講》,載于《哲學譯叢》1987年第4期,略有改動。)對于那些普遍穩固的區分的虛假必然性質(這些區分帶有維特根斯坦這里所謂“絕對價值”的性質),我在這里特別想到的是實用主義論辯,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說,實用主義論辯正確地堅持認為,“從‘某種區分無法在任何情況下都成立’這一事實,無法得出‘無論如何它都不成立’”。(Hi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118)事實上,將某些概念區分進行(人們或許可以說)“本體論化”(ontologization)是一項特別弱的哲學技巧,但盡管如此,索福克勒斯和塞涅卡的戲劇關注的確是此類區分。這兩出劇被算作悲劇(事實上,從黑格爾到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論述中,它們定義了文學文類和哲學寫作的一種亞文類),恰恰出于其穩定的文化、政治甚或神學重要性(gravity),這兩出劇為各種必然(出于同樣重要的原因)終歸失敗的區分賦予了上述重要性。
順著這兩部戲所劃出的弧線,一種形式的倫理—政治邏輯消退而另一種隨之上升(似乎是一種補償)。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劇末(作為這出戲的結果),“屬于城邦”的涵義、公民的涵義、主權者的涵義、歌隊成員或觀眾的涵義,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統治者的故事和城邦故事的不同面向的責任已分攤到公民中間,因而公民之間的關系也被重新定義、重新塑造、中介(mediated)和轉化。正如俄狄浦斯和克瑞翁的家庭關系一樣。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一系列要求結尾,這些要求涉及不同層次并基于各種不同的規范性框架。其中兩個要求特別引人注目。歌隊向觀眾(包括忒拜城民眾和這出戲的觀眾)表明俄狄浦斯已經刺瞎雙眼,令人想起主權者的好運(ēntuchais,明確而反諷地指向俄狄浦斯在l.1080處宣稱他自己是“幸運女神之子”paidatēstukhē s)曾一度激起熱切的模仿乃至嫉妒,然后從俄狄浦斯的隕落中得出了對于忒拜居民的著名訓誡:在死之前不要就任何必死者的幸福或不幸做出判斷(ll.1524-1530)。值得注意的是忒拜城的“居民(enoikos)”和“公民(politēs)”之間的區別。“居民”在索福克勒斯這里并不常見,事實上所指也更廣泛;索福克勒斯劇中唯一另外一處使用這個詞的地方出現在《菲洛克忒忒斯》中,指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動物:尼米亞猛獅(hoi poteNemeasenoikon);柏拉圖在《克力同》(113c)中用這個詞描述亞特蘭蒂斯的原住民伊夫納(Evenor)。歌隊加于觀眾身上的要求,將觀眾(包括忒拜人)轉變成僅僅是空間的占據者。他們是居住者而非公民;他們的生命是動物或原住民的赤裸生命;城邦如今被理解為一個由野獸棲息的空間。更確切地說:一個動物園。當俄狄浦斯請求克瑞翁保護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請求克瑞翁讓他向她們祝福,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基礎只有親屬關系;他的要求并不是基于任何社會的、倫理的或政治的標準。在索福克勒斯那里,牧人故事令人痛苦地揭示了真相,預示著城邦政治生活的終結——政治生活如今不可避免地分裂為僅僅旨在居住的利益和家庭的貴族式要求。忒拜城隨著俄狄浦斯的放逐而恢復了健康,驅散了斯芬克斯和瘟疫的恐懼,但也失去了恰恰使得這座城邦成為政治空間的東西:主權者的創傷、他對命運的敏感、純粹的偶然性、遍及整個城邦的主權者自身的弱點。正如伊俄卡斯忒稱自己與俄狄浦斯的關系是“不名譽的雙重紐帶”:將受傷的主權者以犧牲的方式逐出城邦,拯救了城邦,同時也判了城邦的罪,并隱約開啟了想象替代性方案的可能,即主權的缺陷性、分裂和偶然性并不被驅逐,而是被城邦所接納并分攤到全體民眾:被人們記住、重復、反復推敲。
塞涅卡對于城邦中(為了城邦)說出真相的“真相”(“truth” of truth telling)所做的簡要觀察,首先就令人矚目地將索福克勒斯含糊其辭的事情擺上了舞臺。塞涅卡的真相看起來位于一段殘酷經歷的終點。它與忠誠沖突。而實情(true story)在表面上所采取的殘酷、實情為了拯救城邦而采納的折磨手段,使得真相變成了一種報復工具:說出真相實際上就是以牙還牙,用苦難抵消苦難。[2]塞涅卡有關在折磨之下說出真相的“真相”所做的上述觀察(也是關于真相的運用和結構所做的觀察),并不彼此從屬,也不從屬于某個“說出真相”的規范性觀念,不管它是道德的還是認識論的;它們甚至不是彼此相關的觀察。這幕場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上述無序的觀察與塞涅卡在俄狄浦斯旁白中勾勒的領域之間的對比:“為何還到遠處尋找?如今命運已近了。(Quid quaeris ultra? Fata iamacceduntprope.)”故事的真相在于它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當實情呈現出來的時候,無論如何它都會被人們辨認出(如果不是已經被知曉了的話)。因而這就是為什么福波斯講述的故事會立即被理解,并被認為是真的:牧人的故事重復了俄狄浦斯以某種方式已經知道了的故事,他已經在向自己講述這個故事,他已經對此感到害怕。簡言之,在塞涅卡的城邦中,以及對這個城邦而言,說出真相的真相與其重復和辨認密切相關。(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塞涅卡的城邦中,真相總是一個神話,一個被不斷回憶和重復的公認的故事。)
其次,在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中,“說出真相”的真相同樣與角色的內在性(在非常初期的意義上的“內在性”)相關。俄狄浦斯預先便體驗了自己的故事和城邦的故事,而塞涅卡對這個故事的重復,展現出一種性格特征(統治者在折磨自己;他是城邦的污染物;折磨福波斯是將心理狀態外顯化的方式)、一種內在性的表征(舞臺上演出的故事由此可以以對應的方式呈現出來)。如果觀眾對于如下的戲劇性反諷了然于胸——即酷刑的威脅或體驗在其中既再現了統治者所感受到的(以及不斷加諸自身的)痛苦,也為他將體驗到的酷刑埋下伏筆——那他們就會以同樣方式理解,自身為何會意識到此前戲劇中出現的種種重復,但效果(affect)則截然相反:即理解到存在這樣一種記憶,戲劇可能與之對應也可能不與之對應,但戲劇暗示著這種記憶并從中獲取其身份認同(identity)——一種來自主權者創傷景象的集體認同。
第三,與之相關的是俄狄浦斯與歌隊之間的關系。索福克勒斯的歌隊代表城邦,直接向國王唱出城邦的利益,并作為公民集體而直接與國王對話,但塞涅卡的歌隊則不是這樣。塞涅卡的歌隊作為道德性普遍原則的來源,代表著一種不安的、遲來的、或許可以說是遺留的習俗,在戲劇歷史上它不久就將被拋棄。隨著戲劇空間逐步被理解為心理空間的象征,歌隊的作用就被性格設置和傳統所吸收。
最后,同樣在性格這一點上,塞涅卡的俄狄浦斯表現出極度的犧牲式的(sacrificial)自哀、極大地突出了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的一個特征。塞涅卡的俄狄浦斯向觀眾如是說:
所有你們這些心智孱弱、重病纏身、幾與行尸走肉無異的人們,看哪,我被驅逐而離開這里:抬起你們的頭來,我走之后你們會迎來明澈的天空。起死回生的氣息將吹拂到那些垂死于病榻上的人們身上。去吧,去幫助那些被遺棄的人:我會將這片大地上致死的疾病都帶在自己身上。野蠻的命運、狂暴的疾病、破壞性的瘟疫和遍地的苦難,都跟我走吧,跟我走吧:我歡迎你們做我的向導。[1](PP.110-111)
我們在此看不到任何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結尾處具有的模棱兩可:驅逐是回報和治愈;受傷的主權者的離開給城邦帶來健康和繁榮,使之延續。
簡言之,塞涅卡的《俄狄浦斯王》將索福克勒斯設置的僵局從政治本體論領域轉化到審美領域,并在審美的層面上處理它們。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城邦的持存前提是政治的喪失——被轉化為塞涅卡的喜劇。這種策略僅僅是部分地成功了,但在類似列文所論述的城市中,我們可以發現其末世論所仰仗的正是上述策略。
對我們而言,問題不在于“回到索福克勒斯”(不管這意味著什么),而是在關于城市利益(以及這些利益所需要的倫理秩序)的種種當代表征背后,尋找另一種古老的立場——一種非末世論、非英雄主義、非犧牲的,確切地說是政治性的立場——由此出發,確定在面對城市時倫理判斷所處的位置。是否可能得出某些標準,用以判斷某種行為或情境是否與城市的準則相符,并且這一判斷無需訴諸某種規范性理念,或用審美來代替政治性問題,或訴諸某個概念、某種幻想(例如,有關此類城市或共同體或許會是什么樣子、或許需要什么條件的理念、概念或幻想)?從內攝的(introjected)缺陷性主權這一極具寓言性的意象中能得出什么?
[1]Seneca.Oedipus[M]. John G. Fit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Page DuBois.TortureandTruth[M]. New York: Routledge,1991.
TerribleEthics
Jacques Lezra, tr. WANG Qi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0003, USA)
As the basis of an ethics, ‘terror’ presupposes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bord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its universals.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same story narrated by Sophocles and Seneca, we can find that Seneca’sOedipus, in short, translates the impasses that Sophocles devises from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ontology to that of aesthetics and addresses them at that level. Sophoclean tragedy, the loss of the political that is entailed in the city’s survival, is converted to Senecan comedy. Thus, the thesis of ‘terrible ethics’ leads us to the problem of ‘defective concepts’ and, ultimately, sovereignty.
terror; ethics; sovereignty; oedipus
2012-12-01
雅克·萊茲拉(Jacques Lezra),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主要從事政治哲學、莎士比亞、批判理論等研究;王欽(1986-),男,上海市人,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政治哲學、批判理論等研究。
B82-02
A
1674-2338(2013)01-0035-08
(責任編輯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