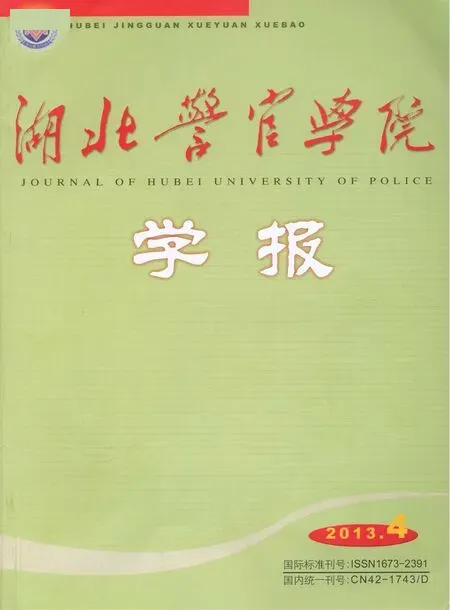論案例指導制度與我國現行司法制度的兼容性
趙文婧
(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山東 威海264209)
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發出實行案例指導制度的改革意見之后,《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若無特殊說明,以下簡稱《規定》)于2010年1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確認在我國建立案例指導制度,主要內容為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案例,指導全國法院的審判、執行工作。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2012年4月13日又出臺了第二批指導性案例。應當說,《規定》的出臺,既是對以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典型案例經驗的總結,又是借鑒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司法改造。同時,也是對我國傳統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的新考驗。檢驗案例指導制度是否符合中國法律發展的現狀和需要,要看這一制度是否有其存在的邏輯正當性和實踐必要性,是否能被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包容、消化以及兩種制度在同一個法律環境下同時運作的兼容程度。
一、中國特色的司法實踐——案例指導制度
我國傳統的法律制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書面的法律法規組成,因而中國是典型的成文法國家。但是“依案而判”的案例制度在我國法律制度歷史上一直存在。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為適應復雜變化的形勢及成文法的局限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將判例運用到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以例斷案”是中國司法一脈相承的歷史傳統,案例指導制度便是這種傳統在現代司法中的集中表現。
案例指導制度的含義是指在以制定法為主要裁判依據的前提下,將指導性案例作為司法審判的輔助性工具,既不動搖制定法的主要法律淵源地位,同時又借鑒了判例法中的具體做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案例指導制度是以指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統一法律適用、確保司法公正、高效和權威作為最終的目的。將指導性案例作為具體解釋法律、填補法律漏洞的載體,為有關法律問題提供明確的指引,為立法提供補充。最終的落腳點是“審慎、公正用好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權威不斷得到昭示和落實”。[1]
邏輯學家哈格認為,雖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屬于不同的推理模式——基于規范的推理和基于判例的推理,但是這兩種推理模式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差異只存在于形式,因而實現歐洲大陸私法體系的一體化是可行的。如果說案例指導制度借鑒了判例法制度,而我國的法律制度就技術特色而言更接近大陸法系,那么傳統的制定法為主的法律制度與案例指導制度是否也存在邏輯基礎上的一致性并能夠在實踐中相得益彰,共存共生呢?
二、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是對社會轉型背景下裁判難題頻現的司法回應
有學者認為案例指導制度在我國的實行,是對中國法制實踐面臨的復雜局勢和迫切需要的順應,也是對世界范圍內兩大法系逐漸融合的發展趨勢的一種呼應。面對迅猛變化發展的社會現實,繁瑣的立法程序和緩慢無聲息的議會使大陸法系國家對立法成本不堪其負。[2]經過不斷的實踐和改革,大陸法系的判例匯編日益完善,填補法律漏洞、調節法規沖突的任務都由法官運用判例得以實現。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本質區別是,對成文法在法源地位中的尊崇似乎被“判決產生法律”這一原則突破。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判例制度在降低立法成本、消除立法滯后、填補法律漏洞等方面的優越性可彌補成文法的局限性。雖然司法判例不能享有成文法規般的正式的、確定的法律約束力,但司法判例在某些國家的司法領域起到了補充成文法的重要作用這一事實已毋庸置疑。
在當今時代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融合的趨勢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大陸法系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判例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的案例指導制度的思路和建設也可以從大陸法系國家的判例制度上得到啟示。
(一)彌補成文法的缺陷,解決司法解釋的合法性難題
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給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機械單純地適用法律條文、依靠三段論的推理方式無法妥善、正確地處理所有糾紛,而近年來因為自由裁量權的不合理使用又使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依據中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審判過程中遇到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發布有法律約束力的細則化解釋來指導下級法院判案。這種解釋方式在當前司法難題頻現,各級法院對于相同問題處理不一的情況下對于統一法律適用具有較強的實際意義,但卻面臨著合法性難題——司法不產生法律卻產生了類似法律規范的抽象規則,司法機構制定的司法解釋常被質疑侵犯了立法機構的立法權。案例指導制度的建立可以解決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統一法律適用但無明確的合法性這一難題。
(二)回應法官對指導性案例的需求
案例指導制度這一概念中,“指導”二字最為關鍵。指導即意味著指示教導,既反映出了這一制度的實施主體中上級對下級的規制地位,又表明這一制度的實施意圖是貫徹最高司法機關的意志,維護司法一體,通過此制度來加強司法管理。司法管理從實踐層面上講是對司法工作者行為依據、行為方式、行為結果的管理,從理論層面上講管理的對象是法官的司法權,也就是自由裁量權。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自于成文法的抽象性,是法官擁有的一種法定的權力,即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根據實際情況自由裁決。從理論上說,法官隨時可以按照他對法條和事實的理解和判斷來裁判案件。他可以無視所有法院以往對同類案件的“判決先例”,從而造成相對普遍的“裁判不一”。[3]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不同的法官對于這個限度的把握顯然不同。事實上,對于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法官也會覺得無所適從,特別是對疑難案件的判決結果導致的社會反映,法官明顯無力招架。若能及時地對自由裁量進行限制,對典型案例的審判提出明確統一的裁判標準,在充分理論論證以及有效權威支撐的情況下,“同案不同判”的問題會得到有力的解決。
三、案例指導制度本身設計的不周延及與司法整體環境的兼容不足
案例指導制度的確定并不僅是一個純粹的司法領域改革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我國根本的法律制度、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關系的政治問題。盡管這一制度擁有許多理論上的優越性,卻無法證明其與我國法律環境、傳統的法律制度完全兼容——即具有邏輯上的正當性和實踐中的合理性。案例指導制度有鮮明的國情和時代特色,其中最核心的特點是承載司法管理職能和以行政化方式運行。這使案例指導制度面臨著難以化解的邏輯難題:案例指導制度本身設計的不周延及與司法整體環境的兼容不足。
(一)制度設計的不周延
1.抽象規則的提煉抑或立法型司法解釋
指導性案例編寫形式初步設想分為首部、指導要點、案情介紹和裁判結果與理由四個部分。[4]這樣的編寫形式運用的是提煉抽象規則的方式,即采用歸納式的表述方式來總結一個案件的基本情況和指導要點。歸納完成后,對法官有指導意義的正是從判決理由中提煉出來的規則。法官必須準確把握在審案件的要點,如民事案件中的民事法律關系,刑事案件中的犯罪構成和要件等,才能確定指導性案例提煉出的規則是否與在審案件爭議的要點一致并可以參照審理。案例指導制度實際上是通過歸納規則進行指導,將案件進行分析后的結果用于司法審判中,為法官提供“快捷”的判決指導。這種脫離具體案件審理過程的提煉是沒有價值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機械司法的泥潭。[5]
如若司法中通過案例進行司法解釋,那么案例指導制度與司法解釋有何區別?代表性觀點認為,案例指導與司法解釋具有互補性:指導性案例以要旨為指導形式,僅有參照效力,彈性較大,可彌補司法解釋剛性過強,柔性不足的問題。[6]上面分析了指導性案例通過規則提煉的方式對新案予以指導,這種條文化的適用方式使其與司法解釋的區別和界限并不清晰。同時,指導性案例與司法解釋效力的高低問題在實踐應用中也遇到了適用瓶頸。所以從當前情況來看,上述預設并不容易實現。
2.指導性案例的選擇和生成路徑
前面講到,無論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淵源還是大陸法系引入的判例制度,判例的生成都是司法過程的自然選擇。判例來源于任何法院的任何判決。而且,判例的效力是“天生的”,判決一經作出就具有判例資格,無需其他審查程序來確認或者審核。而我國的指導性案例的生成和實施控制的程序路徑不是這樣的。《規定》確定的案例生成機制是:第一,指導性案例要符合社會廣泛關注、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具有典型性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或者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五個條件;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負責指導性案例的遴選、審查和報審工作;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業務單位對本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認為符合規定的,可以向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推薦;下級法院和社會人士可向案例指導工作委員會推薦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例;第四,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對于被推薦的案例應當及時提出審查意見。符合規定的報請院長或者主管副院長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指導性案例的遴選程序與最高人民法院基本相同。兩高院的《規定》都在司法程序之外設立了獨立的自下而上的行政性遴選程序,只有經過最高司法機關審批,司法效力已定的案例才能取得指導性案例資格。[7]這樣的案例生成方式是特定化的而不是普遍的或完全開放的,目的也是通過兩院的最高司法地位來確保案例的權威。但這樣一來,案例選擇和生成的主體變得不周延,基層法院無法參與案例的選擇過程而只能接受最終的結果。這樣的生成路徑與成文法的立法無異,限制了指導性案例的類別和數量。
(二)與法律環境的兼容不足
1.統一司法抑或維護法的穩定性
法律的穩定性和適用性是各個法律體系中永恒的、不能解決的沖突傾向。[8]案例指導制度同樣也面臨著是維護法律穩定性還是尋求實踐中法律適用性的問題。
案例指導制度最直接的目的是規范自由裁量權,實現司法統一。最高檢察院要求指導性案例具有“處理效果恰當、社會效果較好”的特點,對指導性案例的穩定性卻不甚重視。這與西方法治國家對判例穩定性的重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英美法審判的一個基本原則便是遵循先例原則,相似問題以相似方式處理。高級法院的判決自身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無論一個判例的有效范圍如何,在其效力范圍內它都將約束后續案件的處理。這與成文法國家重視成文法的系統穩定,謹慎立法的思路是一致的,法源的穩定性是實現法的穩定性的基礎條件。但反觀現行的指導性案例,其主要側重點在于為司法工作者提供審判指南,鞏固一定時間一定范圍的司法統一,更象是為了解決法律適用問題提出的救濟方案,而在其本身的穩定性方面未作推敲。
2.司法行政化的固化與弱化
案例指導制度的出現在應然層面上應降低行政力量對司法獨立的干擾,從而平衡政治因素在司法體系中的過重權力,實現司法獨立。但現實卻是,案例指導制度也是司法行政化的產物,并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發展,進而成為司法行政化的間接推力。《規定》的第1條是這樣表述的:“對全國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確定并統一發布”。換句話說,一個案例的指導意義,不僅僅因為其本身對案件所作的處理有多么公正甚至多么藝術化,最重要的是最高司法權力運用實際上的行政行為賦予了其指導性的地位。行政化方式在我國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硬性表達的行政化行為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將最高司法機關的意圖傳達并貫徹。行政手段的運用強化了司法業務管理,卻也受到了司法審判工作被行政權力滲透的詬病。
另外,司法體制中的等級式的審級與行政機關的等級制不同,下級法院擁有獨立尋找法律依據并審判案件,不受上級法院級別控制和干擾的權力。也就是說,獨立審判權賦予了無論上級法院還是基層法院選擇或者發布指導性案例的權力,同時法院無權強制其他級法院一定也將自己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作為參照判例進行新案的審判。
四、結語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案例指導制度是成文法下使用案例的一種新形式。它借鑒了判例法系以及大陸法系判例制度的有益經驗,是對當前司法困境出路的探尋,在理論設想的層面有解決疑難復雜案件的可能性。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這一制度在我國法律環境中的尷尬位置及其不明晰的發展前景。因而,筆者對案例指導制度與我國傳統的法律制度、法律環境之間的兼容性提出質疑。一種法律制度能否適應體制以及實踐的需要,不能只看制度設計的理想程度,也不能在已經存在的弊端問題上粉飾太平。只有勇于面對實質上的矛盾和沖突,才能真正找到司法改革、司法建設的出路。
[1]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二批指導性案例[EB/OL].http://www.cour t.gov.cn/xwzx/fyxw/zgrmfyxw/201204/t20120414_175938.htm,2012-04-14..
[2]潘榮偉.大陸法系的司法判例及借鑒[J].山東法學,1998(4).
[3]武樹臣.激活案例指導制度化解裁判不一難題[J].判例與研究,2011(3).
[4][5]吳英姿.案例指導制度能走多遠[J].蘇州大學學報,2011(4).
[6]人民法院報社組.關于案例指導制度的調研報告[A].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審判前沿問題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7]秦宗文.案例指導制度的特色、難題與前景[J].法制與社會發展(雙月刊),2012(1).
[8][英]克里夫·施米托夫.英國“依循判例”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J].潘漢典譯.法學譯叢,19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