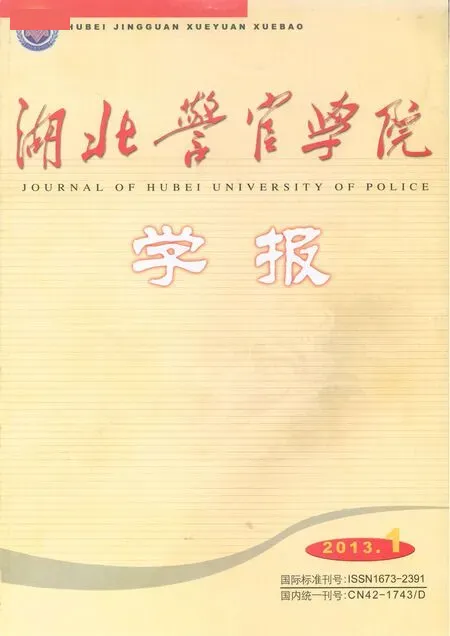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探討
王將軍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重慶401120)
近年來,隨著云南的杜培武殺人案、湖北的佘祥林殺妻案、河南的趙作海殺人案等一些列冤假錯案浮出水面,中國的司法飽受社會各界質疑。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形,比如“躲貓貓”死、“喝開水”死等在看守所的離奇死亡案例。原本寄望保障人權、定紛止爭的法律卻一次次地傷害著無辜民眾,中國司法公信力嚴重下降。中國司法如何做到公正?法律如何真正保障人權?這些問題的根源究竟出在哪里?筆者以為,從刑事法的角度來看,這與中國現行的刑事實體法為主、刑事程序法為輔的錯誤法律指導思想,以及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所產生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息息相關。比如,為了追求實體上的公正,在立法的時候,我們的法律比較偏向于對實體結果的追求,以至于連程序法都被制定成了一部以保證實體公正為主的法律。在這樣的思想和法律指導下,執法和司法自然就變成了一個以強調實體公正為主的過程,忽視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其結果就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局面。因此,要想真正地依靠法律實現司法公正、保障人權,首先要重新定義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審視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概念界定
自19世紀英國法學家邊沁提出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以來,關于實體與程序二者誰主誰輔的爭論持續了近兩百年,形成了實體至上論、程序至上論、價值補充論等幾種觀點。實體至上論也稱為程序工具主義,該學說認為在刑事訴訟中,一切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實體公正,程序法只不過是為了實現實體公正的工具而已。這種觀點否認程序法的價值,過分強調實體法的作用,現在僅為少數人所主張。程序至上論認為,“法律首先是先從程序法發展起來的,后來才有實體法。從邏輯上講,實體法是作為下位階的法,而實現實體法的訴訟法則屬于上位階的法。”[1]這種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人類的基本權利從人之所以為人時就天然地具有……各種權利隨著人類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日益縝密,為救濟權利而不斷演變,演變過程中才能借助程序,乃至后來形成程序法和實體法。”[2]價值補充論認為,“實體法規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現實生活卻是具體的、個別的案件,發生糾紛后,抽象的規范和具體的案件存在著鴻溝,對這種鴻溝的填補和彌合是通過有理性選擇的程序來達到的。”[3]這一觀點雖然“強調程序法對于實體法的補充價值,但它仍然沒有走出‘程序工具主義’的窠臼。”[4]當然還有一些其它的觀點,但和前面所列一樣,“在探索程序法與實體法關系時,總希望將它們孤立開來,比個高低,忽略了他們在訴訟實踐活動和歷史發展的動態消長過程中的聯系與區別。”[5]因此,要想弄清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系,有必要將二者納入到整個法律體系中思考,從法律本身的價值、功能以及具體適用出發予以考察。
(一)既有定義述評
要想弄清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必須首先明晰二者的概念。在英美法系中,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定義主要見于《牛津法律大辭典》。這部辭典關于實體法的定義是“所有法律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及各部門法的主要部分,它是有關特定情況下特別的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權利和應履行的法律義務的法律。”[6]程序法的定義則為“用來表示不同實體法的法律原則和規則的體系。程序的對象不是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是用來證明、證實或強制實現這些權利和義務的手段,或保證在他們遭到侵害時能夠得到補償。”[7]在我國,關于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定義廣泛見于各種法理學教材,大體相似,基本認為“實體法是規定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職責與職權關系的法律……程序法是規定保證實體權利與義務、職責與職權得以實現的方式和手段的法律。”[8]
英美法系中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定義有待商榷,因為關于“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權利和應履行的法律義務”的規定不僅僅存在于實體法中,在程序法中也有有關“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權利和應履行的法律義務”的規定,并且這一問題同樣存在于我國關于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界定中。在法治高度發達的今天,各國程序法中關于法律關系主體的訴訟權利與義務、職權與職責關系的規定也越來越詳盡,而我們卻一味地把這些歸屬于實體法范疇。這不但擾亂了法律分類,不利于法律體系的構建及其發展,更是夸大了實體法的作用,嚴重限制了程序法的發展。這種扭曲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錯誤認識運用到社會實踐中是肯定達不到人們預期的結果的。只要有錯誤認識,預期結果就會有偏差,錯誤認識越多,與預期結果的偏差就越大,有時甚至會完全超出我們的預期和控制范圍。近年來,出現在我國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有必要對這二者的概念和關系重新進行界定。
(二)對二者定義的認識
要想真正地認識程序法和實體法,弄清二者的關系,必須將二者置于整個法律體系及其在社會實踐中的運轉過程予以綜合考慮。從整個法律體系來說,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兩種。因此,在確定兩者的內涵時要分清彼此,確定外延時要涵蓋所有法律。從社會實踐的運轉來說,法律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亦是如此。因此,要想弄清楚實體法和程序法就必須從社會實踐的運轉出發。
人類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這個過程是無數單獨事情運轉的組合。為了便于管理,人們便將這些無數事情予以分類,并對不同類別從其發生到運轉結束確定了不同的規則。這些規則分為靜態與動態兩類,前者是由社會大多數所確定的專門針對各類事情運轉的最終靜態結果的規則,我們稱之為實體規則;后者則是由社會大多數所確定的專門針對各類事情的運轉過程的規則,我們稱之為程序規則。隨著社會的發展,某一部分規則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于是產生了法律。在進入法律體系后,原來的實體規則就成為今天的實體法,程序規則就成為今天的程序法。因此,實體法就是那些在法律體系中,規定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在法律關系運轉結束后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程序法就是那些在法律體系中,規定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在法律關系運轉過程中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由于現代法治通常認為“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9]所以,對于個人的犯罪行為,往往是由代表國家的機關予以追訟。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刑事實體法是規定國家與個人之間,在刑事法律關系運轉結束后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刑事程序法則是規定國家與個人之間,在刑事訴訟關系運轉過程中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
二、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
(一)刑事實體法是程序法的邏輯結果
在刑事法律關系中,刑事實體法是規定刑事法律關系運轉結束后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刑事程序法則是規定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當一個刑事法律關系產生時,我們必須要先經過刑事程序法的這個運轉過程才能夠實現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在刑事法律關系運轉中的主要作用就是根據法律的規定,發現是否有能夠證明犯罪的證據,并根據發現的情況確定刑法的適用,即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而且,并不是每一個被作為刑事法律關系處理的案子都會走完整個刑事法律程序才實現刑事實體法。有不少最初按照刑事法律關系處理的案子都沒有走完刑事法律程序,他們往往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刑事實體結果的實現而終止或結束。刑事實體法并不一定要有定罪量刑結果的出現才算實現,沒有定罪量刑甚至結果被認定為沒有犯罪也是刑事實體法的實現。因為法律的最高價值之一是公正地處理每一個爭點并得出公正的結論,刑事實體法也不例外。
(二)刑事實體法的實現依賴于程序法
當一個被假設為刑事法律關系的案子出現后,我們必須通過刑事程序法來證明之前的假設。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犯罪嫌疑人這一角色,并且隨著刑事程序法不斷向前運轉,犯罪嫌疑人可能離假設中的犯罪人更接近,此時我們很可能就違反程序采取一些手段取證以證明嫌疑人的罪行。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第一,當一個人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后,他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僅是對他懷疑,并不是切實的證明。因此,從公平的角度講,我們不但不應該違反法律程序,還應該在刑事程序法中加大對犯罪嫌疑人那些有可能被侵犯到的權利的保護。第二,如果我們取證的手段違反了正當程序,那么我們很難保證能獲得真實的證據,當取得的證據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實現實體法,而且還可能制造出新的問題,并直接導致第三點。第三,如果違反刑事法律程序,就會侵犯到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權利或職權,以及違反其義務或職責,進而導致新的法律關系的產生,與法律定紛止爭的目的和功能背道而馳。所以,要想真正地實現實體法,就必須嚴格遵守程序法的規定,后者是前者實現的保證。
(三)刑事實體法對刑事程序法有指導作用
由于刑事實體法的實現必須依靠刑事程序法,沒有刑事程序法的正當適用,就很難有刑事實體法的實現。因此,在具體的刑事法律關系中,刑事實體法往往是在刑事程序法終止或結束時才出現。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界定一個法律關系是否應該納入刑事法律關系中?在這個過程中,刑事實體法的規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刑事實體法規定了哪些行為是犯罪,應該納入刑法調整。當一個法律關系發生后,根據刑事實體法,如果其客觀方面符合刑法調整的范圍,它便會納入刑事法律關系調整,即刑事實體法引起刑事程序法的啟動。當啟動刑事法律程序后,刑事實體法仍然指導著刑事程序法的運轉。刑事程序法運轉的結果是刑事實體法的實現,這也是刑事程序法運轉的目的。如前所述,刑事實體法的實現既包括那些出現了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也包括那些不會出現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因此,在刑事程序運轉過程中,需要以刑事實體法為指導,以確定某個行為是否符合實體法規定。
三、結論
綜上所述,將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納入整個刑事法律體系及刑事法律關系運轉中予以分析、界定,當前實體為主、程序為輔的認識是錯誤的。刑事實體法是規定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在刑事法律關系運轉結束后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刑事程序法則是規定刑事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在刑事法律關系運轉過程中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職責關系的法律。刑事實體法是程序法的邏輯結果,刑事實體法的實現依賴于程序法,同時刑事實體法對刑事程序法有指導作用。這二者關系的明確將有利于整個刑事法律體系的構建,更好地指導刑事司法實踐和保障人權,從而減少甚至杜絕冤假錯案的發生。
[1]潘念之.法學總論[M].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25.
[2]江濤.程序法與實體法關系的思辨——就“程序法乃實體法之母”論斷的質疑[J].政法論叢,2004(3):64.
[3]李曉春,楊玉洪.程序法與實體法關系的法理學評析[J].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1(6):75.
[4]李曉春,楊玉洪.程序法與實體法關系的法理學評析[J].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1(6):75.
[5]龔子英.淺論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系[J].法制與社會,2010(1):3.
[6]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865.
[7]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17.
[8]付子堂.法理學初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