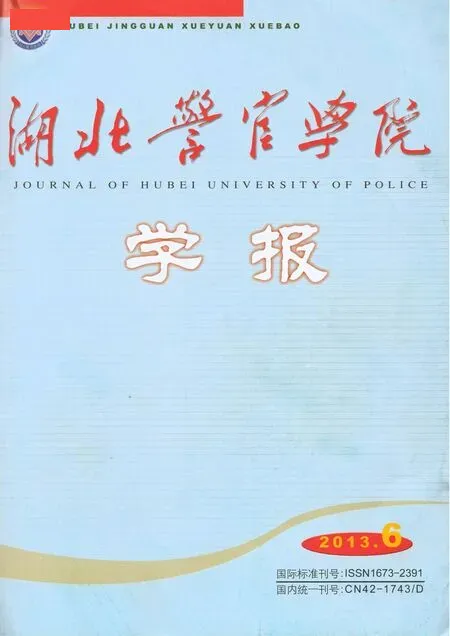被執行人追加:審執分離制度下的審視
周天保
(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江蘇 盱眙211700)
1991年《民事訴訟法》確立了追加被執行人制度,隨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逐漸細化該制度,甚至于2004年還制定了《關于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但由于基礎研究的薄弱,追加被執行人制度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筆者以審執分離為視角,分析該制度存在的問題,以期對該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實踐做法及存在的問題
審執分離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一方面,它體現了權力分立、制衡的思想;另一方面,它要求法院內部分工協作,即先由審判部門審理案件,明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再由執行部門強制執行,實現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因此,審判權是一種判斷權,執行權是一種實現權。嚴格地講,在此理論下,被執行人的追加應當通過審判程序先行確立,道理是很簡單的——不能因為乙對甲所負債務屬實而省略審判程序,直接裁定對乙強制執行。審判與執行程序的價值取向也存在差異:審判程序的價值追求是公正,執行程序的價值追求是效率[1],公正與效率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強制執行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讓權利人的權利能夠盡快轉變為現實。進入執行程序后再讓當事人二次訴訟,無異于讓當事人走了“回頭路”。因此,在不影響公正的前提下,有必要賦予執行機構直接追加部分主體作為被執行人的權利。這不僅使得當事人無須提起二次訴訟,縮短了訴訟周期,也節約了法院和當事人的司法成本。執行追加制度就是公正與效率妥協的結果。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83條規定:被執行人的追加由執行機構作出裁定。不過,這種過于絕對的做法也飽受質疑:一方面,追加被執行人的目的是讓其承擔實體上的義務,本應通過審判進行,至少應將其中復雜的爭議交由審判部門處理,一概交由執行機構處理不當;另一方面,雖然追加程序應當聽證,被追加人也可申請復議,但這與審判程序中的質證、辯論、上訴有著質的區別,由執行機構處理可能導致對當事人權利保護的不足。[2]鑒于此,有的人民法院在《執行規定》的實施過程中進行了變通,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在指導意見中明確規定根據不同的情形,由民事審判庭和執行機構分別對追加的案件進行審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執行權合理配置和科學運行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執行權意見》)中調和了這種公正與效率的沖突,規定“應當通過另訴或者提起再審追加、變更的,由審判機構按照法定程序辦理”,但對何種情形屬于“應當”并未明確。
回顧二十余年的司法實踐,審執分離理念下被執行人追加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裁審分立的標準如何判斷,即何種情形的追加應當通過審理判決的方式進行,何種情形的追加應當通過執行裁定的方式進行。分立標準不明確在實踐中會造成審執之間的相互推諉或者審執之間的管轄爭議。從一概交由執行機構處理到審判機構與執行機構分別處理,人民法院一直在審執之間徘徊,一邊充滿了對效率的追尋,一邊又擔心過分追求效率可能犧牲公正。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司法者的這種矛盾心理:“當著重于效率的時候,便傾向于執行程序中直接處理;當著重于公平的時候,便傾向于由審判程序解決。”[3]如何確定裁審的具體標準,在公正與效率之間尋求恰當的平衡,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司法難題。
二、理論溯源與制度解析
有學者用經濟分析的方法論證了被執行人追加制度的優勢。[4]以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用和執行費用A+當事人權益的實現 B+糾紛最終解決帶來的公平正義感C為總收益,以訴訟執行消耗的司法資源X+當事人的訴訟支出 Y+因追加錯誤導致的司法公信力下降Z+錯誤執行導致的司法賠償PL為總成本,如果總收益大于總成本,即A+B+C>X+Y+Z+PL,那么追加制度具有經濟上的優勢。假如追加制度的實踐標準存在聽證、復議等嚴格的運行機制,理想情況下錯誤的幾率并不高。可以假定Z和PL相比二次訴訟情況下沒有變化,但X和Y卻減少了,與此同時帶來了A的下降、B的不變和C的上升。由于A的下降相比二次訴訟中司法資源的投入和當事人成本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追加制度帶來了訴訟效益的提升。可見,被執行人追加制度具有實踐上的需求。同時,該制度也具有理論的堅強支撐。一般認為,被執行人追加制度源于既判力主觀范圍擴張理論。既判力即終局判決在內容上的實質確定力。詳言之,法院的判決是解決糾紛的最終判斷,既拘束當事人不得重復提出同一爭議,同時也使法院受自己作出判斷的約束。換個角度來說,法院的判決是相對的,只對訴訟的參與者產生約束力,而不及于訴訟主體之外的第三人。但當案外人在特定條件下與訴訟標的產生不可分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對于權利的穩定來說有利無弊,顯然需要使用既判力來調整,法律也規定可在適當的情形下擴大既判力的適用范圍。[5]既判力的擴張帶來了執行力的擴張,以《執行規定》為例,具體情形包括:(1)訴訟系屬后的當事人變更(第79條);(2)訴訟擔當(第76條至第78條)。既判力是司法權威性及終局性的集中體現。它通過對訴訟的強制性終結帶來了司法程序的安定,結束了對訴訟資源無休止的消耗。
以上理由構成了由執行機構進行追加的重要理論基礎。然而,經濟分析的情形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場景,聽證、復議并不必然帶來X、Y的減少,甚至執行亂還會導致C的下降和Z的上升。既判力的理論也不能完全解釋現有的被執行人追加的情形:第一,既判力是就人民法院作出的執行依據而言的,并不包括仲裁裁決書、調解書和公證債權文書;第二,出資不實和抽逃出資者不是既判力和執行力效力所及的范圍,《執行規定》的起草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6];第三,關于既判力的約束力是實體上的還是程序上的,學界仍存在爭議,對其主觀范圍擴張的界限,實踐中有時也比較模糊。前述分析也忽視了程序公正的問題。正當程序要求在法院內部合理分配司法權,進行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正當程序的理念構成了現代訴訟法的理論基礎,審執分立從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做法。2005年,中央司法體制改革要求“在各級人民法院設立執行機構,專司民事行政案件的執行實施工作”。對《執行規定》中的情形,實踐判斷中可能也存在實體上的爭議,交由執行機構裁定確實不妥。即便現行的執行權分立為執行實施權和執行審查權,但通常追加事項的裁定需要執行部門庭、局長的層層審批,兩權行使的主體形分實不分,影響了分權的效果。[7]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追加執行,普遍做法為由執行機構直接裁定追加。但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不能單純取決于夫妻關系的認定,即使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也不一定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法院還需要考慮債務的真偽、性質等實體因素。還有觀點認為,執行依據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可以直接追加,但被執行人的配偶顯然沒有參與作出執行依據的司法程序,也不能以家事代理確立訴訟擔當的存在。忽視了這一事實,無異于強迫當事人接受其未曾預料的結果。最后,執行中存在著執行和解的做法,《執行權意見》將部分案件的管轄權直接交給審判機構,而原執行案件卻由執行機構負責。權利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實現權利,兩個部門共同處理不利于調解的操作。假如由執行機構處理,雙方通過調解達成了執行和解,反而是更加高效的。
三、完善建議與新的思考
如前所述,被執行人追加制度是公正與效率平衡的產物,因此,保留執行機構部分審查權確有必要,但同時,裁審分立需要明確具體的標準。有學者建議,“實體上雙方無爭議且實體責任法律規定明確的,在不影響公正、不損害當事人利益的情況下”由執行機構處理。[8]也有意見認為,應以執行力擴張范圍進行區分,對屬于執行擴張范圍的主體的變更和追加通過執行程序進行,否則通過審判程序進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則認為,變更事項不涉及實體內容的往往事實清楚,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審查可由執行局負責,否則由民事審判庭審查。在我國臺灣地區,如果對債務人是否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之人產生爭議,債務人可以提起異議之訴,債權人可以提起許可執行之訴,皆由執行法院民事庭受理。[9]《強制執行法(征求意見稿第六稿)》即借鑒了臺灣地區的做法。上述建議和做法均有一定道理,但第一種意見和臺灣地區做法將區分標準建立在被追加人是否提出異議的基礎上,只要被追加人提出異議便付諸訴訟,不符合效率要求;第二種意見也存在明顯缺陷,理由前文已述;第三種意見將實體爭議交審判部門處理,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導意見所列舉的非實體爭議并非一定簡單明了,如企業法人的合并,已有的案例中呈現的多次改制、不規范合并、不同合并形式帶來責任承繼上的差別等已充分表明這種非實體爭議的復雜性。
筆者認為,確立裁審分立的標準首先應當兼顧公正與效率。第一,要兼顧實體公正與效率,不通過審判程序的追加不僅應具備實體上的公正,同時應獲得普遍認同。第二,要兼顧程序公正與效率,對實體法上沒有明確規定責任歸屬的追加,不能因為裁定結果最終的正確性而跳過審判程序。事實上,賦予被追加人與一般被告同等的程序參與權,更易讓被追加人接受裁判的結果,盡管有時這種結果對被追加人來說是不利的。此外,確立裁審分立的標準應當考慮審執的權利運行模式。審判權與執行權是人民法院司法權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執行權的行使就是司法權的行使,讓執行機構裁定追加不具有理論障礙。目前,執行權包括執行實施權和執行審查權,被執行人的追加屬于執行審查權的范疇。執行審查的事項與執行實施有著密切的關系,由執行機構進行追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執行的公正高效。同時,為了避免自執自審導致的權力膨脹,有必要限定執行追加的事項,同時適當限制執行權的行使。綜上,可以明確規定由執行機構審查的情形,其他情形仍賦予執行機構審查權,但同時也要賦予異議人訴權。筆者建議:(1)追加私營企業業主、合伙組織合伙人應當由執行機構負責。因為業主和私營企業之間具有主體上的同一性,合伙人和合伙組織具有債務上的連帶性,而且實體責任的擔當有明確法律依據,業主和合伙人也受既判力的約束,由執行機構追加不影響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2)對企業法人或其分支機構的追加應當由執行機構負責。基于法人獨立財產權理論,分支機構無獨立承擔實體責任的能力,相關責任應由法人承擔。法人與其分支機構之間的關系確立也相對簡單。(3)追加執行程序中的擔保人和違反協助義務的案外人為被執行人應當由執行部門處理。執行擔保是擔保人的一種自愿行為,擔保責任的內涵也不存在爭議;協助義務的違反與執行行為緊密相關,義務違反人的責任也由法律明確規定,責任的認定較容易。由執行機構追加可以強化執行的威懾力,也符合公正與效率的要求。(4)除此之外的情形可以通過審判程序進行追加,也可以通過執行程序進行追加,但通過執行程序的追加應賦予異議人訴權,即申請人和被追加人不服的可以提起訴訟。這樣才能較好地兼顧公正與效率的要求。
裁審標準的確立明確了審執之間的分工,但這種分工只是同一法院審判機構與執行機構之間的分工。由于民事案件管轄制度的存在,追加案件的管轄問題也值得思考。如執行機構正在執行過程中的案件需要通過訴訟程序進行追加,是由同一法院的審判機構處理,還是應當考慮地域管轄、級別管轄等規定而交其他法院處理,需要進一步研究。再如追加兩名以上被執行人,被追加主體之間的責任是連帶責任還是按份責任,是否享有請求分擔和追償的權利等,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不斷探索。這些問題《強制執行法(草案)》中均沒有涉及,制度的完善需要實踐的總結和理論的創新。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問題能夠早日得到解決。
[1]譚秋桂.民事執行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
[2]陳小平.試論被執行人的變更和追加[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59.
[3]孫忠志,范向陽.執行與審判的界限[J].人民司法,2005(9):93.
[4]劉進一.淺析被執行人變更和追加的原理[J].研究生法學,2007(5):56-58.
[5]劉璐.民事強制執行重大疑難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37.
[6]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問題研究[J].法律適用,2008(10):67.
[7]童兆洪,唐學兵.我國民事執行改革實踐演進及理性思考[J].法律適用,2005(6):13.
[8]劉亞萍.變更、追加執行主體的三個問題[J].人民司法,2005(4):85.
[9]盧正敏.臺灣執行當事人適格制度述評及啟示[J].臺灣研究集刊,2008(1):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