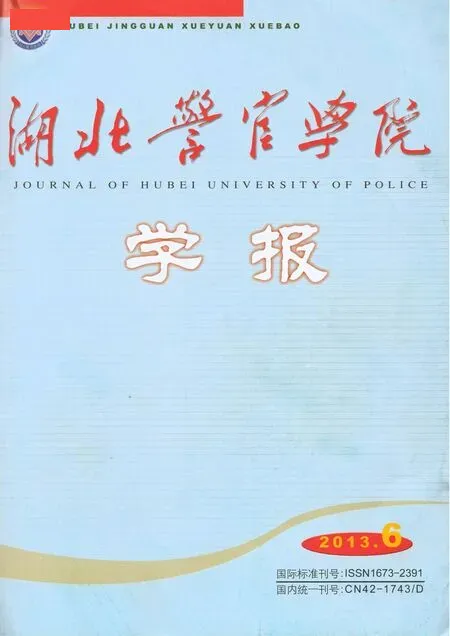瀆職犯罪中“徇私”應(yīng)當(dāng)包括“徇單位之私”
劉昀晟
(中國政法大學(xué) 刑事司法學(xué)院,北京100088)
我國刑法第九章規(guī)定了瀆職犯罪,其中共有十一個條文的罪狀表述使用了“徇私舞弊”,理論界將這些罪名稱為“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關(guān)于“徇私”,可分不同情況:為個人利益而徇私,自然是“徇私”的應(yīng)有之意;為所在單位、集體組織、甚至是特定人員組成的小團(tuán)體利益而徇私,是否屬于“徇私”?對此,刑法理論上與司法實踐中不無紛爭。
一、刑法中“徇私”涵義之紛爭
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jì)要》第六條第(四)項指出:“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yīng)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 (試行)》規(guī)定:“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為牟取本單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節(jié)嚴(yán)重的應(yīng)予立案。”由此看來,對此問題,“兩高”在有關(guān)司法解釋、指導(dǎo)性文件上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最高人民法院認(rèn)為“徇私”僅指徇個人私情、私利,而最高人民檢察院認(rèn)為“徇私”除了包括個人私情、私利,還包括單位之私。
與此同時,理論界也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rèn)為,徇私指的是徇一己之私,僅包括徇個人私情、私利,單位、集體的利益是與私情私利相對應(yīng)的,不屬于私情、私利。[1]很多司法機(jī)關(guān)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采取這種觀點,即對于濫用職權(quán)者沒有謀求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單位甚至是國家利益的情況,大多不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比如,為完成拆遷工作任務(wù),有關(guān)負(fù)責(zé)人將他人的財物強行拉走扣留,此時則不認(rèn)定為濫用職權(quán)罪,更不會被評價為“徇私舞弊”而作為濫用職權(quán)罪的加重情節(jié)處理。
第二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小集體”、“小團(tuán)體”利益肯定說。該說首先否定了“單位之私”可以成為徇私的對象,隨后認(rèn)為除了個人之私以外,“小集體”、“小團(tuán)體”的利益也可以成為徇私對象,并進(jìn)一步論證:(1)“小集體”、“小團(tuán)體”利益是多個特定個人的利益,與單位利益截然不同,本質(zhì)上是個人利益的集合;(2)關(guān)于分支機(jī)構(gòu)的利益、職能部門的利益,可否評價為“徇私”中的“私利”,要分析利益的直接收益是單位還是個人。[2]
第三種觀點認(rèn)為,“徇私”不僅包括徇個人私情、私利,還應(yīng)包括與徇個人私情、私利密切相關(guān)的“徇單位和小團(tuán)體之私”。[3]筆者原則上贊同此觀點,但同時認(rèn)為,在實踐中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小團(tuán)體之私”,所謂“小團(tuán)體之私”應(yīng)歸屬于“單位之私”。所以從嚴(yán)格意義上說,徇私包括“徇個人之私”與“徇單位之私”。
二、“徇私”不限于徇“個人”之私
“徇私”并非僅限于徇“個人私情、私利”,更不可將“私情、私利”與“單位利益”絕對對立,“單位之私”的說法也并非完全不符合邏輯。因為與“私”相對的應(yīng)當(dāng)是“公”,在徇私的犯罪中,“公”是抽象的、不特定的,其真正內(nèi)涵是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正當(dāng)履行職責(zé)所應(yīng)實現(xiàn)的利益、瀆職犯罪所要保護(hù)的法益,并非是與“私人”相對應(yīng)的“單位”。即使是出于單位的利益不正當(dāng)履行公務(wù)職責(zé),“公”的利益同樣得不到實現(xiàn)。將“徇私”解釋為包含“徇單位之私”既不違反邏輯,也不違背“私”的文義。
雖然有學(xué)者認(rèn)為,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fā),“徇私”不應(yīng)包括“徇單位之私”。[4]但筆者認(rèn)為,也難以得出僅限于個人之私的結(jié)論。如果“為了單位利益”也被納入“徇私”,那么刑法第169條規(guī)定的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chǎn)罪,在邏輯上就出現(xiàn)了矛盾,因為既然是為了國家利益,就不存在將“國有資產(chǎn)低價出售”的可能。第169條規(guī)定的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chǎn)罪所保護(hù)的法益是國有公司、企業(yè)財產(chǎn)的國有所有權(quán)和國有資產(chǎn)管理制度,所以只有出于個人利益才能破壞這種國有所有權(quán)的法益。而瀆職犯罪所保護(hù)的法益是“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客觀公正性,以及民眾對該客觀公正性的信賴”。單位之私有悖于公正性的實現(xiàn),將“徇單位之私”解釋為“徇私”的應(yīng)有之義才能起到此條文保護(hù)法益的作用。
這些學(xué)者認(rèn)為,將為徇“單位或者小團(tuán)體”之私而作出的枉法行為納入濫用職權(quán)罪處理,會導(dǎo)致不同種類刑罰之間的不平衡。[5]不可否認(rèn),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徇私枉法行為可以被評價為一種廣義的濫用職權(quán)行為,但又絕非一般的濫用職權(quán)行為,而是性質(zhì)更為惡劣的濫用職權(quán)行為,因此其罪的法定刑應(yīng)高于后者。根據(jù)我國刑法第397條的規(guī)定,濫用職權(quán)罪屬于結(jié)果犯,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濫用職權(quán),并且由于濫用職權(quán)造成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行為人將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與濫用職權(quán)罪不同,徇私枉法罪屬于行為犯,根據(jù)我國刑法第399條的規(guī)定,行為人具有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行為,無論是否造成重大損失,都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見,刑法對徇私枉法罪設(shè)定了相對于一般濫用職權(quán)罪更高的法定刑。如果對行為人出于單位利益而徇私枉法以一般的濫用職權(quán)罪處理,那就必須要求造成重大損失,并且只能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一范圍內(nèi)量刑,這樣的“同罪異罰”嚴(yán)重違背了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
三、“徇私”亦不可等同于徇“小團(tuán)體”、“小集體”之私
至于第二種觀點,雖然認(rèn)識到了除純粹的私人利益之外,還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可以成為“徇私”的應(yīng)有之義,但是“小團(tuán)體”、“小集體”的概念帶來了新的麻煩。多少人、怎樣的組織形式是“小團(tuán)體”、“小集體”?語焉不詳。內(nèi)部職能機(jī)構(gòu)相對于整個單位是“小團(tuán)體”、派出機(jī)構(gòu)相對于上級也算“小集體”,但內(nèi)部職能機(jī)構(gòu)和派出機(jī)構(gòu)又未必不能稱之為“單位”。可見,這樣的概念在實踐中難以準(zhǔn)確區(qū)分。它并非是“單位”和“私人”之間的獨立概念,而是游走于兩者之間的相對概念。也正是基于此,上述第三種觀點表述并不準(zhǔn)確,所謂“小團(tuán)體之私”完全可以屬于“單位之私”。
四、“徇私”包含“單位之私”之合理性和必要性
首先,徇個人之私與徇集體、單位之私對于法益的侵害無異。徇私類瀆職罪所保護(hù)的法益是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履行職務(wù)行為的客觀公正性以及公民對該客觀公正性的信賴。只要基于徇私動機(jī)而進(jìn)行瀆職行為,法益的侵害就是在所難免的,這種法益的侵害實現(xiàn)與否與徇個人之私還是徇單位之私無關(guān)。
其次,“徇私”中的“私”更多應(yīng)該理解為與瀆職犯罪所保護(hù)的法益相對立,而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指代出于“私人利益”的動機(jī)。相對于國家的“公利”而言,任何單位、集體、個人的利益都是實質(zhì)上的“私利”。只要故意違反職務(wù)的公正性,不正確履行公務(wù)職責(zé),就是因“私”廢“公”,就是對瀆職犯罪法益的踐踏。
再次,區(qū)分“單位之私”與“個人之私”不具有實踐性與可行性。即便是主張“徇私”僅指徇“個人之私”的學(xué)者也承認(rèn),個人行為與單位行為、個人利益與單位利益總是存在著直接或間接關(guān)系,實踐中有時很難區(qū)分個人之私和單位之私。[6]更何況在當(dāng)前的社會現(xiàn)實中,單位、集體和小團(tuán)體利益與行為人個人私利總是緊密相連的,個人利益包含于小團(tuán)體、集體之中。個人私利也時常包含于單位利益之中,這是與當(dāng)前的分配體系、任用機(jī)制分不開的。[7]例如,個人工作業(yè)績往往是單位業(yè)績的一部分,而個人對單位業(yè)績的貢獻(xiàn)又成為公務(wù)人員升遷晉級的重要砝碼。正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個人的利益與單位利益不可能涇渭分明、截然分開,這就誘使國家公職人員為了個人利益而謀求單位利益。可見,絕大部分所謂徇“單位”、“集體”之私的,結(jié)局都演化為徇個人之私。因此,若將“單位”、“集體”之私排除在徇私對象之外,必然導(dǎo)致處罰范圍的不當(dāng)縮小。這為行為人逃避法律責(zé)任指明了道路。所以,實踐中,既不存在區(qū)分兩者的必要性,也不存在區(qū)分兩者的可能性。
最后,從刑事政策來看,“徇私”不包括單位之私不符合從嚴(yán)治吏的刑事政策。我國目前對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職務(wù)犯罪采取的是依法“從重從嚴(yán)”的刑事政策。這項政策的依據(jù)是:(1)從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身份來看,他是依照法律從事公務(wù)的人員,應(yīng)當(dāng)比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法律水準(zhǔn)和法律意識,因而在適用法律上,需要從嚴(yán)要求;(2)從國家工作人員的權(quán)利義務(wù)來看,國家將管理國家公共事務(wù)的權(quán)力交給國家工作人員行使,使其享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權(quán)利,根據(jù)權(quán)利義務(wù)相一致的原則,也必然要求其履行更多的義務(wù);(3)從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的危害性來看,其利用職務(wù)便利實施犯罪,知法、執(zhí)法而無視法律,其主觀惡性比普通公民要大;(4)“從防治犯罪的需要來看,要有效地遏制犯罪,就必須提高查處犯罪的概率,增大犯罪的成本和風(fēng)險。可見,狹義說拔高犯罪的成立條件,對于國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予以理解和寬容的做法,無疑嚴(yán)重背離了我國的吏治思想和刑事政策。”[8]這不僅不利于從嚴(yán)治吏,打擊犯罪,而且會嚴(yán)重阻礙中國法治的進(jìn)程。
[1]王作富,劉志遠(yuǎn).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司法適用[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3).
[2]牛克乾,閻芳.試論徇私枉法罪中“徇私”的理解與認(rèn)定[J].政治與法律,2003(3).
[3]敬大力.瀆職罪[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57
[4]賈濟(jì)東.“徇私”應(yīng)包括“徇單位之私”[N].檢察日報,2005-07-12.
[5]黎宏.論徇私枉法罪的若干問題[A].中國刑法學(xué)年會文集(第2卷):實務(wù)問題研究(上冊)[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6:239.
[6]施曉生,陸健輝.從寬嚴(yán)相濟(jì)解讀讀職罪的徇私要件[N].檢察日報,2007-04-03.
[7]李文生.關(guān)于瀆職罪徇私問題的探討[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4).
[8]賈濟(jì)東.瀆職罪構(gòu)成研究[M].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07: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