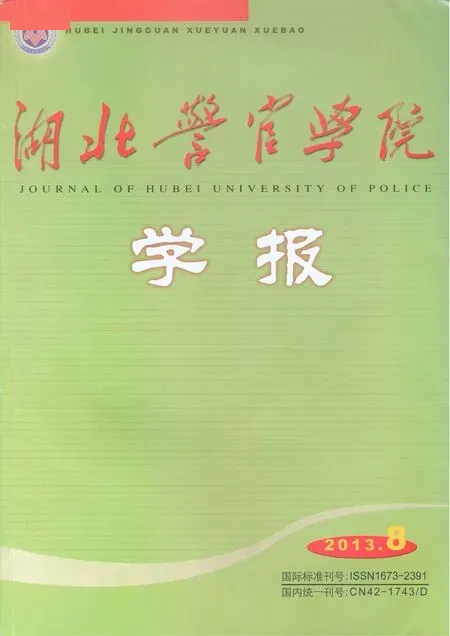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兩個模式
潘正欣,劉兀群
(南京大學 法學院,江蘇 南京210093)
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兩個模式
潘正欣,劉兀群
(南京大學 法學院,江蘇 南京210093)
檢察官“客觀義務”在當今世界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是一個重要概念,通過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歐陸模式和英美模式展開對比考察,進而發現兩者有本質不同。中國屬于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在檢察官制的設計上,必須結合歐陸模式下檢察官客觀義務的特征,以此完善中國的檢察官制。
檢察官;客觀義務;模式
一、引言
檢察官客觀義務是指檢察官為了發現案件真實,不應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而應站在客觀的立場上進行活動,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事實和法律,又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事實和法律,要不偏不倚。[1]狹義的客觀義務是指這一系列已經作為刑事訴訟和檢察的制度和原則,以歐陸模式下的德國、日本為代表;廣義的客觀義務是以客觀性為檢察官履行職務的一般原則,要求檢察官客觀評價案件,公正履行職務,以歐美模式下的美國、英國為代表[2]。
二、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兩個模式
從表面看來,檢察官客觀義務在歐陸和英美都有所體現,不過兩者并不相同,本文擬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歐陸模式和英美模式展開對比分析。
(一)歐陸模式
雖然封建時代的法國已率先設立了國家檢察官制度,但那個時候的檢察官更多的只是“君王的耳目”而已,不具有近代意義上的檢察官制度。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訴訟模式由糾問式向職權主義轉變,偵查、起訴與審判的訴訟職能開始逐漸區分,早期歐陸國家設立了預審法官和審判法官,預審法官負責偵查,審判法官負責審判。在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下,作為“革命之子”,為了防止“肆意專橫”的法官和“警察國家”的夢魘,歐陸諸國設立了專門代表國家公訴的檢察官制,一方面作為“偵查程序的主人”以控制警察權力,另一方面作為“法官裁判之把關者”以限制審判權力的擴張。[3]在此背景下,這種“客觀義務”就由早期糾問式審判中的預審法官轉移至新設的檢察官肩上。檢察官的“客觀義務”由此而成。
在糾問式訴訟模式下,法官居于主導的地位,其有權進行逮捕、訊問、調查及審判。在此訴訟程序中既無原告,又無被告之角色區分,而只有行使調查和審判權的法官以及該職權行使之對象(被糾問者)。同樣,在此模式下偵查與審判二者的訴訟職能高度集中,并無現代意義上的控訴方與審判方的角色區分。因此,在這樣一種糾問式訴訟模式下,承擔“調查”任務以求“發現事實真相”的偵查法官就不得不擔負起“客觀公正”地調查之義務。法諺有云:“辯論是發現事實真相的發動機”,只有存在“兩造對抗”的辯論,才能更全面的發現事實真相。而在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控、辯、審三方訴訟構造的糾問式訴訟模式中,并沒有被告人有效辯護這一“他造對立”,所以為了保證案件的客觀真實和不枉不縱,糾問式下的法官就必須承擔某種“客觀義務”,以保障刑事追訴的正確性。雖然現代國際社會已幾乎普遍廢除這種控審合一的預審法官制度,但是我們在法國刑事訴訟程序中仍然可以看到偵查法官(預審法官)承擔有一定的“客觀公正”義務之端倪:預審法官的作用就是收集所有的證據材料,但是應當做到“公正”。因為預審法官應當“不僅查找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而且還應當查找利于被告人的證據”[4]。
所以,歐陸模式下檢察官的“客觀義務”是與糾問式向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轉變息息相關的,其直接繼承于糾問式的法官,這背后的指導理念則在于保證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案件的客觀真實。
(二)英美模式
比較而言,英美模式下的檢察官“客觀義務”更多地來自于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糾偏。對英美法系歷史傳統中的對抗式訴訟模式來說,訴訟只是一場競技,檢察官只是訴訟當事人一方,而沒有所謂的“客觀義務”。直到進入20世紀前期之后,在純粹當事人主義和極端對抗式的訴訟模式下,擁有國家權力的控訴方和私人辯護方之間實力越來越懸殊,為了防止在形式平等下出現實質不平等,出于“天平向弱者傾斜”的法理,英美模式下的檢察官也開始承擔起部分的“客觀義務”來。如早期英美普通法并沒有證據展示制度,檢察官被允許保留指控被告人的證據和將在審判時出示的大量秘密。直至最近幾十年在正當程序革命之下,證據披露規則才對被告方越來越有利,檢察官必須同時披露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材料[5]。
由此可見,與歐陸模式下檢察官的“客觀義務”直接繼承自糾問式法官的“客觀義務”相比,歐美模式下的檢察官這一義務并非來自于此。
(三)歐陸模式與英美模式之深層差異
歐陸模式下的檢察官所要承擔的客觀義務要比英美模式更多。
如日本井戶田侃教授所稱,在早期日本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其實存在著一個由檢察官、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三者所組成的一個三角形的“訴訟構造”[6],在偵查階段的審前程序構造中,檢察官高居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上,扮演著一種類似法官一樣的裁判者角色,其要在“客觀義務”這一絕對正義的法則下對警察在偵查中的強制處分行為作出審查和裁決。而這種針對審前偵查行為的司法審查在英美模式下是交由法官來裁決的,但在歐陸模式下曾經卻由檢察官以一種背負“客觀義務”的方式作出“客觀”的裁決,可見在歐陸模式下檢察官的“客觀義務”遠非英美模式同日而語。
又如上訴制度,上訴的本來宗旨是救濟提出上訴請求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上訴的內容必須是提出對請求人有利的主張,這被稱為“沒有利益,就沒有上訴”,因此申請不利于被告人的上訴是不合法的。對于歐陸模式下的檢察官來說,其不僅可以提出對被告人不利的上訴,由于要求法院“正確適用法律”因此檢察官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出(對自己不利卻對被告人有利的)上訴也是合法的。相反,被告人不像檢察官那樣負有“正確適用法律”的“客觀義務”,所以不能提出對自己不利的上訴請求。[7]但是在歐美模式下由于獲勝的當事人不能上訴,只有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可以上訴。當然美國只有在例外情況下初步指控被駁回的檢察官才可以提起中間上訴,[8]而英國治安法院中只有“失敗的檢察官”[9]才可以上訴。可見在上訴制度這方面,英美檢察官相比于歐陸的同行來說顯然“客觀義務”較為淡薄。
究其原因,歐陸模式下的檢察官客觀義務與糾問式以及后來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唇齒相依,其一以貫之的宗旨在于為了保證“官方調查活動”的客觀真實。在這里,追求“客觀真實”才是整個檢察官“客觀義務”的本質原因。因為在糾問式以及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一切“官方調查”活動的主導權在控訴方這里,辯護方幾乎不參與審前程序的“真相挖掘”。“辯論是發現事實真相的發動機”這樣的法理并不能在控辯嚴重失衡的糾問式以及職權主義下有所發揮作用的空間,同時將一切客觀真實的義務交由主導庭審的法官一方來進行,顯然不能保證案件的客觀真實,所以才必須由檢察官在公訴的同時承擔一定的“客觀義務”;其不僅是當事人,更需“對被告有利之情況加以調查”。否則,就有違其對“真實性”及公正性之義務。因此,在客觀真實本應由相對的兩造對抗來實現卻無法真正存在“兩造對抗”的時候,自然只能將保障客觀真實的重任交由檢察官這位“法律的守護人”來執行。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糾問式和職權主義下為了保障客觀真實而作的制度安排,其并沒有選擇“兩造對抗”這一制度,而是選擇了“雙司法官”模式,即國家同時擁有原告與法官的權力不變,只是將此兩種權力分由兩個不同的機關來行使。要完成一項有罪判決,必須這兩個機關(檢察院與法院)均認為可罰。[10]換言之,這種保障客觀真實的義務交由法官與檢察官二者共同承擔,檢察官“客觀義務”的“正義”方可實現。
在糾問式及職權主義下,必然要檢察官作為“準司法官”承擔起“客觀義務”,檢察官和法官一起在刑事訴訟的流水線上一同把關,以保障客觀真實和不枉不縱。理解了這一點,就理解了為什么在歐陸模式下,檢察官一方面作為公訴人擔負訴訟一造的同時,另一方面又承擔起不管被告有利無利均應一視同仁予以照顧的“客觀義務”這種矛盾的角色。以此推斷,也就理解了檢察官到底是應為一造當事人還是中立法律守護者,檢察官到底作為行政官還是司法官,檢察一體還是檢察獨立這些圍繞檢察官制爭論了好幾個世紀的根源所在,也就能對“我是誰?”這樣一個困擾所有檢察官的問題有所回答。
相反,英美模式下的檢察官客觀義務來自于對抗式訴訟下“訴訟競技”的糾偏和修正,其理念并不是為了保障案件的客觀真實。英美模式下的刑事訴訟,在司法至上、司法最終裁決和法律保留等原則下,構建起了對整個刑事訴訟尤其是審前程序的司法審查機制。在這樣的司法審查機制中,由于司法至上原則的確立,審判方高居控辯雙方之上,檢察官并不是“站著的法官”,而只是訴訟當事人一方。其承擔的“客觀義務”相對于歐陸模式來說也極為有限,僅僅在證據收集、證據開示等狹小領域。和歐陸模式下的“客觀義務”要求檢察官“積極地”采取各種行為來保障案件的客觀真實和被告人權利不同,英美模式下的“客觀義務”只要求檢察官“消極地”不對被告人采取不利行為和濫用權力追訴即可,用一句英國法學家的話來說就是“控方應當對被指控者謹慎的公平,但不需要唐吉可德式的慷慨”[11]。由于其并沒義務要像歐陸的同行那樣“積極地”采取各種措施和制度(比如檢察官為被告人之利益而上訴)來保障對被告人的客觀中立和司法正義,在本質上歐美模式下的檢察官仍然是追訴之一造。換言之,這種較弱程度的“客觀義務”并沒有讓英美模式下的檢察官訴訟角色有任何根本性的撼動,其仍然是作為訴訟一造之當事人。
三、對中國的啟示
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其實與檢察官應為“獨立自主”之官署抑或“受指令拘束”之機關、實行檢察一體(行政官)抑或檢察獨立(司法官)[12]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深層次司法制度問題有關。未來的檢察官“客觀義務”何去何從必將與這個根本問題息息相關。
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刑事訴訟程序也逐步受到英美法系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英美模式下將檢察官“當事人”化的做法,中國對此或許需要有所保留。我國作為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偏重職權主義模式,并且刑事訴訟追求實質的客觀真實,做到犯罪事實都要“查證屬實”以求“不枉不縱”和“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目的。這些都要求我國的檢察官制在設計上以歐陸模式為基礎,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積極有效地承擔起客觀義務,適當借鑒英美模式的有益制度,從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符合中國刑事訴訟司法實踐的檢察官制。
[1]陳永生.檢察官客觀義務理論的起源與發展[J].人民檢察,2007(1 7).
[2]龍宗智.中國法語境中的檢察官客觀義務[J].法學研究,2009(4). [3]林鈺雄.檢察官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16.
[4][法]貝爾納·布洛克.法國刑事訴訟法[M].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21.
[5][美]愛倫·豪切斯泰勒·斯黛麗,南希·弗蘭克.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M].陳衛東,徐美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 02:368.
[6][日]松本一郎.檢察官的客觀義務[J].法學譯叢,1980(2).
[7][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下卷)[M].張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91-217.
[8][美]愛倫·豪切斯,泰勒·斯黛麗,南希·弗蘭克.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M].陳衛東,徐美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 02:551.
[9][英]約翰·斯普萊克.英國刑事訴訟程序[M].徐美君,楊立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641.
[10][德]克勞思·羅科信.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8-99.
[11][英]約翰·斯普萊克.英國刑事訴訟程序[M].徐美君,楊立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93.
[12]林鈺雄.檢察官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
D926.3
A
1673―2391(2013)08―0154―03
2013-04-15 責任編校:鄭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