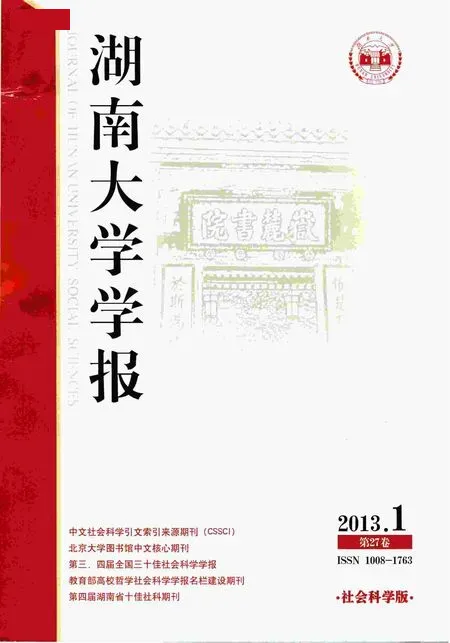皮錫瑞《王制》研究評(píng)析*
吳仰湘
(湖南大學(xué) 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一 清代《王制》研究概況
《王制》是《小戴禮記》的一篇,雖然全文只有四千余字,卻記載了儒家關(guān)于治理國家、管理社會(huì)的各種制度,諸如班爵定祿、封建授田、設(shè)官分職、巡守田獵、朝聘喪祭、國用稅賦、立學(xué)施教、貢士用人、定刑執(zhí)法、養(yǎng)老尊賢等等,內(nèi)容十分廣泛,規(guī)制非常嚴(yán)密,因而被視作“王者之大經(jīng)大法”[1](P309)。早在兩漢時(shí)期,《王制》就大量滲入政治生活,成為今文經(jīng)學(xué)在禮制方面的代表,與《周禮》所代表的古文學(xué)分庭抗禮[2](P159-163)。清代漢學(xué)興盛,三《禮》研究十分發(fā)達(dá),專詳朝章典制與禮樂刑政的《周禮》和《王制》備受重視。《周禮》一直被信為周公政致太平的結(jié)晶,《王制》則被視為孔子立法改制的作品,因此抱著經(jīng)世熱情和改革夢想的清儒,紛紛把目光聚焦到它們上面,其中雖不免有經(jīng)學(xué)今古文的畛域之見與門戶之爭,但“《周禮》與《王制》的重要性儼然是并駕齊驅(qū)的”[3](P34)。雖然清代的《禮記》學(xué)在整體上遠(yuǎn)不如《周禮》學(xué),可是《王制》研究的熱鬧程度,并不遜色于《周禮》研究。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4],清代研究《王制》的專書有談泰《王制里畝算法解》一卷和《王制井田算法解》一卷、耿極《王制管窺》一卷、廖平《王制訂》一卷和《王制集說》一卷、程大璋《王制通論》一卷和《王制義按》三卷等①程大璋兩書出版于民國十九年,但據(jù)卷首鄔慶時(shí)《程先生傳》,兩書應(yīng)成稿于清末。又論者多提到康有為的《王制義證》和《王制偽證》,但兩書實(shí)是擬議而未成之作。,專文則有俞正燮《〈王制〉東田名制解義》、程廷祚《〈王制〉作者考》、黃式三《〈王制〉封國說》、陳壽祺《〈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孫星衍《〈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鄒漢勛《〈王制〉周尺章前解》、許傅霈《〈王制〉周尺考》、章太炎《〈王制〉駁議》、劉師培《〈王制〉篇集證》等數(shù)十篇。在這些研究中,既有訓(xùn)詁名物、辨章學(xué)術(shù)的嚴(yán)謹(jǐn)探討,更多通經(jīng)致用的政治訴求,把《王制》作為經(jīng)世變法、托古改制的理論依據(jù)乃至現(xiàn)成方案。
醉心素王改制、熱望維新變法的晚清今文學(xué)派,是《王制》研究的生力軍。治經(jīng)兼宗今古的俞樾,最早將《王制》與素王學(xué)說直接聯(lián)系起來。《達(dá)齋叢說·王制說》先簡要批評(píng)盧植、鄭玄關(guān)于《王制》成書時(shí)代的說法不足以成立,然后聲稱:“《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他發(fā)現(xiàn)公羊師說多與《王制》符合,由此斷言:“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guī)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俞樾不僅主張以“素王之法”看待《王制》,還提出一條提高《王制》地位的大膽意見:“宋儒于《戴記》中表章《學(xué)》、《庸》二書,愚謂《王制》一篇體大物博,或猶在《中庸》之上乎?”[5]這些說法雖未經(jīng)過嚴(yán)密論證,但后來的今文學(xué)者如廖平、康有為等紛紛加以采取。
廖平對《王制》的研究最多,在提高《王制》的經(jīng)典地位方面貢獻(xiàn)很大。他提出“《王制》統(tǒng)六經(jīng),故今學(xué)皆主之立義”,把《王制》確立為今文經(jīng)學(xué)的核心,直接與以《周禮》為中心的古文經(jīng)學(xué)對立,所謂“以《王制》主今學(xué),《周禮》主古學(xué),先立兩旗幟,然后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建立起內(nèi)部同條共貫、彼此壁壘分明的今古文經(jīng)學(xué)兩大陣營。最特別的是,廖平首倡“以《王制》為經(jīng)”,依經(jīng)、傳、記的層次,對《王制》全文重新加以梳理、排比,撰出《王制訂》,使《王制》得以獨(dú)立成書、自成體系,又約集同人編撰《王制義證》,擬取經(jīng)傳、諸子、緯候及兩漢今學(xué)先師舊說,“務(wù)使詳備,足以統(tǒng)帥今學(xué)諸經(jīng)”[6]。后來刊行的《王制集說》,“凡六經(jīng)、傳、注、師說,依次分纂,以證《王制》”[7],應(yīng)該就是《王制義證》的定稿。康有為也對《王制》極為關(guān)注,稱“《禮記·王制》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經(jīng)緯天人之書,其本末兼該,條理有序,尤傳記之所無也”,因此仿效宋儒從《禮記》中抽取《大學(xué)》自成一書的成法,提出將《王制》獨(dú)立,“使孔子經(jīng)世之學(xué)一旦復(fù)明于天下”[8]。他還一再宣講《王制》的微言大義,為維新變法制造理論依據(jù),為引進(jìn)西方政制尋找歷史資源。
二 皮錫瑞一生《王制》研究述要
在1884年前后成稿的《禮記淺說》中,皮氏有關(guān)《王制》篇的札記共14條,多是指陳鄭注、孔疏在訓(xùn)解與典制方面的失誤。例如“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皮氏指出:“五祀有二說,此注據(jù)《祭法》,《曲禮》注據(jù)《月令》,有戶、灶,無司命、厲。司命為天星,厲為外鬼,似不當(dāng)祭,從《曲禮》注為正。”[9]鄭玄解《曲禮》“五祀”援引《月令》之說,解《王制》“五祀”另用《祭法》之說,皮氏認(rèn)為《王制》中大夫所祭之五祀不應(yīng)有司命、厲,因此指出鄭注不妥。對于“天子使其大夫?yàn)槿O(jiān)”,孔疏引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是以殷制來解《王制》,皮氏卻提出“殷制不可考”,轉(zhuǎn)而據(jù)周制加以彌補(bǔ):“周制,大國有孤一人,三卿,其二命于天子,或即殷制三監(jiān)之遺。《周官》:‘建其牧,立其監(jiān)。’鄭注《儀禮》‘諸公’曰:‘容牧有三監(jiān)。’”[9]
在1892年以來撰作的《經(jīng)訓(xùn)書院自課文》中,皮氏討論《王制》的專門之作有《齊魯二國封地考》、《“小學(xué)在公宮南之左大學(xué)在郊”考》及《“虞庠在國之西郊”當(dāng)作“四郊”考》上下篇,多是針對鄭注而作,既有糾其誤者,也有證其是者。例如,“小學(xué)在公宮南之左,大學(xué)在郊”,鄭注“此小學(xué)、大學(xué),殷之制”,皮氏卻認(rèn)為是“自古以來天子、諸侯之通制”,明言“自鄭君以后,說者多誤”[10](卷三)。又如,鄭玄在“公、侯田方百里”注文中提出周公“益封”說,宋儒多以為疑,皮氏則以為“鄭所云加封公、侯,即指齊、魯二國言之”,據(jù)鄭玄《詩譜》所說,征引《史記·周本紀(j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漢書·地理志》以及《左傳》等資料,證齊、魯確有益封事,并說:“明乎二國有益封之事,則《周禮》、《王制》皆不誤,《孟子》與戴《記》、《史記》、鄭《詩譜》義皆可通。后人不能證明,或以《孟子》、《王制》疑《周禮》,謂古無五百里、四百里之國。案鄭君謂:‘孟子在赧王時(shí),《王制》之作,復(fù)在其后。’是《王制》即本于《孟子》。《周禮》雖未必周公手定,亦當(dāng)出于周末,與《孟子》、《王制》相后先。若周無五百里、四百里之國,何能鑿空立論?若周無益封諸侯之事,鄭亦何能附會(huì)其說?”可見皮氏力證鄭注正確,提出“《周禮》古文說,《王制》今文說,其說多不可通,惟鄭康成能疏通證明之”,表彰鄭玄“能兼疏今古文,皆不背其說”,[10](卷二)并采鄭玄之說,認(rèn)為《王制》本于《孟子》,也不可簡單否定《周禮》。
在1896年撰成的《鄭志疏證》中,皮氏多次論及《王制》,并與《周禮》相提并論,一再指出“《周禮》,古文;《王制》,今文。《周禮》皆周制,《王制》多殷制”,“《周禮》古文說,是周制,《王制》今文說,是殷制”[11](卷四),既強(qiáng)調(diào)《王制》與《周禮》分屬于今、古文,又肯定鄭玄兼通今古的努力。例如,《王制》說三等封國之制,鄭注有一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不得解,鄭玄作了回答,皮氏在疏證鄭玄答詞時(shí),特取《齊魯二國封地考》的研究成果,力主鄭玄益地加封之說確然可信,進(jìn)而指出:“然則《周禮》、《王制》所言封國制度,非不可通。鄭君以斥界、加封之義疏通二書,使各不相背,斯為通識(shí),不得謂其強(qiáng)為傅會(huì)也。”[11](卷六)在疏證鄭玄《答臨孝存〈周禮〉難》時(shí),皮氏更對《王制》的成書時(shí)代及其性質(zhì)作了專門討論。針對盧植所謂漢文帝令博士作《王制》之說,他先援引何焯、丁晏的考證結(jié)論,然后指出:“《王制》無一言及封禪,亦不專說巡狩,非漢文博士作甚明。《王制》一書,多同《孟子》。篇首‘王者之制祿爵’云云,即與孟子答北宮锜大同。據(jù)鄭答臨碩《王制》之作在孟子后,或即孟子弟子所作。”可見他仍是根據(jù)鄭玄之說,提出《王制》“或即孟子弟子所作”。皮氏還依鄭注《王制》多歸諸殷制之說,論述《王制》的性質(zhì):“鄭解《王制》,多以殷制為說,‘《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云云,乃公羊家言。近人謂《王制》即《春秋》立素王之法,王者即謂素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之類,其說有據(jù)。《王制》是殷制,自與《周禮》不同。”[11](附錄)他雖提及俞樾以《王制》為《春秋》素王之法的新說,卻是用來論證鄭玄援據(jù)公羊家言而以殷制解《王制》的做法正確。皮氏主張“《王制》多殷制”、“《王制》是殷制”,全是采信鄭玄之說,以殷制來理解《王制》,可見他對《王制》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尚未根本改觀。
皮氏晚年撰《經(jīng)學(xué)歷史》、《經(jīng)學(xué)通論》,對《王制》作了更多論述,其中引人矚目的有四點(diǎn):
其一,力主《王制》獨(dú)立。皮氏先在《經(jīng)學(xué)歷史》中強(qiáng)調(diào)《王制》在經(jīng)典體系中的獨(dú)特地位:“《王制》一篇,體大物博,與《孟子》、《公羊》多合,用其書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禮》,尤為簡明,治注疏者當(dāng)從此始。”[12]接著在《經(jīng)學(xué)通論》中力主“治經(jīng)者當(dāng)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注疏》”[13](P69),又專作一篇“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yùn)》亦可分篇?jiǎng)e出”,援引歷史上《禮記》各篇獨(dú)立的先例,宣稱“《王制》為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yīng)分篇?jiǎng)e出”[13](P79),提出應(yīng)將《王制》從《禮記》中獨(dú)立出來。
其二,重新考論《王制》的成書時(shí)代及其性質(zhì)。皮氏不僅否定了盧植、孔穎達(dá)的說法,而且質(zhì)疑鄭玄的判斷,辨析說:“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為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13](P68)他以《王制》合于《公羊傳》,不再依孟子推斷《王制》的成書時(shí)代及其作者,轉(zhuǎn)而提出一種新見:
《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guī)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后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fā)前人所未發(fā),雖無漢儒明文可據(jù),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門學(xué)者原本圣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于《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jīng)始有可通之機(jī),《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jīng)者能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13](P69)
他對俞樾之說加以補(bǔ)證,認(rèn)為《王制》必定出于孔門,并揭示出確定《王制》出自圣門對于經(jīng)學(xué)研究的重要意義。他提出《王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這一對《王制》性質(zhì)的判斷,與他原來認(rèn)為“《王制》是殷制”大異。
其三,比較《王制》和《周禮》的異同優(yōu)劣。皮氏在廖平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從區(qū)分今、古文經(jīng)學(xué)的角度,對舉《王制》和《周禮》并加以比較:
《王制》為今文大宗,與《周禮》為古文大宗,兩相對峙(自注: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一是周時(shí)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禮》尊之太過,以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過,以為漢博士作,于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王制》,據(jù)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據(jù)何劭公說,亦出戰(zhàn)國之時(shí)。是其出書先后略同,而為說不同,皆由圣門各據(jù)所聞,著為成書,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xué)者誠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13](P68-69)
皮氏既以《周禮》和《王制》在經(jīng)學(xué)屬性上彼此對峙,又承認(rèn)二者同出圣門,皆是制法以待后世之用,糾正前人對它們尊崇過當(dāng)、貶抑太甚的不當(dāng),不過,“《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一語,流露出他對《王制》和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偏愛。
其四,對《王制》鄭注的態(tài)度沿而未改。皮氏強(qiáng)調(diào)說:“鄭君兼注三《禮》,調(diào)和古、今文兩家說,即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強(qiáng)求通,論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沒也。”他以鄭玄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說”,對前人指責(zé)鄭玄“牽合無據(jù)”加以辯護(hù),稱他“亦非盡無據(jù)也”,進(jìn)而指出:“如鄭說,《周官》、《王制》皆可通矣。”[13](P54)皮氏雖對鄭注牽強(qiáng)附會(huì)、泯滅家法不以為然,對鄭玄在《周禮》和《王制》上顯分軒輊也有所不滿①例如皮錫瑞評(píng)析說:“鄭《駁異義》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君雖不以《王制》為漢博士作,而視《周禮》則顯分軒輊。故或據(jù)《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駁《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禮,而于朝聘直以為晉文霸制,并不以為夏、殷之禮矣。”引見《三禮·通論》,第55頁。,卻對他折衷三《禮》、調(diào)和今古的良苦用心相當(dāng)贊賞。
三 《王制箋》的內(nèi)容要點(diǎn)
皮錫瑞主張《王制》應(yīng)從《禮記》中分篇獨(dú)出,《王制箋》的撰寫使之變成了現(xiàn)實(shí)。《師伏堂日記》丁未年二月初十日載:“閱《王制注疏》,欲改定一過,以《王制》為孔子素王之制,可解周與夏、殷之紛。”皮氏想改定《王制》的鄭注、孔疏,從孔子創(chuàng)立素王之制入手,解決前儒對《王制》所載禮制屬夏、屬殷與屬周的爭論。第二天,皮氏即動(dòng)手工作,“奮志作《王制箋》”,至六月中旬大體完成,八月間再加校正,翌年由思賢書局刊行,成為皮氏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
《王制箋》既是皮氏一生《王制》研究成果的總結(jié),也是他晚年覃精研深、經(jīng)學(xué)思想完成重大轉(zhuǎn)變的體現(xiàn)。他在自序中說:“今據(jù)俞樾說《王制》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鄭君箋《詩》,以毛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jù)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汩亂經(jīng)義。”全書主旨就是闡述《王制》何以是素王之制,圣人如何為后世立法,同時(shí)辨明今、古文家法,對鄭注、孔疏及清儒誤說錯(cuò)解《王制》之處加以指摘,申明《王制》的今文學(xué)特質(zhì)。綜觀全書,其主要內(nèi)容可總括為以下幾個(gè)方面:
其一,對《王制》字句、文本的考證與勘訂。
皮氏對《王制》文句作細(xì)心審校,或自抒新見,或援引成說,彌補(bǔ)前儒闕失,解決不少疑誤。例如,“冢宰制國用”,其職相當(dāng)重要,但鄭注、孔疏均闕略不解,皮氏先以《白虎通》為據(jù),再引陳立《白虎通疏證》之說,指出今文冢宰屬殷制,是大夫,古文冢宰屬周制,是卿,二者完全不同。又如,“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前儒有以“則”字屬下句者,皮氏指出:“經(jīng)云‘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則’,皆以‘則’字絕句。”[14](P19)按《白虎通·考黜》明列九賜之名,其三曰樂則,并說“能和民者賜樂則”,又有一段說:“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足證皮氏之說可信。這是《王制箋》中考證最為精彩的兩例[15]。其他如“虞庠在國之西郊”,皮氏引孫志祖的考證和阮元校勘記之語,認(rèn)為“二說證據(jù)極明,‘西郊’當(dāng)作‘四郊’無疑”,[14](P44)均援據(jù)精確①按,孔疏在解“小學(xué)在公宮南之左,大學(xué)在郊”時(shí),比較殷、周異制,說“周則大學(xué)在國,小學(xué)在四郊,下文具也”,明稱周制小學(xué)在四郊,其所謂下文,即“周人養(yǎng)國老于東膠,養(yǎng)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可見作疏者所據(jù)本正作“虞庠在國之四郊”。。前儒多據(jù)“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一語,判定《王制》成書于漢代,皮氏則認(rèn)為:“‘古者’以下,當(dāng)為漢人之言,禮家附入記中,如《大戴·公冠》篇有孝昭冠辭之比。盧植以為漢博士作,孔疏以為秦、漢之際,以其中有“周尺”云云,當(dāng)在周亡后也。而以此概全經(jīng),則誤矣。”[14](P47)《王制》篇末又詳述“六禮”、“七教”、“八政”之目,明顯是解說經(jīng)文司徒一節(jié),皮氏為此再次提出:“上文云‘司徒修六禮以節(jié)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不云六禮、七教、八政細(xì)數(shù)如何,恐讀者不解,故此復(fù)列細(xì)數(shù)于后。嘗疑‘古者以周尺’以下為后人附記,故此數(shù)節(jié)皆上文所已言而未詳者。當(dāng)時(shí)義本口授,恐后不能盡知,乃更詳言以告后人,如《儀禮》諸篇之有記。此節(jié)尤曉然易見,以上文不詳其目,故列其目以附于末也。”[14](P50)他以《儀禮》各篇有附記、《大戴禮記·公冠》雜有漢昭冠詞相比況,認(rèn)為《王制》篇末數(shù)節(jié)出現(xiàn)秦漢人語和解經(jīng)之詞并不奇怪,不能據(jù)此而懷疑《王制》全篇,言之成理②今天學(xué)術(shù)界討論《王制》成篇時(shí)代,多以“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為界,將《王制》分成前后兩部分,認(rèn)為前一部分為經(jīng)文,后一部分是秦漢人對前面經(jīng)文的解釋。參見王鍔:《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學(xué)刊》2006年1期;《〈禮記〉成書考》,中華書局2007年,第172-178頁。。
其二,對《王制》鄭注錯(cuò)誤的糾正。
皮氏前期已多次指摘鄭注《王制》在訓(xùn)詁與名物方面的失誤,《王制箋》進(jìn)一步對鄭注訓(xùn)釋文字、解說典禮、引述史事等錯(cuò)誤加以糾駁。例如,巡守一節(jié)說“命典禮考時(shí)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鄭注:“同,陰律也。”鄭玄以“同”為名詞,與日、律、禮、樂、制度、衣服平列,全句當(dāng)讀作“命典禮考時(shí)、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皮氏據(jù)孔疏說先儒以“同”為“齊同”,指出“鄭君之前無解為陰律者”,并引《漢書·律歷志》、新莽《量銘》、《東觀漢記》、《白虎通·巡守》、張衡《東京賦》,論證兩漢人皆以“同”為“齊同”,用作動(dòng)詞,明言“鄭君過信《周禮》,茍異先儒,《周禮》雖有‘同律’之文,亦 未 明 言 此 ‘同 律’即 《尚 書》、《王 制》之 ‘同 律’也”[14](P17),辨明鄭玄據(jù)《周禮》而訓(xùn)作“陰律”,是故意立異,且與下“律”字重復(fù),實(shí)不可取。根據(jù)皮氏所論,此句應(yīng)讀作“命典禮考時(shí)、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③孫希旦解曰:“訂其得失謂之考,齊其參差謂之定,一其乖異謂之同,凡此皆所以正其不正也。”可見不以鄭注“陰呂”之說為然。沈嘯寰、王星賢點(diǎn)校此句作“命典禮考時(shí)、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得孫希旦本意(《禮記集解·王制》,第328頁)。朱彬《禮記訓(xùn)纂·王制》仍從鄭注。。又如,司空一節(jié)說“司空執(zhí)度度地”,鄭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鄭玄以《周禮》中作為冬官卿的司空來解說《王制》司空,皮氏則據(jù)《韓詩外傳》、《白虎通·封公侯》、《尚書大傳》所載司空職掌,認(rèn)為此司空依今文經(jīng)說“當(dāng)為三公之司空,不當(dāng)為六卿之司空”,強(qiáng)調(diào)夏、殷官制與《周官》六卿不同,指出“鄭引六卿之司空以解三公之司空,不知名同實(shí)異,蓋于今、古文家法未盡了然”[14](P35)。他以兩漢今古文經(jīng)學(xué)官制不同,論證不能將《周禮》司空與《王制》司空混為一談,舉證十分有力。
其三,對鄭玄不明家法、混淆今古的批評(píng)。
與皮氏此前表彰鄭玄調(diào)和今古截然不同,《王制箋》屢屢指斥鄭注昧于今古家法。他在自序中,即明言鄭玄“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為證,則昧于家法,而自生葛藤”,并指陳鄭玄注解土地、封國、官制、征稅、祀典、學(xué)制等六個(gè)方面的缺失。在具體箋釋《王制》經(jīng)文時(shí),皮氏更隨處辨析鄭玄作注強(qiáng)作解事、淆亂今古家法的錯(cuò)誤。例如,“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一節(jié),鄭注有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皮氏雖然堅(jiān)持齊、魯二國實(shí)有加封之事,證明鄭注有所依據(jù),但對鄭玄和同今古文的做法大加非議:“《周禮》以為公、侯之封有四五百里,周初亦非全無其事,惟辭不別白,以為通制,則與《孟子》不合,亦與事實(shí)全乖。鄭引《周禮》以解《王制》,和同今、古文說,因齊、魯有加封之事,欲以概之九州。案《周禮》一書,何休以為六國人作,蓋亦當(dāng)時(shí)有志之士采摭周法,參以己見,定為一代之制,竊比素王改制之意。而封國大小全然不同,蓋以周初本有四五百里之封,遂欲定為通制。后人不知二書皆出周末,于《周禮》則推而上之,以為周公所為;于《王制》則抑而下之,以為漢儒所作。或據(jù)《王制》、《孟子》駁《周禮》,或據(jù)《周禮》駁《王制》、《孟子》,徒滋聚訟,未有折衷。以鄭君之明,而于二書未觀其通,強(qiáng)欲調(diào)停,多乖事實(shí)。”[14](P3)又如,“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一節(jié),鄭注備舉歷代朝聘之法:“此大聘與朝,晉文覇時(shí)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wèi)、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shù)來朝。”孔疏又引《左傳》昭三年文,解說鄭注“晉文覇時(shí)所制”。皮氏根據(jù)何休《公羊解詁》、許慎《五經(jīng)異義》及鄭玄《駁五經(jīng)異義》所說朝聘制度,從解經(jīng)是否遵守家法加以評(píng)析:“何氏不引《周官》、《左傳》以解《公羊》,具見家法之嚴(yán)。許、鄭雜引今、古文以解經(jīng)。許以《公羊》說為虞、夏制,與群后四朝不合,以《左氏》說為周禮,亦無明文可證。鄭據(jù)《周禮》以疑《王制》,斷為文、襄之制。《王制》作于周、秦之際,其時(shí)《左傳》未出,未必是據(jù)《左傳》,且公羊家必不用《左氏傳》,此當(dāng)各從家法解之。經(jīng)云大、小聘與朝,或是本于殷、周,或是損益殷、周之制,素王立法,不當(dāng)以不合《周官》疑之。”[14](P16)
其四,對《王制》作者及性質(zhì)的論證與闡發(fā)。
皮氏在箋釋《王制》首句“王者之制祿、爵”時(shí),詳論說:
此經(jīng)所謂“王者”,謂為后世王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者也。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后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實(shí)亦斟酌四代虞、夏、商、周,與答顏淵問為邦兼取夏時(shí)、殷輅、周冕、《韶舞》相類。《王制》即素王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鄭君見其與《周禮》不合,別之為夏、殷禮。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采夏、殷,然既已經(jīng)孔子損益,定為一王之法,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鄭君未曙于此,故雖極力彌縫,猶多參差不合。孔疏專申鄭義,亦苦同異紛紜。后儒多信盧植之言,以為漢博士所定一代之制。不知《王制》體大物博,用其書可以治天下,非漢博士所能作也。鄭君以為在孟子后,蓋以其與《孟子》多合,似出孟子之徒。考《王制》一書與《孟子》大同小異,當(dāng)是作此書者與孟子各記所聞,未見其必出于孟子后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王朝連天子言之,以子、男合為一,故凡五等;侯國連君言之,故凡六等。此經(jīng)王朝不連天子,以子、男分為二,故凡五等;侯國不連君,故亦五等。《孟子》之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明天位與共之義,當(dāng)與臣下同分勞。此經(jīng)之不連天子與君言者,所以見人君獨(dú)立之尊,初非臣下所敢并。此其立意與《孟子》稍不同者,足見此書非盡出孟子矣。[14](P1-2)
此處要論有二:第一,強(qiáng)調(diào)《王制》中的“王者”并非三代舊王,而是后世新王,認(rèn)為孔子創(chuàng)立素王新制,原是留待后世之王取法,明確主張《王制》出自孔子之手,并對盧植所說《王制》出于西漢博士、鄭玄認(rèn)為《王制》似出孟子之徒的說法作了否定。第二,強(qiáng)調(diào)孔子并非“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而是斟酌四代,對虞、夏、商三代之禮加以損益,對文、武、周公之制也有所取舍,所以《王制》作為一代新法,既不合于《周禮》,也非三代舊制。《王制》為孔子所定“素王新制”,從此成為《王制箋》全書主意,皮氏在以下箋釋中,始終依循此論,對《王制》本文進(jìn)行疏解,力證《王制》與《春秋》及漢代今文家說相合,闡發(fā)孔子創(chuàng)法立制之義。
為進(jìn)一步論證《王制》是孔子所定素王之制,皮氏從群經(jīng)、傳記、諸子和兩漢史書中尋覓材料,特別是引用《公羊傳》、《穀梁傳》、《孟子》、《荀子》,以及兩漢今文經(jīng)師之說如《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鹽鐵論》、《白虎通》、《論衡》、《五經(jīng)異義》等,以《王制》所說與之相通或相近,證明《王制》確屬今文經(jīng)學(xué),必是素王定制。例如,“千里之外設(shè)方伯”一節(jié),皮氏根據(jù)《白虎通》與《公羊傳》同引《王制》此文,認(rèn)為:“據(jù)此,足征《王制》與《春秋》相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14](P8-9)。又如,朝聘一節(jié)說“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孔疏引《駁五經(jīng)異義》所載《公羊》說相同,皮氏因此說:“《公羊》說與《王制》正同,此《王制》為素王定制之一證。”[14](P15)皮氏還經(jīng)常從鄭注、孔疏中覓取證據(jù),如“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段,孔疏引鄭玄《釋廢疾》說:“孔子雖有圣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后王。”皮氏據(jù)此提出:“鄭《釋廢疾》足征孔子改法實(shí)有其事。《公羊春秋》三時(shí)田,為孔子所改之法,則《王制》三時(shí)田與《公羊》合者,亦當(dāng)為孔子所改之法明矣。”他又據(jù)何休《公羊解詁》之說,認(rèn)為“古本四時(shí)皆田,孔子作《春秋》,以夏乃長養(yǎng)之時(shí),恐傷害幼穉,故為后王立法,夏不田,止用三時(shí)田”,進(jìn)一步論述孔子立法救時(shí)之義[14](P23)。在《王制箋后序》中,皮氏還專門討論《荀子·王制篇》與《禮記·王制》在文字與思想方面相互吻合的詳情,對《王制》的成書問題作了補(bǔ)充論述:
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賢所記,當(dāng)時(shí)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jīng)條理之密,則此經(jīng)必有所授,以為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為漢博士作,不亦遠(yuǎn)乎?
皮氏通過揭示《孟子》、《荀子》與《王制》的差異,強(qiáng)調(diào)孟、荀兩大賢猶未盡得《王制》精髓,西漢博士自然不能有此大作,重申“此經(jīng)必有所授,以為素王之制,似可無疑”。
為突出《王制》是素王所定新制,皮氏又在書中多次比較《周禮》、《王制》的優(yōu)劣高下。他在自序中說:“《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表面上對《周禮》、《王制》平等相視,事實(shí)上對《王制》信愛有加。例如,“天子,百里之內(nèi)以共官,千里之內(nèi)以為御”,鄭注“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孔疏:“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此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皮氏批評(píng)說:“口率出泉是漢法,貢禹以為古所無有,而《周禮》先有之,故漢人以為末世瀆亂不驗(yàn)之書。《王制》為孔子所定,必?zé)o此等弊法。”[14](P8)又如,《王制》規(guī)定“公家不畜刑人”,《周禮》則完全相反,皮氏以《禮記·曲禮》、《公羊傳》及何氏解詁、《白虎通·五刑》、《鹽鐵論·周秦》或徑引《王制》,或持論相同,因此認(rèn)為:“漢五經(jīng)今文說皆如是。蓋素王改制,因吳子近刑人致禍,乃有不畜刑人之戒,以視《周官》多設(shè)內(nèi)官,啟后世奄人之患者,所慮為深遠(yuǎn)矣。”[14](P14)
皮氏在論證《王制》確屬素王新制的同時(shí),還反復(fù)闡述孔子創(chuàng)法立制以救時(shí)弊、垂后世的良苦用心,彰顯《王制》中的良法美意。例如,在箋釋“諸侯之下士視上農(nóng)夫,祿足以代其耕也”時(shí),他寫道:“祿以代耕,非止下士,自‘君,十卿祿’以及‘庶人在官’,皆有代耕之義,《孟子》所謂治人者食于人也。明乎此義,則君祿亦有限制,不得以一國為己私;吏胥之祿亦無贏余,但可與農(nóng)人同糊口。君不以一國為己私,則不濫用國帑;吏胥與農(nóng)人同糊口,則不欺壓平民。此古義之最善者。”[14](P4)皮氏認(rèn)為,限制國君之祿可避免君主視一國為私產(chǎn),控制吏胥之祿可防止官吏欺壓平民,要求統(tǒng)治者以天下為公、愛護(hù)民眾,實(shí)際上是用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來詮釋中國古代經(jīng)典。對于《王制》興學(xué)立教的規(guī)定,皮氏認(rèn)為“其制最善,皆后世所當(dāng)效法者”[14](P38)。正因?yàn)槠な舷嘈拧锻踔啤肥强鬃訛楹笫谰膭?chuàng)設(shè)的良法美制,所以他特意加以箋證,如自序所說:“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于郢書治國乎?”可見皮氏全力發(fā)明素王新制,是希望能夠措之于現(xiàn)實(shí),改制變法,迎來王道蕩蕩的太平盛世。
四 《王制箋》的成就與不足
《王制箋》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主要在對《王制》中所謂“素王之制”作了最為充分的論證和闡發(fā)。自俞樾首倡《王制》為孔門素王改制立法之作,廖平、康有為等均取信其說。皮氏受俞樾影響自不例外,乃至在《王制箋自序》中宣稱“今據(jù)俞樾說《王制》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似將全書奠基于俞樾新論之上,后來章太炎批駁《王制箋》,就先否定俞樾之說,稱“先師俞君以為素王制法,蓋率爾不考之言,皮錫瑞信是說,為《王制箋》”[16],試圖從根本上動(dòng)搖皮氏之箋。胡玉縉作《王制箋》提要,也先指出“是編以《王制》為素王之制,據(jù)俞樾說”,并以俞樾之論不可信據(jù),批評(píng)“皮氏是箋,毋乃過信”[15]。其實(shí),《王制箋》并未全部立足于俞樾說,而自有其立論的基礎(chǔ)。在箋釋《王制》開篇“王者之制”時(shí),皮氏就鮮明地提出:“此經(jīng)所謂王者,謂為后世王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者也。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后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徒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實(shí)亦斟酌四代虞、夏、商、周,與答顏淵問為邦兼取夏時(shí)、殷輅、周冕、《韶舞》相類。”[14](P1-2)他強(qiáng)調(diào)孔子并非僅從周文返回殷質(zhì),而是斟酌四代,創(chuàng)立素王新法。而細(xì)察俞樾《王制說》,是“以公羊師說求之《王制》,往往符合”,又以鄭注《王制》常指其中某制為殷制,遂依公羊家說“《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得出《王制》為素王之制的結(jié)論。兩相比較,皮氏對《王制》素王之制的界定,與俞樾有明顯差異。皮氏評(píng)論鄭玄說:“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則已知《王制》之出于孔門,又以《王制》為多殷制,引‘《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則已知《王制》之通于《春秋》,特未明言為素王之制耳。”[14](P1)指出鄭玄雖知《王制》出于孔門且通于《春秋》,但不知孔子損益四代自創(chuàng)一王新法,所以未能識(shí)別《王制》作為素王之制的真實(shí)面目。依皮氏所說,從認(rèn)同《王制》通于《公羊春秋》,到確認(rèn)《王制》為素王新制,其中尚有一間需達(dá)。俞樾雖明言《王制》為素王之制,但與鄭玄一樣有一間未達(dá),所以皮氏雖援引俞樾之論,但只評(píng)價(jià)“俞說近是”,有所保留,并非完全信據(jù)①皮錫瑞在《經(jīng)學(xué)通論》中引錄俞樾《王制說》要點(diǎn)后評(píng)曰:“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fā)前人所未發(fā),雖無漢儒明文可據(jù),證以《公羊》、《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門學(xué)者原本圣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可見對俞樾說完全信服,與《王制箋》同引俞樾此說而僅評(píng)曰“俞說近是”顯然有異,但今日研究者尚未覺察到這一點(diǎn)。。章太炎、胡玉縉認(rèn)為皮氏完全采信俞樾說而作《王制箋》,實(shí)未細(xì)審皮、俞持論之異②按,俞樾謂《王制》為孔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皮錫瑞卻主張《王制》出自孔子本人。。概言之,對于以素王之制說《王制》,俞樾有椎輪肇始之功,廖平、康有為有繼起奮進(jìn)之力,皮錫瑞最后集其大成。晚清從今文學(xué)立場研究《王制》的著述雖然較多,要以《王制箋》成就最高。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檢視清代《禮記》研究成績時(shí)稱:“《禮記》單篇?jiǎng)e行之解釋,有皮鹿門錫瑞之《王制箋》,康長素有為之《禮運(yùn)注》,劉古愚光蕡之《學(xué)記臆解》,各有所新發(fā)明。”將《王制箋》列居清代《禮記》單篇?jiǎng)e出研究作品之首,確有學(xué)術(shù)史的眼光。
《王制箋》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集中體現(xiàn)在對《王制》鄭注的批評(píng)上。清儒對《王制》兼采前代、不純用古法而自成一代之典的特點(diǎn)有著相近的認(rèn)識(shí),因此對鄭注以《周禮》解說《王制》紛紛加以指謫。例如乾隆時(shí)期《禮記》研究大師孫希旦說:“漢人采輯古制,蓋將自為一代之典,其所采以周制為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為損益不純用古法者。鄭氏見其與《周禮》不盡合,悉目為夏、殷之制,誤矣。”[1]又如嘉道時(shí)期的朱彬,在《禮記訓(xùn)纂》中引王懋竑之說進(jìn)行批評(píng):“《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時(shí)去先秦未遠(yuǎn),老師宿儒猶有一二存者,皆采取六經(jīng)、諸子之言,如班爵祿取之《孟子》,巡狩取之《虞書》,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取之《公羊》,諸侯朝聘取之《左氏》。古書今不可盡見,蓋皆有所本也。惟《周官》未出,故所言絕不同。注家多以《周禮》證之,宜其乖戾而不合也。”[17]再如晚清著有《禮記質(zhì)疑》的郭嵩燾,在論《王制》“次國之上卿當(dāng)大國之中”一段鄭注時(shí)指出:“《王制》自引《左氏》之文,以明三卿之等視國大小為差,不必專為聘會(huì)言之。注家必以此求合《周禮》,固無當(dāng)也。”又在論“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一段鄭注時(shí)說:“王者建中定制,略示大法而已。鄭注通九州五服之?dāng)?shù)以求合《周禮》,遂據(jù)此以為殷制,亦稍泥矣。”[18]可見,批評(píng)鄭注《王制》牽合《周禮》而膠執(zhí)鮮通,在清儒中幾近共識(shí)。皮氏確信《王制》為素王之制,為糾摘鄭注設(shè)置了一個(gè)更為明晰的參照。他分析說:“《王制》即素王之制,其中損益周制,或取或否。鄭君見其與《周禮》不合,別之為夏、殷禮。孔子斟酌四代,未嘗不采夏、殷,然既已經(jīng)孔子損益,定為一王之法,則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矣。鄭君未曙于此,故雖極力彌縫,猶多參差不合。”[14](P2)皮氏指出鄭玄不識(shí)素王新制,援依《周禮》解說《王制》,遇有不合之處,就歸為夏、殷之制,因此牽強(qiáng)附會(huì),勞而無功。《王制箋》對鄭注錯(cuò)誤的糾駁并非全部正確,但在皮氏“素王新制”說的燭照下,鄭注《王制》淆亂三代禮制的闕失顯露無遺。他還提出:“禮家記載各異,有夏、殷禮,有周禮,有周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王制》損益三代,故或從周,或從夏、殷”[14](P31),“《王制》損益三代,而不盡與夏、殷同,與周有合有不合”[14](P11),因此后人解說《王制》,不能局限于其中一代之制,尤其不能牽引《周禮》強(qiáng)說《王制》。皮氏在箋釋中還提出一條原則性的意見:“據(jù)《周禮》之合者證明此書,可也;據(jù)《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書,非也。”[14](P11)此說不僅可以用來指導(dǎo)《王制》研究,對于整個(gè)三《禮》研究也有理論參考價(jià)值,所以胡玉縉稱譽(yù)此說“實(shí)為通人之論”[15]。現(xiàn)代著名學(xué)者呂思勉在論《王制》時(shí),提出:“孔子作六經(jīng),損益前代之法,以成一王之制,本不專取一代,故經(jīng)傳所說制度,與《周官》等書述一代之制者,不能盡符。必知孔子所定之制與歷代舊制判然二物,乃可以讀諸經(jīng)。若如鄭注,凡制度與《周官》不合者,即強(qiáng)指為夏、殷,以資調(diào)停,則愈善附會(huì)而愈不可通矣。細(xì)看此篇注疏,便知鄭氏牽合今古文之誤。此自治學(xué)之法當(dāng)然,非有門戶之見也。”[19](P53)皮氏力主各依家法解經(jīng),《王制箋》對鄭玄注解的批評(píng),正可借用此說加以評(píng)定。
當(dāng)然,《王制箋》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乃至嚴(yán)重的缺失[15]。皮氏既堅(jiān)持認(rèn)為《王制》是孔子所定素王之制,又不無模糊地說“《王制》出于孔門”,又說“此書非盡出于孟子”,還肯定“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后,當(dāng)?shù)闷鋵?shí)”,均涉游移。關(guān)于《王制》的形成時(shí)代,本已聚訟千古,清儒窮究而迄無定論,《王制》的著作之人,更已無從稽考,而皮氏從改制變法的時(shí)代需要出發(fā),將它從歷來認(rèn)為是西漢博士應(yīng)詔抄撮之作,抬升為孔子素王變法改制之作,并與《周禮》立異對峙。但是,這一充滿激情同時(shí)不無臆斷的舉動(dòng),不僅減損《王制箋》的學(xué)術(shù)品質(zhì),也激起古文家的反感和批駁,乃至最終拖累《王制》。章太炎正是不能認(rèn)同晚清公羊家“以經(jīng)術(shù)作政術(shù)”的行為,對《王制箋》大加訾議,連同《王制》一并詆毀:“《王制》者,博士鈔撮應(yīng)詔之書,素非欲見之行事。今謂孔子制之,為后世法,內(nèi)則教人曠官,外則教人割地,此蓋管、晏之所羞稱,賈捐之所不欲棄,桑維翰、秦檜所不敢公言,誰謂上圣而制此哉!”①章太炎:《駁皮錫瑞三書·王制駁議》,《國粹學(xué)報(bào)》1910年第3號(hào)。對章太炎之說,劉小楓在《〈王制〉與大立法者之德——〈王制箋校箋〉序》中有一個(gè)極好的評(píng)論:“糾纏于考據(jù),有的時(shí)候也會(huì)丟失大體。無論是否孔子所作,總歸是個(gè)了不起的大圣人(西洋說法稱‘大立法者’)所作——對我們今人來說,重要的是得領(lǐng)會(huì)《王制》作者的用心(確切些說,苦心孤詣)。章太炎否認(rèn)的與其說是《王制》的作者,不如說是《王制》的品位。”引見王錦民《王制箋校箋》,華夏出版社2006年,“序”第7頁。其實(shí),皮氏等晚清今文學(xué)家想肯定《王制》對后世變革政制的價(jià)值,并無必要將它指為孔子所定素王之制。這是在尊孔崇經(jīng)觀念影響下,推崇《王制》太過,情感勝過了理智。楊向奎提及“《王制箋》中多斥《周官》而主《王制》的議論”,由此評(píng)說清代今文學(xué)家的得失:“今文家說《周官》有是處,有不是處。是處是否定其為周公書,而以為出于六國時(shí),因而有六國制度摻雜其間。不是處是否定《周官》中有宗周之政典。實(shí)際《周官》一書有宗周時(shí)代之典章制度,亦有戰(zhàn)國時(shí)代的政典及編纂者的理想在內(nèi)。《王制》則多理想制度,以為王者之制理應(yīng)如此云云。就此而論,說《王制》為后王改制書,但不必出于孔子,更不應(yīng)有素王說。”[20](P45)認(rèn)同將《王制》說成是儒家圣賢改制之作,但不必歸于孔子本人或倡導(dǎo)素王改制之說,這一公允、持平之論,用來評(píng)判《王制箋》的得失可謂貼切②較多接受清代今文學(xué)思想的民國學(xué)者張爾田,就提出一種經(jīng)過修正的說法:“《王制》是漢時(shí)博士所作,大抵皆孔子門徒共撰所聞,后人通儒各有損益,圣人定禮之口說幸而獲存者也。”引見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頁。。胡玉縉論《王制箋》說:“其書義據(jù)閎深,條例明晰,雖屬一偏之說,要自不可廢也。”[15]皮氏的一偏之處,不在張揚(yáng)《王制》意美法良,而在鼓吹孔子素王。
五 結(jié) 語
乾嘉學(xué)者尤其晚清今文學(xué)家重視《王制》,皮錫瑞在廣泛吸取前人的考證成果與思想學(xué)說的基礎(chǔ)上,對《王制》的文字訓(xùn)詁與名物典制、《王制》鄭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書時(shí)代及其性質(zhì)、《王制》與《周禮》的異同優(yōu)劣等問題作了反復(fù)探討,最后撰成《王制箋》一書,將清代的《王制》研究推進(jìn)到一個(gè)新的高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皮錫瑞一生經(jīng)學(xué)立場的改變,他的《王制》研究表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他壯年研讀《王制》注疏,是在古文經(jīng)學(xué)的范圍內(nèi)力糾鄭注、孔疏的缺失。中年執(zhí)教南昌經(jīng)訓(xùn)書院后,他治經(jīng)兼宗今古,所以轉(zhuǎn)而從今、古文相分來審視《王制》、《周禮》,一再表彰鄭注調(diào)和今、古,甚至提出《王制》與《周禮》可以相通。及至晚年,他逐漸轉(zhuǎn)向今文經(jīng)學(xué),專以公羊?qū)W家的眼光看待《王制》,批評(píng)鄭注不明素王新制、淆亂今古家法,并將《王制》與《周禮》顯分軒輊。對于《王制》的成書問題,他先是依據(jù)鄭玄之說,相繼提出《王制》“即本于《孟子》”、“或即孟子弟子所作”;后來轉(zhuǎn)采俞樾之論,認(rèn)為《王制》出自孔門;最后再對俞樾之說加以修正,主張《王制》出于孔圣,尊之為經(jīng)。關(guān)于《王制》的性質(zhì),皮氏先是采信鄭注,認(rèn)為“《王制》多殷制”、“《王制》是殷制”;后來改稱《王制》是圣門學(xué)者所定一王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最后提出《王制》是孔子所立一王之法,“是素王新制,非夏、殷舊制”。因此,通過檢視皮氏《王制》研究及其對待鄭注的態(tài)度,可以相當(dāng)清晰地看出他從專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獨(dú)尊今文的治經(jīng)歷程。而縱觀清代學(xué)界對《王制》的研究,也有一個(gè)從拘守古文到兼治今古再到崇信今文的歷程。由此也可以說,皮錫瑞的《王制》研究,正是清代經(jīng)學(xué)演進(jìn)的一個(gè)縮影。
[1]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 華有根.西漢禮學(xué)新探[M].上海: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8.
[3] 高明.禮學(xué)新探[M].臺(tái)北:學(xué)生書局,1978.
[4]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
[5] (清)俞樾.九九消夏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5.
[6] (清)廖平.廖平選集上冊[M].成都:巴蜀書社,1998.
[7] (清)廖平.廖平選集下冊[M].成都:巴蜀書社,1998.
[8] (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二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
[9] (清)皮錫瑞.禮記淺說(卷上).[M].長沙:思賢書局,1899.
[10](清)皮錫瑞.經(jīng)訓(xùn)書院自課文[C].善化師伏堂,1895.
[11](清)皮錫瑞.鄭志疏證[M].長沙:思賢書局,1899.
[12](清)皮錫瑞.經(jīng)學(xué)歷史[M].長沙:思賢書局,1906.
[13](清)皮錫瑞.三禮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4.
[14](清)皮錫瑞.王制箋[M].長沙:思賢書局,1908.
[15]胡玉縉.王制箋提要[A].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jīng)部)[C].北京:中華書局,1996.
[16](清)章太炎.駁皮錫瑞三書[J].國粹學(xué)報(bào),1910(3).
[17](清)朱彬.禮記訓(xùn)纂[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8](清)郭嵩燾.禮記質(zhì)疑[M].長沙:岳麓書社,1992.
[19]呂思勉.經(jīng)子解題[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5.
[20]楊向奎.楊向奎學(xué)術(shù)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