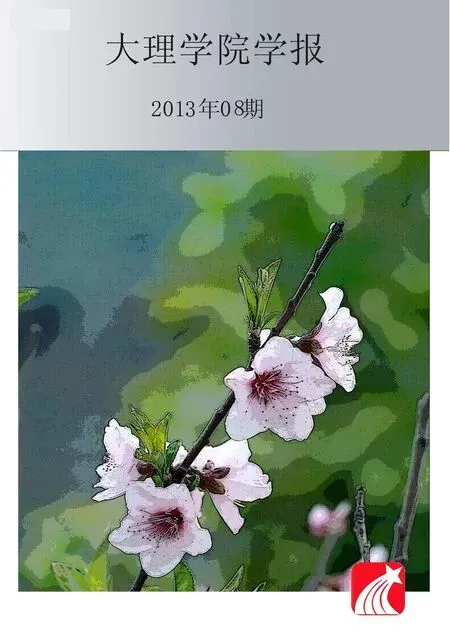自由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基石
趙映香
(大理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云南大理 671003)
一、誰(shuí)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真正主體
毋庸置疑,人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主體或主詞。比如在“人是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動(dòng)物”這一判斷中,內(nèi)涵著兩個(gè)結(jié)構(gòu):一個(gè)是橫向的主謂結(jié)構(gòu),在此結(jié)構(gòu)中,“人”是相對(duì)主詞(說(shuō)它相對(duì)是因?yàn)樗€可以做謂詞,比如“張三是人”,而主詞“張三”是絕對(duì)主詞,因?yàn)樗豢梢栽僮鲋^詞,即我們不能說(shuō)“這是張三”“那是張三”等,除非“張三”是在同名異義上使用),“創(chuàng)新性的”“動(dòng)物”是謂詞,系詞“是”把二者連接了起來(lái)。一個(gè)是縱向的意指結(jié)構(gòu),在此結(jié)構(gòu)中,主詞“人”意指著人這個(gè)主體或?qū)伲约胺褐钢T如“張三”等眾多的個(gè)別對(duì)象。但由于“人”是一個(gè)普遍實(shí)體詞,對(duì)任何普遍實(shí)體詞都可以通過(guò)引入不同的屬性作為標(biāo)準(zhǔn),然后把它們劃分為抽象性程度不同的普遍實(shí)體詞。顯然,劃完或劃出“人”這個(gè)種所包含的各層級(jí)的屬不是本文的任務(wù),本文的任務(wù)或目的是緊跟本文主旨對(duì)其作一個(gè)示范性的劃分。
比如若引入屬性詞“生活領(lǐng)域”,則“人”可以分為“經(jīng)濟(jì)人”“政治人”和“文化人”。因?yàn)槲覀兛梢哉f(shuō)“經(jīng)濟(jì)人是人”“政治人是人”和“文化人是人”。以上是對(duì)“人”這個(gè)普遍實(shí)體種詞所作的劃分,我們還可以對(duì)人所包含的屬,即對(duì)“文化人”“經(jīng)濟(jì)人”和“政治人”再作劃分,通過(guò)劃分得到更低的屬。當(dāng)然,劃分標(biāo)準(zhǔn)要始終如一,比如若再引入屬性詞“高校領(lǐng)域”,則“文化人”可以分為“辦學(xué)者”“治學(xué)者”“大學(xué)生”。因?yàn)槲覀兛梢哉f(shuō)“辦學(xué)者是文化人”“治學(xué)者是文化人”“大學(xué)生是文化人”。
以上劃分所得的“文化人”“辦學(xué)者”“治學(xué)者”“大學(xué)生”相對(duì)于“人”這個(gè)種詞來(lái)說(shuō),是普遍性和抽象性相對(duì)更低的實(shí)體屬詞,但終究不是絕對(duì)主詞或個(gè)別詞。它們的意義或價(jià)值在于最終用來(lái)述謂個(gè)別詞或絕對(duì)主詞,如“張三”“李四”等,即做個(gè)別實(shí)體詞的謂詞,所以,個(gè)別實(shí)體詞所意指的個(gè)別對(duì)象是所有普遍實(shí)在意義的歸宿。比如我們可以說(shuō)“張三是大學(xué)生”“大學(xué)生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李四是辦學(xué)者”“辦學(xué)者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王五是治學(xué)者”“治學(xué)者是文化人”“文化人是人”。它們之間是包含與被包含的同質(zhì)性關(guān)系。當(dāng)然,不同屬種系列之間是異質(zhì)性的關(guān)系。
綜上所述,雖然人、文化人、辦學(xué)者、治學(xué)者、大學(xué)生、張三等都可以充當(dāng)文化創(chuàng)新的主體,但人、文化人、辦學(xué)者、治學(xué)者、大學(xué)生都是相對(duì)主詞,它們的區(qū)別僅在于其普遍性和抽象性程度的不同。所以,文化創(chuàng)新的真正主體是高校領(lǐng)域中的一個(gè)個(gè)具體的只做主詞不做謂詞的諸如“張三”“李四”“王五”等。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shuō):“實(shí)體(substance),就其最真正的(truest)、第一性的(primary)、最確切的意義而言(most definite of the word),乃是那既不可用來(lái)述說(shuō)一個(gè)主體又不存在于一個(gè)主體里面的東西,例如某一個(gè)個(gè)別的人或某匹馬(individual man or horse)。但是在第二性的意義(secondary sense)之下作為屬(species)而包含著第一性實(shí)體(primary substances)的那些東西也稱為實(shí)體(substances);還有那些作為種(genera)而包含著屬(species)的東西也被稱為實(shí)體。例如個(gè)別的人是被包含在‘人’這個(gè)屬里面的,而‘動(dòng)物’又是這個(gè)屬所隸屬的種;因此這些東西——就是說(shuō)‘人’這個(gè)屬和‘動(dòng)物’這個(gè)種——就被稱為第二實(shí)體(secondary substances)”〔1〕(括號(hào)中的英文摘自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edited by Richard McKeon,The modern library,2001:9)。
二、文化創(chuàng)新的主體應(yīng)該是自由的
確立了一個(gè)個(gè)具體的張三、李四、王五等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真正主體后,接下來(lái)要回答的問(wèn)題是:張三、李四、王五等作為文化創(chuàng)新的真正主體應(yīng)該是怎樣的?問(wèn)題簡(jiǎn)言之就是:主體應(yīng)該是怎樣的?本文的答案是:主體應(yīng)該是自由的。很顯然,答案是不證自明的。因?yàn)槿绻粋€(gè)個(gè)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張三、李四、王五等是不自由的話,那么就意味著他們是受束縛的、被強(qiáng)迫的、被越俎代庖的,即他們?cè)谖幕I(lǐng)域不能自由地思和做(“自由:自己能做主。”參見(jiàn)古樂(lè)府《孔雀東南飛》:“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辭海》(縮印本),舒新城、陳望道主編,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2002:2284。“自由”對(duì)應(yīng)的英文是“freedom”和“l(fā)iberty”。前者來(lái)自德語(yǔ),后者則來(lái)自拉丁語(yǔ)。在英語(yǔ)世界,大都是不加區(qū)分地替換著使用這兩個(gè)詞。參見(jiàn)(美)漢娜·皮特金:“‘Freedom’與‘Liberty’是孿生子嗎”,陳偉、劉訓(xùn)練譯,《第三種自由》,興奇、劉訓(xùn)練編,東方出版社,2006:312-345)。這樣一來(lái),每一個(gè)能以“我”自稱的一個(gè)個(gè)具體的張三、李四、王五等文化人的真正主體地位就被否定、擱置。也就是說(shuō),這樣一來(lái)自由就只是某一特權(quán)或某一個(gè)人的自由,有名有姓的眾多的個(gè)別的人卻沒(méi)有自由。正如馬克思所說(shuō):“沒(méi)有一個(gè)人反對(duì)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duì)別人的自由。可見(jiàn),各種自由向來(lái)就是存在的,不過(guò)有時(shí)表現(xiàn)為特殊的特權(quán),有時(shí)表現(xiàn)為普遍的權(quán)利而已”〔2〕167。顯然,沒(méi)有了自由的真正的主體,也就不會(huì)有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大師以及真正創(chuàng)造性的成果。本文的答案除了具有邏輯上的依據(jù)以外,還具有充分的哲學(xué)史依據(jù)。下面就揀選一二來(lái)加以佐證。
在《西方哲學(xué)英漢對(duì)照詞典》的“自由”詞條中,談到了自由與思想文化之間的相關(guān)性,自由是“涉及思想和行動(dòng)的概念,它有兩個(gè)相關(guān)聯(lián)的方面:一是消極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或‘解脫’(freedom from),即沒(méi)有外部的約束、強(qiáng)制或強(qiáng)迫而行動(dòng)的力量,另一個(gè)是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或‘自主’(freedom to),即主體在各種選擇方案中選擇他自己的目標(biāo)和行為方式的力量。在上述的一般規(guī)定之下,自由具有各種形式,諸如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思想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結(jié)社自由(freedomofassociation)和各種經(jīng)濟(jì)自由(various economic freedom),它們?cè)跉v史上是最重要的自由形式”〔3〕。
這些自由確實(shí)很重要,不同的哲學(xué)家或政論家分別對(duì)其中一種或幾種進(jìn)行了討論。比如17世紀(jì)英國(guó)偉大的詩(shī)人和政論家彌爾頓(John Milton)就集中討論了“出版自由”〔4〕。160多年后,即公元1811年,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也就是《論自由》的作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父親,繼續(xù)討論了“出版自由”〔5〕。而其兒子約翰·密爾在《論自由》(1859年)中開(kāi)篇就開(kāi)宗明義地指出了他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會(huì)自由(Civil,or Social Liberty),“也就是要探討社會(huì)所能合法施用于個(gè)人(individual)的權(quán)力的性質(zhì)和限度”〔6〕。密爾在書(shū)中具體討論了社會(huì)自由或公民自由中的思想自由(liberty of thought)、討論自由(liberty of discussion)和個(gè)性自由(liberty of individuality)(括號(hào)中的英文摘自隨書(shū)贈(zèng)送的英文本On Liberty)。邦雅曼·貢斯當(dāng)(Benjamin Constant)則在1819年討論了“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即公民自由和個(gè)人自由〔7〕。而馬克思則討論了新聞出版自由。其論述特別體現(xiàn)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huì)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2〕136-202。比如他指出:“自由確實(shí)是人的本質(zhì),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duì)者在反對(duì)自由的現(xiàn)實(shí)的同時(shí)也實(shí)現(xiàn)著自由;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dāng)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guò)來(lái),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2〕167-168。“沒(méi)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huì)成為泡影(the absenc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makes all other freedom illusory)”〔2〕201(括號(hào)中的英文摘自Karl Marx,F(xiàn)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第43卷,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1975:180)。總之,“西方人歷來(lái)有把真作為獨(dú)立價(jià)值來(lái)追求的智識(shí)趣味,在近代經(jīng)過(guò)無(wú)數(shù)像馬克思那樣的斗士的奮力抗?fàn)帲种鸩綘?zhēng)取到了自由地追求真知的政治權(quán)利及其制度保障。這樣一種智識(shí)傳統(tǒng)和法權(quán)制度使得西方的智識(shí)生產(chǎn)發(fā)展成了一個(gè)新知識(shí)、新思想層出不窮的龐大產(chǎn)業(yè)”〔8〕。由此,“我們可以醒悟的是:一個(gè)民族,無(wú)論如何不能禁錮其成員的頭腦,否則就會(huì)喪失把握命運(yùn)的能力;一個(gè)學(xué)者,無(wú)論如何不能放棄自由思想的權(quán)利,否則就會(huì)思想失職而有負(fù)天下”〔8〕。
自由和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在笛卡爾的哲學(xué)中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主要體現(xiàn)在開(kāi)始提出時(shí)振聾發(fā)聵,而后變得耳熟能詳?shù)拿浴拔宜迹饰以凇被颉拔蚁耄晕沂恰敝小?shí)際上,笛卡爾這一思想的理論用意或需求并不復(fù)雜,他只不過(guò)想尋找一個(gè)思想的起點(diǎn)或直接性前提即“我在,我思”。這里的我是個(gè)別詞“我”即“實(shí)踐主詞”所指的實(shí)踐主體。而且這個(gè)我不是別人就是笛卡爾自己。因?yàn)榈芽栕约壕吞寡裕J(rèn)為書(shū)本上的學(xué)問(wèn)、眾人同意或贊成的說(shuō)法等都覺(jué)得不可靠,所以希望在有生之年把過(guò)去接受的意見(jiàn)統(tǒng)統(tǒng)自主地懷疑一遍,以便把錯(cuò)誤的意見(jiàn)統(tǒng)統(tǒng)從心里連根拔除。“我的打算只不過(guò)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屬于我自己的基地上從事建筑”〔9〕13。笛卡爾起初把自己關(guān)在暖房里自主地想,想來(lái)想去給自己定了3條準(zhǔn)則。為了順利完成自己的清掃工作,他從暖房里走出來(lái)跟人們交往,到處游歷。整整9年,在世界各地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看熱鬧,仔細(xì)思考每一問(wèn)題,特別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懷疑、可以弄錯(cuò)的地方。這樣就把過(guò)去馬馬虎虎接受的錯(cuò)誤一個(gè)個(gè)連根拔掉。他說(shuō)他這并不是模仿懷疑論者,學(xué)他們?yōu)閼岩啥鴳岩桑瑪[出永遠(yuǎn)猶疑不決的架勢(shì)〔9〕12-23。“因?yàn)槭聦?shí)正好相反,我的整個(gè)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確信的根據(jù),把沙子和浮土挖掉,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9〕23。這樣看來(lái),笛卡爾無(wú)非是想強(qiáng)調(diào)每一個(gè)人的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必要性,是想喚醒每一個(gè)有名有姓的個(gè)體即“自由本體”去積極地思和做,不輕易放棄自己作為“實(shí)踐主體”的資格。“自由本體”是指每一個(gè)有名有姓的個(gè)人。而每一個(gè)有名有姓的個(gè)人都能以“我”自稱,就像邏輯專名“這”作為所有個(gè)別詞的代表可以指任何一個(gè)個(gè)別事物一樣,所不同的是,“這”用來(lái)指認(rèn)知的對(duì)象,“我”用來(lái)指實(shí)踐的主體。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可以稱作“實(shí)踐主體”〔10〕。而這種思和做是我獨(dú)立自主地思和做,不是別人強(qiáng)迫或代表我去思和做。眾所周知,正是笛卡爾那自由的頭腦創(chuàng)造出了令人難以望其項(xiàng)背的哲學(xué)思想,發(fā)明了那令人驚嘆的解析幾何。
三、自由是怎樣的
“張三是自由的”,在這個(gè)實(shí)然判斷中,“張三”是絕對(duì)主詞,“自由”是相對(duì)謂詞。說(shuō)自由是相對(duì)謂詞,是因?yàn)樗部梢猿洚?dāng)主詞。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gè)詞都可以充當(dāng)主詞,自由也不例外。當(dāng)自由充當(dāng)主詞時(shí),自由和別的任何詞一樣都有兩種謂詞,一種是表示自由的“怎么樣”的“屬差”詞,即自由的屬性詞,一種是表示自由的“是什么”的“種詞”。比如在“自由是一種自因的狀態(tài)”中,“自因的”是它的屬差或?qū)傩裕盃顟B(tài)”是它的種。這樣一來(lái),就把“自由”與“必然”區(qū)分開(kāi)來(lái)了,因?yàn)椤氨厝皇且环N他因的狀態(tài)”。
我們可以通過(guò)例示,不斷地為自由找出表示它的怎么樣的屬性詞,比如我們可以說(shuō)“自由是自主的”“自由是有選擇的”“自由是有決定的”等等。“自由”除了在理論上具有無(wú)限多的直接的屬性謂詞外,還具有無(wú)限多的間接的屬性謂詞,這些屬性謂詞通過(guò)述謂自由的直接的屬性謂詞來(lái)間接地述謂自由。也就是說(shuō),自由的屬性謂詞做主詞時(shí),也有用來(lái)述謂它的無(wú)限多的屬性謂詞,屬性謂詞又有屬性謂詞,等等,以至無(wú)窮。比如“自主是獨(dú)立的”“自主是無(wú)干涉的”“選擇是主動(dòng)的”“選擇是情愿的”“決定是由己的”“決定是無(wú)脅迫的”等等。在這里,屬性謂詞“獨(dú)立的”“無(wú)干涉的”“主動(dòng)的”“情愿的”“由己的”“無(wú)脅迫的”歸給主詞“自主”“選擇”“決定”的意義同樣是“怎么樣”,表明自主具有獨(dú)立性、無(wú)干涉性,選擇具有主動(dòng)性、情愿性,決定具有由己性、無(wú)脅迫性。它們做主詞時(shí)又可以被在理論上無(wú)限多的屬性謂詞所述謂,這些屬性謂詞又可以被另一些在理論上無(wú)限多的屬性謂詞所述謂等等,以此類推,不一而足。顯然,我的任務(wù)不是找全自由的各層級(jí)的屬性謂詞,而是為如何層層打開(kāi)自由的屬性謂詞或?yàn)樽杂扇绾畏强斩椿蚓唧w化做一個(gè)示范,刻畫一個(gè)層層展開(kāi)的自由的述謂結(jié)構(gòu)。
通過(guò)分析自由的內(nèi)涵,最終目的是為了使自由的內(nèi)涵達(dá)到具體化。當(dāng)我們說(shuō)“張三是自由的”時(shí),雖然自由的主詞的外延達(dá)到了具體性,即主詞是個(gè)別詞或絕對(duì)主詞。但謂詞“自由”的內(nèi)涵卻是空洞的。所以,如果“張三是自由的”屬實(shí),那么“張三是自主的”“張三是可以選擇的”“張三是可以決定的”等等也同樣應(yīng)該是屬實(shí)的。如果“張三是自主的”屬實(shí),那么“張三是獨(dú)立的”“張三是不被干涉的”等等也同樣應(yīng)該是屬實(shí)的。如果“張三是可以選擇的”屬實(shí),那么“張三是主動(dòng)的”“張三是情愿的”等等也同樣應(yīng)該是屬實(shí)的。如果“張三是可以決定的”屬實(shí),那么“張三是由己的”“張三是不被脅迫的”等等也同樣應(yīng)該是屬實(shí)的。只有這樣,自由的外延和內(nèi)涵才達(dá)到了雙重的具體性。
綜上所述,在文化領(lǐng)域特別是在文化創(chuàng)新的重陣——大學(xué),就應(yīng)該提倡北京大學(xué)前校長(zhǎng)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xué)精神,以及清華大學(xué)的前教師陳寅恪的“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學(xué)精神〔11〕。中山大學(xué)的徐長(zhǎng)福教授認(rèn)為:“這兩種精神是一顆種子的兩瓣,相合于‘思想自由’或‘自由之思想’。依此,其聯(lián)讀的正確順序應(yīng)為: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把這四句話稱為中國(guó)大學(xué)精神的‘四句教’”〔12〕。兩位先生播下的大學(xué)精神的種子要開(kāi)花結(jié)果,還需國(guó)人辛勤的耕耘和認(rèn)真的守護(hù)。
四、自由與規(guī)范的關(guān)系
當(dāng)然,本文所說(shuō)的自由不是任意的、放縱的自由,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13〕的自由。下面簡(jiǎn)要地談?wù)勛杂膳c規(guī)范的關(guān)系。一方面,自由是道德規(guī)范、倫理規(guī)范和法規(guī)的基石。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康德有明確的說(shuō)法,他認(rèn)為自由是“道德的基石(foundationstones of morality)”〔14〕(括號(hào)中的英文摘自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by J.M.D.Meiklejohn,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York Street,Covent Garden,1947:292-293)。以賽亞·伯林對(duì)此有深刻的看法,他認(rèn)為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都是被決定的話,那么,某些居于人類思想核心的倫理的和道德的概念與詞語(yǔ)的意義與用法,將不得不受到修改,甚或被根本改變。但事實(shí)上,現(xiàn)如今,人們還是在不厭其煩地使用著這些概念和詞語(yǔ)。更有甚者,許多公開(kāi)宣稱這一學(xué)說(shuō)的人卻很少實(shí)踐他們所鼓吹的學(xué)說(shuō);“實(shí)踐常常欺騙信條,不管它表白得多么真誠(chéng)”〔15〕11。而且奇怪的是,他們似乎并沒(méi)有意識(shí)到他們的這種言行不一致的情況。“給予道德褒貶、對(duì)人的行為進(jìn)行贊揚(yáng)或譴責(zé)的習(xí)慣,就意味著在道德上他們對(duì)這些行為負(fù)責(zé)”〔15〕6。“如果我判斷一個(gè)人的行為實(shí)際上是被決定的,他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行動(dòng)(感受、思考、欲求與選擇),那么我必須說(shuō),這樣一種褒貶用在他身上是不適當(dāng)?shù)摹H绻麤Q定論是對(duì)的,那么功績(jī)與應(yīng)得的概念,就像我們平常理解的那樣,就沒(méi)有用途”〔15〕9。另一方面,每一個(gè)有名有姓的個(gè)人作為“自由本體”就必須文責(zé)自負(fù),即必須受到道德、倫理和法律的約束和規(guī)制。總之,只有在先驗(yàn)的意義上承認(rèn)自由是人的本性,經(jīng)驗(yàn)世界的規(guī)范才有效。而經(jīng)驗(yàn)規(guī)范則不斷地佐證著先驗(yàn)自由的存在。
另外,本文這里講的自由是學(xué)術(shù)探索方面的自由,它是獨(dú)立自主之學(xué)術(shù)人格得以正常發(fā)育的基因或基石,這里所談的學(xué)術(shù)自由或思想自由與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的“宣傳教育有紀(jì)律”并不矛盾。也就是說(shuō),在民族國(guó)家和階級(jí)社會(huì)時(shí)代條件下,毛澤東同志倡導(dǎo)的“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的方向與“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的方針之間并不矛盾,只要把二者有機(jī)地統(tǒng)一起來(lái),那么就會(huì)呈現(xiàn)出自由實(shí)現(xiàn)學(xué)術(shù)的百花齊放,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達(dá)致社會(huì)的長(zhǎng)治久安的局面。
〔1〕亞里士多德.范疇篇 解釋篇〔M〕.方書(shū)春,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59:12.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尼古拉斯·布寧,余紀(jì)元.西方哲學(xué)英漢對(duì)照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5.
〔4〕彌爾頓.論出版自由〔M〕.吳之椿,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58:1-60.
〔5〕詹姆斯·密爾.論出版自由〔M〕.吳小坤,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08:1-35.
〔6〕約翰·密爾.論自由〔M〕.程崇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59:1.
〔7〕邦雅曼·貢斯當(dāng).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M〕.閻克文,劉滿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6-47.
〔8〕Xu Chang-fu.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 and Kang Youwei’s Predictions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J〕.Studies in Marxism,2011(12):118-119.
〔9〕笛卡爾.談?wù)劮椒ā睲〕.王太慶,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0.
〔10〕徐長(zhǎng)福.實(shí)踐主詞、實(shí)踐主體和自由本體:從“我”說(shuō)起〔J〕.現(xiàn)代哲學(xué),2010(4):24-32.
〔11〕陳俊偉.自由面面觀〔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9:79-104.
〔12〕徐長(zhǎng)福.治學(xué)精神和辦學(xué)精神不可分離〔N〕.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0-04-08(3).
〔13〕孔子.論語(yǔ)〔M〕.長(zhǎng)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31.
〔14〕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9.
〔15〕以賽亞·伯林.自由論:修訂版〔M〕.胡傳勝,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