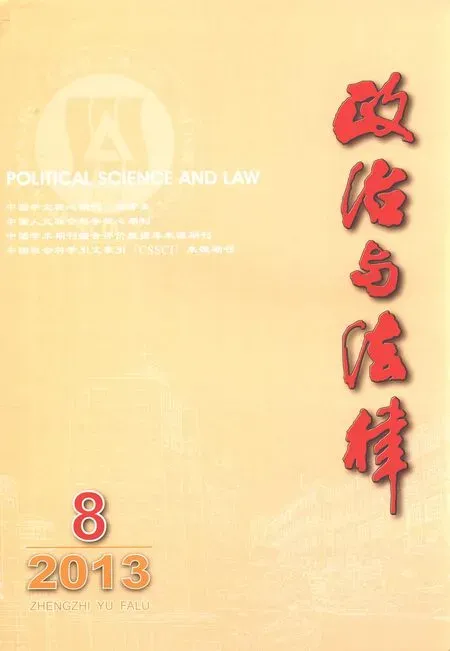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與憲法核心之保障*
柳 颯 涂云新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廣東廣州510320;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與憲法核心之保障*
柳 颯 涂云新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廣東廣州510320;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憲法修改在于緩解憲法規范的穩定性和社會現實恒動性之間的緊張關系。以修憲限制理論為基礎,憲法修改不得變更和不可傷害憲法核心,同時也必須捍衛和保障對憲法存立具有本質性重要意義的憲法價值。首先,憲法修改的邊界在于不得侵犯制憲權的領域,以修憲之名而僭越制憲權的憲法修改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憲法破壞;其次,憲法修改的邊界應該止于不可變更和不容侵犯的憲法核心,這些憲法核心包括基本人權原則、國民主權原則、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等;再次,對修憲條款本身的修改應該被置于憲法修改限制理論最為嚴格的適用標準上而予以反對。德國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憲法學說認同和平主義的憲法原則是內涵于兩國憲法中不容侵犯的憲法內核,因而,對德國和日本憲法中的軍事和國防條款的修改應該予以高度警惕和強烈反對。
憲法修改;修憲限制;憲法核心;德國基本法;日本憲法;實證主義
憲法修改是憲法為適應社會情狀變遷而保持憲法生命力的一種重要途徑,就憲法修改與憲法本身所要求的安定性之間的關系來看,憲法修改的界限與憲法根本價值的保障成為了學界熱烈探討的理論問題。在立憲主義興起之初,傳統的憲法學理論倚重人民主權(國民主權)學說服務于制憲的理論需求,難免顯露出強烈的革命主義傾向,而在革命浪潮席卷歐陸之后,新興的憲政法治國家隨之建立,實證主義憲法學逐漸將立憲時代憲法所荷載的價值和理念予以貫徹和融通,并形成了蔚為大觀的景象。然而,面對憲法規范與憲法現實之間近乎永恒的矛盾,憲法修改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正如中國著名的比較憲法學家王世杰和錢端升先生所言,憲法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實際上,都不含有不可變性。1憲法修改是一國憲法實施過程中具有重大社會關切的議題,它在實務上的運作不僅包括修憲主體、修憲提案、修憲程序、修憲技術等諸多具有實踐面向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法理上關于憲法修改的界限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統攝諸多修憲技術難題的根本問題,例如憲法修改能否觸及實證憲法的一般原則?修憲權能否及于實證憲法本身所規定的不可變更的部分?修憲的
限制是否涵蓋修憲條款本身?掏空憲法本質內涵的憲法修改能否仍然被認為是一種修憲權的正當行使?在這些重大理論問題上,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憲法理論承認了憲法的修改不能突破“憲法核心”(Verfassungskerns/Constitutional Cores)2的觀點。這些觀點隨后被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憲法學說所吸收和借鑒。循此,本文將論述的主軸線置于憲法修改與憲法核心所保障的根本價值上來,通過闡述大陸法系國家具有代表性的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來澄清經由修憲而實施憲法中的理論困惑。
一、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
在憲法修改有無限制的理論爭議中,學界存在著“無限制說”和“有限制說”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其中,憲法修改的無限制理論的立論基礎主要在于“國民之主權”不受限制,故憲法的修改亦無限制。這種理論看似具有強大的理論說服力,實際上忽略了“制憲”與“修憲”的區別,當憲法的修改逾越了修憲權的權能范圍后,修憲權就代替了制憲權,修憲活動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從而成為一種披著修憲外衣的制憲活動。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的立論基礎在于修憲權與制憲權的二分,對憲法存立具有根本重要者不得成為修憲的對象,而憲法修改在于保障包含“國民主權原則”在內的憲法核心。德國憲法學者關于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已有諸多著述,在這個方面,日本憲法學理論大都直接或者間接受到德國憲法學說的深刻影響。
(一)卡爾·施米特的修憲限制理論
關于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德國法學大儒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觀點。卡爾·施米特嚴格區分了制憲權(Pouvoir constituant)與修憲權(Verfassungs?ndernde Gewalt),并指出:制憲權是一種構成有關國家的政治性實在的樣式與形態的、具體性的“整體決斷”(或曰“綜合決斷”)的政治意志,是一種不包括修憲權的純粹的法秩序的創立權;而修憲權則屬于“被憲法所制定的權力”。換言之,制憲權超越于憲法之上,是一個超實定法的概念,而修憲權卻是一個為憲法所規范和控制的權力。3施米特進一步區分了憲法廢止、憲法廢棄、憲法中止和憲法破壞等不同的概念,憲法修改意味著他所說的憲法律(Verfassungsgesetz)的廢止、修正和增減,但是作為決斷意義上或者實證法意義上的憲法(Verfassung)仍然具有正當性和體系性。易言之,憲法修改僅僅是憲法的自我更新,絕非憲法的自我破壞或者廢棄。施米特認為“修憲權”是根據憲法規范授予的,這就意味著,個別或若干憲法法規可以用另一些憲法規范來取代,但前提條件是,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其同一性和連續性得到了維持。因此修憲權只是一種在保持憲法的條件下,按照憲法律規定的程序做出變更、補充、增刪的權力,而不是一種制定新憲法的權力。它也不能變更、擴展修憲權自身的根據,或者用別的根據來取代這個根據。比如,它不能按魏瑪憲法第76條的程序來修改第76條本身,規定憲法法律可以通過國會的簡單多數決議予以修改。4
(二)漢斯·凱爾森純粹法學派之修憲理論
純粹法學派代表學者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的修憲限制理論建立在他所謂的“基本規范”之上,他吸收了新康德學派對國家法的認識論精華并將其憲法學說建立在“存在”(Das Sein)和“當為”(Das Sollen)的區分之上,并認為憲法上的國家在本質上只能屬于一種法律秩序的理念(Ordnungsgedanke)。凱爾森賴以建構其法律效力層級體系的合法性來源在于他所假設的一個不可再被向后推導的“基本規范”(Grundnorm),這個基本規范成為了國家法秩序的正當性源泉。5雖然很多學者批判該“基本規范”為不可證
實的且必須求助于自然法的觀念來正當化,但我們必須看到凱爾森所謂的“基本規范”是一個超實證憲法的效力來源,它是法秩序在邏輯上逆推的一個必然,對于這個基本規范,實證憲法是不能夠變更和修改的。循著凱爾森純粹法學的觀點,憲法之修改只能經過嚴格的修憲程序為之,且修改的界限在于維護和貫徹“基本規范”蘊含的法價值和法理念。基于“二戰”之后德國自然法思想復興的背景可以看到,凱爾森所謂的“基本規范”是一個取向于保障“人之價值和尊嚴”的根本規范,也是憲法修改不可變更和不可傷害的。
(三)荷斯特·耶姆克憲法內涵性之修憲理論
德國基本法時期的憲法學家荷斯特·耶姆克(Horst Ehmke)對憲法修改持“有界限”的理論,他于1953年出版的《憲法修改的界限》一書可視為“二戰”后德國公法學者在修憲問題上的代表性作品。荷斯特·耶姆克認為修憲權行使得以憲法核心(Verfassungskerns)所保障的內容為其邊界,而憲法之核心存在于三個方面。首先是存在于超越實證憲法的要素之中(Verfassung transzendente bzw au?erhalb der Verfassung liegende Momente),這些超實證法的要素是任何修憲者都不能夠通過憲法修改而予以變更的,例如一國的地理位置、經濟與科技的因素、國際法上的規定,這些均是一國國內憲法規范力所不能輕易改變的部分。6其次是內涵于憲法之中并且“與實證憲法本身有本質關聯性(Der mate riale Zusammenhang der positive Verfassungsbestimmungen)”的部分。修憲權在任務上只能修改憲法而非產生一個憲法廢止(Verfassungsbeseitigung)的結果,即修憲不能鏟除一部實證憲法在法拘束力上的正當性來源,若要變更這種正當性來源,那就變成了一次制憲行為(Verfassungsgebung)本身的任務,而非內涵于憲法內在要素之本意所形成的(nicht im eigenlichen Sinne)。7最后,憲法核心還存在于實證憲法關于修憲條款的法規范。例如德國基本法第79條第3款規定的人性尊嚴原則和聯邦國原則不得成為修改的對象,該條文不具有憲法上決定拘束性之作用(keine konstitutive Wirkung),而僅僅具有宣示性之憲法本質(deklaratorische Natur)。8
(四)宮澤俊義“八月革命說”影響下的修憲理論
日本憲法學家宮澤俊義在憲法的修改問題上贊同耶利內克的絕對界限的觀點,他認為使實定法作為實定法而成立的根據在于“服從創造命令者”(oboedientia facit imperantem),憲法只有在能自我實現時才是有效的法。成功的革命顯示,成文憲法至上存在著更高的法原理,依據該原理,根據革命而應該承認日本憲法具有效力。9同時,宮澤俊義強調憲法問題實質上不只是法律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宮澤俊義認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義是日本政治體制的最終決定權屬于國民……這樣的變革,不僅日本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合法做到的,即使依照天皇的意志,也不可能合法完成……這個事情是憲法意義上的革命……投降就完成了一次革命……通過8月革命,日本政治的根本前提就從神權主義變成國民主權主義了。”10故1946年《日本憲法》的制定在憲法評價上屬于制憲。宮澤俊義認為以“占領憲法”、“強加憲法”為由主張修改憲法,只是政府基于現實政治策略而使用的借口。11
(五)蘆部信喜與高橋和之的修憲限制理論
日本傳統的“有界限”說通過分析憲法規范的形式性邏輯構造,構筑根本規范——憲法修改規范——普通憲法規范這樣的位階秩序,論證修改根本規范的不可能性,但是在蘆部信喜教授看來,日本傳統的有界限說還不足以戰勝源于法實證主義和主權全能論的無界限說,他從四個方面進一步加強了日本的有界限說:在與人權的憲法保障不即不離
的關系中揭示國民制憲權的思想意義;明確制憲權與作為“制度化的制憲權”的修憲權之間的關聯;從歷史、邏輯上明確憲法至上的意義內涵和價值內涵;構筑一種制憲權也受到超實證法所拘束的根本規范的概念。一言以蔽之,蘆部信喜教授將尊重基本人權原理、國民主權原理和和平主義視為修憲的界限。12蘆部信喜教授及其弟子高橋和之在后來的憲法學說發展上繼續否認和反駁了經過實定法上的修正程序任何憲法規范都可以被無限制修改的觀點。他們對于憲法修改界限的理由主要基于四點考量。其一,權力的層級結構。修憲權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憲法制定權力”,若修憲權將應稱為是自身存立之基礎的制定權之所在(國民主權)加以變更,則屬于所謂的自殺行為,在理論上不被容許。其二,人權的根本規范性。人權與國民主權共同立足于“個人尊嚴”的原理之上成為了近代憲法的本質與理念,修憲權不能變更憲法之“根本規范”的人權原則。其三,日本憲法前言的意圖。日本憲法在前言中提出人權與國民主權是“人類普遍的原理”,宣明“排除一切違反此原理的憲法、法令及詔赦”,這不僅是政治性希冀的表明,也是對憲法修正案具有法意義界限的理論加以確認。第四,和平主義憲法。與國內的民主主義(人權與國民主權)相互結合不可分割的、被稱為是支配近代公法進化之原則的國際和平的原理,必須被理解為是處于修憲權范圍之內的。13蘆部信喜和高橋和之的觀點顯然受到了德國具有代表性的憲法學說和國家法學說的深刻影響。他們關于修憲權本質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憲法制定權力”的論述觀點源自于卡爾·施米特的制憲權學說,而二者關于人權的根本規范性作為修憲界限的論證受到凱爾遜純粹法學派的影響。蘆部信喜和高橋和之關于日本憲法前言意圖的理解和對和平憲法本質的論證又受到了“二戰”之后德國新康德主義法學派的影響。
二、憲法修改限制理論的功能導向——憲法核心之保障
(一)憲法核心的概念內涵
憲法核心(Verfassungskern)有時也被稱為“憲法核”。我國臺灣地區憲法學家陳慈陽教授系統闡釋了德國憲法學說上憲法核心的概念,在他看來,憲法核心是指以人性尊嚴與以人的基本價值為基礎的自由民主憲法秩序,以及為了保障此秩序所必要的諸如法治國家、權力分立、正當法律程序與社會國原則等憲法基本原則。14憲法核心的理論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憲法學家莫里斯·奧里烏(Maurice Hauriou)的制度理論,他所主張的“不可控制的主權也即不可完全委代的國家主權”可被視為憲法核心理論的萌芽。15憲法核心的概念和理論在大陸法系的德國形成頗具影響力的一種憲法學理論,而后被日本憲法學家所繼受。相應地,由于中國傳統的比較憲法學多采用大陸法系的憲法理論,憲法核心的理論也為我國所承認。韓大元教授認為憲法規范主要由憲法制定規范、憲法核、憲法修改規范與憲法律組成,不同的規范之間形成不同的等級系列,即在憲法規范內部存在上位規范與下位規范,下位規范服從上位規范,下位規范不得改變上位規范。16我國臺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499號解釋文”中明文宣示:“‘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于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17
(二)憲法修改限制理論確保憲法核心的不可變更
憲法修改之限制理論最大的功能莫過于該理論駁斥了基于法實證主義的無界限說和
主權全能論的無界限說,建構了修憲權行使的界限,正如蘆部信喜教授所言,修憲權的界限問題可謂是與憲法理論中最本質部分相關的問題。18在德國,憲法核心被認為是“不可變更的”(unab?nderlicher Verfassungskern),德國魏瑪時期著名的憲法學者卡爾·施米特吸收了西耶士(Sieyè s)的制憲權理論并融合了盧梭(Rousseau)、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人民主權學說發展出決斷主義憲法學。施米特認為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決斷,它是由源自于政治現實力量或權威的政治意志所形成的,代表此一政治意志之制憲權更決定了憲法條文之性質,即決定了實證意義的憲法,同時這也是實證憲法中不可變更之核心,除此之外的實證憲法條文則可由修憲權加以修改。19在新近的“里斯本條約案”20判決中(Das Lissabon-Urteil),德國聯邦法院仍然借助了“不可變更的憲法核心”所捍衛的民主原則(Demokratieprinzip)來判斷里斯本條約和聯邦德國條約批準程序法是否與德國基本法一致。21日本憲法學教授清宮四郎通過構筑根本規范——憲法修改規范——普通憲法規范這樣的位階秩序,論證修改根本規范的不可能性。22在清宮四郎看來,憲法核是一種根本規范,它提供實定法的客觀合理性的依據,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實定法創始的出發點,這種根本規范可以被稱之為“憲法的憲法”。23
(三)憲法修改限制理論提供憲法核心實證化之路徑
由于憲法設定了政治過程的游戲規則(Spielregel)和法律原則,憲法修改在很大意義上兼備了政治性和法律性,自耶利內克(Jellinek)和美濃部達吉等古典憲法學者以來的德國和日本主流學界都致力于將憲法核心予以法律上的實證化研究。比如持憲法修改限制理論的德國學者荷斯特·耶姆克認為,憲法核心存在的一方面就是實證憲法的規定(kraft positiver Verfassungsbestimmung),他列舉了德國基本法第79條第3款所保障之內容,并將該內容視為“不可變更之憲法核心”。24在筆者看來,憲法修改限制理論在兩個方面為憲法核心的實證化提供了法理支持和理論路徑。第一,修憲限制理論從憲法哲學上否定了憲法修改的無界限理論。正如本文所論及的,憲法修改的無界限論的哲理根據在于一種所謂的主權全能論,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國民擁有制憲權,而基于國民主權的修憲是不受實在法限制的,那么憲法的核心也可以由掌握主權的國民所修改和變更。在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看來,制憲權分為源生性的制憲權和制度化的制憲權,后者雖然與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但是修憲權并不可能再次啟動源生性的制憲權,因為在邏輯上國民行使修憲權只能受制于前面舊有的制憲權,要啟動一個新的制憲權,國民只有通過革命,而非通過法律。第二,修憲限制理論實際上區分了憲法規范的效力層級,憲法規范中宣示或者隱含對于憲法存立具有本質重要性的規范才是憲法核心,而在憲法核心之外的其他普通規范,仍然可以通過修憲程序而變更。至于凱爾遜所謂的“根本規范”(Grundnorm)屬于超實證法意義上的憲法規范,它是憲法正當性的源泉,修憲權當然無法通過實證法的程序進行變更。通過對憲法規范的區分,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就保證了憲法一方面可以適應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可以維持憲法核心的不可變更性。
(四)憲法修改限制理論維護憲法核心所欲保障的國際法律價值
自“二戰”之后,為避免后世再遭當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以尊重人權和促進和平為要旨的國際法律價值逐步被現代各國所認可并融入到現代各國的憲法之中。以人權為例,“二戰”后,幾乎所有的現代憲法都規定了人權保障條款,同時,人權保障也被認為是現代憲法的終極目的。由于現代憲法將國際法法律價值內化于憲法規范之中,并且,這些國際法律價值也成為了一種具有本質重要性的憲法理念,故也可以將這種國
際法律價值視為憲法核心所欲背負的使命和價值追求。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在功能上便有義務去維護這些國際法律價值,任何關于憲法的修改都不得減損或者消滅這些國際法律價值。在日本,尊重基本人權、國民主權(主權在民)及和平主義(放棄戰爭)被視為日本憲法的三大原則,其中和平主義原則廣泛被認為是日本憲法的核心原則。德國基本法第1條宣示了德國尊重和保障世界的和平(Friedlichkeit)和正義(Gerechtigkeit)的理念,基于對德國基本法第1條和第79條的體系解釋,和平原則由此成為德國憲法中不可變更之核心,25同時,德國基本法第26條也明確規定了德國不得破壞“各國人民的和平相處”(friedlichen Zusammenlebens der V?lker)。
三、修憲限制理論在德日憲法修改中的應用
一九四九年德國基本法與一九四六年日本憲法在“戰后”國內法律秩序重建的語境中被稱為“外造憲法”(Externally Imposed Constitution/aufgezwungene Verfassung)26。與世界上大部分實證憲法相同,為了使靜態的憲法條文能有彈性地適應現實憲法生活中各種力量的運作與妥協,德、日兩國憲法容許其規范在不同的條件下加以修改或就個別條文加以刪除。27德、日兩國憲法修改的通說認為憲法修改不同于普通法律的修改,它只能通過嚴格的立法程序來修改,而憲法修正案應該具有成文法律(geschriebenes Gesetz)一樣的外觀。28德、日兩國憲法學界雖然也存在著一些持“憲法修改無限制論”的學者,并且這些學說也在影響或塑造著兩國的修憲實踐,但是,歷經六十余年的修憲實踐,兩國憲法中的國防軍事條款仍然未發生文本上的改動,這雖然不能全部歸結于“憲法修改限制理論”影響的結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德、日兩國的憲法學說亦存在完全禁止和限制軍事國防條款修訂的支持者。筆者將在此處探討德日兩國修憲限制理論是如何適用于兩國憲法的修憲實踐的。
(一)德日憲法的修改條款
依照日本早期憲法學家美濃部達吉的總結,在成文憲法國家內,憲法修訂的方法大體可以分為兩種:其一,基于憲法的制定權(pouvoir constituent)必須存于國民自身的思想,憲法的修正不屬于普通的立法部門的權能,而屬于國民之直接的權能,屬于僅為此目的而組織的憲法會議(convention)的權能;其二,關于憲法的修正,委之于普通的立法部門的權能,但是其決議的方法須比普通的立法更為鄭重。此外聯邦制國家內,亦有必須將憲法的修改交付聯邦各州討議的。29德日同屬于成文憲法國家,兩國的修憲條款設計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德國基本法第79條為德國的修憲條款(?nderungen des Grundgesetzes),其構造見表1。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了日本憲法的修改問題,其構造見表2。

表1 德國基本法第79條

表2 日本憲法第96條
(二)以日本憲法第9條為例
日本憲法專章規定了“放棄戰爭”的原則,第二章第9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
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30筆者在此從三個方面理解第9條的憲法內涵,第一,放棄戰爭。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憲章》決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恢復和平秩序,開啟了建立侵略國的非軍事化和政治制度民主的國際努力。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這也就意味著日本接受了國際社會關于侵略國“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決議。這種放棄戰爭的政治原則通過日本憲法的實定化已經轉變為日本憲法中的“和平主義”原則。第二,放棄戰爭力量。戰爭結束后,日本軍隊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解除了武裝,在麥克阿瑟1945年10月16日的一份聲明中,他宣稱:“今天日本各地已經完全解除了武裝力量,軍隊已不復存在了。”31第三,交戰權之否認。日本憲法第9條明白宣示“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交戰”和“交戰狀態”原為國際法的法律術語,自國際法之父格勞修斯在其名著《戰爭與和平法》中討論戰爭的合法性之后,實證國際法一直致力于以法律手段限制和規制戰爭。1907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是這方面的最早嘗試,1949年的“日內瓦四公約”32的共同第2條中明晰了“戰爭如何開始”這一法律問題:或者通過宣戰(declaration of war)或者通過武裝沖突(armed conflicts)33。由此可見,日本憲法第9條所宣示的“交戰權之放棄”明顯使得日本失去了經由“宣戰”而發動對他國戰爭的可能性。再進一步推進,日本是否可以在遭受他國武裝沖突時被迫卷入戰爭狀態而行使其《聯合國憲章》第51條所規定的自衛權呢?此處可以分為兩種解釋和兩種回答。假若做廣義解釋,《聯合國憲章》第51條所規定的自衛權(self-defense)是國家的一種“天然權利”(inherent rights),而從超實證法的角度看,日本在遭受他國武裝攻擊之時亦得享有此種權利。假若做狹義理解,從實證法的角度看,即使日本在遭受他國武裝沖突之時也不得行使其自衛權。筆者認為其理由有二:其一,從實證憲法學的角度看,日本國憲法第9條之核心內涵在于維護“和平主義原則”,而該原則在任何時候(包括武裝沖突的狀態下)都不得被減損。文意解釋和目的解釋都支持這種觀點——第9條第1款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這已經是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了第9條的立法原旨。而第9條第2款指出為達到第1款所規定的目的,日本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其二,從實證國際法的角度看,“波茨坦公告”限定了日本戰爭權限,日本對該公告的接受表明日本愿意履行其國際法上的義務。而波茨坦公告可以被視為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的準備文件(Travaux Préparatoires),而日本接受《聯合國憲章》并成為其一員,就意味著日本仍然受到相關戰爭權條款的國際法約束,從而“憲章”第51條之自衛權條款并不適用于日本。《日本憲法》第9條第2款的規定還關涉到日本自衛隊合憲性的爭議。蘆部信喜和高橋和之教授認為日本現在的自衛隊,一旦從其人員、武裝、編制等實際狀態加以判斷,則相當于《憲法》第9條第2款中所言的“戰爭力量”。而日本亦有學者持“無武力之自衛權”論,認為雖然自衛隊處于違憲狀態,但既然存在自衛權,就允許其保持不超出“不具有攻擊性武裝和作戰能力、為了處理通常警察或消防無法應對的災害或紛爭而建立的自衛組織之最小限度防御能力”界限的軍事力量。34
(三)對修憲條款本身能否修改的探討
修憲條款本身能否成為憲法修改的對象呢?這里的問題在于德國和日本是否能夠通過《德國基本法》第79條和《日本憲法》第96條的修改來逐步修改憲法中的其他關鍵條款。考察德國和日本的制憲思想,可以知道無論是《德國基本法》第79條還是《日本憲法》
第96條都設計了一種修憲正當性較高的國民投票制,其思想基礎在于近代自然法學派所主張的根本法(lex fundamentalis)、近代立憲主義的憲法思想和有關主權與代表的學說。德國傳統的主流憲法學觀點均認同憲法所欲保障的不受傷害和不可變更之憲法內核,而《德國基本法》第79條的功能就在于:吸取“魏瑪憲法”遭受頻繁修改而終致破壞的慘痛教訓,將不受傷害的憲法核心置于此條款的規范效力下,永固憲法上的基本決定。相比而言,日本憲法學者蘆部信喜也認為通過修改“修憲條款”而修改憲法的其他關鍵條款無異于一種法邏輯上的矛盾,類似于憲法的自我否定和自殺行為,是不被允許的。35筆者認為通過修改“修憲條款”而修改憲法的其他關鍵條款在理論和邏輯上存在三大障礙。第一,修憲條款本身成為修改對象后,修憲門檻的提高或者降低皆淪為一種恣意,這會造成憲法在邏輯上可以被無限修改的可能,憲法也因此不能獲得一種邏輯上的圓滿。第二,“修憲條款”的規范功能之一便是保障憲法不可變更和不受傷害的內核,這也是采用成文憲法的各國都無一例外地對修憲設置了較高門檻的原因。修改“修憲條款”的后果便極有可能廢除憲法不可變更和不受傷害的核心。第三,修改“修憲條款”,即使是在國民投票的情況下為之,都會導致修憲權侵入制憲權,若“修憲條款”本身可以被變更,則這種變更就極有可能導致先前制憲權行使的意義被后來的修憲權拋棄或者置換。在日本,于2006年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及其內閣持有強烈的修憲主張,2007年5月,安倍內閣促使日本國會通過了《國民投票(公決)法》(日文又稱:憲法改正手続法)36。根據該法,經過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各三分之二同意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60日至180日內須提交國民投票;18周歲以上的日本國民擁有投票權,不設最低投票率限制,過半數贊成憲法修正案即正式通過。此法被廣泛認為是日本已經事實上解決了修改憲法的程序問題。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并且一直力圖加速日本的修憲進程,在日本國會公布的修憲議題中,日本憲法第9條便在其中。由于第9條的修訂難度比較高,安倍內閣也在改變修憲策略,日本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于2012年4月27日公布了“日本國憲法修改草案”37,該草案規定國會兩院的簡單多數即可提出憲法修正的議案,然后將憲法修改交付國民投票,但是有效投票人數的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憲法修正案。由此可見,日本現任內閣推動修憲的目的在于通過推動修改《日本憲法》第96條來最終達到修改第9條。將日本新近的修憲動議置于學理的評判上,不難發現日本企圖通過修改其憲法的修憲條款來達到修改第9條的做法仍然會在修憲法理上面臨相當大的挑戰和非議。
(四)關于修憲進一步的探討:內涵于憲法的國際法價值
近年來,由于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深層次互動,國內憲法秩序也受到了國際強制法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通過憲法核心所設定的和平主義理念而彰顯。最為明顯的例證之一便是國際強行法(Jus Cogens/peremptory norm/zwingenden V?lkerrechts)成為了憲法修改的界限。國際強行法也被稱為絕對法或者強制法,是國際法中為了滿足國際社會較高利益而存在的不得被制定法減損的強制性規則。38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條明定:“……一般國際強行法規則指列國國際社會作為整體接受并承認為不得背離且只能由發生在后面而具有同一性質的一般國際法規則予以更改的規則。”39一般認為國際法上的強行法規范包括禁止戰爭、反人類罪、酷刑、種族滅絕,而新近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性審判機構的法理發展,又進一步將“通過侵略性戰爭而取得別國領土”作為國際強行法的規范對象之一。40最先在國內憲法的修憲條款中引入強行法作為修憲邊界的國家是瑞
士。瑞士聯邦憲法(BV)規定了瑞士修憲的兩條路徑:其一,根據憲法第138條和139條,由人民提出修憲動議(Initiative);其二,由瑞士聯邦國民議會和參議院提出修憲建議。根據憲法第192條至第194條之規定,瑞士聯邦憲法的修改可以及于其一部分也可以是其全部,但唯一的例外便是根據憲法第194條第2款,瑞士聯邦憲法的修改不得違反國際法中的強行法規定。德國和日本同為《聯合國憲章》、《羅馬規約》的締約國,兩國承擔懲處準備或者正在發動侵略戰爭行為的國際義務,更進一步,若兩國通過修改憲法上的軍事條款而擴張軍事力量則有違背國際強行法的可能性。根據荷斯特·耶姆克(Horst Ehmke)的修憲限制理論,這種修憲行為違背了內涵于憲法之中并且“與實證憲法本身有本質關聯性(Der materiale Zusammenhang der positive Verfassungsbestimmungen)”的部分——在德國為內生于基本法之中的“侵略戰爭之禁止”的規范,在日本則為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原則。
四、結論
憲法修改關涉到憲法規范的穩定性和社會現實的恒動性,通過憲法修改來使得憲法適應社會現實的發展和變化無疑是一個極為奏效的憲法實施的手段,但是,如何確保憲法本身所具有的安定性的品質并且使得憲法的規范效力在同一性和永續性的法理邏輯上展開始終是憲法修改所必須直面的問題。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并非扼殺了憲法規范的活力,相反,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過捍衛憲法的根本價值來保持憲法本身應該具有的生命力。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不僅界定了修憲行為本身的限度,同時最終在于保障不可變更和不容侵犯之憲法核心,這也正是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實證主義憲法學說努力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的憲法學者也受到了德國和日本修憲限制理論的影響。首先,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認為修憲行為本身的邊界在于不得侵犯制憲權的領域。基于制憲與修憲二分的理論,修憲行為與制憲行為存在本質上的差別,雖然從歷史上、邏輯上看,修憲權可以被視為一種制度化的制憲權,但是憲法修改不能變更制憲權所構筑的根本規范,以修憲之名而僭越制憲權衍生出來的根本規范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憲法破壞。其次,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在功能上保衛了對憲法存立具有本質性重要意義的憲法核心,對于德國和日本而言,尊重基本人權原則、國民主權原則、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和和平主義原則都可以被視為不可變更和不容侵犯之憲法核心,從而都應該是憲法修改的界限。任何修憲活動若破壞了上述憲法核心都應該被視為一種嚴重的背離憲法根本價值的違憲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掏空憲法核心的憲法修改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修憲權的正當行使。再次,針對修憲條款本身能否修改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承認修憲條款對于憲法核心理論實證化的巨大作用,修憲條款本身就在于維護憲法本身的至上權威、防止憲法淪為恣意的政治游戲,故對修憲條款的修改應該被置于憲法修改限制理論最為嚴格的適用標準上,無論是對修憲程序、修憲時機還是對修憲條款自身規定的修憲范圍上的修改,都會危及不可變更的憲法核心。當修憲條款本身被修改時,修憲條款本身的拘束力被破壞殆盡,憲法內核被侵蝕的可能性就會迫在眉睫,其后果極有可能是憲法的自殺行為。最后,德國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憲法學說認同和平主義的憲法原則是內涵于兩國憲法中不容侵犯的憲法內核,由政府推動的對憲法中的軍事和國防條款的修改會抵觸憲法核心所欲保障的國際法律價值,并且,這種修改若與國際社會整體利益和較高利益相背離,則其修憲行為在學理上應該被給予高度的警惕和戒備,在實踐上應該遭到國際社會的否定性評價和譴責。憲法修改的限制理論同樣也是我國憲法學界具有影響力的一種學說,以
這種理論為基礎的憲法修改對于我國現行憲法的實施必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注:
1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373-374頁。
2日本名城大學(Meijo University Nagoya)教授Hisao Kuriki肯定了德日憲法中的所謂“憲法核心”理論(Der Kern der Verfassung)。參見Hisao Kuriki:Die Theorie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im Verfas sungswandel,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Vortr?gefürdeutsch-japanischenSymposieninTokyo 2004 und Freiburg 2005,Berlin:Duncker&Humblot,2010.S.14。
3杜強強:《論憲法修改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林來梵:《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頁。
4[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頁。
5Hans Kelsen,Reine Rechtslehre,Wien:Franz Deuticke,1960,S.229.
6、7、8Horst Ehmke,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Duncker&Humblot,1953,S.92.其中文翻譯參見陳慈陽:《憲法規范性與憲政現實性》(第二版),臺北翰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頁,第27頁,第28頁。9、12、18、22、35[日]蘆部信喜:《制憲權》,王貴松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頁,第102頁,第109頁,第109頁,第104頁。
11邱靜:《戰后日本的知識分子護憲運動與護憲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
10[日]山下威士、真水康樹:《8月革命說與4月制定說——日本國憲法是何時制定的?》,《北大國際法與比較法評論》2010年第10期。宮澤俊義的憲法學說最為核心的觀點就是:通過“八月革命”,日本憲法由神權主義向國民主權主義發生了實質性的變革。
13、34參見[日]蘆部信喜:《憲法》(第三版),林來梵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8頁,第53-54頁。
14陳慈陽:《憲法學》,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83頁。
15龍晟:《憲法核心理論芻議》,《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16、23韓大元:《論憲法規范的至上性》,《法學評論》1999年第4期。
17參見“司法院”公報,第42卷5期,第1-59頁;“總統府”公報,第6339期,第3-76頁;“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十三)第685-788頁;守護“憲法”60年,第159-162頁。
19、24、27陳慈陽:《憲法規范性與憲政現實性》(第二版),臺北翰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2頁,第28頁,第48頁。
20BVerfG,2 BvE 2/08 vom 30.6.2009.
21Dietrich Murswiek,Art.38 GG als Grundlage eines Rechts auf Achtung des unab?nderlichen Ver fassungskerns,Hinweis zum Aufsatz von Murswiek in JZ 2010,702f.
25Schwarz,Friedlichkeit alsGrundpflicht--DieHerausforderungderGrundrechtsdogmatikdurch den Fundamentalismus.Hinweis zum Aufsatz von Schwarz in BayVerwBl 2003,326f;T.Maunz&G. Dürig,Grundgesetz-Kommentar,GG Art.26.,67.Erg?nzungslieferung 2013.
26基于德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有的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以同盟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強烈介入了德日戰后憲法的制定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德國基本法還是日本憲法都可以被稱為“外造憲法”。另外,例如前南斯拉夫、東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的憲法均屬此類,參見Andrew Arato,Constitution Making Under Occupation:The Politics of Imposed Revolution in Iraq,1st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然而學界對于“外造憲法”的觀點和看法卻不盡一致。曾經是伊拉克臨時政府《過渡行政法》(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TAL))起草委員會法律顧問之一的紐約大學法學院Noah Feldman教授認為“外造憲政主義”(imposed constitutionalism)在早期德日制憲中曾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在晚近諸如東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的制憲過程中面臨著“人民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的強烈影響。參見Noah Feldman,Imposed Constitutionalism,37 Conn.L.Rev.857;Simon Chesterman,Imposed Constitutions,
Imposed constitutionalism,and Qwnership,37 Conn.L.Rev.947;Mark W.Janis,Human Rights and Imposed Constitutions,37 Conn.L.Rev.955.在德國,英文中的“外造憲法”有兩種不同的翻譯,一為本文正文中所使用的aufgezwungene Verfassung,一為oktroyierte Verfassung(亦可直譯為“占領憲法”)。參見J?rg Berlin,Bürgerfreiheit statt Ratsregiment:Das Manifest der bürgerlichen Freiheit und der Kampf für Demokratie in Hamburg um 1700,2.Auflage,2012,S.216;日本憲法頒布六十余載以來,日本學界一直存在對“外造憲法”(中日學術界也有學者借助日文中的漢字翻譯為“強加憲法”)合法性的種種挑戰,這在日本被稱為“強加性憲法論”(押し付け憲法論),參見佐藤功,「押しつけ憲法論」論議の再燃,世界第221號,巖波書店,1964;[日]蘆部信喜:《憲法》(第三版),林來梵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頁;包霞琴:《90年代后日本修憲論及其特點分析》,《日本研究》2004年第2期;憲法改正はなぜ達成されなかったか―戦後日本の憲法改正運動の変遷から―http://www.hmt.u-toyama.ac.jp/ir/sotsuken/2004/final/ shimizu-final-rev.pdf,2013年6月3日最后訪問。
28Carl Schmitt,Die Verfassungslehre,8.Aufl.,Berlin:Duncker&Humblot;1993,S.14.
29[日]美濃部達吉:《憲法學原理》,歐宗佑、和作霖譯,湯唯點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頁。
30其原文和英文官方譯文如下:第九條日本國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國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國権の発動たる戦爭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國際紛爭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二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國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ARTICLE 9.Aspiring sincerely to an international peace based on justice and order, the Japanese people forever renounce war as a sovereign right of the nation and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s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2)To accomplish the aim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land,sea,and air forces,as well as other war potential,will never be maintained.The right of belligerency of the state will not be recognized.
31參見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ronten/02ronten.html,2013年3月7日最后訪問。
32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一公約《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的公約》(Geneva Convention I);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二公約《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的公約》(Geneva Convention II);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三公約《關于戰俘待遇的公約》(Geneva Convention III);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四公約《關于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Geneva Convention IV)。
33日內瓦第一公約在考慮到經由“武裝沖突”而導致戰爭狀態進入的情況時指出:本公約適用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間所發生之一切經過宣戰的戰爭或任何其他武裝沖突,即使其中一國不承認有戰爭狀態。
36該法的正式名稱為:日本國憲法の改正手続に関する法律(日本國憲法修改手續相關法律),平成19年5月18日法律第51號。
37自由民主黨:日本國憲法改正草案,http://www.jimin.jp/policy/policy_topics/pdf/seisaku-109.pdf,2013年6月26日最后訪問。
38李浩培:《強行法與國際法》,載李浩培:《李浩培文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頁。
39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Article 53,Article 64,May 23,1969,1155 U.N.T.S 331,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679(1969).
40Marc Bossuyt en Jan Wouters:Grondlijnen van internationaal recht,Intersentia,Antwerpen enz.,p.92.(2005);Prosecutor v.Furund?ija,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2002,121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213(2002).
(責任編輯:鄭平)
D F2
A
1005-9512(2013)08-0062-11
柳颯,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涂云新,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挪威奧斯陸大學(U ni versi t y of O sl o)國際法專業碩士。
*本文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一般項目“中國近代憲法的實施與變遷”(項目編號:12SFB2013)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