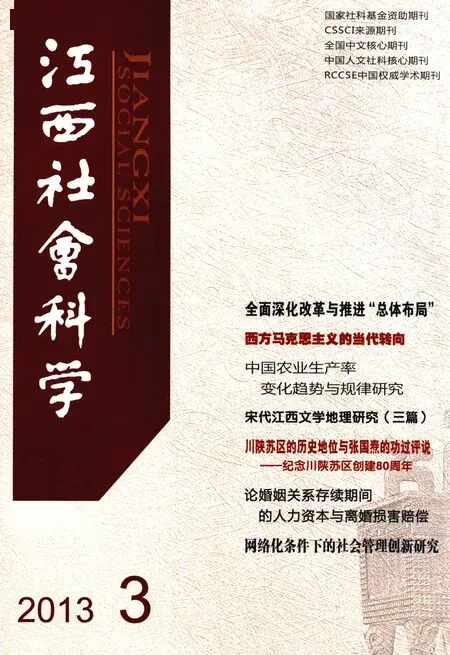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響
■顏 沖
唐宋時期儒釋道開始趨向融合,然而三教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唐時期,儒釋道三教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儒家與佛教的矛盾以及道教與佛教的矛盾。到了宋代,儒釋道之間的斗爭主要表現在儒家和佛教之間,儒家和佛教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儒家入世和佛教出世思想之間的沖突。如何化解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之間的矛盾是儒釋道三教融合進程中勢必解決的問題,宋代居士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作出了重要貢獻。以往學者在對儒釋道“三教融合”或對宋代居士的研究中大多忽視了此點,本文專門闡述宋代居士“儒釋無二、三教融合”論對宋及以后儒釋道三教融合的作用和影響。
一、宋代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及儒釋道三教關系
宋王朝重整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將三綱五常系統化,強化忠君愛國思想教育,同時,利用佛教和道教來控制百姓的思想行為,以此緩解被統治者的反抗情緒。同時,儒、釋、道三家出于自身發展的要求,宋代三教之間的斗爭開始緩和,而相互的融合進一步加深,出現了更多“三教融合”的理論。佛教方面,如宋初佛教首領贊寧認為:帝王“為邦合遵于眾圣”,如信奉佛教,又“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則“其于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耶?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并得出結論說:“三教即和,故法得久住也。”[1](卷下,P255)著名僧人智圓把三教比作治病的三種藥,鼎的三只足。契嵩面對當時的排佛論,“作《原教》、《孝論》十余篇,明儒釋道一貫,以抗其說”[2](卷首《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P648)。道教方面,道士張守真在《翊圣保德真君傳》中論述了三教互補的理論。[3](卷中,P654)張伯端認為:“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后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4](《序》,P914)儒家方面,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的著作《太極圖說》就明顯是主張三教融合為一的代表作。
這時期,儒釋道之間的斗爭主要表現在儒家和佛教之間,至于道教方面,盡管對佛教仍有貶損之詞,但在社會上遠不如儒家對佛教的攻擊影響大。我們這里說的儒家是宋代出現的新儒家,即對儒學進行第二次改造的儒家。新儒家主張重整封建倫理道德,并講究“經世致用”的實用性,這些都與佛教的出世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出現了許多排佛的士大夫,如范仲淹、宋祁、石介、歐陽修、曾鞏和司馬光等人,他們都留有篇幅不等的攘斥佛教的文字,排佛的觀點也大多表現在倫理道德和經濟這兩方面。如宋祁激烈抨擊僧徒們“不徭不役,坐蠹齊民”[5](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費疏》)。石介撰文攻擊佛教:“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遠裔……”[6](卷五《怪說上》)這些攻擊佛教的理論歸根結底還是源于儒家入世治世與佛教出世思想之間的矛盾,入世間法的核心是君臣父子、仁義五常,而出世間法的要義則是成佛作祖、超脫三界。因此,如何解決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的矛盾,是佛教界精英和士大夫中那些從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對佛教甚有好感并有深入研究的佛教居士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的矛盾,也成了儒釋道三教進一步融合過程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宋代居士的“儒釋無二、三教融合”論
宋時,居士佛教得到很大發展,官僚士大夫參禪活動全面展開。南宋禪師道融在《叢林盛事》中記載:“士君子相求于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7](卷二)可見,士大夫參禪學佛在宋代成了一種時髦的社會風氣,許多居士開始對儒家和佛教的思想進行對比研究,紛紛提出“儒釋無二、三教融合”的觀點。
雖然對佛教有好感、有研究的居士在數量上有一定規模,但是,徹底皈依佛教的官僚士大夫終究是少數。長期的世俗生活和儒家思想熏陶,使他們在本質上難以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在最終的選擇上,他們大多傾向于三綱五常、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因此大多數居士所論的“儒釋無二”思想是站在儒家立場進行調和。在處理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矛盾的問題上,他們也是站在儒家立場,援佛入儒,吸收并利用佛教思想來維護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而這種對儒家和佛教之間矛盾的調和,促進了儒釋道三教的進一步融合。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李綱等著名佛教居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不過也有極少數虔誠信仰佛教的居士,他們所提的“儒釋無二”則是從佛教立場出發“援儒入佛”,如王日休等。下面就以這些著名居士為例,來了解宋代居士“儒釋無二、三教融合”的思想。
蘇軾一生與儒、釋、道都有很深的淵源,他學貫“三家”,幼年時就由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8](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P1117)。到“比冠”之年,更是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書。宋人王十朋《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對此有記載:“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9](附錄二,P2833)廣博的學識,卓越的才智,使蘇軾能夠洞察諸家學說思想之機妙,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到儒、釋、道的通融之處。其三教融合的觀點在他貶居黃州所作的《祭龍井辯才文》中就有論述: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凈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10](卷六十三,P1961)
蘇軾認為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是“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在主張三教融合的同時,他也看到了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的矛盾。為了調和這種矛盾,蘇軾模仿契篙所提出的:“儒所謂仁義理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2](卷八《寂子解》,P686)也對儒佛兩家的重要概念做比附: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匱。[10](卷二十《觀世音菩薩頌》,P586)
可以看出蘇軾在具體的觀點上雖與契篙有所不同,但在方法上其實是一樣的。而蘇軾的“四本無”、“大圓覺”更是從更高的層次徹底消弭了儒、釋兩家的界隔。在他逝寂的那年,他還寫了一篇文章,以強調儒釋的同一無二:
孟子則以為圣人之道,始于不為穿窬,而穿窬之惡,成于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圣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10](卷十二《南華長老題名記》,P393)
文中,蘇軾引用孟子的話,來說明圣賢之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差別其實往往在一念之差,而佛教認為普通人與佛之間也在一念之間,只要具有“一念正真”,普通人也可以成佛。所以蘇軾說儒家與佛教“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可見,人的一念之差形成人的善惡觀,這點在儒學與佛法之中都是相通的,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其實是同一無二的,這就是蘇軾調和儒佛矛盾、融通兩者思想的總結。
無盡居士張商英也會通三教,他對三教的社會作用有著深刻的理解,在三教融合成為主流社會思潮的氛圍下,他也積極倡導三教融合。面對一些士大夫不斷提出的排佛理論,張商英提出了自己的護法理論,并對儒釋二家進行了對比:
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11](P643)
文中,張商英對儒家入世和佛教出世的思想進行了相當全面的比較,他對這兩種不同思想進行對比的目的,不是說明它們之間的矛盾性,而是通過對比來說明儒家入世和佛教出世思想的互補性。在張商英的思想里,儒家的主體地位是無法撼動的,他提出儒家和佛教思想互補性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援佛入儒,吸收佛教的思想來幫助儒家的治世,從而調和它們之間的矛盾。
我們從張商英的撰文中,可以進一步了解到他的援佛入儒的思想。張商英在《護法論》中對佛教輔助儒學的功能進行了闡述,他說:
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后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為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于眾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于一切眾生。
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盤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后世圣君,為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凈,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茍能以禪律精修,于天地無愧,表率一切眾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圣,上助無為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為如來弟子矣。[11](P640)
文章強調了佛教能“使其折伏憍慢,下心于一切眾生”,“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圣,上助無為之化,密資難報之恩”等有助于社會治理的功能。這些治世的功能就是張商英援佛入儒,使其輔助儒學治世的原因。可見張商英雖然是宋代著名的佛教大居士,但在調和儒家入世和佛教出世思想矛盾的時候,還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儒家的立場上。
王安石一生的學術宗旨是要建立新經學、新儒學來統一全社會的思想。他建立的新儒學的最大特點,是融合了道、佛、法等其他流派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想。這種想法在其主政時期,已有所表現,他與神宗曾有過如下對話:
安石曰:“……臣觀佛書,乃與經合,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合擾符節。”上曰:“佛,西域人,言語即異,道理何緣異?”安石曰:“臣愚以為茍合于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易。”上曰:“誠如此。”[12](卷二三十三,熙寧五年五月甲午條)
在這段話中,王安石將佛經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認為佛書與六經本一無二,因為其真理是本一的,不以地域之異而異,兩者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神宗也認為佛陀雖說異域之語言,但所說“道理”和儒家似無二致。
此外,王安石還將佛教出世超脫的境界與儒家的“仁義”進行了比較,如他在《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中就認為:“(佛老之徒)多寬平不伎,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于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于彼,而可與言者邪?”[13](卷三十五)在他看來,佛家的“不伎”,相似于儒家的“仁”,而佛家的“無求”,則類似于儒家的“義”,從而認為佛教的境界與儒家是一致的。
黃庭堅雖然是佛教居士,但他一生始終以儒家之徒自居,一直為儒學的復興而努力,他認為儒家之道是根本,佛、道二家則為其所用,并力圖從儒家的立場出發,圓融佛、道兩家思想。如在《與王雍提學》中,他就明白地肯定了儒佛同一的觀點,“大概佛法與《論語》、《周易》意旨不遠”[14](卷十九)。認為儒家《論語》的主要思想與佛教“遷善改過,不自覆藏”是一樣的。在肯定儒佛同一的同時,他也不斷吸收佛教的思想,以期達到真正的“內圣外王”,如在《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中所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于世教,豈小補哉?”[15](卷四,P568)可見,黃庭堅以儒家的刑賞為“外王”,而把佛教“心凈無欲”超脫于世間之外的出世精神用以治其內,由此調和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的矛盾,并促進了儒釋的進一步融合。
李綱是位儒釋道三教兼治的佛教居士,但究其根本,還是以儒為“正道”的儒者,正如他在《拙軒記》中所說:“究余生于釋老,味正道于吾儒。”[16](P1271)李綱對唐宋以來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甚為推崇,因此在調和儒釋道三教關系方面,也有很多的論述。如在《三教論》中說道:“治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弗論以助教化,以通逍遙。”[16](P1360)他主張以儒學為治國之本,以釋道二教輔助教化,并認為:“釋氏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16](P1360)利用佛教“六度”修行,來達到減輕人們內心的壓抑性情感目的,也就是所謂的通“逍遙”。又如,吳敏給在雷陽的李綱寫信,求出世之法,問《易》與《華嚴經》二者之別時,李綱回信說:“《易》立象以盡意,《華嚴》托事以表法,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最后總結說:“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16](P1068)總的說來,李綱對于釋道二教,并未真正虔誠信仰,對于它們的發展,還是主張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他調和儒釋矛盾,推崇儒釋道三教合一,主要是為了援佛道入儒,維護儒家的統治地位。
除了上述站在儒家立場上對儒佛矛盾進行調和的士大夫居士外,也有少數虔誠信仰佛教的士大夫居士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矛盾進行調和,王日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龍舒增廣凈土文》中對修行凈土宗追求出世間法進行了辯解,認為凈土宗的出世間法與儒家的世間法是相互共通的:
儒釋未嘗不同也。其不同者,唯儒家止于世間法,釋氏又有出世間法。儒家止于世間法,故獨言一世而歸之于天。釋氏又有出世間法,故知累世而見眾生業緣之本末,此其所不同耳。[17](卷一《凈土起信四》)
文中認為儒家和佛教都是戒惡勸善的,佛教的十大戒律以及戒貪、嗔、癡“三毒”與儒家的德、義、禮、信思想是相一致的,從這點來說,佛教也是入世的,與儒家一樣也是世間法,但是“儒家止于世間法,釋氏又有出世間法”,佛教的出世間法中包含了世間法,由此得出,佛教出世間法是高于儒家的世間法。可見,王日休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兩者矛盾進行調和,是“援儒入佛”,這同蘇軾、張商英、王安石等居士“援佛入儒”的做法完全不同,不過在對儒佛矛盾的“調和”效果上是一致的。
三、宋代居士三教融合論的影響
宋代,居士佛教進入了一個非常興盛的時期,隨著居士佛教的迅猛發展,宋代的佛教居士隊伍得到了壯大。據文獻記載,宋代佛教居士應該有一百多位,其實嚴格地說,宋代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居士階層,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其總數量遠不止這一百多位。而文獻所記的一百多位居士都是居士階層的精英,這些士大夫居士或是位高權重的朝廷官員,或是聞名于世的文壇巨匠,或是兩者兼具,其不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性作用,他們大多皆精通儒、釋、道,其思想不僅代表了宋代居士佛教的主流,在儒家及道教中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在唐宋儒、釋、道進一步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他們調和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思想矛盾,主張儒釋無二、三教合一的觀點,自然成為一種流行的思想潮流。
雖然在宋初也有一些高僧倡導“儒釋無二、三教合一”,對佛教居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他們從佛教的立場來提倡“儒釋無二”,其目的是以佛教為主,援儒入佛,在儒和佛的境界之高低上更多的是傾向于佛高于儒。如智圓稱:“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為之內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18]
(卷十九《中庸子傳上》,P110)他認為儒是“飾身”的外典,而佛教則是“修心”的內典。契嵩在強調佛教與儒家一樣高度重視孝道的同時,也意識到出家人對父母在奉養上不足的問題,于是他又提出了孝行與孝理。“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2](卷三《原孝章第三》,P660)孝行就是孝在行動中的具體表現,而孝理則是決定這些具體表現的本質。他認為,行孝行是小孝,明孝理才是大孝,提出佛教明孝理比單純地奉養父母雙親境界要高得多。宋代僧人這種從維護佛教立場上倡導的“儒釋無二”思想,與宋代居士以維護儒家統治地位為根本、援佛入儒的“儒釋無二”觀點,是有所區別的。顯然,相比而言,宋代居士的“儒釋無二”思想更容易得到統治者以及社會各階層的認可,由此能更為廣泛地促進以儒家思想為統治地位的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發展。
宋代居士“儒釋無二、三教融合”的思想對后世的三教融合思想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代著名居士劉謐所撰的《三教平心論》,對儒釋道三教關系進行了論述,劉謐也將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無常進行了比較和融通,并認為“三教之興,其來尚矣,并行于世,化成天下。以跡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疏焉”,并得出儒、釋、道究其根本是一而非三的三教融合論。元代僧人釋祥邁所撰的《至元辯偽錄》也對儒釋道三教進行了比較,他認為:“佛教慈悲利生為本,老君謙退遠害為功,儒法濟民忠孝為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后患,慈悲行則可以濟群靈窮性命,沿淺至深,表里相救。”明洪武年間,居士沈士榮著《續原教論辯解》十四篇,從心性方面闡述三教一致,歸于至善。明末的四大高僧無不高唱“三教合一”的論調,云棲祩宏認為三教同源又同理,他說:“三教……理無二致,而深歷然,深淺雖殊,而同歸一理。此所以為三教一家也。”[19](《三教一家》,P290)紫柏真可極力批評那些將儒家與佛教思想對立起來的片面觀點:“我得仲尼之心而窺六經,得伯陽之心而達二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自古龍無首吉,門墻雖異本相同。”[20]
(卷一《題三教圖》,P100)“夫身心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于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人天百萬,圣凡交羅,獨迦葉氏亦得之,自是由阿難氏乃至于達磨氏、大鑒氏、南岳氏、青原氏,并相繼而得之,于是乎千變萬化……世出世法,交相造化。”[21](卷十二《釋毗舍浮佛偈》,P840-841)他認為儒釋道本為不可割裂的一體,并把佛教所講的“湛然圓滿而獨存”的“先天妙心”定為三教之本。憨山德清在談到入世與出世時提出:“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則一偏,缺二則隘。”[22](卷三十九《學要》,P777)他把儒家經典《春秋》與佛教的參禪,作為追求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基本要素,并從“三教唯心,萬法唯識”的觀點出發,認為“三教本來一理”、“三圣本來一體”,三教“體用皆同”,從而得出經世、忘世、出世皆一的結論。清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都積極主張融合佛儒,譚嗣同的《仁學》尤為儒佛合一之作。從后世居士、僧人的這些言論可以看出,他們倡導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在宋代居士三教融合論上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
東漢佛教初傳之時,首先是出現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后經過近千年的相互斗爭與融合,在唐宋之際,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漸讓位于三教合一。宋代理學家以“棄名取實”的辦法引入佛理,并對佛道思想吸收改制,以革新儒學。隨著新儒學的出現、發展及最終被定于一尊,儒佛道三教終于形成了以儒家為主,以佛、道為輔的最佳組合形式,綿延千年之久。宋以后,三教合一逐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流,至今仍在社會文化生活中潛移默化地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儒佛道三教長期的融合過程中,宋代士大夫居士主動調和儒家入世與佛教出世之間的矛盾,積極倡導“儒釋道三者為一”的思想,可謂功不可沒。
[1](宋)贊寧.大宋僧史略[M].大正藏本(第5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2](宋)契嵩.鐔津文集[M].大正藏本(第5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3]翊圣保德真君傳[M].道藏(第3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4](宋)張伯端.悟真篇[M].道藏本(第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5](宋)宋祁.景文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8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6](宋)石介.徂徠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7](宋)凈善重集.禪林寶訓[M].大正藏本(第4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8](宋)蘇轍.欒城后集[C].北京:中華書局,1990.
[9](宋)蘇軾.蘇軾詩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2.
[10](宋)蘇軾.蘇軾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宋)張商英.護法論[M].大正藏本(第5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1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3](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4](宋)黃庭堅.山谷老人刀筆[M].清刻紛欣閣叢書本.
[15](宋)黃庭堅.山谷別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1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16](宋)李綱.李綱全集[C].長沙:岳麓書社,2003.
[17](宋)王日休.龍舒增廣凈土文[M].大正藏本(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18](宋)智圓.閑居編[M].萬續藏經本(第10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19](明)礖宏.正訛集[M].大藏經補編本(第2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20](明)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別集[M].萬續藏經本(第1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21](明)紫柏真可.紫柏尊者全集[M].萬續藏經本(第1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22](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游集[M].萬續藏經本(第1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