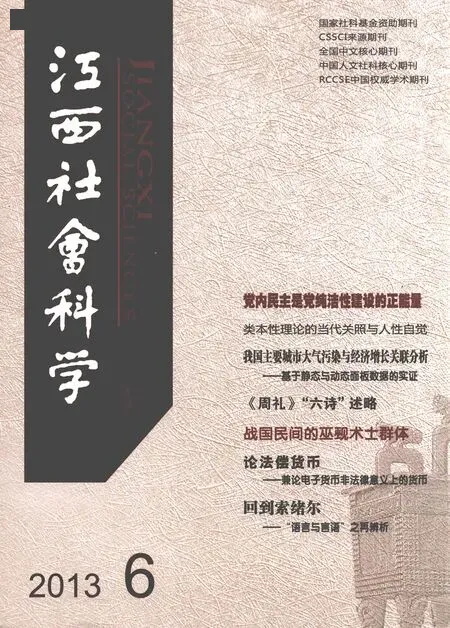原始佛教的本體論意蘊
■宇恒偉
一、問題的提出
古希臘哲學、古代中國哲學和古印度哲學被譽為世界三大哲學。其中,古希臘哲學是典型的西方哲學,古代中國哲學和古印度哲學則是東方哲學的代表。近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展開,東西文化的交流和對話成為一種新的趨勢。東西哲學的比較也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
古代以及近現代的西方哲學在路徑上有很大的差別,以致諸多學者提出,后現代消解了西方哲學,或者說,傳統西方哲學的追求在后現代主義中并不存在。其中,本體是最被后現代主義放棄的一個概念。現代以前的西方哲學,本體概念幾乎貫穿于哲學發展的始終,而本體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的不斷演化也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近代以來,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都被以本體概念來詮釋和構建內容以及體系,這種方法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的本來面目。關于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是否合法的問題成為新的學術話題。實際上,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黑格爾極力推崇以古希臘哲學為源頭的西方哲學,而對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嗤之以鼻:“史上哲學的發生,只有當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了的時候。精神必須與它的自然意識,與它沉陷于外在材料的情況分離開……東方及東方的哲學之不屬于哲學史。”[1](P112)換言之,黑格爾認為,哲學應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也就是說,哲學的產生必須是獨立的,不受政治制度的制約。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哲學剛開始產生的時候與社會政治生活、其他學科沒有直接的關系;二是哲學所思索的問題具有獨立性。黑格爾發現,東方哲學與宗教含混不清,并且在內容上缺乏創見和獨立性。以西方哲學的范式來看待東方哲學顯然突出的只是西方哲學的特點,但東方哲學特點恰恰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
從本體論的角度審視印度佛教哲學就會發現,東方哲學在人類關懷的終極問題上同樣具有本體的意義。只是在具體的展現形式上、有些方面不同于西方哲學,有些則是所有哲學共同關注的問題。因此,思考原始佛教的本體論問題既可以開拓新的視野,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補充西方哲學的不足,能更清晰地認識以佛教哲學為代表的古印度哲學的基本特征。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軸心時代”理論,他認為,在公元前200年以后600年左右的時間內,在古希臘、中東、古印度以及古中國等多個地方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圣者”,他們對于人類哲學的闡發成為歷史上不同哲學的源頭。具體到古希臘哲學中,本體雖然是首先出現的一個語詞,然而近代以來它廣泛影響于東方哲學。因此,本體雖是作為西方哲學源頭的重要詞匯,但是完全可以借用于對佛教哲學的解讀。
二、原始佛教的本體傾向
本體論是西方哲學出現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最早由德國哲學家沃爾夫提出,在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中有明確的定義:“本體論,論述各種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學范疇,如‘有’以及‘有’之成為一和善,在這個抽象的形而上學中進一步產生出偶性、實體、因果、現象等范疇。”[2](P189)根據這個定義,本體論實則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一般認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實際上,柏拉圖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雖沒有形成系統的本體論思想,但是從某些層面已經觸及本體論的有關問題。泰勒斯、蘇格拉底等對世界本原問題的追問實際上也是一種本體論。
本體在古希臘哲學中具有特殊的含義,它是在對萬事萬物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通過個性總結出共性,通過現象總結出本質,進而進行理論提升的一種學說。柏拉圖的理念論被當作最初的本體論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的。所以,俞宣孟講道:“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里表述了一種新的理念論。在這個新的理念論里,柏拉圖拋棄了事物對理念的分有說,也暫時置我們的世界不顧,專門到理念世界里去經營理念間的關系。”[3](P270)一方面,萬事萬物分有了理念;另一方面,理念也是現實世界的本質。本體論的主旨在于理念以邏輯發展的形式形成了現實世界。因此,本體論就是一種邏輯學。當然,這種邏輯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不太一樣,后來基督教的上帝造人、“單子論”等學說才是本體論最經典的表達方式。應當看到,后來西方哲學的諸多本體論實則偏離了柏拉圖最初的本體論,因為本體論在西方哲學發展中進一步衍生出了本質、基礎、本原等含義。
本體論雖然有非常明確的指向,但是其內涵不斷變化。以柏拉圖的理念論為參照,對于認識原始的特征仍然是有所裨益的。原始佛教理論從幾個方面展現了與本體論相近的傾向。
1.原始佛教也在探討世界的本質問題。比佛教更早的婆羅門教以及與佛教同時代的沙門思潮一直在探尋世界從哪里來的問題。作為古印度正統宗教的婆羅門教,崇尚“我是梵”、“梵我合一”、“祭祀萬能”等三大綱領,對于人類在天地之間的處境進行哲學反思。其中,以《薄伽梵歌》、《奧義書》等基本方式展現出對世界的思考。在婆羅門教看來,“梵”是創生萬物的神靈,和人一樣具有情感。從這個層面而言,“梵”具有和古希臘哲學“始基”相同的意義,即和本原是一樣的。在婆羅門教的觀念中,梵天和現實世界之間具有統一性,所有的現實事物都可以從中找到根源,找到原初意義。這和柏拉圖的“理念論”是非常相似的。以現象和本質以及本原等問題反觀婆羅門教,能非常清晰地看到本原問題具有普遍性。雖然“梵”不是直接關于本體的邏輯規定,但是在最終的指向上有本體的傾向。沙門思潮的“地、水、風、火”等也是追問世界的本質。作為反婆羅門或者反傳統的宗教,原始佛教提倡無明的反面般若就是通過認識層面反思世界的本質。相對于《薄伽梵歌》為代表的古印度傳統,原始佛教則具體通過對法、我等問題的探討,在分析層面表現出本體論的特征。
2.原始佛教哲學從人生哲學開始,進而涉及諸如輪回轉世、涅槃等問題,與本體論也有一定的聯系。從苦開始,十二因緣成為重要的理論。有生才有死,生是死的根由。生、有、取、愛、受、觸、六入、名色、識、行、癡依次構成了生死流轉過程中的因緣。釋迦認識到癡是最具有決定性的根源。癡消失了,業行、心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等也會隨之消失。這種認識的更深層次植根于輪回轉世。輪回轉世既是一個宗教話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從人類的思維向度看,輪回必須有轉世的主體,但是又與“無我”相矛盾。這個二律背反問題是在哲學領域解決的。部派佛教哲學對補特伽羅問題的探討就屬于輪回轉世范疇。從人生哲學所觸及的輪回轉世等思想看,原始佛教哲學的本體論傾向是非常明顯的。應當承認,原始佛教對于輪回的探討并沒有很精細的理論論證,但卻是滲透于佛教發展始終的最為重要的理念之一。輪回觀念的繼續發展不僅表現出本體論,經過大乘有宗的發揚帶而有了更多認識論和邏輯學的色彩。
三、原始佛教本體論的具體呈現
原始佛教哲學主要是從因果問題展開,以必然性和偶然性問題為補充,通過形而上學的探討集中展現了本體論的傾向。
(一)因果關系是原始佛教哲學本體論的核心體現
作為沙門思潮的一種,佛教和其他沙門思潮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和婆羅門教更是尖銳對立。但是,對于因果關系的探討則是共同的,即佛教也力圖解釋人類苦悶的根源。從因果關系的邏輯中看,因果之間也是相互制約的。一般而言,原始佛教一直在強調萬法待于因緣,即因緣制約著萬法。但對于什么是因緣卻很難解釋。根據佛陀的看法,不僅萬法之間是相互聯系的,而且因緣之間也是相互聯系的。根據一般的思維,果產生于因,但這是否意味著有所謂的第一因呢?根據古希臘哲學的回答,這個第一因就是本原,就是始基,后來逐漸被界定為上帝。根據“因緣和合”的思想,很容易就能推導出萬法依賴于眾因緣。因緣是否有第一個?按照“十二因緣”的說法,所有的煩惱都可以追溯到無明。但是,和古希臘的本原不一致的是,本原強調的是萬法創生的問題,而十二因緣則是從認識層面,即般若層面進行論述的。顯然,和婆羅門教不同的是,“梵天”作為創造神被原始佛教否定了。要消除煩惱,不在于追問什么是萬法的最初因,而是要深入到認識層面進行分析。因此,《雜阿含經》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非常典型地描述了佛教的緣起論。原始佛教的因果并不僅僅限于認識層面,而是與佛教的現世和來世觀念相一致的。原始佛教繼承了古印度傳統的輪回觀,認為因果和業報也是相聯系的。既然有多重因果,要獲得何種因果,就要看個人的修行。這樣,業報輪回就獲得了可依賴的基礎。除此之外,萬物對因緣的依賴還與法的本性相關,所謂“諸法無我”就說明萬物沒有最終的本性,一切都要從因緣中尋求答案。雖然原始佛教的因果觀和本體問題截然不同,但是其中展現的邏輯理路基本一致。在萬法構成的世界中,萬法和我、輪回的關系則是通過“諸法無我”這個理念而體現的。
(二)必然和偶然的關系是原始佛教哲學本體論的補充
佛教哲學的因緣和西方典型的本體論是不同的,但是又隱約滲透著本體論的意蘊。借用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問題審視古印度佛教哲學能更深入地了解印歐語系中的公度。同時要注意到,古希臘哲學的本原具有典型的宇宙生成論的含義,反觀古印度的原始佛教則并沒有相關的理論。不過,在西方哲學的后續發展中,本質、基礎等問題也是本體論的進一步演化。原始佛教中,因緣是萬法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基礎條件,不僅萬法之間存在著聯系,而且萬法之間的聯系成為制約萬法的因緣。從萬法依賴于因緣來看,本原的確不適用于原始佛教,因為原始佛教并沒有探討萬法的起源問題。相反,在“十四無記”問題上,佛陀堅決反對,并認為這和現實訴求是脫節的。但是,佛陀對于“十四無記”的排斥并不意味著原始佛教沒有本體訴求。如果說本體指向的是萬法從哪里來這個問題,那么原始佛教只是從一個側面否定了對未知世界的探尋。在對現實世界的思索中,佛陀認為萬法是無常的,這說明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永恒的實體存在。因此,原始佛教實則從反面表現了本體的內容。
(三)世界的有無、大小、有限無限等問題是原始佛教哲學本體論的直接體現
佛教不同派別對其他一些理論問題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什么是佛與什么是阿羅漢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佛說正確與否也被討論;補特伽羅有無的問題開始逐漸顯露出來;供養制多有無功德;心性染凈等問題都被當作佛教學說的問題加以爭論。其中,訶梨跋摩在《成實論》中集中對各派的問題進行了總結,并提出“十論”為各派不同爭論的焦點:法是否實在;一切現象是否都有;“中陰”有無;領會四諦是頓得還是漸得;羅漢有無退轉;隨眠與心是否相應;心性是否本凈;未受報業是否還存在;佛是否在僧數;人我是否存在。對于這十個問題,不同佛教派別往往有不同的看法,這說明在理論層面上部派佛教已經開始出現巨大的分野,在修行層面當然也會存在巨大差別。此外,諸如佛像崇拜等問題開始出現,并引起紛爭。其中,補特伽羅是一個核心問題。根據南傳佛教的說法,阿育王在雞園寺供養上萬出家人,這其中當然有非佛教徒。他有一次著名的結集,這次結集將各種不同的觀點分條陳述結成《論事》。據說各種不同觀點有上千條。第一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補特伽羅問題。指輪回轉生之主體而言,即“我”之異名。佛教主張無我說,故不承認有生死主體之真實補特伽羅。但為解說權便之故,而將人假名為補特伽羅。佛教中,犢子部、正量部、經量部等,卻承認補特伽羅為實有。其他各派,并未直接承認,但默許存在。這種說法遭到了主持結集的目連子帝須的反對。當時的各派向各地傳播,分裂也日益加重。后來,特別是隨著唯識宗的發展,補特伽羅問題才成為典型的本體論問題,因為唯識宗正式通過邏輯的方式解釋主體和客體關系的。
(四)對法的看法也集中展現了原始佛教哲學的本體論特色
龍樹在《中論》中對“空”作了這樣的說明:“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空”實際上是對“性空幻有”的進一步認識。般若經集中論述的是“性空幻有”思想。所謂“性空”指的是一切都沒有實在的自性;現象雖無自性,但以“幻有”的形式呈現出來,因而也是一種有。當認識到這兩點時,也就達到了空。一方面,法是空無自性的;另一方面,法是假名。只有認識到這兩點,才符合中道。法空無自性,指法依賴于因緣。而從思維或認識講,法是人們給予事物的名號,它本身并無意義,并非真實存有。因而,“亦是中道義”以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結尾,體現出中觀。龍樹的“空”觀,從因果關系入手,以本質和現象的關系為貫通,以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為歸宿,通過簡潔的語言,描述出“中觀”豐富的內涵。與此一致,原始佛教對法的看法,如對色認識的理論色彩有欠嚴謹,但在邏輯理路上和中觀是完全一樣的。
(五)心性問題也是原始佛教哲學本體論關注的問題之一
佛教哲學中的心性學說與佛性、唯識、佛陀觀等密切相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心性也被包容于佛性、唯識、佛陀觀內。作為貫穿印度佛教的成佛問題,心性一直是一個中心話題。從現代學科層面看哲學,佛性基本上屬于哲學問題。心性學的貫穿作用表現在它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天人關系、名實關系、知行關系、理等范疇和概念都與此相關或闡發而來。在心性問題上,既有“心性本凈、客塵所染”的看法,也有不一定凈的看法,這涉及心與境的關系、心性的地位和性質等問題。“南方上座的《法聚論》,對心的性質、好壞、地位、階段等詳加分析,得出了八十九種范疇。”[4](P43-44)很明顯,這種分析方法和柏拉圖的本體論非常相似。
四、小結
原始佛教哲學沒有典型的本體論,因果關系、無限有限、輪回轉世、法我等思想雖然很容易通向本體論,但是柏拉圖的本體論最主要的是采用邏輯方法,而原始佛教哲學在這方面非常欠缺,在中期佛教哲學中這個問題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特別是佛教哲學的因明學,即邏輯學開始成熟,唯識宗等理論層面最為豐富的學說支撐著佛教不斷發展。
佛教哲學的因緣具有不同于西方本體論的獨特性,但它隱約地呈現著某些本體的軌跡和內容。在佛教中簡單地套用本體是不合適的,但佛教用自己獨特的形式表現出了大致相同的內容。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本原就是萬物賴以存在的始基,而這是典型的生成論的觀念。佛教的因緣表達的是萬物的聯系性。因緣生法指萬物依賴于各種條件而存在。兩者的差別非常明顯,本原表示萬物由它生成,并且在邏輯和時間上本原也先于萬物而存在。因緣指的是事物的聯系性和條件性,既然事物是相互依賴的,那么就不會有誰產生誰的問題。所以,因緣不具有本原意義,它是一種非本體論。但非本體還是對本體問題的一種看法,只不過它采取了否定的態度。佛教的“無我”、“無常”和涅概念集中表現了佛教關于本質的認識。無常說明世間萬物是變化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東西,即無自性、無體。無我是承認沒有主體的存在。涅是對無我、無常以及人死后的說明。所以,佛教以非本體的形式表現了本體的內容。
佛教哲學本體論問題的意義主要在于,通過西方哲學范式對東方哲學加以解釋,進而了解不同哲學之間的異同,為東西方哲學的交流提供借鑒。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5](P121)佛教領域中,佛教哲學有很多表現,可以利用分析方法進行分割,例如因明學、因緣學說等。佛教哲學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佛教哲學與西方哲學可以相比較而顯現出自身的特點。以因明為例,它與形式邏輯在某些方面有些類似,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多樣性和共通性。二是佛教哲學在某些方面具有自身的特點,顯現出與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不同的內容。
[1](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2](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3]俞宣孟.本體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