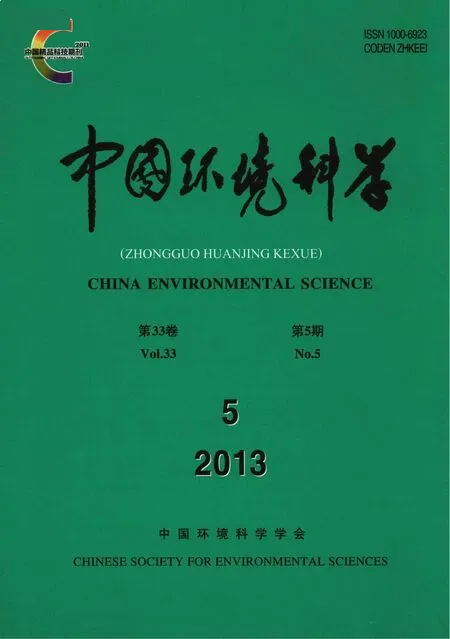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郭利成,陳秀玲,賈麗敏
(1.福建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福建省濕潤亞熱帶山地生態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福建 福州 350007;2.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地質與環境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29;3.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4.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城市環境與健康重點實驗室,福建 廈門361021)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地表灰塵在城市地表的分布不斷擴張,成為典型的非點源污染之一[1-5].對此,多數學者認為城市地表灰塵是指分布于城市不同區域表面,易于遷移并且粒徑小于0.920mm的固體顆粒物[6],是城市大氣塵埃與地表塵土長期在人與自然力作用下的綜合體,是城市環境中各種污染物質的“源”和“匯”[1,7].在一定的外動力條件(如風、車輛行駛等)下,城市地表灰塵能夠和大氣顆粒物相互混合,成為城市環境中典型的“點、線、面”型污染[8-9].此外,城市地表灰塵所附帶的各種污染物質能夠在城市不透水下墊面上發生強烈的徑流效應,從而進入城市流域,通過城市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形成潛在的污染生態效應[10].因此,城市地表灰塵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7,8,11-19].
目前,對于城市地表灰塵的研究成果主要依賴于傳統的物理和化學分析方法,其測樣成本高、樣品受損程度大、方法復雜等缺點限制了城市地表灰塵的研究,而環境磁學具有進樣量少、靈敏度高、操作簡單、耗時少、破壞小、價格低等優點[20-21],在相關學科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22-23].大量研究表明[21],工業活動、燃料燃燒、汽車尾氣等污染物主要的成分是不同磁性礦物,具有不同磁學特征,故環境磁學是研究城市污染程度的有效手段之一.國內外不同學者對城市降塵、街道塵埃等城市顆粒污染物的來源、粒度、元素濃度、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進行多角度研究[24-45],且我國對城市灰塵磁學特征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北京、西安、蘭州等污染嚴重的城市,而福州市的研究鮮有報道[46-47].其中,福州市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中心城市,是福建省的文化、政治、科研中心,也是中國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度較高的地區之一,經濟發展迅速,環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經濟增長呈正相關[48],故環境污染物的有效監控是保障福州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城市公園是城市居民提高身心健康的最佳場所之一.因此,本文對海峽西岸中心城市——福州市進行公園灰塵的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研究,有助于提高福州城市環境質量,對深入開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環境磁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福州市(25°15′~26°39′N、118°08′~120°31′E)位于大陸東南沿海的閩江下游地區,所在地屬于典型的河口盆地,盆地四周群山峻嶺所環抱,海拔多在600~1000m,地勢自西向東傾斜.福州市屬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夏長冬短,年平均溫度為16~20℃,1月平均溫度6~10℃,7月平均溫度24~29℃,年均降水量 900~2100mm,無霜期達 326d,年平均日照數為1700~1980h,年相對濕度約77%.地帶性土壤為紅壤,市區河漫灘和河流階地上的隱域性土壤類型為潴育水稻土.2010年統計數據表明,福州市市區面積1786hm2,常駐人口 292.18萬人, GDP為1545.23億元,福州市規劃人均綠化面積到2020年達15m2,綠化覆蓋率達到48%.

圖1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采集點分布示意Fig.1 Distribution of dust sampling sites of parks in Fuzhou
2 材料與方法
2.1 樣品采集
為了較系統的研究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特征,本文以福州市區范圍內的 11個公園(森林公園、溫泉公園、西湖公園、茶亭公園、南江濱公園、金山公園、烏龍江濕地公園、倉前公園、亞峰公園、長安山公園、勞動者公園)作為研究對象(采樣點分布見圖1).于2011年6~10月,按照梅花均勻采樣法,每個公園布 26個采樣點,根據各個公園的規模以及人群集散程度,分別在人群比較密集的公園門口、公園道路、休憩區、娛樂區等地,用塑料鏟和毛刷清掃灰塵,將每個公園中各點采集樣品混合成一個混合樣,分別放入事先已標記好的聚乙烯塑料袋中密封保存.
2.2 實驗方法
所有采集樣品自然風干,過2mm尼龍分樣篩以剔除非灰塵物質,裝入8mL磁學專用樣品盒、稱量、壓實,供磁測.選用英國Bartington 公司生產的 MS2型磁化率儀測定樣品磁化率(χ):包括低頻磁化率(0.47kHz)和高頻(4.7kHz)磁場中的磁化率(χlf、χhf),并計算出百分頻率磁化率值(χfd%=(χlf-χhf)/χlf×100%);用美國 ASC 公司生產的IM-10-30脈沖磁化儀(磁場范圍在0~300 mT和1T)磁化,用Minspin小旋轉磁力儀測定樣品的等溫剩磁(IRM)和飽和等溫剩磁(SIRM);選擇部分代表樣品,用振動樣品磁強計(VSM-VersaLab)及磁電效應綜合測試系統測量樣品的磁滯回線,其中最大磁場設定為 1T.環境磁學通常設定 1T的磁場中所獲得的等溫剩磁為飽和等溫剩磁(SIRM),反向磁場包括-20,-40,-100和-300mT,在本文中表示為 SIRM 的百分含量,依次為
S-20mT,S-40mT,S-100mT 和 S-300mT,樣品在剩磁值為
零時的反向磁場大小,稱之為剩磁矯頑力Bcr;定義軟剩磁 Soft=(SIRM-IRM-20mT)/2,硬剩磁HIRM=(SIRM+IRM-300mT)/2,F300mT(%)=(IRM300mT/SIRM)×100%,S-20mT(%)=(IRM-20mT)/SIRM)×100%,S-100mT(%)=[(SIRM-IRM-100mT)/(2×SIRM)]×10 0%,S-ratio=-IRM-300mT/SIRM.樣品前處理和測量均在福建師范大學濕潤亞熱帶山地生態省部共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和福建師范大學材料與物理創新實驗室完成.所測量的磁化率、等溫剩磁結果均用質量進行校正,獲得質量磁化率(χ)、等溫剩磁(SIRM、IRM)等.
3 結果與分析
3.1 福州市公園灰塵的磁化率和頻率磁化率
福州市公園灰塵χ變化范圍為 42.50×10-8~895.51×10-8m3/kg,平 均 值 為 269.80×10-8m3/kg;χfd%變化范圍為 0~2.18,平均值為 0.73.福州市公園不同功能區中,公園門口和道路灰塵χ相當且最高(表 1),休憩區最低;公園灰塵χfd%最高為休憩區,而門口最低.χ和樣品的磁性礦物的類型、粒徑和含量直接相關,可粗略估算樣品中亞鐵磁性礦物(如磁鐵礦)的含量[21],而χfd%是反映沉積物中接近穩定單疇(SSD)與超順磁性過渡態的磁性顆粒存在的指標,可以反映超順磁性顆粒的相對含量[49].福州市公園灰塵χ總體偏高,且χfd%總體偏低,直接反映了福州市公園灰塵中磁性礦物含量總體較高,超順磁性顆粒幾乎不存在.旺羅等[28]研究發現,污染區χ越高,而χfd%越低,樣品污染程度越高,故福州市公園灰塵污染程度較高,不同功能區污染程度:門口>道路>娛樂區>休憩區.
3.2 福州市公園灰塵的剩磁及其組合參數
由表1可知,福州市公園灰塵SIRM總體偏高,變化范圍 1048.84×10-5~15991.40×10-5(A·m2)/kg,平均值為 6175.07×10-5(A·m2)/kg,休憩區和門口SIRM較道路和娛樂區高.由于SIRM不受順磁性和抗磁性礦物影響,但極易受磁性顆粒大小、形狀的影響,主要體現樣品中等溫剩磁的主要貢獻者(亞鐵磁性及不完全反鐵磁性)含量,和χ散點分布圖可以指示磁性礦物類型和數量[20].因此,福州市公園灰塵SIRM總體偏高,表明福州市公園灰塵中亞鐵磁性和反鐵磁性礦物含量較高,公園灰塵的磁性礦物中游客停滯區比流動區高;SIRM與χ關系圖呈散點分布(圖2),線性關系差(R2=0.101),說明福州市公園灰塵部分樣品以亞鐵磁性礦為主,而其余部分樣品則以高矯頑力的反鐵磁性礦物(赤鐵礦等)為主,但均為高低矯頑力磁性礦物的混合樣品.
福州市公園灰塵Soft變化范圍313.50×10-5~6425.16×10-5(A·m2)/kg,平均值 為 2174.03×10-5(A·m2)/kg,HIRM 變化范圍 22.31×10-5~2314.18×10-5(A·m2)/kg,平 均 值 為 312.74×10-5(A·m2)/kg,Soft遠大于 HIRM,在公園的四個不同的功能區也是 Soft遠大于 HIRM; S-ratio變化范圍0.71~0.99,平均值為 0.91; S-20mT平均值 29.59%,S-100mT平均值為 85.84%,F300mT平均值達 91.41,公園四個功能區規律基本一致;SIRM/χ變化范圍 1.99~ 137.62×103A/m,平均值為 30.82×103A/m,門口、道路和娛樂區的SIRM/χ值接近,小于休憩區,但總體偏小.其中 Soft主要反映多疇(MD)和假單疇磁性晶粒(PSD)的低矯頑力亞鐵磁性礦物含量,HIRM 反映高矯頑力的不完全反鐵磁性礦物含量[44];S-ratio通常也可以反映樣品中高矯頑力組分(如赤鐵礦)與低矯頑力組分(如磁鐵礦)含量的相對多少[20],且已有報道中表明三價鐵磁性礦物 S-ratio值高于斜反磁性礦物[49];S-20mT、S-100mT和F300mT可以指示樣品中亞鐵磁性礦物的含量和相對含量[42],S-20mT達 30%和 S-100mT達80%可以說明樣品主要磁性礦物為亞鐵磁性礦物[50], F300mT隨著亞鐵磁性礦物含量的增加而增加[51]; SIRM/χ也可以反映磁性礦物的類型[52],實驗證實,磁鐵礦 SIRM/χ值約為 1.5×103~50×103A/m,赤鐵礦 SIRM/χ值大于 200×103A/m,而磁黃鐵礦 SIRM/χ值也較高.綜合分析,可知福州市公園灰塵Soft遠大于HIRM,四個不同的功能區也是Soft遠大于HIRM,S-ratio整體較高,SIRM/χ低于 137.62×103A/m,且 4個不同的功能區SIRM/χ均值較小.因此,福州市公園灰塵的剩磁組合參數均表明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整體上表現為亞鐵磁性礦物特征,即部分樣品以低矯頑力磁性礦物為主導的磁學特征掩蓋以高矯頑力磁性礦物為主的樣品.

表1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的環境磁學基本參數統計Table 1 Summary of magnetic parameters of park dust samples in Fuzhou City
由圖2可看出,SIRM和Soft的呈良好的線性相關(R2=0.9544),而觀察福州市公園灰塵等溫剩磁獲得曲線(圖 3)和退磁曲線(圖 4)特征,磁場強度在300mT時,灰塵的等溫剩磁占飽和值 80%以上,且灰塵剩磁矯頑力在30mT左右,反映低矯頑力的亞鐵磁性礦物主導了公園灰塵的剩磁[46,53],而灰塵剩磁在 300mT之后繼續增加[54],證實了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存在高矯頑力磁性礦物組分.結合SIRM與χ關系圖呈散點分布特征,再次證實了福州市公園灰塵部分樣品以高矯頑力特征為主導,但被以低矯頑力特征主導的樣品所掩蓋.
3.3 福州市公園灰塵的磁滯參數
磁滯曲線(loop)是分析樣品軟、硬剩磁組分的有效手段之一[42],其閉合處的場強能夠有效反映主導磁滯行為的磁性礦物.圖5和圖6顯示,除二環公園娛樂區外,其余功能區均表現蜂腰型特征.但磁場強度均在 0~200mT 之間,灰塵磁化強度快速增強,200~1000mT之間增強速率減小,且直到500mT曲線才開始閉合且趨于飽和,500mT以上隨著磁場的增加磁化強度仍有增加,Bcr在10~50mT之間.表明二環內公園娛樂區磁性礦物主要是低矯頑力的亞鐵磁性礦物(主要是磁鐵礦)和少量的高矯頑力磁性礦物(主要是赤鐵礦)混合物[44].而其余功能區磁性礦物為高矯頑力的反鐵磁性礦物和少量的低矯頑力磁性礦物混合物.對比二環內外磁滯回線特征,發現二環外磁滯回線的閉合區間面積明顯大于二環內,揭示了二環外公園灰塵樣品磁性礦物以硬磁性礦物為主,也反映二環內外的磁性特征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二環內集中了城市人類活動,而二環外人類活動減弱,自然環境影響增強,故二者的磁滯回線特征差異很可能與不同因素組合有關.

圖2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χ和χfd%、SIRM和χ、Soft和SIRM相關關系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χ and χfd%,SIRM and χ, Soft and SIRM for park dust samples

圖3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的等溫剩磁獲得曲線Fig.3 Isothermal remanent magnetization (IRM)acquisition curves for selected dust samples

圖4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的退磁曲線Fig.4 Back-field demagnetization curves for selected dust samples

圖5 福州市二環內公園灰塵樣品磁滯回線Fig.5 Magnetic hysteresis loops for park dust samples from inside area of the second ring road

圖6 福州市二環外公園灰塵樣品磁滯回線Fig.6 Magnetic hysteresis loops for park dust samples from outside area of the second ring road
前文分析可知,公園灰塵樣品均以低矯頑力或高矯頑力磁性礦物為主,故以剩余磁化強度和飽和磁化強度比值(Mrs/Ms)為縱坐標,以剩磁矯頑力和矯頑力比值(Bcr/Bc)為橫坐標繪制的 Day圖是確定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的粒度最理想的方法[55],實驗證實,Mrs/Ms>0.5 且Bcr/Bc<1.5的樣品以單疇(SD)顆粒為主;Mrs/Ms<0.5且Bcr/Bc>4的樣品以多疇(MD)顆粒為主;介于二者之間的樣品以假單疇(PSD)顆粒為主.由福州市公園Day圖(圖7)可知,公園灰塵磁性顆粒位于單疇(SD) 顆粒下方和假單疇(PSD)顆粒的左側及其邊界線上,顯示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主要為較粗的SD顆粒和較細的PSD顆粒,但二環外公園磁性礦物顆粒較二環內粗.

圖7 福州市公園灰塵樣品Day圖Fig.7 Day plot of the ratios Mrs/Ms and Bcr/Bc for park dust samples
4 討論
4.1 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參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前文分析表明,福州市公園灰塵整體表現出主要磁性礦物以多種低矯頑力較粗SD顆粒與較細PSD顆粒的亞鐵磁性礦物為主,帶有少量的高矯頑力磁性礦物(赤鐵礦等).其中福州市公園灰塵χ和SIRM總體偏高,灰塵χfd%低,直接反映了福州市公園灰塵中磁性礦物含量總體較高,而幾乎不含超順磁顆粒,且χ與χfd%之間呈負相關(圖2),即公園灰塵χ偏高的主要貢獻者是非自然沉降物質的積累[28];Soft遠大于HIRM,S-ratio均大于 0.9,S-20mT平均值 29.59%,S-100mT平均值為85.84%,F300mT平均值達 92.7,分析等溫剩磁獲得曲線和退磁曲線特征發現灰塵Bcr小于 50mT,而SIRM/χ也總體偏低,均說明了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整體以低矯頑力亞鐵磁性礦物特征為主,但SIRM與χ線性關系差(R2=0.101),磁滯回線的蜂腰型特征,進一步說明了福州市公園灰塵部分樣品是高矯頑力的反鐵磁性礦物為主,剩余部分樣品以低矯頑力的亞鐵磁性礦物為主,尤其在二環內公園娛樂區表現明顯,且這部分樣品的磁學特征在整體上掩蓋了高矯頑力特征.這很可能與福州城市化發展密切相關.
福州市由于現代工業、交通建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大量建筑廢棄物、水泥、磚塊等碎屑物質進入公園綠地土壤,且福州市為盆地地形,由西向東傾斜的地形條件易于夏季臺風的進入,并在盆地中停滯一段時間,導致灰塵吹揚混合降落公園地表,而公園游客步行或乘車游行與游玩活動、公園植樹、拆遷建設等人為活動增加了灰塵進入公園并遷移擴散,同時福州市公園基本上靠近交通要道,汽車尾氣污染物顆粒也容易進入公園上空,隨著降雨而到達地表,大量不同來源鐵磁性礦物顆粒的進入直接導致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含量增加.然而,夏季臺風所攜帶風化殼殘積物,如南方紅土中的高矯頑力磁性礦物(赤鐵礦和針鐵礦)[47],由于福州市盆地地形的滯留效應,也能夠引起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含量的增加.采用 Day圖對福州市公園灰塵顆粒大小進行判別,發現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主要為較粗的SD顆粒和較細的 PSD 顆粒.同時,大部分學者研究發現[56-58],人類活動帶來的磁性礦物顆粒大小主要分布在PSD~MD附近.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的顆粒大小較前人研究結果細,一方面,福州市受冬季風影響小,而西安和蘭州地區冬季風影響大,也有可能導致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顆粒較細;另一方面,其與夏季臺風對人類活動所排放的磁性礦物顆粒與臺風攜帶的風化殼殘積物中的磁性礦物顆粒進行混合后沉降過程密切相關.因此,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參數特征揭示了福州市作為海西建設的中心城市受交通、城市建設等人類活動的干擾、由西向東傾斜的盆地地形條件與公園高綠化覆蓋率的影響,夏季臺風攜帶灰塵顆粒在盆地中產生滯留效應,且公園覆被截留作用,導致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含量較高,其中臺風攜帶的南方紅色風化殼殘積物的反鐵磁性礦物主導了部分樣品的磁性特征,但其余部分樣品以人為活動排放的污染物顆粒的亞鐵磁性礦物特征為主,同時整體上掩蓋了部分樣品的反鐵磁性礦物特征,直接說明了公園灰塵樣品的磁性礦物特征是其磁學特征變化的一個良好指示劑.
4.2 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關系分析
樣品磁性主要受控于磁性礦物組成和含量及其晶粒特征[59].福州市公園灰塵χ變化范圍為42.50×10-8~895.51×10-8m3/kg,平均值為 269.80×10-8m3/kg,比福州市公園土壤χ平均值[60](123.50×10-8m3/kg)高,指示了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含量較高.其中前文分析已表明,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主要是較粗SD顆粒與較細PSD顆粒的亞鐵性磁性礦物(磁鐵礦)或反鐵磁性礦物(赤鐵礦),即夏季臺風對人類活動所排放的磁性礦物顆粒與臺風攜帶的風化殼殘積物中的磁性礦物顆粒進行混合后沉降引起福州公園灰塵的磁鐵礦含量高,較大部分污染物磁性礦物顆粒細.但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礦物磁性主要受哪些灰塵自身內部因素影響需要進一步分析.
城市地表灰塵主要來源于人類活動、工業活動、燃料燃燒、汽車尾氣等非自然沉積物遷移[6],故灰塵磁性礦物含量與粒徑大小對磁性大小影響需要通過磁性礦物的遷移規律及其與磁化率的回歸模型來定性和定量判定.從沉積動力學角度對磁性礦物的沉積規律進行定性分析[61],根據物質遷移規律公式:J=β(ρs-ρ)D,其中J為臨界剪應力,ρs和D為泥沙顆粒密度和粒徑,ρ為水的密度,β為與顆粒形狀及遷移介質雷諾數有關的系數.在一定的動力條件下,泥沙能否遷移顆粒粒徑和密度,據此來討論同一動力條件下,不同顆粒粒徑 和 密 度 的 顆 粒 遷 移 規 律 ,即β1(ρ1-ρ)D1=β2(ρ2-ρ)D2,假設顆粒的形狀與遷移介質的性質相同,β1=β2,故(ρ1-ρ)D1=(ρ2-ρ)D2,表明同一動力條件下,顆粒密度越大,所能遷移的顆粒粒徑越小.依據沉積動力學分析,假設公園灰塵來源主要是高密度的磁鐵礦(5.175g/cm3),利用 Maher等[59]研究得出χ在0.03~0.01μm出現一個高峰的結果,采用王建等[62]建立的χ與磁鐵礦百分含量之間的回歸方程S=49.18P+4.95(其中S為χ/10-7m3/kg,P為磁鐵礦百分含量,%),模擬計算出福州市公園灰塵部分以磁鐵礦為主的樣品中磁鐵礦含量平均值為44.79%.模擬結果中出現磁鐵礦含量異常高的現象,這與二環內公園娛樂區灰塵樣品的亞鐵磁性礦物特征掩蓋了其余樣品的高矯頑力特征及福州市公園灰塵整體表現低矯頑力特征不符,說明灰塵樣品還存在大量弱磁性礦物,但另一個方面也說明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化率的增加主要是受到磁性礦物含量的影響.
4.3 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特征的空間變化
福州市公園灰塵具備高χ、低χfd%的特征組合,和蘭州[26,38]、昆明[63]和西安[43]街道塵埃磁性特征一致,然而不同地區χ不同,控制因素也有所差異.福州市公園灰塵χ(269.80×10-8m3/kg)低于蘭州街道塵埃(399.51×10-8m3/kg)[38]和西安街道塵埃(487.05×10-8m3/kg)[43],高于武漢街道塵埃(70.1×10-8m3/kg)[64]和昆明街道塵埃(46.50×10-8m3/kg)[63].其中,蘭州市受地形、氣候、工業布局影響,導致街道塵埃χ升高,西安市街道塵埃χ升高的主要人為源是交通污染及冶金行業,昆明作為旅游發展城市,其χ和日常生產與生活活動有關,武漢遠離西北沙塵源,工業污染及交通因素影響其χ大小.而福州市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中心城市,其工業活動影響弱,主要受制于城市化建設過程中人為活動頻繁,交通污染物不斷增加,自西向東傾斜的盆地地形有力于夏季臺風的進入產生滯留效應,公園內娛樂活動活動等影響均直接或間接導致公園灰塵χ升高.由此可知,不同地區不同地表功能區χ的升高和不同的城市化水平和地帶性環境差異有關.
同一地區不同功能區的磁學參數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表征不同的環境意義.本文發現大部分灰塵磁學特征在公園內部功能區基本一致,但福州市公園不同功能區中,公園門口和道路灰塵χ相當且最高,休憩區最低,公園灰塵χfd%最高為休憩區,而門口最低,說明了公園門口和道路灰塵磁性礦物較休憩區多.主要是公園門口人流量大,日常生產和生活活動頻繁,及公園道路有一定量游客出行都將產生大量的磁性顆粒,導致灰塵χ的增加,即污染程度較高.同時,對比福州市二環內外公園灰塵χ與磁滯回線特征,二環外公園(森林公園、金山公園、烏龍江公園、勞動者公園和南江濱公園)灰塵χ普遍較低,且二環外磁滯回線閉合區間較寬,除二環內娛樂區外,其余功能區磁滯回線為蜂腰型,即二環內娛樂區以低矯頑力特征為主導,其余功能區表現為高矯頑力特征.由于福州二環線以內的區域是交通最主要的通道,大量以公交車、出租車和私家車為主的機動車輛在該區域行駛,且福州城市建設力度不斷加大,市政工程、內河整治工程、房地產開發等建設活動產生高含量的磁鐵礦顆粒物在建筑材料運輸過程中灑落,尤其在夏季臺風進入福州盆地產生滯留作用下,易于進入公園灰塵中,造成二環內公園灰塵磁性礦物含量較高,而疊加季風作用的二環外公園的人為活動影響小,其磁性礦物含量較低,但二環內公園娛樂區娛樂活動頻繁,擋風設施良好,減弱夏季臺風滯留效應,而交通、城市建設、人為活動帶來的污染物影響更為強烈,故表現出明顯的亞鐵磁性礦物特征.因此,福州市公園灰塵磁學特征(χ、χfd%、IRM及其組合參數、磁滯回線)可以作為福州市城市污染物監測的一種重要的替代指標.
5 結論
5.1 福州市公園灰塵χ、χfd%、SIRM、S-ratio、SIRM/χ平均值分別為 269.80×10-8m3/kg、0.73、6175.07×10-5(A·m2)/kg、0.91、30.82A/m,其主要磁性礦物以亞鐵磁性礦物或者反鐵磁性礦物為主,為較粗SD顆粒與較細PSD顆粒.
5.2 交通、城市建設等人類活動的干擾、以及由西向東傾斜的地形條件、夏季臺風的滯留效應等因素導致福州市公園灰塵部分樣品是高矯頑力的反鐵磁性礦物為主,剩余部分樣品以低矯頑力的亞鐵磁性礦物為主,且灰塵磁化率的增加主要是受到磁性礦物含量的影響.
5.3 磁性特征在空間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受城市化和地帶性環境影響,和區域功能區差異也密切相關.通過福州市公園灰塵磁性特征的空間變化分析,發現其磁學特征(χ、χfd%、IRM及其組合參數、磁滯回線)可以作為福州市城市污染物監測的一種重要的替代指標.
[1] Adachi K, Tainosho Y. Single particle characterization of size-fractionated road sediments [J]. Applied Geochemistry,2005,20:849-859.
[2] Ball J E, Jenks R, Aubourg D. An assessment of the availability of pollutant constituents on road surface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8,209:243-254.
[3] Bris F J, Garnaud S, Apperry N, et al. A street deposit sampling method for metal and hydrocarbon contamination assessment [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9,235:211-220.
[4] Charlesworth S M, Everetta M, McCarthy R,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deposited street dusts in a large and a small urban area: Birmingham and Coventry, West Midlands, UK [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3,29:563-573.
[5] Day J P, Hart M, Robinson S M. Lead in urban street dust [J].Nature, 1975,253:343-345.
[6] 杜佩軒,田 暉,韓永明.城市灰塵概念、研究內容與方法 [J].陜西地質, 2004,22(1):73-79.
[7] 常 靜,劉 敏,侯立軍,等.城市地表灰塵的概念、污染特征與環境效應 [J]. 應用生態學報, 2007,18(5):1153-1158.
[8] 杜佩軒,田 暉,韓永明,等.城市灰塵粒徑組成及環境效應—以西安市為例 [J]. 巖石礦物學雜志, 2003,21(1):94-98.
[9] Inyang H I, Bae S.Impacts of dust on environmental systems and human health [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6,132(1):5-6.
[10] 楊士弘.城市環境生態學 [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2.
[11] 林 嘯,劉 敏,侯立軍,等.上海城市土壤和地表灰塵重金屬污染現狀及評價 [J]. 中國環境科學, 2007,27(5):613-618.
[12] 王麗麗,劉 敏,歐冬妮,等.上海城市地表灰塵重金屬粒級效應與賦存形態研究 [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6:64-70.
[13] Shi G T, Chen Z L, Xu S Y, et al. Potentially toxic metal contamination of urban soils and roadside dust in Shanghai,China [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09,156(2):251-260.
[14] 錢 翌,劉崢延.青島城市公園灰塵重金屬的形態分布及健康風險評價 [J]. 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 2011,24,(4):20-23.
[15] Banerjee A D. Heavy metal levels and solid phase speciation in street dusts of Delhi, India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3,123:95-105.
[16] Deletic A B, Oee D W. Pollution build up on road surfaces [J].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5,131(1):49-59.
[17] Roger S, Montrejaud-Vignoles M, Andral M C, et al. Mineral,physical,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solid matter carried by motorway run off water [J]. Water Resource, 1998,34(4):1119-1125.
[18] Lee P K, Yu Y H, Yun S T, et al. Metal contamination and solid phase partitioning of metals in urban roadside sediments [J].Chemosphere, 2005,60:672-689.
[19] 張志明,方鳳滿,楊 丁,等. 城市地表灰塵的分形特性分析 [J].土壤, 2010,42(1):142-147.
[20] Thompson R, Oldfield F.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M].London:Allen Unwin, 1986,15-281.
[21] 姜月華,殷鴻福,王潤華.環境磁學理論、方法和研究進展 [J].地球學報, 2004,25(3):357-362.
[22] Desentfant F, Petrovsky E, Rochette P. Magnetic signature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of stream sediments and correlation with heavy metals:Case study from South France [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04,152:297-312.
[23] 王 博,夏敦勝,余 曄,等.環境磁學在監測城市河流沉積物污染中的應用 [J]. 環境科學學報, 2011,31(9):1979-1991.
[24] 夏敦勝,楊麗萍,馬劍英,等.中國北方城市大氣降塵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 中國科學D輯, 2007,37(8):1073-1080.
[25] 鄭 妍,張世紅.北京市區塵土與表土的磁學性質及其環境意義[J]. 科學通報, 2007,52(20):2399-2406.
[26] 王 冠,夏敦勝,劉秀銘,等.蘭州市城市街道塵埃磁學特征時空變化規律 [J]. 科學通報, 2008, 53(4):446-455.
[27] Xie S J, Dearing J A, Bloemendal 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in street dust,Liverpool, UK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9,241(1-3):205-214.
[28] 旺 羅,劉東生,呂厚遠.污染土壤的磁化率特征 [J]. 科學通報,1999,4(10):1091-1094.
[29] Yang T, Liu Q S, Chan L S, et al. Magnetic investigation of heavy metals contamination in urban topsoils around the East Lake,Wuhan,China [J].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2007,171:603-612.
[30] Gautam P, Blaha U, Appel E, et al. Environmental magnetic approach towards the quantification of pollution in Kathmandu urban area, Nepal [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2004,29:973- 984.
[31] Manno E, Varrica D, Dongarrà G. Metal distribution in road dust samples collected in an urban area close to a petrochemical plant at Gela, Sicily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6,40(30):5929-5941.
[32] Al-Khashman O A. Heavy metal distribution in dust, street dust and soils from the work place in Karak Industrial Estate, Jordan[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38(39):6803-6812.
[33] Anagnostopoulou M A, Day J P. Lead concentrations and isotope ratios in street dust in major cities in Greece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lead in petrol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6,367(2/3):791-799.
[34] Faruque A, Hiroaki I. Trace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street dusts of Dhaka city, Bangladesh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6,40(21):3835-3844.
[35] Shilton V F, Booth C A, Smith J P, et al. Magnetic properties of urban street dus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the West Midlands, UK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5,39(20):3651-3659.
[36] Michio M, Fumiyuki N, Hiroaki F. Size and density-distributions and source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urban road dust [J]. Chemosphere, 2005,61(6):783-791.
[37] 張春霞,黃寶春,李震宇,等.高速公路附近樹葉的磁學性質及其對環境污染的指示意義 [J]. 科學通報, 2006,51(12)1459-1468.
[38] 夏敦勝,余 曄,馬劍英,等.蘭州市街道塵埃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 環境科學, 2007,28(5):937-944.
[39] 夏敦勝,王 冠,馬劍英,等.蘭州市大氣降塵環境磁學特征研究[J]. 中國沙漠, 2007,27(5):859-865.
[40] 張 崧,Heller F,靳春勝,等. 2006年4月17日北京降塵的粒度分布與磁學特征 [J]. 第四紀研究, 2008,28(2):354-362.
[41] 王 博,夏敦勝,余 曄,等.城市降塵磁性特征對比及其環境意義[J]. 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0,46(6):11-17.
[42] 王 麗,夏敦勝,余 曄,等.北疆地區城市大氣降塵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 中國沙漠, 2010,30(3):699-705.
[43] 李 鵬,強小科,唐艷榮,等.西安市街道灰塵磁化率特征及其污染指示意義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0,30(3):309-314.
[44] 田世麗,夏敦勝,余 曄,等.西北地區河谷城市大氣降塵環境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 環境科學, 2011,32(9):2761-2768.
[45] 豐 華,劉秀銘,呂 鑌,等.蘭州市大氣降塵磁學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 地理學報, 2012,67(1):36-44.
[46] 盧升高.中國南方紅土環境磁學 [J]. 第四紀研究, 2007,27(6):1016-1022.
[47] 劉彩彩,鄧成龍.南方紅土的磁性礦物組成及其區域性差異[J].第四紀研究, 2012,32(4):1-8.
[48] 黃一綏,張 靈.福州市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計量分析 [J].環境科學與管理, 2010,35(2):62-65.
[49] 潘永信,朱日祥.環境磁性研究現狀和進展 [J]. 地球物理學進展, 1996,11(4):87-98.
[50] 張衛國,俞立中,許 羽.環境磁學研究的簡介 [J]. 地球物理學進展, 1995.10(3):95-104.
[51] 周文娟.環境磁學磁性參數簡介 [J].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自然科學、醫學版), 2006,26(1):82-89.
[52] Peters C, Dekkers M J. Selected room temperature magneticparameters as a function of mineralogy, concentration and grainsize [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Parts A/B/C, 2003,28(16-19):659-667.
[53] 夏敦勝,余 曄,馬劍英,等.大氣降塵磁學特征對城市污染源的指示 [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07,21(12):110-115.
[54] Thompson R, Bloemendal J, Dearing J A, et a1.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of magnetic measurements [J]. Science, 1980,20:481-486.
[55] Day R, Fuller M, Schmidt V A. Hysteresis properties of titanomagnetites: Grain-size and compositional dependence [J].PhysEarth Planet Inter, 1977,13:260-267.
[56] 夏敦勝,魏海濤,馬劍英,等.中亞地區現代表土磁學特征及其古環境意義 [J]. 第四紀研究, 2006,26(6):937-946.
[57] Xia D S, Chen F H, Bloemendal J, et al. Magnetic properties of urban dustfall in Lanzhou, China,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8,42(9):2198-2207.
[58] Wang X, Qin Y. Magnetic properties of urban topsoils and correlation with heavy metals: a case study from the city of Xuzhou, China [J]. Environmental Geology, 2006,49(6):897-904.
[59] Maher B A. Magnetic properties of some synthetic submicronmagnetites [J]. Geophysical Journal, 1988, 94(1):83-96.
[60] 陳秀玲,李志忠,靳建輝,等.福州城市土壤pH值、有機質和磁化率特征研究 [J]. 水土保持通報, 2011,31(5):176-181.
[61] 劉振東,楊 凌.城市道路塵埃的磁性特征及其環境意義 [J].地質科技情報, 2005,24(3):94-98.
[62] 王 建,劉擇純,姜文英,等.磁化率與粒度、礦物的關系及其古環境意義 [J]. 地理學報, 1996,51(2):155-163.
[63] 梁 濤,史正濤,劉 勇,等.昆明市城區旱季塵土磁化率特征及環境意義 [J]. 熱點地理, 2010,30(1):45-49.
[64] 李海峽.武漢東湖周邊道路塵埃的磁性結構特征及其環境意義[D]. 武漢:中國地質大學, 2003:27-28.
致謝:本實驗的室內分析測樣工作由福建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胡凡根研究生、福建師范大學能源與物理學院吳建鵬研究生等協助完成,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強小科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所古地磁與年代學實驗室劉平老師、張春霞老師對本文英文摘要校正、相應圖件繪制、相關磁學參數及其意義等給予了大量幫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