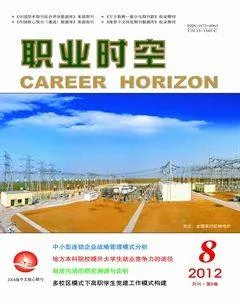簡論中國文學史上的“負心漢”
摘要:從《詩經》到南戲后期高明的《琵琶記》、明代馮夢龍擬話本《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從近代曹禺的《雷雨》到現代嚴撲、華萃深的《秦香蓮》,這些作品中都有不少“負心漢”形象。他們在眷情與絕情中沖突,在人性沒有泯滅和個人欲望中徘徊、思考。他們的罪惡是永恒的,良心發現也是永恒的,罪惡與良心的沖突一直延續,這正是“負心漢”形象系列的普遍性和特殊意義所在。
關鍵詞:中國;文學史;負心漢
“負心漢”最早出現在《詩經》中的《氓》、《谷風》中,樂府民歌《白頭吟》、《上山采蘼蕪》也有描寫“負心漢”的:“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話我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這是側面描寫負心漢形象,讀了這段文字,在我們的腦子里就形成了這樣一個負心漢形象:朝三暮四,對妻子殘暴,性格比較單一。而樂府民歌中的《上山采蘼蕪》所寫的“負心漢”則與《詩經》中所寫的不同,樂府民歌采取正面描寫,它是這樣的故事情節:被遺棄的女子偶爾邂逅前夫,便問“新人復何如?”答曰:“新人不如故,”全詩隱約包含了丈夫被外界所迫遺棄妻子的心理,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產生遺棄現象的社會原因。“負心漢”則比《詩經》所寫的要復雜得多的“負心漢”形象。兩者對比會發現:前者形象比較單一,后者則比較復雜。至此,“負心漢”的形象在文學史上便有過兩種類型,這對后來的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宋元南戲前期以前,受《詩經》中的《氓》、《谷風》影響較大,從宋元南戲后期到近現代,則受《上山采蘼蕪》影響。
《琵琶記》中的蔡伯喈則是一個舊情難忘,對婚姻忠貞不渝的“正面人物”,在議親時,他想的是“縱然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血。待早朝,上表文,要辭官家去。”成親后,他對妻的思戀化為“春心寄杜鵑”,最令人感動的是他拒絕遺棄前妻,他堅決表示“縱有辱沒殺我,終是我的妻房,義不可絕。”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高明筆下的“負心漢”并不那么可惡,他處在一個進退維谷,十字交叉的人生路口,后來由于蔡伯喈的軟弱,封建勢力的強大,才不得不屈服。文章有一句話揭示了造成蔡伯喈悲劇的原因:“文章誤我,我誤爹娘,文章誤我,我誤妻房,”文章,即封建科舉制度。這就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封建的科舉制度,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是文章也有不足之處,就是把造成悲劇的一切罪過都歸于封建社會制度,把罪過都推向了皇帝所代表的封建觀念,只注重外部原因,而沒有把筆墨多停留在蔡伯喈的軟弱上,沒有從“負心漢”本身來找原因。文章想把人物性格復雜化,但是由于沒有把握好這個題材的特點,使人物停留在某個特定的圈子里——人物理想化了。
到了明代,把社會原因和“負心漢”本身性格弱點結合起來的寫法。才趨完整,馮夢龍的擬話本《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可為代表。李甲遺棄杜十娘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社會制度的原因——“為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這是違背孝道,封建禮數的;其二本身性格決定的,即“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惑與浮議”。這篇文章中李甲的形象比較復雜而略顯單薄,復雜表現在李甲“忠厚至誠”和杜十娘真心相愛,但是中途畏縮不前,沒有激進的勇氣,到后來由于良心發現,折磨而死。為什么說形象而略顯單薄呢?因為這篇文章寫李甲內心活動不多,心理描寫不細膩,因而他的內心世界沒有突現在我們面前。再由于篇幅短小的原因,沒有從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展現李甲形象的復雜性。
在曹禺《雷雨》出現以前,可以說沒人真正把“負心漢”寫得完美,他們或多或少有些不足之處,到近代《雷雨》中的周樸園的出現,才給“負心漢”注入新鮮的血液,給中國文學史上人物畫廊又添了新的一頁。
《雷雨》中的周樸園的經歷可以歸納為五個情節,即30年前的同居、遺棄,30年來的懷念,30年后的絕情,最后的相認。關于30年前的同居,曹禺對周樸園的評價是“玩弄”一詞(1962年語),后對王朝聞誒到“糟踏”一詞(1978年語),可見,周樸園這個“負心漢”很偽善,30年前的遺棄則可看出周樸園的殘忍、絕情,這是迫于家庭壓力的緣故。30年來的懷念則可看出周的人性并沒有泯滅,對愛情還是忠貞的。也許有人認為資本家的本質是虛偽的,他對侍萍的懷念是虛假的。但是作者曹禺在1980年兩次肯定周樸園的“人性”認為“周樸園也是一個人,不能認為資本家沒有人性,愛他所愛的人,在他生活圈里需要感情的溫暖,這也是他的人性”(見夏竹《曹禺與語文教師讀<雷雨>》《語文戰線》1980年2期),可見,周樸園對魯侍萍的懷念是真誠的。30年后的絕情則又說明他的軟弱、無能、令人可恨。最后的相認說明周樸園的良心并沒有消失,又讓人憐憫。所以說周樸園集真與偽,丑與美,惡與善于一體,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曹禺把一個“負心漢”寫得有血有肉,性格豐滿,完善,既可恨又可憐,體現了復雜美和單純美。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文學史中所描寫“負心漢”的作品都是以男子的負心為中心來結構全局,對“負心漢”的態度往往是憤懣,同時作品也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摧殘,奴役。雖然如此,筆者總覺得“負心漢”并不那么可恨,甚至有些可憐,這就要求我們要具體分析人物的心理特征,把人物放到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去分析。
回顧一下文學史上“負心漢”形象,就會發現:宋元南戲前的“負心漢”,大都使人覺得厭惡,從道德責任感來看,他們沒有對社會負責,而對妻子的遺棄,應受到人民的譴責。但是從宋元南戲后期開始寫的“負心漢”則使人同情,他們往往是身不由己,自己也是受害者。
首先,他們都受到了環境的制約,蔡伯喈、李甲、周樸園他們對妻子的遺棄,并不是出自本意,而是對強大封建勢力妥協的結果。我們知道,他們生性都比較懦弱,在封建思想的影響下,不可能有強烈的反抗個性。應當承認:封建勢力的強大及其對人的異化作用。“負心漢”的周圍往往有一位執行封建禮教職能的長輩,他們不具有最終自由選擇的權利。但他們屈從于家庭、社會,即當他們人性受到摧殘時,悲劇也就釀成了。他們的悲劇在于:他們自覺地把傳統理論觀念化為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武器,而這樣做,他們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可以說,他制造了別人的悲劇——遺棄自己的妻子,同時又制造了自己的悲劇——良心受譴責,受到痛苦的煎熬。故宋元南戲后期的“負心漢”和癡情女都是封建道德的犧牲品,所以在評論“負心漢”時,不要把矛頭指向負心漢本人,應該把矛頭指向當時社會制度,因為社會環境制約人、異化人、摧殘人性。
其次,要肯定他們的良心發現。良心,就是自己對自己所進行的道德的反思。不要錯誤認為:反動的剝削階段沒有良心發現,對李甲后來被良心發現折磨而死要值得同情,同樣,對周樸園后來良心發現促使周萍和其母相認也應肯定。良心發現可以說是一張正義情感的復蘇,能意識到道德錯誤總比毫無自審意識要好得多,只要“良心發現”是自我意識的道德痛苦,就應值得肯定。
從“負心漢”形象系列我們還看到:作者并沒有把“負心漢”的結局都寫到“良心發現”的極端,沒有把他們寫成一個有是有非,值得爭議的人物,使他們在眷情與絕情中沖突,在人性沒有泯滅和個人欲望中徘徊、思考,因而他們的罪惡是永恒的,良心發現也是永恒的,罪惡與良心的沖突一直延續,這正是“負心漢”形象系列的普遍性和特殊意義所在。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Scorned Man"
CHENG Hui
Abstract: From the "book of songs" to a later dynasties of the story of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