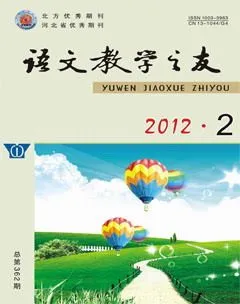豈是行路風與塵 實為世道多艱辛
自洛之越 孟浩然
遑遑三十栽,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作家,他一生未仕,潔身自好,詩風清淡閑逸。李白稱他“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贊嘆說:“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贈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說他“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可見,孟浩然一生恬淡自適、格調高雅,是一個有氣節有情趣的隱士。
但孟浩然畢竟身處盛唐,既無“亂世”隱居的必要,又有盛世功業的呼喚,為什么會隱居終生?除了性格的原因外,恐怕這首《自洛之越》會給我們一些答案,因為它不僅寫出了作者自“洛”至“越”地理上的行程,更寫出了作者自“仕”而“隱”的心路歷程。
首聯“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正一語道破了作者前半生的追求和困頓。孟浩然早年隱居家鄉,40歲才到京城長安。這40年,孟浩然隱居、吟詩,已經頗有詩名。在以辭章取士的唐代,我們很難說,有哪位詩人是在為吟詩而吟詩,為隱居而隱居。也許是性格的原因,使得孟浩然并沒有李白那樣張揚非凡、毫不掩飾的政治目的的表白,但毋庸諱言,他的人世之心也是非常強烈的。他在《南陽北阻雪》一詩中曾說“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而《田家作》中更直抒“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揚雄曾因獻《甘泉賦》而受到當時皇帝的賞識)。可見,隱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或者說只是“名義”,而其背后是為科舉、為入世作著認真積極的準備的。但結果呢,他的仕途并不順利,長安并沒有接納這個有著遠大抱負的才子和詩人。雖然他不止一次表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希望有達官貴人可以引薦推舉,但現實是科舉無望,舉薦無人。在這句詩中,“遑遑”二字寫盡了作者前半生的急迫和憂慮,韜光養晦、北上京城、科舉應試、獻賦自舉、交友求薦……這一路實在是匆忙而辛苦,但結果卻是“書劍兩無成”!
失意和寂寞是難免的。但人和人的不同不在于“失意”,而在于面對“失意”時的選擇。李白贊孟浩然的“高山仰止”并不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是“棄世”的,天生就是“出塵”的。那對于唐代,反而不正常。孟浩然的高潔之處在于,即使他熱衷仕進,也始終沒有放下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格調”。顯然,他的失敗與他不樂于趨承逢迎,耿介不隨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有關。而這一切又和他前期所生活的“襄陽”,和那個山水形勝、人杰地靈,造就過漢陰丈人和龐德公的襄陽密不可分。于是,在失落、寂寞甚至憤怒之后,孟浩然選擇了“離開”。
“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頷聯的兩句其實是一個倒裝。因“風塵厭洛京”,才復“山水尋吳越”。此聯的“對仗”渾然天成,了無痕跡,卻內涵豐富,極具象征意義。“洛京”與“吳越”,一北一南卻是兩種生活方式和境界。“洛京”,繁華的,政治的,也是“風塵”的。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里安身立命。杜甫曾在這里“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李白在這里三年也只能感慨“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吳越”,山水的,性情的,個人的,也是閑適的。杜茍鶴有詩《送友游吳越》,不僅描繪了此地的田園沃饒、山川佳麗,更寫出了這里的人情之美:
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桔,無水不生蓮。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經年。
吳越風情,實在是撫慰失意游子的良藥,所以,雖然難免感傷與寂寞,但在看透了官場的黑暗之后,山水間的自適不也是另一種生命價值的實現?
“風塵”二字,在中國的詩歌和文學里,有著太豐富的含義。風吹塵起,已經豐富到令人難以捉摸、難以確論。世俗的紛擾與污濁,人情的雜亂與冷漠,亦或是仕途的辛苦和無奈。《晉書·虞喜傳》中說虞喜是:“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這里的“風塵”與孟浩然之“風塵厭洛京”之“風塵”最為接近,仕途的風沙塵埃,仕宦生活的艱難危險絕非自然的風雨霜雪塵土所能比擬!
但是,最能表現作者的灑脫及其與官場的決絕的,是頸聯兩句:“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此時“泛湖海”的孟浩然,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欲濟無舟楫”的苦悶者了,做—個長揖,感謝并且告別那些權貴達官:我走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這個“長揖”,雖不像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那樣振聾發聵,但灑脫中帶著點幽默,還帶著點嘲諷。同時,也暗合了當初他希望借助當權者的引薦而未成的事實。
和很多被埋沒的賢良一樣,孟浩然的“離開”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充滿了心酸和無奈的。但重要的是,這“離開”中既有不茍同、不合流的潔身自好,也有些因失望、絕望而反彈的剛強與堅決。最重要的是,在離開之后,他真正把自己放逐山水,去尋求靈魂的寧靜、完成獨立的人格了。在這一點上,他是像極了陶淵明的。正像陳貽瞅先生所說的:“他們生活雖似出世而精神是人世的,他們都有抱負,都經受了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矛盾的痛苦,都認識并揭示了現實和官場中的黑暗與丑惡,都冀求完成一種獨立的不媚俗人格。”也許正因為如此,在此詩的尾聯,作者自然而然地借用了陶淵明《責子》中的詩句,“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但與陶淵明面對“天運”的平和幽默相比,孟浩然顯然更多了一份憤激,所謂“誰論世上名”是有些落拓不羈的。
聞一多先生論孟浩然詩時,曾說:“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但與此同時,聞一多也認為孟浩然詩的境界雖高,但在詩歌的“用力”和才氣的顯現上,也沒有完全做到莊子所說的“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他說,孟詩還是“有點累”的,而能做到既“似之而非”又“免乎累”的,“除陶淵明,還有誰呢?”這里盂浩然和陶淵明的區別就在于,孟浩然的“詩才”與“沖淡”還是多少有點“痕跡”的,但陶淵明“淡”已經是詩與人的合二為一了。這一點,在此詩中,也恰恰表現在最后—聯的借用上。陶淵明說:“唉,既然天意給了我這樣幾個不爭氣的孩子,那也沒辦法,還是喝酒吧。”表面看是對孩子的責備,實則充滿了慈愛、憐惜,在戲謔和詼諧中甚至帶著點舐犢情深的寵愛,那“飲酒”也就多了一份閑適和快樂。而孟詩呢?“誰論世上名”的表白反而有些刻意,帶有借酒消愁之嫌疑和以苦為樂的憤激了。
縱觀全詩,結構嚴謹,開闔自如,從洛京到吳越,實際上,是從仕途的仆仆風塵,到自我人格的完成和堅守。這條路,孟浩然走得也并不輕松,但是,他走通了。
參考文獻:
①陳貽焮《陳貽焮之文選·談孟浩然的隱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②聞一多《唐詩雜論·名家說唐詩》,天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