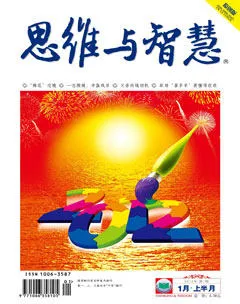將自己放低到塵埃
邢軍紀(jì)的《最后的大師:葉企孫和他的時(shí)代》中寫(xiě)了著名物理學(xué)家葉企孫的兩件軼事。
20世紀(jì)20年代,葉企孫做清華大學(xué)物理系主任時(shí),系里有個(gè)勤雜工叫閻裕昌,此君勤勞、聰明、肯學(xué)習(xí)鉆研,葉企孫將他安排到實(shí)驗(yàn)室有意培養(yǎng)。閻裕昌很快掌握了技術(shù),葉企孫破格提拔他為實(shí)驗(yàn)員,輔助講課。勤雜工在那個(gè)時(shí)候地位極低,被稱為“聽(tīng)差”,這個(gè)稱呼明顯帶有歧視意味,盡管身為閻的直接上司,葉企孫卻特別尊重閻裕昌,從不叫閻為“聽(tīng)差”,開(kāi)口閉口都是“閻先生”,他也教育學(xué)生同樣這樣做,不允許他們喊閻裕昌“聽(tīng)差”。
上世紀(jì)初,物理學(xué)剛剛從西方傳進(jìn)來(lái),是一個(gè)熱門(mén)專業(yè),許多新生進(jìn)了清華大學(xué)后都想讀物理系。葉企孫總是認(rèn)真地對(duì)每一位提出要求的學(xué)生進(jìn)行面試、核查,他首先查看分?jǐn)?shù),分?jǐn)?shù)高的只簡(jiǎn)單地問(wèn)幾句就辦手續(xù)。分?jǐn)?shù)不合適的,他絕對(duì)不會(huì)說(shuō)你成績(jī)不好,沒(méi)有達(dá)到物理系所要求的門(mén)檻,而是非常和藹地告訴面前的學(xué)生學(xué)物理會(huì)面臨許多困難,不僅修完全部課程很難,畢業(yè)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很多人聽(tīng)他這樣說(shuō)也就自動(dòng)放棄了,有個(gè)別的不愿放棄的同學(xué)懷疑問(wèn)題出在自己的分?jǐn)?shù)上,死活要求葉企孫實(shí)言相告自己的得分,葉企孫卻從不愿說(shuō)出分?jǐn)?shù),只是耐心勸說(shuō)他們放棄原來(lái)的打算。
葉企孫如此尊重別人,甘愿放低自己,不是因?yàn)樽约赫娴牡桶喾矗藭r(shí)的他在清華正如日中天,高聳得像珠穆朗瑪峰。葉企孫才華橫溢,16歲就完成了《考證商功》這篇才華橫溢的學(xué)術(shù)論文,兩年后發(fā)表在《清華學(xué)報(bào)》上。此后他一發(fā)不可收,又在《清華周刊》發(fā)表了《革掛解》《天學(xué)述略》,在《清華學(xué)報(bào)》發(fā)表《中國(guó)算學(xué)史略》,深得梅貽琦等老師的器重。赴美留學(xué)后,葉企孫又寫(xiě)出了《用射線方法重新測(cè)定普朗克常數(shù)》這篇轟動(dòng)世界物理學(xué)界的論文,被美國(guó)人稱為這是“一個(gè)偉大的進(jìn)步”。由于它的精確,此后15年里,世界物理學(xué)界對(duì)這個(gè)測(cè)定無(wú)人再敢問(wèn)津。清華是把他作為杰出人才引進(jìn)來(lái)的,從個(gè)人的職業(yè)影響力來(lái)說(shuō),當(dāng)時(shí)的葉企孫是清華大學(xué)物理系僅有的兩名教授之一,梅貽琦出任教務(wù)長(zhǎng)后他又變成了唯一的一個(gè),是學(xué)校少壯派教授的領(lǐng)袖,備受大家推崇。如此情況下,還能將自己放低到塵埃,非常不容易。
將自己放低到塵埃,必須不怕淹沒(méi)了自己。像葉企孫,才華出眾,人品非常高尚,然而,他不屑于宣傳、張揚(yáng)自己,這樣很可能形成如此局面:以個(gè)人素質(zhì)論,這個(gè)人確實(shí)極其厲害,但社會(huì)上的人出于某種隔膜也許并不覺(jué)得他厲害。假若不具有一定的犧牲精神,假若不對(duì)名利多一點(diǎn)超脫,一個(gè)人很難抵達(dá)如此境界。
世界上有兩種牛人,一種有點(diǎn)小成績(jī),就千方百計(jì)張揚(yáng)自己,總覺(jué)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完美無(wú)缺,自己擁有的每一種特長(zhǎng)都人所不及。葉企孫這類人不同,一方面他確實(shí)擁有極高的天賦,出類拔萃的才華;另一方面他更有一顆平常心,能夠充分認(rèn)識(shí)到每一個(gè)人都可能有別人不具備的長(zhǎng)處,因此自覺(jué)地不拿自己的長(zhǎng)處跟別人的短處比,自然也就不會(huì)覺(jué)得自己如何高人一等。換句話說(shuō),葉企孫將自己放低,不是出于刻意,而是出于對(duì)他人已經(jīng)顯現(xiàn)或潛在的能力的欣賞。
一個(gè)人敢將自己放低到塵埃,讓靈魂接受大地和天空的雙重滋潤(rùn),恰恰可以成就自己的高峻。
(編輯 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