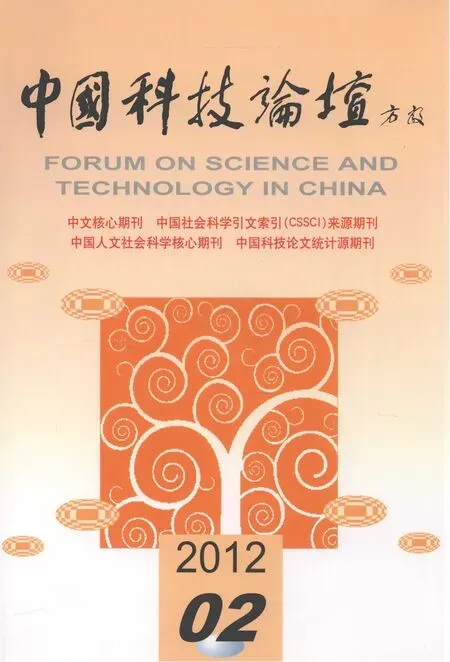當代科技價值體系的反思性特征
米丹
(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37)
當代科技價值體系的反思性特征
米丹
(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37)
當代科技風險的性質和表現形態打破了科技價值體系的傳統運作邏輯,傳統工業化科技價值體系的基礎和合理性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在當代科技價值體系內部,一種新的運行邏輯正在建立,其動力來源于世界風險社會中科技價值體系的反思性新特征,首先表現在科技價值體系的自我對抗中。科技價值系統的自反性、科技價值觀念的自我沖擊、科技價值創造中的質疑與挑戰以及科技價值實現中的矛盾體現構成了這種自我對抗的主要內容。
科技價值體系;反思性;風險社會
1 科技價值系統的自反性
1.1 科學知識的內在矛盾
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早就包含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之中。“只要自然科學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1]“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的絕對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但是這個真理的存在是無條件的,我們向它的接近也是無條件的。”[2]但科學知識的這種相對性長期以來都被人們忽視了。而在風險社會面前,知識的內在不確定性暴露無遺。“科學無論在外部還是在內部都不能再享受理性的護佑。它們變得獨立于真理并且缺乏真理。”[3]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形象地揭示了知識在風險社會中的尷尬境遇:“當代西方社會與知識的關系是一種非恨即愛的關系,一方面,人們追求它,贊美它,……然而,同時,社會對求知感到不安,常常不信任那些聲稱‘知道’的人。”[4]自然科學的這種不確定性不斷影響著自然觀和科學觀的發展。
啟蒙運動以來的很長時期,科學知識是以“純知識”(Pure Knowledge)的形態出現的,這種認識得到了古典歸納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支持和擁護,并在20世紀為埃米爾·迪爾凱姆 (Emile Durkheim)、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大師所推崇和加強。直到20世紀中后期,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否證式科學發展觀打破了實證主義傳統,指出科學理論的猜測性或假說性。“任何科學理論都不能被看做是確定的確立的或證實的”,“科學理論都是可否證的”[5]。“消除錯誤導致我們的知識即客觀意義上的知識的客觀發展,導致客觀逼真性的增長,它使得逼近(絕對的)真理成為可能。”[6]之后,逐漸形成了以漢森 (N·R·Hanson)、托馬斯·庫恩 (Thomas S. Kuhn)和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科學成為一種發展知識的方法論框架或理論范式,并受著歷史條件的制約。20世紀七八十年代,涌現出了一股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和解釋的思潮。默頓的科學社會學闡明了科技活動不僅受到外部社會諸因素的強烈影響,而且在內部也是社會化的存在。“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則將科學知識完全納入了社會的范圍。巴恩斯(B.Barnes)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滲透著利益因素;著名物理學家皮克林(A.Pickering)歸納出實驗與理論二者之間的共生關系從而有力地支持了知識本性的社會學解釋。隨著科學哲學的發展,拉卡托斯(I.Lakatos)、勞丹(Larry Laudan)、夏佩爾(Dudley shapere)等致力于將各派對立的觀點合理地統一起來,旨在向更全面和合理的方向發展。
1.2 科學內在價值與技術自然價值的交叉與沖突
科學的內在價值和技術的自然價值的價值標準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求真,追求真理性;后者主要求善,追求效用性。而“現代科技的社會風險的日益擴大首先根源于科學與技術的一體化——科學的技術化;技術的科學化;相對應領域的科學與技術的銜接;科學與技術銜接后相互滲透、相互包含以至融合成連續整體”。[7]這種風險的內在機制則表現為科學與技術內在價值標準的交叉與沖突,由各司其職轉向互相逾矩。
首先,科學的技術化使科學內在價值的價值標準功利化。
科學技術化在這里主要指科學理論向技術實踐的轉化[8]或指技術導向的科學[9]。實際上功利性確是包含于科學價值之中的。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科學并不是脫離了現實的抽象實體,而是緊密地與實踐聯系在一起。“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一個方面,一種形式”[10],但是這種功利性屬于科學社會屬性的范圍,是其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就內在價值而言,科學則是非功利的。
然而,在科學的技術化過程中,卻出現了科學內在價值的功利化傾向,效用性、經濟性代替了真理性成為某些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準則和導向。科學理論向技術的物化過程,將拋棄科學的求真理求客觀,而代之以求實用求功效;將拋棄科學的追求真理的一元標準,變為尋求技術實現的多元標準;將拋棄科學的認知目的,轉化為實踐目的[11]。
其次,技術科學化導致科學方法向技術領域的風險移植。
在科學內在價值中,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實則建立在批判和懷疑精神之上,科學在不斷地被否證、修正的過程中發展,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因為科學對社會的結果往往通過技術的中介進行,而技術的發展在科學化之前主要是基于經驗的長期積累。這種長期的積累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不斷地驗證、改進過程,因此也是一種避免技術不良后果的現實方法。但是當技術獲得了科學的特征之后,它產生風險的機制和水平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首先,技術研究與復雜實踐分離開來而轉移至被抽離化的實驗室中。另外,技術直接依據科學理論產生,省卻了現實的經驗積累過程。錯誤的檢驗直接搬到了社會中,技術擴散一旦發生問題社會便首當其沖。
1.3 科技固有價值和科技社會價值的交叉與沖突
(1)科學的內在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易位沖突
在(古典)工業社會,科學主要被看做追求真理的活動,科學的內在價值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科學社會化的日益增強,科學的社會價值日益凸顯,并成為引導科學發展的主要因素。
科學的內在價值排除功利,各個學科沒有輕重、主次之分;而科學的社會價值則更多體現功利性的一面,它要求科學為社會服務并帶來切實的利益。在科學社會價值占主導的當代,科學追求真理和追求功利便產生了沖突。而現實中社會價值的導向往往是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科技政策和科研經費往往偏向于對經濟有直接或間接促進作用的科學研究,學科間的不平等地位由此產生。這使得一些科學家在得不到資金支持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真理轉而追求功利,更有甚者,為了金錢和名利,不顧真理性標準,弄虛作假。學術界的欺騙行為與社會過分強調科學的社會價值尤其是經濟價值不無相關。
(2)技術內在價值向社會價值的機械移植
技術內在價值標準和社會價值標準是根本不同的,內在價值主要體現效用性,而技術的社會價值則以社會的需要或社會全面進步為標準,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各種需求的相互協調的統一體,而不是某一個領域的特殊利益和需要。但是,長期以來,技術的社會價值標準機械地模仿了技術的內在價值標準,主要體現為經濟效用性。當前,科技體制社會化過程中,國家關于科技風險等問題的政策和措施往往力度不夠,也缺乏統一的標準。近幾年的世界氣候大會便可見一斑,其更多地只表現出某種象征意義。這種現象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將技術內在價值標準機械地應用于技術的社會價值標準。
現代技術與社會已融為一體,技術社會化和社會技術化的不斷增強;現代技術所潛藏的風險也日益全球化。這就要求技術的社會價值不僅要體現效用和功利,更要兼顧整體利益。
2 科技價值觀念的自我沖擊
2.1 現代科技理性批判思潮
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對科技的批判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演變為世界的焦點。
唯意志論者認為,理性是不確定的和靠不住的,只能認識表象而不能達到人及世界的本質意義。唯意志論者通過貶低理性進而否定科學,強調意志在解釋現象世界中的核心作用。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認為,現象世界的一切都只是“我”的表象,而世界“實際存在的支柱”則是“我”的意志 。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則明確地將理性和科學當做權力意志的工具和產物,斷言科學和理性扼殺了生命意志并使生命“機械化”和“非人格化”。“所有詮釋方式中最不重要的。……機械世界也必然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12]
新世紀哲學的創造人胡塞爾 (E.Edmund Husserl)及其現象學揭示了自然科學通過對生活世界的抽離化而背棄了真正的理性精神。胡塞爾批判實證主義科學 “將所有那些人們歸之于或嚴或寬的形而上學概念的問題,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含糊地稱作是‘最高的和終極的問題’統統丟棄了”。[13]“對形而上學可能性懷疑,關于作為新人指導者的普遍哲學的信仰的崩潰,恰好表明對‘理性’的信仰的崩潰,”[13]這種“理性”是傳統意義上的“最終賦予一切被認為的存在物,一切事物、價值、目的的以意義的東西”。[12]胡塞爾揭示了科學的局限性,致力于尋求永恒價值和絕對真理、實踐理性和純粹理性的統一。
法蘭克福學派則對工業化過程中的科技異化展開了批判。盧卡奇(Ceorg Lukacs)首先將科技理性與階級問題聯系起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則認為現代科技已經異化為意識形態。“今天,統治不僅通過技術而且作為技術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斷擴大,技術為不斷擴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領域的政治權力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14]另外,馬爾庫塞還批評作為現代科學思維基礎的形式邏輯、當代數理邏輯和符號邏輯將社會經驗以及事物的本質和規范排除在外。“在形式邏輯的統治下,關于本質和現象相沖突的概念,如果不是無意義的,也是可以犧牲掉的;物質的內容被中性化……終極原因脫離了邏輯的秩序。”[14]馬爾庫塞認為,科學原本蘊含的真善美的觀念被剝奪了,只剩下工具和奴役。
20世紀中后期還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他們認為科技理性只是常規科學家和技術官僚們的思維定式,把它作為普遍的價值標準是新的信仰主義和教條主義。美國學者霍蘭德指出:“現代科學進步本打算解放自身,結果卻危險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類社區之根,以及它的傳統之根。……正是毫無限制的現代技術的驅動力把軍事活動推到了一個新的令人膽戰心驚的境地。從邏輯上講,危機歸根到底不是來自于軍事而是來自于新的現代技術的無方向性的文化環境。”[15]英國物理學家大衛·伯姆(David Bohm)曾寫道:“在20世紀,現代思想的基石被徹底動搖了,即便它在技術上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事物正在茁壯成長,其根基卻被瓦解了。瓦解的標志是,人們普遍認為生命的普遍意義作為一個整體已經不復存在了”。[16]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認為應該消除科技理性和倫理價值的分裂,主張科學的返魅。“現代科學將世界描繪成一架機器,使現代意識背離了目的、責任和整體;后現代科學的任務是,讓我們保持現代分析工具的銳利,使其發揮適當的作用,并將使我們回到那個花園中,小心而謹慎地工作。 ”[17]
對于(古典)工業社會時期“科學至上”的神話,這些批判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們揭示了蘊含在科技價值中的辯證法。在當代科技風險的新形式之下,認識到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2.2 科技政策社會化和全球化所隱含的矛盾
(1)科技政策的社會化和全球化帶來科技社會價值的片面發展
科技政策的社會化體現的主要是國家利益和社會發展目標,在實際運行中,往往以經濟為導向。科技政策片面發展在風險全球化的背景下 “產生了新的國際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業化國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業化國家間的不平等。它逐漸破壞了國家司法的秩序”。[3]“危險的工業已經轉移到低工資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不是巧合。在極端的貧困和極端的風險之間存在系統的‘吸引’。”[3]這種狀況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科技政策時矛盾重重,但環境往往向經濟妥協。正如貝克分析,在可見的因饑餓而死亡的威脅和不可見的因有毒化學物質而死亡的威脅之間的爭論中,那些基于物質貧困提出的論據是勝利者。“資方可以制定嚴格的安全條例,知道它們無法實行,卻硬說條例得到遵守。通過這種方式,資方使自己保持清白,廉價地和問心無愧地把事故和死亡的責任推卸給人們對危險在文化上的無知。當災難真的發生,貧困國家的司法混亂和利益紛爭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制定出一種抹殺和混淆的政策,通過有選擇地界定問題以限制災難性的后果。”[3]
事實上,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風險也將世界置于同一水平之下,發達國家的環境特權終將不復存在。
(2)科技政策的社會化和全球化帶來了新的矛盾和風險因素
首先,很多情況下,科技政策中對“科技負效應”問題的處理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文化的或象征的意義。禁止克隆人的法令在大規模追逐人體器官克隆的試驗背景下變成了軟約束[18];而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全球環境問題依然嚴峻。據聯合早報網(2011.01.15)報道全球歷來最熱10個年份中的9年,均發生在21世紀的頭十年。而全球氣候大會卻舉步維艱。這些現象是科技政策社會化與全球化之間矛盾的顯現,也是科技社會價值的矛盾顯現。在震驚世界的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災難之后,世界各國開始重新評估核安全,但是,標準仍然局限于科技理性的范圍,核利益主導仍然是核政策的核心。
其次,科技政策的社會化和全球化加劇了科技的社會化和全球化,從而帶來了新的風險因素。當代科學技術已發展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經濟的全球化開拓了新的科技政策的全球化,繼而加速了科技的全球化。各個國家都在制訂科技政策和建立相應的國家機構,科研組織也趨向于變得完全置于國家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之下。科技與社會一體化的加劇使現代科技的社會風險愈來愈突出。科技全球化使得大科學系統變得更加復雜化和精細化,對其把握和控制也就愈困難。雖然美國和原蘇聯在冷戰期間的核競賽早已結束,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整個世界核競賽的來臨,圍繞核問題的沖突成為當代世界戰爭的重要誘發因素。
3 科技價值創造中的質疑與挑戰
一方面,當代科技風險對知識及因果鏈條的確定性提出了極大地挑戰,即使是專家有時面對風險也會不知所措。當代科技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打破了嚴格的因果鏈條,而風險則往往由于原因不明而被弱化甚至否認。這未必出于專家的個人意愿,或可以稱之為一種“被迫的或不得已的不負責任”。因果鏈條的斷裂導致的原因不明為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的參與提供了空隙,由此,風險的評估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政治經濟的目的。
另外,科技活動中利益影響因素的滲透可能使科學成為風險的生產者。科勞恩(W.Krohn)曾指出,17世紀以來的科學有一個基本假定,即科學理論陳述和結論的正確或錯誤,以及實驗室中實踐的成功或失敗,都是獨立于社會道德規范之外的。迄今為止,科學行為脫離由錯誤或失敗而造成的社會性后果,仍被看做是科學的一項基本權利。但是,他認為,這一假定只適合于如下兩種理想狀態:第一,實驗室“控制”狀態下的操作必須對實驗室之外的現實社會毫無影響。第二,科學話語“控制”狀態下的理論主張必須對科學之外的日常話語毫無影響。或者說,理論主張的合法性僅靠科學內部的認可條件獲得可靠性,而不會進入社會的交流系統加以傳播。科勞恩認為,實際上科學行為很難滿足上述兩個條件,實驗活動往往像其他任何活動一樣不可避免地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同時它也會對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產生影響[19]。尤其是在當代,各種高新技術與社會關系復雜性的增長與人們認識這種復雜性能力的有限性形成鮮明的對比,不能完全理解各種因素在技術過程中的相互依賴性,從而使社會性風險迅速提高。
4 科技價值實現中的矛盾體現
4.1 科技風險評估中的不確定性
首先,現代科技風險評估中的經驗數據嚴重缺乏。現代科技風險“低概率、高危害”的特征,很多情況下為科學家提供的樣本數量是非常少的。在大科學的時代,可能一個項目只有少數幾個大實驗室具備科研的能力,從而使實驗本身的重復性和科學的主體性下降。另外,當代科技風險具有貝克所說的“不可計算”性特征。當今一些災難性的事件比如核災難,并不像汽車事故那樣頻繁發生。只有在日本海嘯核災難實際發生之后,新的評估指標才會出現。而有些科技風險,比如基因風險,是一種長期積累效應,短期內也無法提供有效的經驗數據。
最后,沒有充分考慮到系統的相互作用。風險評估的方法傾向于是分析性的,即往往把系統分解為構成的要素,再計算每一個要素的風險概率。但實際情況卻是,在科技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技術風險是系統相關的,技術風險的“蝴蝶效應”加劇了風險評估的不確定性。另外,專家們只能較好地掌控屬于自己領域的知識,但現實世界不可能只分配給專家屬于自己領域的問題,而不與其他領域發生關聯。“專家的人性缺點在于,他們在某一個領域的成功會導致他們設想(有時候實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自己的結論在其他領域中也同樣成立。”[20]
4.2 科技風險治理中的責任缺失
在風險社會中,科技風險治理表現出一種貝克稱之為“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狀態,即在現代制度下無法為科技風險所帶來的損害找到明確的責任人。它也有效地解釋了“現代社會制度怎樣和為什么必須不可避免地承認災難的真實存在,同時又否認其存在,掩藏其起源并排除補償或控制。換一種方式說,風險社會的特征是愈來愈多的環境的法律和法規的擴張。然而同時,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機構似乎明確地為任何事負責”。[21]
貝克將這一現象的形成歸因于當代科技風險或制度風險的“人為不確定性”特征與風險社會的“定義關系”之間無法協調的矛盾。“在風險社會,我們必須把定義關系看得類似于卡爾·馬克思的生產關系。風險社會的定義關系包括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構成風險識別和評估的特定規則、制度和能力。它們是風險政治運行于其中的法律的、認識論的和文化的權力模子。”[21]貝克將這種定義關系用以下四個問題來加以說明:
第一,誰將定義和決定產品的無危害性、危險、風險?責任由誰決定——由制造了風險的人,由從中受益的人,由它們潛在地影響的人還是由公共機構決定?第二,包括關于原因、范圍、行動者等等的哪種知識或無知?證明和“證據“必須呈送于誰?第三,在一個關于環境風險的知識必定遭到抗辯和充滿蓋然主義(Probabilism)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充分的證據?第四,誰將決定對受害者的賠償?對未來損害的限制進行控制和管理的適當方式是什么[21]?
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狀態使當代科技風險治理陷入了困境:難以準確界定風險的最終危害結果;難以明確界定風險所帶來的后果的責任承擔者;難以找到關于風險的充分的證據;難以形成明確的賠償機制;難以決定對未來損害進行控制和管理的適當方式;難以承擔起事前預防和事后解決的責任等。因此,對現代科技風險的管理與治理超出了單純的科學、專家、政治的管轄范圍,而逐漸變得需要社會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
5 反思性與后科技管理時代
科技價值體系的反思性特征是“懷疑論”的自我運用,這種反思性不會將科學技術消融或擊潰,恰恰相反,正是當代科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是科技價值體系走向自我成熟與完善的標志。反思性正在促使建立起一種科技價值體系新的運行邏輯,也開啟了后科技管理時代的大門。
在傳統科技管理和風險評估中,科學技術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幾乎占據了絕對權威的地位。依據庫恩的范式理論,科技實踐局限在一個封閉的共同體中并一直遵循以下原則:解謎工作的方式在那個共同體看來是成功的和進步的;持不同意見者被忽略了,或作為門外漢被令人討厭地打發走了。因此,即便我們從外部來看一些科學或技術的解謎體系是有根本缺陷的或近乎空洞的,但共同體依然有著充足的信念并保持意見的一致[22]。但是,隨著科技價值體系反思性特征的逐步顯現,這種封閉的以范式為基礎的常規實踐突然發現自己處于一種極其尷尬的境地:新的科技風險問題不斷被制造出來,而傳統的規范及方法對此則表現出無知的狀態。這時,科技實踐就進入了后常規科學的實踐領域(見圖1)。由常規科學向后常規科學模式的轉化根本上源自于科技價值系統中主導價值的轉移(見圖2)。

圖1 三種評估方式及其應用領域

圖2 三種評估方式與主導性科技價值轉化
在三種風險評估方式中,應用科學和專業咨詢都屬于傳統的風險評估,處理不確定性和決策厲害程度均不是很高的領域。應用科學的研究主體為科研專家,主要任務是技術系統內的解謎工作,風險主要來源于科技系統內部的不確定性,以科技固有價值標準為主導,主要表現為系統內部科技方法和理論的真理性和效用性,而較少涉及科技系統之外的利益問題。專業咨詢的評估方式更注重可行性,開始滲透主體的利益和價值因素。專家們往往被要求對決策或行動的后果承擔某種道德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可能源于科技系統內部,但解決途徑卻往往不能單單靠系統內部的方法論,而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將部分社會因素納入其中。在傳統風險評估中,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責任和地位是決定性的,具有壟斷的權威性。
而到了后常規科學時期,評估所面臨的是極高的決策厲害性和不確定性的風險領域,主要對象是諸如核風險、基因風險等當代科技風險。社會化和全球化是當代科技風險的重要特征,不確定性影響到生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因此,當代科技風險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科技的社會價值。由于科技社會價值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使得當代科技風險管理超出了任何一門單獨的學科和專業,超出了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壟斷權威性范圍。
相對于傳統風險評估,后科技時代政府的作用將愈加重要,并在風險管理中承擔重要責任。尤其當潛在科技風險被模糊評估且無定論時,政府必須將多元、公眾、開放、民主納入視野。同時,當代科技風險后果的嚴重性和長期性使得短期利益行為變得不可行,政府必須著眼于未來并制定合理的政策。后科技時代風險管理和評估的困境來源于當代科技風險與風險社會“定義關系”之間的矛盾。如果說生產關系是以財富分配為主的社會的主導關系,那么定義關系則是風險社會中風險分配的主導關系;如果說生產關系表明了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那么定義關系則表明了在風險制造和治理的過程中人們之間所形成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如果說生產關系體現了國家生產和分配物質資料的制度形式和權力關系,那么定義關系則體現了風險生產和賠償的制度形式和權力關系。因此,后科技管理時代,能否處理好風險社會的“定義關系”將成為政府作用的關鍵所在。
隨著公眾科學素質的提高,其在公共政策中的參與程度也正在逐漸增強,這為后科技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包括科技風險在內的社會風險防范和危機管理,并通過制度創新和政府再造,建立起完善的預警機制、高效的應對機制、完備的法律機制、開放的溝通協調機制、制度化的組織機制、政府間合作機制和國家間合作機制以及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23]。
當代科技風險促使了科技價值體系的反思性轉變,而就在這種“反思性”中,科學技術得以重新審視自身。這樣一種歷史性的“重新審視”恰是后工業時代科學技術內在動力的獲取過程,蘊藏并開拓著后常規科技實踐可持續之路的希望與機會。
[1][德]恩格斯.自然辯證法[A].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C].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1.
[2]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M].曹葆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28.
[3][德]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強譯.風險社會[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6,21,45,47,205.
[4][英]弗蘭克·富里迪.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47.
[5][英]布賴恩·瑪吉.波普爾的哲學觀與政治觀——與K.波普爾的對話[J].哲學譯叢,1980,(6):54.
[6][英]波普爾.客觀知識[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35.
[7]趙萬里.科學技術與社會風險[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8,(3).
[8]周春彥.關于科學技術化的“化”的哲學思考[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17(3):27.
[9]段偉文.對技術化科學的哲學思考[J].哲學研究,2007,(3),76.
[10][德]馬克思,[德]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4-35.
[11]周春彥.關于科學技術化的“化”的哲學思考[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17(3):28.
[12][德]尼采著,余鴻榮譯.快樂的科學[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285.
[13][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1.16,23.
[14][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2.135.
[15][美]喬·霍蘭德.后現代精神和社會觀[A].[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64-65.
[16][英]大衛·伯姆.后現代科學和后現代世界[A].[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82.
[17][美]弗雷德里克·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與后現代科學[A].[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132-135.
[18]楊力行,劉酈,劉文輝.科技社會化與社會科技化[M].武漢:崇文書局,2006.43-44.
[19]Wolfgang Krohn.Sociey as alaboratory:the socialrisk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1994,21(3):174.
[20][英]哈里·奧特韋.公眾的智慧,專家的誤差:風險的語境理論[A].[英]謝爾頓·克里姆斯基,[英]多米尼克·戈爾丁編著.徐元玲,孟毓煥等譯.風險的社會理論學說[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47.
[21][德]烏爾里希·貝克著,吳英姿,孫淑敏譯.世界風險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72,149,191,192.
[22]西爾維奧·O.馮拖維克茲和杰羅姆·R.拉弗茲.三類風險評估及后常規科學的誕生[A].[英]謝爾頓·克里姆斯基,[英]多米尼克·戈爾丁編著.徐元玲,孟毓煥等譯.風險的社會理論學說[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85,302-303.
[23]徐瑞萍.科技時代的社會風險與政府管理——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及其對政府危機管理的啟示[J].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4):71.
Reflexivity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 Dan
(College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The properties of contemporary S&T risks break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the valu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SST).The base and rationality of the VSST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ized society are constantly challenged and questioned.A new kind of operation logic is forming.Its power comes from the new characteristic“reflexivity”of the VSST in risk society.The“reflexivity”firstly embodies the self-confrontation of the VSST—the negative value bor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VSST’s every elements resists conversely its own basis which includes self-confrotation change of the system compose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values;self-assaul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s;suspic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reation of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ST)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realizing process of the VST.
Valu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flexivity;Risk society
2011-06-18
米丹(1979-),女,河北正定人,科技哲學專業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科技與社會。
F062.3
A
(責任編輯 劉傳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