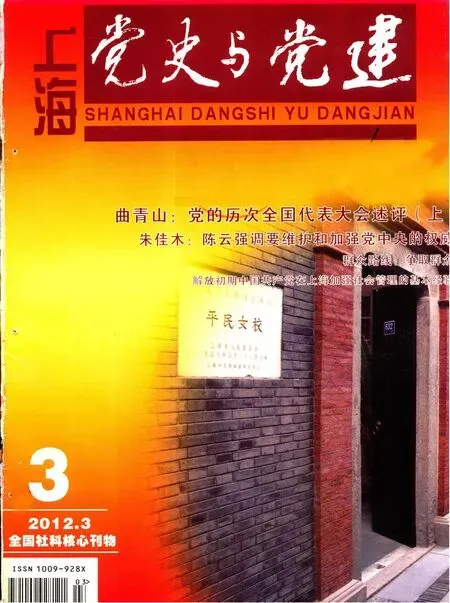關于對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研究
● 吳海勇
關于對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研究
● 吳海勇
本文梳理了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發展的三階段,指陳當代研究存在的問題,并對研究前景作出積極展望。
國共合作;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綜述
一、從往事追述到史料鉤沉,促成專題研究在新時期的展開
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國國民黨“一大”后,決議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以下簡稱“上海執行部”)于1924年2月25日在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召開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并定于3月1日正式辦公。到1925年底,該部辦公地被西山會議派強占,國民黨中央遂終止上海執行部行使職權。經歷近兩年風雨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劃上了句號。
由于上海執行部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在“四一二”后建立起來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對此有所忌諱,此后產生的國民黨黨史著述均不見述及上海執行部,直到國共開啟了第二次合作,才在1940年出版的《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中略有述及。[1]偶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兩篇報章短文,一為1936年的《小史料:上海執行部之驅逐共黨》,另一為1938年的《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時代》,終究改變不了上海執行部被打入歷史“冷宮”的狀況。隨后臺海兩岸長時間處于緊張對峙狀態,很長一段時間內,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處于沉寂狀態。海峽對岸,臺灣學者對上海執行部歷史的冷落持續,1994年出版的煌煌巨制《中國國民黨史述》中對于上海執行部也僅一筆帶過。[2]
兩相比較,中國大陸學界對這段歷史的關注趨向回暖的走勢。大陸學界對上海執行部歷史的涉及,至遲可追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梅龔彬曾被上海執行部聘為宣傳委員會委員,他有關五卅運動的回憶自然地提及了上海執行部。[3]1963年,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有關同志還對曾任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的張廷灝進行了訪談。[4]然而,就相關史料的公開與專題研究而言,還是要等到改革開放新時期。
1980年《新文學史料》第1期刊載茅盾的《文學與政治的交錯:回憶錄(六)》,述及上海執行部的建立、管理區域范圍,以及機構設置與人員組成,提到列寧追悼會、平民教育工作,實際上揭橥了共產黨人在上海執行部相關運動中的努力。同年,羅章龍在某座談會上也深情憶起上海執行部的往事。[5]
以此為起點,有關上海執行部的史料在短期內層見迭出。《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刊載了《吳玉章自傳》,其中提到作者在“五卅”后,受上海執行部提議回川組織國民黨(因四川國民黨為西山會議派石青陽、謝持等所包辦),改組當地國民黨,選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等往事。1982年出版的《廣東文史資料》第37輯系“黃埔軍校回憶錄專輯”,其中不乏黃埔人對當年赴上海執行部參加黃埔軍校入學考試的回憶,特別是郭一予《我對黃埔軍校的片斷回憶》還提及了毛澤東對報考人員的接待。[6]1983年初,由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辦的《黨史研究資料》,將該館收藏的1924年2月至3月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油印件)全文刊印,并作“編者按”介紹時代背景。3月,上海歷史研究所派人進京找羅章龍訪談,相關內容發表于《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輯,內含上海執行部的史事。[7]
1984年,《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增辟現代史資料欄,即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資料專輯為一通“威風鑼鼓”,集中發表了1963年訪談張廷灝的整理稿《回憶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劉重民1926年的《上海黨務報告》(部分)與任武雄的《關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后殿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史料選輯”,系從當時的上海《民國日報》、上海執行部印發的傳單以及上海執行部內刊《黨務月刊》中摘出。同年稍后,羅章龍的《椿園載記》出版。該書專設有“上海執行部國民黨主持人”一節,[8]提供了更多的歷史細節。年初,《團結報》發表羅章龍回憶上海執行部合影的文章,[9]客觀上為該書的問世作了前期宣傳。
隨著相關史料的披露,上海執行部研究隨之起步。在這一領域,任武雄的研究工作涉足較早。他早在1963年就參與了對張廷灝的訪談工作。多年在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收集的相關史料,為其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82年,任武雄發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10],就有所涉及上海執行部。1984年《黨史資料叢刊》第一輯中,他發表了《關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一次就此展開專題論述。同年,他又發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一文,文字更詳,且首次采用了1983年對丁君羊的訪談材料。[11]
二、20世紀最后15年上海執行部的相關研究概況
1985年后,任武雄繼續在上海執行部的研究領域擴大影響。比如,1985年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五卅運動的發動》,1987年發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的斗爭》,1989年發表《國共第一次合作在上海的活動》,皆設專節論及上海執行部。[12]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任武雄接連發表了《毛澤東在中央局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動》、《毛澤東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動大事年表》,均涉筆上海執行部;[13]另有“任止戈”署名文章《毛澤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14],亦出自任氏之手。
任武雄的堅持,使其處于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的前沿位置,相關的研究也彌補了同時期權威黨史部門的不足。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執行部歷史得以進入上海地方黨史。1989年問世的《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收錄了相關內容。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出版,其中“與國民黨右派的斗爭”章節即為任武雄受邀執筆,且以上海執行部為主打內容。這是上海執行部進入中共上海地方黨史正本的開始,同時也代表了該研究在20世紀末的水準。
在20世紀最后15年間,對于上海執行部研究具有實質性助推力的還來自于該專題之外,主要有:中共早期人物研究的進步、民國歷史研究的發展、相關回憶文章的發表以及民國人物日記、蘇聯解密檔案等相關史料的整理出版。
中共早期人物研究方面,惲代英、向警予、侯紹裘等人的研究在20世紀的最后15年間皆有進展,其中不乏與上海執行部相關的內容。特別是何先義等人整理的《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跡年表》,有關向警予任職執行部婦女部后的內容,[15]皆有補于上海執行部的歷史。
民國史方面,國共合作史的一些專題亦有助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如第一次國共合作在蘇浙皖等地資料的匯編出版,提供了上海執行部職責范圍的史料。曹力鐵的《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對五卅運動中的上海執行部運作多有揭橥。[16]附帶提及,這階段學術界有關張靜江、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葉楚傖等國民黨人物的研究也有所進展,雖深度與針對性有限,但亦有助于對上海執行部歷史的了解。
回憶文章方面,熊輝的 《黨的老朋友——喻育之》[17]、郝長興的《先父郝兆先的早期革命經歷》[18],分別述及喻育之和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的經歷,為上海執行部研究提供有意義的歷史細節。關于對上海執行部任職的國共雙方要員留下的唯一合影中人員的辨認亦有進展。周氏后人指出,合影后排右一原認為是戴季陶,實為其先父周佩箴,進而又指出中排左二為其伯父周頌西。[19]
這一時期,民國人物日記、蘇聯解密檔案等相關史料相繼整理問世。原受命負責上海執行部工作的邵元沖雖終未赴任,但一直身居要職,不僅見證了國共相爭,而且后來還成為西山會議派的成員,成為國民黨“分共”的重要推手之一。1990年出版的《邵元沖日記》中不乏與上海執行部直接相關的內容。[20]20世紀末,聯共(布)與共產國際解密檔案在中國翻譯出版,其中,黃仁事件后(檔案編者時間判定有誤)中共中央寫給鮑羅廷的信,揭示了國共在上海執行部角力方面的重要內幕,[21]絕對不可輕忽。
三、21世紀以來相關研究的突進
步入21世紀,有關上海執行部的宣傳與研究齊頭并進,前景更趨看好。在宣傳方面,除報刊發表的若干宣介文章之外,相關內容集聚于毛澤東類專書上。2003年出版的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系》,專設章節“活躍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22]。2006年張萬祿的《毛澤東的道路:1921-1935》,亦有專門章節“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日子里”[23]。2009年6月,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舉辦“永恒的豐碑——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物文獻展”,展出了上海執行部的若干手稿、信函、電文、薪資冊等,加上媒體的宣傳報道,進一步激發了人們的興趣。
在學術方面,上海執行部研究的突進愈見明顯。主要有三:
一是對“環檔”等資料進行探寶式發掘與初步解讀。1930年初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成立后,對存放于環龍路44號的檔案(簡稱“環檔”)進行過接收與整理。[24]爾后,“環檔”等檔案隨著國民黨政權渡海去了臺灣,最終入藏國民黨黨史館。中國大陸學者對臺灣館藏“環檔”等史料的探尋,實際上始于20世紀末。楊天石到臺灣查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檔案早于1996年,相關文章發表則始于2001年,[25]對大陸學者無疑具有示范作用。2002年,史洛對“環檔”的一份上海執行部經費收支表進行了專門分析。[26]2003年,田子渝發表《在臺北發現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兩份史料》,其一為毛澤東寫于1925年底的《關于上海〈民國日報〉審查結果報告》(“漢檔”),涉及上海《民國日報》在1924年的劣跡,[27]存錄了毛澤東當年任職于上海執行部時期的記憶。同年出版的深町英夫專著引用了《中央宣傳部部長毛澤東上中執會函》(1925年12月26日,“漢檔”),矛頭也指向上海《民國日報》[28],與上一檔案可以合觀。而楊天石發表于同年的《毛澤東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則堪稱運用“環檔”研究上海執行部的典范之作。[29]2005年發表的梁尚賢《臺灣國民黨檔案中的一組重要史料》,鉤沉出一份1924年廖仲愷發給上海執行部胡漢民的密電文。[30]同年刊發的田子渝《1995年至2005年宣傳、研究惲代英新成果評析》,又鉤出1924年至1925年惲代英任職上海執行部時期的3封信函。[31]青年學者苗青的《國共合作見證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對新近展示的上海執行部薪資冊進行分析,[32]在學術上可謂預流。
二是歷史親歷者的記錄、事跡繼續得以出版與披露。李曉光《懷念父親李宇超》[33]、喻育之《百歲自述》[34],分別涉及曾任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委員的李宇超和上海執行部干事喻育之的事跡。2007年,《謝持日記未刊稿》得以付梓出版[35],為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又增添了一份親歷者的記錄。
三是國共合作史、西山會議派等研究取得長足進展。2001年王奇生的《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年國共黨際關系再考察》[36]和2002年楊奎松的《“容共”,還是“分共”?——1925年國民黨因“容共”而分裂之緣起與經過》[37]俱為長篇大論,有新的創見。楊奎松后又撰寫出版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38]。此外,曾成貴《中國國民黨漢口執行部解析》接通了上海執行部拓展職責、兼管兩湖的歷史。[39]李攀的 《上海國民黨基層組織研究——以1924-1927年為界》,從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上海黨建角度透視了上海執行部的運作。[40]對于西山會議派的歷史,中國大陸學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所涉足,新世紀初尚紅娟的相關研究成果具備了學術前沿水準,[41]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多可參考。①
四、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有關上海執行部的歷史研究以中國大陸學術界為主,且明顯呈現出三階段的特點。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以大陸相關知情人的歷史追憶與史料公開為先導,上海執行部研究迅速跟進,清理出大體史脈,此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1985-2000年這15年間,對既有研究成果進行了交叉專題的整合,并最終實現了經典化重寫工作,使上海執行部歷史寫入上海地方黨史正本。此外,相關學術研究的進步,以及有關史料的披露,亦對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有積極意義,只是未能為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及時吸納。21世紀,上海執行部研究進入第三階段。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緩和,始于20世紀末的大陸學者赴臺灣查檔收獲在此階段得以發表,由此帶動新一輪的赴臺查檔熱潮。對臺灣藏“環檔”、“漢檔”等檔案的發掘利用,一時間較其他史料的發掘與相關研究的進展,之于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似更具學術推動力。
歷史研究必須建筑在豐厚史料的基礎上,新史料的發掘每每能推動學術研究的突破,當代學者對臺灣檔案的興趣即基于此,這對于史料較為稀缺的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來說更是如此。然而,倚重“環檔”不應偏廢對大陸史料的發掘運用。事實上,就上海執行部專題而言,當代學者對大陸史料的了解多僅限于第一階段成果,甚至連這都未必盡數掌握。此外,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要實現突進,還應即時吸納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賦予此專題以新的視域。唯有如此,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方能走出低水平重復的層級。
就近期而言,臺灣相關部門不允許查檔者對“環檔”、“漢檔”等檔案進行復印,給大陸學者赴臺查檔、全面掌握這部分資料增加了困難,這成為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的瓶頸問題。在大陸學界努力推進上海執行部歷史研究的進程中,真誠希望臺灣學者能夠加盟到相關研究中來,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為人類社會存一份歷史本真,這理應是中華學人的共同追求。
[1]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M].重慶:黃埔出版社,1940.148.
[2]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M].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94.
[3][10][11][12][13]任武雄.黨史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0,201-212,200,254-256.260-279.213-217,228-239.330-331.342-344.
[4]張廷灝.回憶國民黨上海執行部[J].黨史資料叢刊,1984(1).118.
[5]黃啟權.王荷波傳[J].黨史研究與教學,1983(7).
[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廣東文史資料(第37輯)[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73.
[7]羅章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國共合作[J].黨史資料叢刊,1983(4).
[8]羅章龍.椿園載記[M].北京:三聯書店,1984.296-303.
[9]述直.從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談起:羅章龍回憶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 [N].團結報,1984-1-7.
[14]任止戈.毛澤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J].黨史研究資料,1993(11).
[15]何先義,唐德佩,何先培.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跡年表[J].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3).
[16]曹力鐵.國民黨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J].近代史研究,1989(3).
[17]熊輝.黨的老朋友──喻育之[J].湖北文史資料,1994(1).
[18]郝長興.先父郝兆先的早期革命經歷[J].江淮文史,1995(2).
[19]陸米強.一幀國共兩黨成員合影照片引出的故事[J].上海檔案,1998(4).
[20]王仰清,許映湖.邵元沖日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535-536.
[22]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系[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
[23]張萬祿.毛澤東的道路:1921-1935[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24]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 (上冊)[C].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61.346.喬寶泰.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冊)[C].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381.387.593.
[25]楊天石.《瞿秋白的聲明》與國共兩黨的“分家”風波——讀臺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檔案[J].黨史縱橫,2001(12).
[26]史洛.賬單里有文章[J].檔案與史學,2002(5).
[27]田子渝.在臺北發現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兩份史料[J].中共黨史研究,2003(5).
[28]深町英夫.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52.
[29]楊天石.毛澤東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J].百年潮,2003(6).
[30]梁尚賢.臺灣國民黨檔案中的一組重要史料[J].百年潮,2005(4).
[31]田子渝.1995年至2005年宣傳、研究惲代英新成果評析[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5(5).
[32]苗青.國共合作見證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J].世紀,2010(2).
[33]李曉光.懷念父親李宇超[J].炎黃春秋,2007(9).
[34]喻育之,肖志華,施裕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要事見聞錄[J].武漢文史資料,2011(3).
[35]謝持.謝持日記未刊稿[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6]王奇生.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年國共黨際關系再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1(4).
[37]楊奎松.“容共”,還是“分共”? ——1925年國民黨因“容共”而分裂之緣起與經過[J].近代史研究,2002(4).
[38]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39]曾成貴.中國國民黨漢口執行部解析[J].民國檔案,2009(4).
[40]李攀.上海國民黨基層組織研究——以1924-1927年為界[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8.
[41]尚紅娟.革命黨精英在聯俄容共后的蛻變—西山會議派之再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8.
注釋:
①以上僅就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國知網”收錄的學位論文)展開綜述,有關職能部門的內部研究報告暫不在論列,無所新見的專題論文更不贅言。
D231
A
1009-928X(2012)03-0014-04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一處副處長
■ 責任編輯:周奕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