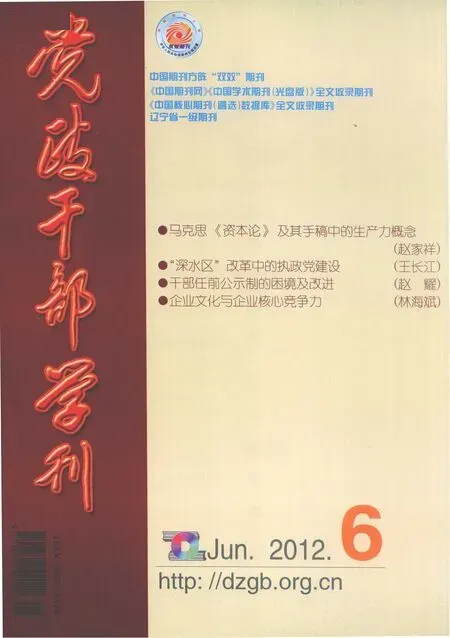預期、生活成本及生產組合的發展※
——東北某村的經濟合作組織
李洪君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2)
預期、生活成本及生產組合的發展※
——東北某村的經濟合作組織
李洪君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2)
在經濟不發達的東北村莊里,合作經濟組織主要表現為以承包山林溝塘為主的生產組合。由于承包周期短、成本沉淀、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的作用,這種生產組合罕有擴大再生產者,也難以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這樣的村級經濟基礎之上,雖有鎮政府牽頭,組建種種以經濟作物為主的專業性協會,但尚難以發展成為跨區域的合作經濟組織。
生產組合;經濟合作組織;生活成本
國外農業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單戶經營很難從容應對市場狂潮,組織起來的農戶才會生活得更好。政學兩界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期待很高,把它看做是克服家庭分散經營、小規模、低商品率、低效益、競爭力弱等弊端的“弱者的武器”。其具體特征是,農民自愿自主,政府主導,以人為本(農民的現代化),城市資本和技術支持(反哺),城鄉、工農業和社會協調推進而成。對于大部分非明星村莊來說,經濟合作組織并沒有形成上述圖景。本文且對東北常見的農戶經營組合做簡單描述,并初步討論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前景等相關問題。
一、國內農戶聯合經營的類型
目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大致可分三類。1.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不過,也有人認為,鄉政村治下的“一塊牌子,兩套班子”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不算作真正的合作經濟組織,因為它經社合一,全民參與。2.專業合作組織,即按生產經營同類農產品的產業鏈聯合起來的業緣性合作經濟組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學者根據合作組織的功能,將其分類為采購、銷售、加工、服務綜合型五種。根據合作經濟組織與政府的關系,將其分為自辦、官辦、官民結合型。也有學者主張可分類為能人/大戶帶動型、農技部門牽頭型、農業龍頭企業聯結型、農產品批發市場中介型、基層供銷社改造型等五種。3.聯合體或生產組合,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的合伙人組成的臨時性組織。它不需要完備的組織結構體系,也不需要登記注冊。這其實是傳統的生產方式(伙耕、伙種)的復制,同時也是持久性的大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的前身。在國內,這種生產組合/聯合體是很常見的。如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博鰲村的西瓜種植聯合體,長坡鎮的農產品加工型聯合體。
二、生產組合:東北S村主要的合作經濟組織
S村位于吉林省H市H鎮東部一盆地之內,包括6個自然村(屯),彼此相距6里左右,是一個松散型聚居的村莊。目前共有440戶家庭,1602名村民;共有耕地261坰(公頃)。村莊經濟不發達。村民以從事農業種植為主。耕地以旱田為主,水稻只占耕地面積十分之一左右。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村民尚播種小豆、高粱、谷子、芝麻等雜糧;此后,村民基本種植玉米、黃豆兩種作物。耕地會為每戶帶來3000-5000元左右的收入。在農閑時節,村民可以從事捕捉林蛙、打松塔、采摘蘑菇等副業。
在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S村,家庭經營的規模總是有限。單個家庭的不經濟(以及無能為力),對合作生產有著很強烈的需求。由于工業幾乎沒有,因此,靠山吃山,承包山林采伐任務、承包溝塘養蛙就成為有限的副業項目。幾萬、十幾萬元的先期投資,多由幾戶合伙經營才能完成。幾個合伙人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不存在委托代理關系。這種簡單的合伙經營,最初是以血緣、親緣關系為主(學界有人將其視為家庭經營的放大)。不過,村民很快就發現,兄弟經營弊多利少,常常鬧得不歡而散。于是,跨越血緣、親緣,在本地范圍內尋找合伙人就越來越多地取代了原初的親屬圈合伙關系。
地緣生產組合。受制于土地,曾是費孝通的一本英文專著名稱,以地緣來考察農村社區的結構與行動,是上世紀30年代社會學家不約而同的切入點。“差序格局”這一表述本身亦包含因參照對象不同而變化的地緣關系。“本地/同鄉/自己”的概念,是隨著年齡、活動領域、參照物的不同而充滿彈性的。街道、屯、村、鎮、縣、市(地區)、省,都可以在不同語境下成為村民對“社群”的認同單位。一般說來,由于兒時基本都在自己家街道附近玩耍,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對他所屬的街道是充滿感情的。隨歲月而成長起來的朋友,基本是村民基于地緣來考慮的首選合作對象。如伙耕。在80年代,常有兩家合養一頭牛者。村民鄭某與鄰居S常年合伙耙地、撿柴禾:一方有手扶拖拉機,適于水稻春季耙地;一方有牛,適于冬季撿柴禾,以及一般性農業生產用途。
隨著生產領域的擴大,屯成為村民尋找合伙對象的“本地人”的認同單位。由于屯距較遠,相鄰的屯民即使認識,也只是點頭之交。只有屯內的熟人,才知根知底。生產組合的生產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某一方隨時可以選擇退出。也沒有嚴格的賬簿制度或其他書面法律文書予以約束,很大程度上要靠參與人的道德自覺。如下這種生產組合完全是在本屯內方能產生。
D屯王某買了一個脫粒機、一輛小四輪拖拉機,他與同屯的周某合作,周某買三輪車,負責收糧、運糧。因為,村民希望在玉米脫粒之后盡快將其賣掉,否則玉米會很快“掉秤”(水分蒸發,損失重量)。王、周二人一個負責買,一個負責脫粒,同時又共同雇了十個青年裝卸工,組成一個聯合體。該聯合體從糧農手里將其“打玉米”(脫粒)的工作承包下來。報酬是每斤玉米抽取一分錢。一個冬天,王、周便各賺一萬多元。
這種合作,雙方各出資金購買屬于自己的生產工具,在一個經營項目上互相分工,利潤則依“工種”而分配,是一種穩定性較差的生產組合。王某可以隨時與其他買糧者合作,周某亦然。如果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屯,信息溝通、交通、與第三人合作等等,都是難以確定的因素。
合伙人共同出資組建具有初級賬簿制度的生產組合,如承包溝塘以捕/養蛙,是S村較為典型的生產組合。S村為林地所包圍,一直以來(或許是幾千年),村民都是上山下河去捕蛙,以貼補家用。2000年,林場將其所屬的林地承包給林場下崗、失業職工,以增加這些職工的收入。承包費用在萬元左右。林場職工自己管理不過來,便將這些林地轉包出去。下家還可以再轉包出去。這個時候,一萬元的承包費已經上漲到10萬元左右了,而且承包期也常被分割為一至五年不等。如林場Y家以一萬元承包的溝塘,賣給鄰村的張某,索價5萬元。張某自己管理了一年,以7萬元的價格再次轉包給D屯的張某。張如果愿意,還可以再次轉包出去。L屯曲某承包后溝后,以18萬的價格賣給同屯四位村民。為何會有層層轉包?皆因林蛙常常在森林里做較大范圍的遷移(估計有十幾公里)。因此,正如本地俗語所講,誰也不知道哪塊云彩會下雨,誰也不會知道哪個溝塘會下蛤蟆 (意即蛤蟆多)。這種偶然性、風險性讓一些行事謹慎的人選擇將溝塘再次轉包出去,雖然賺得少些,但是穩妥。通常,距離林場駐地愈遠,信息愈遲滯,那里的村民愈易成為再次轉包人。
2005年夏,村民A聽說東南岔屯的溝里有一個蛤蟆溝要 “轉包”。承包期是4年,索價35000元。他在同屯內找到村民F、Z、L來共同承包。本來還考慮了另外一個村民,但這幾個人一商量,覺得這個人在金錢上有些“愛小”(貪小便宜),還是四個人承包了。每人出資8000多元,向承包人轉包下這個蛤蟆溝。每人另出資500元作為當年的活動經費。當年秋天中秋節之前,便開始一系列的工作。(1)先是要搭一個小木屋。小木屋呈人字形,用胳膊粗細的木桿子搭好框架后,再覆以青草與黃泥。屋內有炊灶與炕,以供幾人食宿。(2)需要清理山腳下的蛤蟆趟子。一般情況下,被承包的溝里的山腳下都有蛤蟆趟子的痕跡,只需要清理一下即可。蛤蟆趟子有一米來寬,向山的一側用塑料薄膜擋起來,后者每隔10米左右用一根深插入土的高約一米的棍子固定住。一捆120元的塑料薄膜標稱能擋500米,實際上可擋約450米左右。他們承包的這個溝里的的蛤蟆趟子有8里多,需要9卷塑料薄膜。(3)做好擋膜之后,還需要在趟子上每隔20、30米挖一個直徑50厘米、深50厘米的坑(在8里多長的蛤蟆趟子里挖這些坑,是相對較累的體力活兒)。當蛤蟆自山坡上下來的時候,會遇到擋膜,于是它們不得不沿著擋膜蹦跳以尋找出口,這當中,它們便會掉進小坑里無法出來;等待它們的是被捉走的命運。(4)深秋時節,吃得肥飽的蛤蟆漸漸從山上下來,到河里或是溝塘里過冬。如果有雨,則會成群地蹦跳下山。這時候,單單依靠幾個承包人來巡邏、捉撿,人力顯然不足。他們還需要從本屯雇兩三個信得過的年輕人來幫忙,一日工30元左右。收獲的蛤蟆要在當天過秤,記賬。次日交由某人帶回屯里去或售或暫時保存起來。(5)建一深水池,以供林蛙冬眠。(6)收入情況。林蛙的價格不太穩定。在2005年時,雌蛙80-100元/斤、雄蛙16-20元/斤。2005年秋,A等人承包的這個蛤蟆溝為他們帶來了21000元總收入。去掉3000元成本。當年每人分得4500多元。2006年,Z因故退出,他余下來的6000多元的股份則由余下三人購買,每人的出資額變成了8800元。該年林蛙數量不多,只賣得14000元,去掉成本,每人分得4100元。二年經營所得,基本上與其先期投入持平。承包期還有二年到期。這二年的林蛙收入為其純利潤。三人預計,這兩年里每人可得8000元左右收入。平均算下來,四年里,此項投資項目可帶來年均2000元的收入。
這種聯合體并不會把利潤分割出一部分來進行再投資。主要原因是,聯合體是基于短期承包期而臨時組建的。承包期一般5年左右。到期后,原承包人可以續簽,但要面臨其他競爭:如果其他人能夠給出更高的價格來,那么,為了能夠繼續承包林蛙溝,原承包人不得不跟進(提高競價)以獲取承包權。在此情況下,如果承包人在自己承包期內進行一些固定資產方面的投資,在下一輪承包時,這些投資將成為“雞肋”:或為了它而加大競價力度,或是讓它成為沉淀成本。
三、預期、生活成本及生產組合的前景
國內其他地區的這種生產組合/聯合體的未來,一是走向更寬廣更深層次的聯合,甚至發展為一相對獨立的實體,一是分崩離析為個體戶。由于缺乏生產性實體,缺乏長期投資的機會,在S村,這些聯合體發展成為合伙企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討論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因素時曾提及,形式理性的法律所提供的穩定的預期將是企業家擴大再生產的制度保障之一。在S村,政策是相對穩定的,但政策所帶來的頻繁的承包周期,以及相隨而來的競價所帶來的成本的不確定性,侵蝕了農村社區經濟合作組織走向形式理性進程,亦阻礙了承包人擴大經營的動力,抑制了相應的企業家精神。我們知道,一些合伙企業,就是由這種生產組合發展而來的。經濟發達了,分工細密了,人們的活動能力增強了,這種生產組合就會越來越多,那么,生成更具有活動能力的合作經濟組織就指日可待。
在HS鎮政府的推動下,一些專業性合作經濟組織出現了。鎮政府鼓勵村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貝母、黑豆果、甜菜等,期待區域種植會形成規模,以增強市場競爭力。目前,只有貝母、林蛙類專業合作組織呈現較好的發展勢頭。二者都是由政府牽頭組建。鎮政府甚至幫助本地貝母種植戶申請了商標。據HS鎮政府多種經營辦李某介紹,鎮政府只是發揮提供銷售信息的作用。種植戶自動成為某協會會員,無須繳納會員費,也無會員大會。在我看來,這種單純的以政府作為能動者的“協會”的可持續性不甚樂觀。HS鎮政府還在期望H市政府能夠在跨鎮層面上予以推動,以形成更大的品牌效應。但國內其他地區的跨區域合作組織,基本都是市場驅動者。似乎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跨區域合作經濟組織才會水到渠成。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這種初級經濟組織的發展,缺乏積累資本及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的內在動力。200年前的歐洲的家庭、家族及社區型經濟組織的發展,在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框架內,是以積累財富來響應“上帝的選民”的感召從而構成內在的發展動力。[1]在21世紀的東北農村,正值超前的消費文化席卷大地之時。我所訪談的上述若干經濟組織的從業者都表示,他們每年自經濟組合中所獲收益的大部分,都在當年被消費殆盡。誠然,長期的通貨膨脹因素削弱了村民繼續積蓄的熱情,不過,在城市及大眾媒體所引領的“我消費,我幸福”的生活范式下,日益提升的生活水準(耐用消費品、肉蛋奶類高蛋白質食物攝取量、閑暇時間及相關經濟支出等)擴大了村民的消費支出,削弱了可能的資本積累,從而在客觀上構成了阻礙初級經濟組合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的進程。
[1][法]尼古拉·埃爾潘著.孫沛東譯.消費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30).
責任編輯 張小莉
C91
A
1672-2426(2012)06-0094-03
李洪君(1974- ),男,吉林樺甸人,沈陽師范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改革開放以來東北農村消費文化變遷的實證研究”(10CSH020)階段成果。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文化視角下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L11CKS015)階段成果。
- 黨政干部學刊的其它文章
- 發展文化事業與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