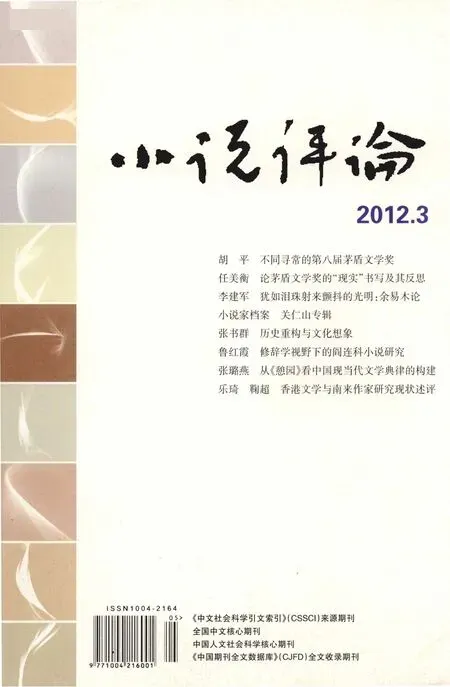從《憩園》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典律的構建
張璐燕
在一個各式各樣“經典”層出不窮的年代,人們以諸如“紅色經典”、“魯迅經典全集”、“朱自清散文經典全集”、“中國中篇小說經典”等名義,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甄選,一方面是勢所必然的,另一方面又不禁讓人心生疑慮:由于缺乏必要的距離,這些所謂的“經典”真的能經的起歲月的淘洗嗎?或者說,如果真的有所謂“現當代文學經典”的話,又是哪些質素的存在,使這些作品區別于中國古典及世界文學史上的其它經典之作,而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呢?
雖然對于《憩園》的評價一直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是,現在的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還是傾向于承認,《憩園》至少是包含了一些可以構成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的因素的。因此,通過分析《憩園》文本所包含的經典性因素,或許將有助于我們發現構成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的部分典律之所在。
一
與巴金的其它小說相比,《憩園》的最大特征在其復雜性。這種復雜性首先表現在小說的結構方面。相對于巴金小說經常采用的單線結構,《憩園》的結構非常類似于一出戲劇:《憩園》講述了“我”、姚國棟、楊夢癡、萬昭華、姚小虎、寒兒等人的身世經歷和情感體驗,故事的主體是“現在的故事”,各個人物“過去的故事”通過回溯來體現,并對“現在的故事”的發展、突變造成直接的影響。再加上瞎眼女人和老車夫的故事這條隱含線索,使《憩園》在較短的篇幅內包含了繁復的內容,“而且故事之間及其各自內部意緒的沖突構成了文本價值取向與情感指向的復雜性,形成了作品的復調品格。”也就是說,由于《憩園》中“各個故事中的多種思緒彼此詰問、相互質疑,”①即使是人物的同一行為,出于不同的價值立場和觀察角度,也有著迥乎不同的認識與評價。因此,作者對于人物的價值判斷在這里被暫時擱置,《憩園》在情感表達方面因此呈現出一種復雜難明的特質。
比如,在批判楊夢癡腐化墮落、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他對于家園的深深眷戀、對于美好事物的無限熱愛、對于家人的真誠懺悔,都讓人不由自主地對他有所寬宥;姚國棟的眼高手低、言不顧行固然讓人覺得好笑,但他對朋友的古道熱腸、對親人的深摯之愛,又讓人不禁對他的不幸遭遇給予深切同情;萬昭華的溫柔善良、充滿愛心使《憩園》整體上的灰暗色調帶上了一抹溫暖人心的亮色,但她種種幫助別人的設想卻只是停留在口頭,對于所處環境的無力擺脫使她成為一只無法真正飛翔的“籠中鳥”;“我”對于社會的冷靜觀察、對于他人的真誠救助、對于存在意義的痛苦思索,體現出一個啟蒙者的可貴品質,可“我”始終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不管是楊夢癡、姚國棟,還是萬昭華、寒兒,“我”的介入對于他們的命運沒有產生絲毫的改變……
就像許多論者指出的那樣,使《憩園》包含了如此豐富歧異的情感的緣由,是因為巴金本人人到中年、初建家庭,心態變為平和;是因為時代的變遷,過去家族罪惡的制造者如今也成為封建制度的犧牲品;是因為戰爭的艱苦環境,使巴金進一步體認到人的凡俗本性;是因為“‘我’對寫作價值的消解,意味著對五四新文學確立的改良人生、療救人生的啟蒙主義功用的懷疑,一定意義上也是對時代賦予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變革社會責任的疑慮”②。這一切使得《憩園》中的人物更接近生活本身,而不是某種價值觀念的載體,《憩園》因此也就成為一出關于“人”的悲劇:“《憩園》真正要哀悼的主要是作為‘人’的楊夢癡、萬昭華、姚國棟等因自身存在的人性弱點而導致或將要導致的‘非人’待遇。這是難以避免卻又不能不正視的人間悲劇。”③
對于“人”的悲劇的揭示及正視,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同于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人”的意識的覺醒,使現代中國人不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外來的拯救上,而必須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必須獨自面對“人”的生存困境并做出自己的選擇。在這一選擇過程中,由于發現社會的黑暗與不公、人性的丑陋與卑劣以及“人”的脆弱和無奈并產生悲劇精神也是在所難免的。在此意義上,“在文學經典的價值維度中,文學精神始終是最重要的一維,而對于‘五四’后的中國文學而言,悲劇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構成了其文學精神的某種核心。”④這種現代文學精神使中國現當代作家不能僅僅滿足于為讀者營造一個遠離塵囂的美麗夢境,而是借助自己的作品書寫普通人柴米油鹽的瑣碎生活和備受煎熬的內心世界,再現他們掙扎求生過程中感受到的希望與幻滅、幸福與失落,現當代文學作品由此也很難擁有簡單明晰的價值判定和包治百病的萬用良方,而充滿了種種必須承受的人生苦痛,表現出一種濃重的悲憫意識。
二
那么,面對“人”存在的苦痛與人生的荒寒,必須自我負責的現代中國人該如何應對?以暴易暴,用自己和他人的犧牲換取未來美好生活的選擇是否值得踐行,就像巴金早期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
《憩園》中對于楊家長子楊和形象的處理因此變得極富暗示性。與巴金筆下的其他“長子性格”不同,楊和不僅意識到自己身上肩負的家庭責任,更有決心和能力履行這一責任;他不會停在原處、自怨自艾,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親人走向末路,而是一個有著鐵一般手腕的堅決地行動派;他敢于挑戰父親的權威,動用自己的關系逼父親出去工作,甚至不顧社會輿論將不成器的父親趕出家門;在家產被父親全部敗光的情況下,他用自己的雙手養活了家人,收獲了屬于自己的愛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巴金小說中少有的成功者,一個充滿希望的新人。然而,與楊夢癡和寒兒對于憩園的深情依戀不同,他對這個生長于斯、充滿祖輩溫馨記憶的園子沒有絲毫的溫情,而以強硬的態度代父親簽字將憩園賣給別人;在楊夢癡已經表示了對于家人的真誠懺悔,也了解到他食不果腹的生活處境之后,楊和依然對父親拒不接納,這也是導致楊夢癡最終悲慘死去的一個主要原因,小說對于他心理活動的刻意回避,正反映了巴金對這一人物的復雜態度。“如果說在他身上體現了巴金的毀滅沖動的話,那么這可能不是本我的弒父沖動,而是作者內心的通過毀滅來謀求新生的欲望。這個欲望在巴金40年代之前的作品中有著大量的表現,但卻是第一次被作者與無情二字如此徹底地嫁接在了—起。”⑤下意識中,巴金希望塑造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強有力的人物,以滿足他改變現狀的強烈內在需求,卻又無法接受與這種性格伴生的楊和的冷酷無情,在他身上,反映了巴金對于暴力與正義問題的深入反思,體現了巴金對于知識分子或者說文學價值的重新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這絕不意味著巴金對于自己前期觀念的徹底拋棄。終其一生,巴金的創作中都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那就是對于人類和自己民族永難磨滅的“愛”。因為這顆愛人的心,正如巴金的早期散文《我的心》所說的,“這幾年來我懷著這顆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創痕。”⑥巴金深深地為這無愛的黑暗世界而苦痛,并因此把尋找破除這一黑暗世界的路徑作為他人生與創作最重要的目標。只不過在他早期的小說里,巴金寄希望于通過暴力來實現“愛”的目的,到了40年代則“愛”既是巴金追求的目標同時又成為祛除黑暗的手段,從而顯示了他文學觀念的內在調整。
某種意義上,抗戰后期顛沛流離的惡劣環境使人到中年的巴金深刻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與人生的無奈,他也因此認識到知識分子的價值主要不在于對于暴力革命的直接參與或傾力謳歌——事實證明這既不是知識分子所擅長的也不是可以毫無疑義地加以履行的——而在于“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干每只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⑦,通過文學創作給讀者美的享受、愛的熏陶,讓他們看到人間的希望、獲得前行的力量。
可是必須加以認真考慮的是:巴金對于這種“愛”的解決方式真的是絕對信賴而沒有絲毫疑慮嗎?相對于小虎之死這一悲劇性結局所顯示的某種生活的現實性與必然性,可以在別人的影響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瞎眼女人和老車夫故事結尾的虛幻性與偶然性也就顯而易見了。極具意味的是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文學作為一種虛構藝術的價值才真正得到凸顯:“這個虛構的幾經變更的故事展示了如下兩個維度的意義:一是在現實中無能為力的“我”用白日夢的方式給虛構世界的痛苦人生一種想像的慰籍與幫助;二是對在懷疑中漸顯虛妄的寫作價值的重新確認,既然‘我’的寫作無法成為療救病態人生的一劑良藥,那么就讓它發揮一點減輕病痛的作用,以悲天憫人的態度給無望無助的人們些許心靈的安慰。”⑧文學的作用主要不是立即改變現已存在或即將到來的現實,而是由于寄托了人類對于愛與美的永恒理想,成為感受到存在的荒誕性的現代人的一條精神自救之路,其是否能夠產生實際的效果是不必加以過多考慮的。
三
正是從這個角度,如果說所謂“典律”只是一種編選的角度,一種內在的價值選擇,當代人不斷命名“經典”、由自己選擇哪些作品屬于“經典”的行為本身,就是對于自我藝術鑒別能力的一種肯定,顯示了當代人樹立屬于自己的文學價值尺度的努力,反映出一種與現代線性思維方式相一致的強烈的自我認同沖動。那么,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典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應該是與現實生活的密切相關性。換句話說,“古人把‘經’理解為一成不變的思想權威,或超乎凡庸的圣人之所造作,其實經典所以為經典,并不在其玄學的先驗權威,而只因為它全面深刻地總結了民族生活的歷史經驗,反映了民族命運的本質。經典也是發展的、凡俗的,和每一顆關懷民族命運的普通的心靈息息相通。”⑨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與其說是和古典文學經典一樣提供某種關于生活問題的權威解釋或者答案,不如說是提供一種關于生活可能性的思考,一種現代中國人對于人生價值和道路選擇痛苦思考的形象,所謂“文學經典”必須有一種現代精神的融入,與其是“僵尸的樂觀”,不如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如布魯姆指出的,“……對千百萬非白種歐洲人來說,莎士比亞代表了他們的傷悲,他們與莎氏用語言所塑造的人物認同。對他們來說,莎氏的普遍性不是歷史的而是最基本的,因為他們的生活被他搬上了舞臺。在他的人物之中,他們看到和遇到了自身的苦惱和幻想,而不是早期商業化倫敦城所顯示出的社會能量。”⑩展現當代中國人的“苦惱和幻想”,批判他們精神上的種種缺陷,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通過對他們生存際遇與艱難選擇的再現,促使人們真正思考有關“人”的存在的本真問題,呼喚一種更美好生活的到來,理應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必須具備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如同一些審慎的學者所擔憂的那樣,過于輕易地將那些沒有經過時間沉淀的作品目之為“經典”的舉動,正從側面顯示出人們心態的浮躁和內心的極度不自信,長期以來對于他者眼光的過度重視也使我們的文學成為外來理論的演練場,使我們的一些作家和評論家成為西方觀念的模仿者與操演者,而失去了屬于自己的最根本的東西。其實,民族經典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可能正在于“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誰和我們所到達的位置”?保持與中國特有文化傳統和獨特審美心理的緊密關聯性,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成為真正屬于現代“中國”人的文學,這或許也是我們在構筑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典律時不得不注意的一個問題。
注釋:
①②譚杰:《〈憩園〉:啟示意圖與情感真實的沖突》,《南昌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6期。
③聶國心:《〈憩園〉〈寒夜〉:巴金走向絕望的文學巔峰》,《齊魯學刊》2009年第2期。
④黃萬華:《文學精神與文學經典》,《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1期。
⑤姚新勇:《〈憩園〉:五四啟蒙文學的一個轉折性象征》,《文學評論》2002年第4期。
⑥⑦孔惠惠等選編:《巴金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365頁。
⑧劉世楚:《〈憩園〉人物談》,《湖北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1期。
⑨郜元寶:《魯迅六講》(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
⑩[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