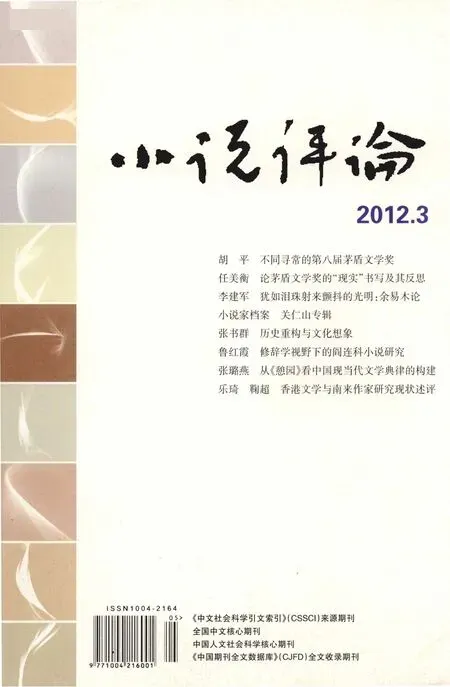現實精神與理想情懷:關仁山訪談錄
孟繁華,關仁山
孟繁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你與河北作家何申、談歌并稱為河北“三駕馬車”,成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代表性作家。你的創作受到了廣泛關注,之后,你接連創作出《天高地厚》等多部長篇小說,可以說,你的創作是與當下中國鄉村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和切近的創作,同時也是一位堅持現實主義方法的作家,你如何理解現實主義?
關仁山:我是被列為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作家行列。感覺很復雜,在創新的年代,許多人眼睛里,現實主義即使不是死亡了,至少認為陳舊了,過時了。還有人認為,我們的創作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原因是缺乏獨立個性和批判精神。我理解的現實主義是一種現實精神,一種價值立場和一種表達生活的方式。我記得,1996年,當時“三駕馬車”集中發表了一些作品,還有外省一些作家的作品,續接上了八十年代前半期轟轟烈烈的“改革文學”的大潮,將中斷了十年的現實主義重新拾起,吸收了探索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許多優點,顯示了中國作家社會責任感的回歸和高揚。這一潮流中的眾多作家目光的焦點各不相同,作品對現實生活的關注熱情是一致的。我跟何申、談歌兩位老兄聚集在這一稱號下,既有友誼,也向他們學到很多東西。我們也常常討論,現實主義的傳統是什么樣子的?字典里這樣說:現實主義是文學藝術上的一種創作方法。通過典型人物、典型環境的描寫,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舊稱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要反映現實生活本質。究竟什么是生活本質?恐怕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進行真實而有勇氣的寫作,看來要踏過“生活流”尋找生命的文本,實際上還是要確立“人學”的本質。如果小說停留在“問題”的展示上,是膚淺的。中國這個大家庭,問題實在很多,現實主義創作貼近時代、觸及問題,是我們作家歷來介入社會干預生活的一個傳統方式。社會轉型期,必然給社會帶來各種艱難和問題,過去在“左”的路線下,現實主義走偏了,往往給文學賦予的東西太多,文學承擔的也過多,有失文學自身的規律。可是文學遠離現實社會,也是有局限的。我認為好的小說,既是社會的,也是走進心靈的。90年代中期的文學,還有還原民間的傾向。追尋生活本質,但是,通過對現實主義深入理解,我們的創作還需要調整,作家應該將現實問題轉化為藝術的靈魂。我對自己創作進行反思,已經逐步退正,但是,批判鋒芒還不夠,銳氣還不足。在下一部長篇中,要對現實世界進行深入理解,反映到作品中,就要充溢著人生苦難和人性光芒。我很欣賞邵燕君博士在《與大地上的苦難擦肩而過》文章中的一段話:“相信當作家把自己的根扎回這片依然苦難沉重的大地后,對于作家的使命,文學的責任,‘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會做出新的思考。但愿,勞苦人真實的血淚會重新灌滿他們已逐漸干枯、輕飄的筆,寫出‘莊嚴、嚴肅、深刻的作品,重續起現實主義令人尊敬的傳統,不再與大地上的苦難擦肩而過。”這番話情真意切,這是批評家對作家的期待。按我的理解,小說變得很迷茫,很功利,很輕佻,很圓滑,離真正現實主義越來越遠。作家重新思考的時候,作家就應該覺醒,真正的現實主義方法就蘇醒了。蘇醒后的作家會獨立思考,會理性判斷,會變成勇士的,勇士總比懦夫好,思考總比麻木好。所以,必須在現實寫作中注入更多的想象力和原創精神。現實主義不會消亡,現實主義應該不斷發展、豐富和深化。
孟繁華:你是一位對現實生活比較敏感的作家,總是快捷地用小說反映正在發生的現實生活,比如《麥河》比較快地涉及到“土地流轉”問題,《信任》寫到現在進行中的經濟轉型,《白紙門》寫了渤海灣一個漁村的時代變革,等等。你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非常難能可貴,我又感覺這對作家是一種挑戰,你在創作上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能否結合你寫過的鄉土、官場和城市談一談解決辦法。
關仁山:提倡作家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所以,“貼近”是我的必然選擇。我這人喜歡表現當代現實生活的小說,這是內心的熱情。我感覺,小說絕非命定地與現實保持遙遠的距離,長篇完全能夠對當代社會問題和時代風貌作出及時而出色的描繪,引起讀者的共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說:“我更關心的是現在這個時代,因為時代在急速地變化,一個作家不應該回避他每天生存的這個變化的空間。”但是,貼近是有難度的,現實生活不好表現,在當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難,首先是認知的困難。為什么?因為沒有拉開距離,這不僅是現實距離,同時也是審美距離。都說距離產生美嘛!當代性最難把握,現實生活是多變的,龐雜的,復雜性有目共睹。要把當今社會生活寫得真切,具有強烈感染力,非常困難,因為讀者都在親歷,缺少陌生感和神秘感。我覺得,作家面對現實要迎難而上,硬拼。我把這種硬拼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有距離的認知,損傷的審美,要用別處做藝術找補。比如創作《麥河》,對土地流轉是肯定還是否定?走哪一條道路都不通,因為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階段。那么,就把這些大事件往背景上推,將“土地流轉”的復雜性與農民的人性相連接,來表達農民對土地的情感,并讓這種理想情懷飛騰起來,從而抵達生命本質。前幾年,中央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繼包產到戶以來農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我國第三次地權改革。如今全國好多農村都進行了土地流轉。“流轉”中的農民更加自由,也不斷增加著收入,但是,也是問題重重。過去對鄉村約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經失效。不尊重生活這種復雜性。,就會犯一些幼稚錯誤,甚至會幫倒忙。其實,今天的復雜局面,就有過去行政命令,長期照搬照套有關。比如,有人說要搞市場化,我們一試就十幾年,還是有問題,有人又說,市場無效論。有人說,要想社會穩定,最好辦法就是把農民繼續束縛在土地上,這一小塊土地可以維持他們的基本生存,土地基本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可是,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推給個人的?讓土地成為防止農民流動的穩定劑,可是,這個國家發展到今天,誰有資格讓一個群體為另一個群體必須作出犧牲?我們覺得,今天不存在一個整體的農民,農民個體身份在分化,每個農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選擇的自由,他有權力遷徙到大城市,當然他也可以選擇留在鄉村。農民只想通過自己卑微的勞動改變自己和子女的命運,任何人都不能扼殺他們的選擇,凡是剝奪和扼殺,都是不義的。我們現在的農民不需要啟蒙,也不需要同情,他們不再安貧樂道,更不愿意做犧牲品,他們也開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們需要城市,喜歡現代化,也喜歡美麗家園,更喜歡在藍天下自由的享受生活。農村問題急迫而嚴峻。鄉土敘事還處在模式階段,怎樣才能找到適應新情況的新的寫作手法,讓我們困惑,我無法面對這樣巨大的農村變化。一個小村莊,有幾十億富翁,有中產,有一般貧困戶,還有很窮的農民。怎樣概括它?這是一個嚴峻而復雜的問題。仇視城市嗎?廉價謳歌鄉土嗎?展示貧苦困境嗎?整合破碎的記憶嗎?每一個單項都是片面的,應該理性看待今天鄉土的復雜性。另外,我把今天“土地流轉”放在一百年土地變遷中審視,看得就清楚多了,這只是大河中的一朵浪花,無法徹底解決農民與土地問題。農民在土地上要走的路還很漫長。
在當下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里,文化精神多么重要。可是,不少人把尊嚴走丟了,失去了文化精神。描寫現實,不能放棄追問。比如我創作長篇小說《白紙門》時,小說主人公疙瘩爺心靈曾經是多么高貴,但隨著物欲在他的生活中占有越來越多的位置,他一點點地變了,尊嚴也走丟了,變成了一個低俗而沒有靈魂的人。老人的悲劇令人痛心。而在大雄、麥蘭子這些后代人身上,也經歷了尊嚴的拷問。他們在經濟大潮拼搏中尋找到了丟失的尊嚴。所以說,我找到了一個認知的切入口,想通過對渤海灣漁家日常生活的描述,對四季變化的描寫,希望向讀者展示一幅波瀾壯闊的雪蓮灣漁村人物畫、風俗畫和風景畫。在這樣的氛圍里尋找一個思想支點:尊嚴!對于轉型期急劇變化的生活,作家應該有一個立場和價值判斷標準。一般讀者都愿意從樸素的生活中去感悟深刻的道理,從而審視現實、審視人的自身。甚至是在思考中追問。文學應該對世界的本質、人的核心問題進行追問。追問的前提,必須樹立起明確的判斷生活的尺度,樹立起自己的價值觀念。因而現實主義寫作立場、看取生活的角度以及選擇運用的形式技巧等,就應該是獨特的。過去對生活中的丑惡有無奈的認同,缺少明確的善惡判斷。所以,我在《白紙門》中力圖通過對現實的再現,把自己的價值判斷、精神姿態體現的明確一些,增加作品的批判性。批判、譴責丑惡,也是為了找回作為人的高貴和尊嚴。
描寫城市生活也是一樣。最近我創作了一些都市生活的小說《飄雪》、《根》、《馬座陶燈》等等,我想,作家要努力把我們的觸角伸到時代深處,尋找,觸摸,探究。我們這個時代,資本對倫理、靈魂形成了劇烈的沖擊。每一個事件,都像一個石子,投入湖面,激蕩起波浪。我們每個人的靈魂都有震蕩。我感覺,這種震蕩就是小說的觸發點,震蕩的結果是命運的轉身和人性的變異。他們活脫脫、興奮于、煎熬于這個時代,與這個時代同呼吸,與這個時代喜怒哀樂,他們追求,他們撞擊,他們轉身,他們變異。小說可能解決不了問題,但是能夠記錄這心靈的變異的過程。物質的負累,讓底層百姓四面楚歌的時候,內心所涌現的陌生和絕望,那是樣的鮮活和復雜。拿什么來拯救迷途已久的心?文學,小說。讓小說來溫暖我們的物質世界。找到了這樣轉身的觸發點,就會寫出時代的荒謬與蕪雜,寫出人的掙扎中的繁復與卑微,還能寫出屬于這個時代的大悲哀和大歡喜。
孟繁華:我在不同的場合說過,雖然“先鋒文學”已經落潮,但是,是否受過先鋒文學的洗禮,對一個作家的創作大不一樣。你同意我的這個說法嗎?對你影響較大的西方作家有哪些?
關仁山:您的這個提法我非常贊同。我雖然沒寫過先鋒小說,但我愛讀先鋒小說。我們在寫作的時候,為思想、語言、結構焦慮,絞盡腦汁的時候,還會想到帕慕克的一句話:文學是什么?文學是用一根針挖一口井。當然,先鋒小說給我們最大貢獻是敘述的創新和文體的探索。這對現實主義手法創新,有很大幫助的。當時,我讀過蘇童、余華、馬原的很多先鋒小說。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百年孤獨》、《鐵皮鼓》中受到啟發。文體的演變,還由重視外部世界描寫向內部世界轉變,即由情節小說向精神小說轉變了。這樣更加注重寫人,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法國作家喬治杜亞美說:現代長篇小說就本質而言,是精神長篇小說,長篇小說要想尋求突破,必須從生活故事化模式中脫出來,向心靈化層次躍進,因為人的內心世界是豐富的。經過先鋒文學的摸索,實踐,我感覺到,決定一部小說的藝術質地,就是小說空間不能全被物象占據,應該更多地重視精神、靈魂、詩意和情感。這是感染人的地方,這樣才能讓文本飛揚。那些敘述是神性的,詩意的東西,非常珍貴。比如《百年孤獨》,中國作家都很喜愛這部名著。看過,我們就想,這種魔幻現實主義在中國該怎樣表現呢?
記得,巴爾加斯·略薩,在他著名的《謊言中的真實》一文中談到,小說的真實并不取決于它寫下的是“真實事件”,而取決于小說的說服力,取決于小說想象力的感染力,取決于小說的魔術能力。我覺得真實而可靠的敘述,才能讓小說具有說服力。小說中的真實可靠,說服力有多大,取決于作家的敘述的控制力。小說只有具備很強的說服力,最后才能贏得讀者。他還講到風格和秩序,風格是敘述故事的話語和文字,秩序是對小說素材的組織安排。他對結構的重視,給我們以啟迪。這方面,我還不足,要繼續磨煉的。
藝術方面的問題。各種手段我們都用過了,還能怎樣突破?我讀謝有順的批評文章,給我很大的啟發。他講到小說有自己獨特的文體邊界,其實,這也是先鋒小說的貢獻。小說確實跟詩歌不同,它必須能真實地描寫和還原一個生活世界和物質世界,如果小說光具備這個方面,絕對稱不上是好的小說。除了物質的還原,小說還必須是精神的。說到底,小說還要解釋世道人心、探索人性、為人類的精神作證,這是小說深度方面的區別。好的小說,里面看起來是物質的東西,也可能藏著作者很深的思想。譬如說,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和地洞,魯迅筆下的村莊,你說這些是物質世界還是精神世界?這可能是一個物質世界,但同時也是一個精神世界。物質發達的社會,小說是不是更重視文學的精神功能?所以說,小說中精神不能缺席。
孟繁華:有批評家說你把自己放在“政治保險箱”中,你同意這個說法嗎?你怎樣理解文學的“主旋律”?
關仁山:有人說我是農村題材小說家,還有人說是“主旋律”作家。怎么稱呼,我都不介意的。作家是要靠作品說話的,看“主旋律”作家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在我小說《信任》研討會上,有專家善意提出我把自己放在“政治保險箱”中。我對這樣的提法歡迎,這會讓我警惕。《信任》這部作品是在創作前出版社就限定了方向和邊界的。寫作時心靈是自由的,但是,政治話題沒有完全轉換成文學話題。所以,我覺得人家提法沒錯。對我今后創作敲響了警鐘,警鐘響了,我能感受到是警鐘,這是好事情。如果轉換一個角度開掘,就可能有意外收獲。人們有這樣的普遍認識,政治上保險的作品,自然就淡化藝術特征。人們普遍覺得“主旋律”作品,不缺少關注現實生活的熱情,但是,往往缺乏現實感和批判精神,沒有為讀者提供認知生活真相的平臺,缺少文學感染力,等等。我們有個通常提法:“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其實,我覺得“主旋律”創作是寬泛的,能夠在藝術上有所作為的。因為,這樣巨變時代,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創作源泉,這里有我們需要的精神資源。“生活趨同”化了,如果承認生活趨同的話,恰恰這個時候是在考驗一個作家發現角度的能力,還有一個文學的價值,這時候才最能體現作家的功力。所以,我感覺這類作品,亟需加強思想深度和思想力度,寫出個體靈魂煎熬、躍動,寫出時代變革對人性的真正拷問。我們要在精神氣度上下功夫。
孟繁華:在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文學處理的是什么問題?現實精神和理想情懷的關系怎樣處理?
關仁山:我們這個時代,文學已經邊緣化了。我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考驗,就是市場化。市場和資本要求速度,資本是貪婪的,它要求利益最大化,而作家要創作出不平凡的大作品,需要耐心、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韌力,需要平常心。既要有速度,還要高質量,這種矛盾怎樣解決?這樣的文學問題怎么處理?需要才氣和智慧,需要我們共同來探索。我感覺,對于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自己的思考,自己藝術表達還遠遠不夠——我覺得作家創作一個作品,要真正從自己的內心出發,出于自己內部的真實表達,這樣會更真實一些,它的文學生命力可能會更久遠一些。
物質世界,現實盡管很殘酷,但是,我們還想保存一種理想境界。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彼岸的。生活中美好的東西怎樣保全?處于時代漩渦中的人將如何把握自己的命運?我們企盼一個讓美好盡情綻放的環境,即便這是一種理想,也是好的。如果我們連理想都沒有了,生活還有什么希望?時代還能進步嗎?我想,文學還是向善的,是來溫暖我們這個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