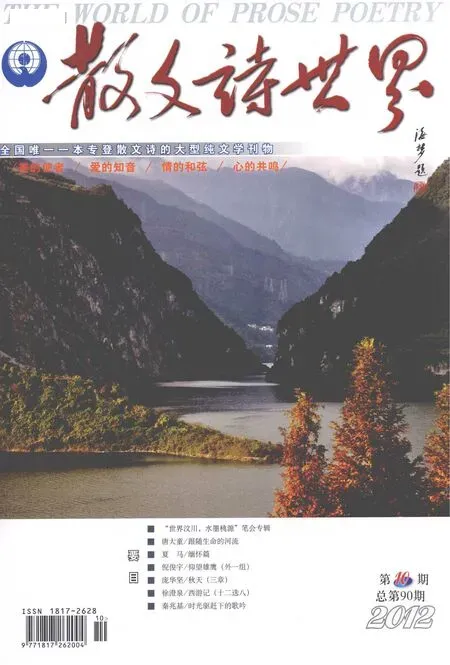西游記(十二選八)
四川 徐澄泉
在蘭州喝三炮臺
西北名飲三炮臺,過去聽說過,現在正喝著。
我在蘭州黃河一條茶船上,品著祁連山雪水沏的三香茶,為炎炎夏日清熱瀉火。
心靜了。心空了。心明了。想到發明三炮臺的蜀人正是我的好親戚,我就明白了他們樸素的思想——
“天蓋之,茶蓋也”;“地載之,茶托也”;“人育之,茶碗也”。
我在蘭州黃河這條茶船上,想到黃河之水天上來,想到黃河是我母親河,想到女媧摶黃土造人,人捏泥土鑄瓷。
一沖。二泡。三飲。茶過三巡,我喝出滿腹疑問——
黃河為什么是“黃河”呢?黃河水能沏三炮臺嗎?多少杯三炮臺的茶水才能匯成一條黃河?
我將碗中殘汁傾盡黃河,順手舀起一碗黃河之水,從中尋找問題的答案。
祁連山雪光
從蘭州前往敦煌,一路戈壁荒漠,像我乘坐的這列慢車,一路漫長。
我向往了幾十年的河西走廊啊,祁連山的雪光,從南向北灑下來,把你,把我,把廣袤的夜晚,徹底照亮!
我在慢車上睡得太死。
瘋狂的風沙,漫長的荒涼,涼州、甘州、酒泉、嘉峪關、玉門、瓜州,偶爾的綠洲,頑強的草木,沒有誰能叫醒我的美夢。我在夢中奔跑,一路向西。速度,比慢車更慢。
我享受我的慢生活。
早晨五點,一輪新日從北山的肩膀滾下來,從黃河之東追過來,血球似的,滾到這列慢車的窗口。我用尼康相機的鏡頭擋了一下,血紅的光芒,雪白的光芒,就斜刺在祁連山的臉上,把祁連山龐大的身軀燒得透亮。
游嘉峪關,叩問歷史
從山海關蜿蜒而來,從明朝逶迤而來。
導游說:嘉峪關來歷不凡!
時間和風沙合作,嘉峪關六百多年的歷史越寫越厚。歷史和現實共鳴,嘉峪關遠播的名聲越叫越響。“中外鉅防”,“河西第一隘口”,“天下第一雄關”。
我不禁感嘆:嘉峪關,固若金湯!
游遍嘉峪關,我要發問了——
既然叫做關,就該擋住一些什么吧。嘉峪關的關,擋住了吐魯番的引兵南犯么?擋住了絲路商賈的往來穿梭么?擋住了禁煙英雄林則徐西去放逐的命運么?擋住了沙漠戈壁的東襲么?
即使駐守在此的游擊將軍們奮力抵擋了一陣子,風沙還是入關了。(奉勸諸君:千萬不能與山海關清軍入關相提并論!)嘉峪關抵擋了一輩子,卻把自己越擋越瘦了。
那么,對于時間的進攻,歷史的叛變,是抵擋,還是不抵擋呢?
導游無言以對!
在玉門,尋找一根硬骨頭
我到玉門,不是過問春風的事。
我在尋找一根硬如鋼鐵的骨頭。
忽然想起一個叫做“鐵人”的人,他是否就是那根堅硬的骨頭?
那時候,整個中國都缺鐵,更缺少煉鐵的油。
就是不缺鐵鑄的人!
玉門鉆井工人王進喜,拉起他的鐵哥們,去大慶,把鋼鐵的身軀再煉一把火候。
人拉肩扛運機器。破冰取水,盆端桶提保開鉆。縱身跳進泥漿池,把肉身當做鋼鐵使,攪拌水泥壓井噴。
這一攪,就把大慶油田乃至中國的油海,攪得風生水起。
“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把中國貧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
我在玉門“鐵人”故居紀念館,又聽到我讀小學就已熟悉的聲音。循聲走過去,我就找到了那根硬如鋼鐵的骨頭——
紀念館內,矗立一座高大的銅像。他是“鐵人”王進喜!
玉門關的關
風沙步步逼進,城垛節節敗退。
我以為:玉門關,再也沒有退路了。
長城烽燧,蜿蜒兀立;鹽堿沼澤,沙漠戈壁;商賈駝鈴,絲路迢遙;哈拉湖淺,疏勒河干。玉門關,突破東南西北的重圍,仰仗芨芨草和駱駝刺的喂養,承受歷史和陽光的撫慰,
勉強茍活到如今。
“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白草枯。”千年前的詩句,千年后的讖語。玉門早已非咽喉,關城早已無兵丁。張騫、班超,王之渙、岑參,古人早已作古人。玉門關,只剩兩口空門洞:一口吸進風,一口吐出沙。不向東輸西域的玉石,不往西送中原的絲綢,兩只空洞的大眼睛,與我對視,靜觀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溫柔的春風,酷烈的朔風,膠著在漠野,大戰三百回合,給那個胡說“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古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瓜之州
“京口瓜洲一水間。”王安石所說的瓜洲,不是我要說的瓜州。
大漠駝鈴,古道石窟,絲路藝術,瀚海蜃景,胡楊秋色,清泉綠洲。西域這個瓜州,賽過江南那個瓜洲。
薛仁貴擁兵鎖陽城,大破突厥兵;萬佛峽,榆林窟,敦煌莫高姊妹窟;唐玄奘東千佛洞留下取經圖,啟迪后學吳承恩;康熙夜夢橋灣城,怒斬貪官程金山。
祁連山下,疏勒河畔,春風又綠,西域江南岸。
我在瓜州,停車坐愛蜜瓜甜,抱走一顆大蜜瓜。(豬八戒,西行路上吃西瓜,是否吃的瓜州瓜?我在瓜州啃蜜瓜,絕對比他更奢華!)
買兩袋羅布麻,活血養顏降“三高”。
買三斤“不老藥”,鎖陽加上肉蓯蓉,可以補腎陽,益精血,養好精,蓄好銳,擇吉日,還來瓜州游。
尋找敦煌美女
敦煌街頭。我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四處尋找養眼的美女。
敦煌沒有美女!不堪風沙和烈日的騷擾,敦煌的美女,躲進男友和丈夫的懷抱去了,躲進藝術的宮殿去了,躲進神話的界面去了。
敦煌美女啊,你在哪里?
走進莫高石窟,一縷香氣向我襲來,一個裙裾飄逸彩帶飛舞的仙女乘著彩云,從西天那邊飛過來。我在一幅壁畫上凝神定氣,與她幸福地遭遇片刻。這個用千年歷史煉成的美女,也在千年之后,遭遇我的愛慕。她羞羞答答地躲在幽暗的石壁之上,作窈窕淑女之狀。
我消受不起這樣的美女,就把一幅飛天石版畫請回家:讓飛天,且歌且舞,反彈琵琶;任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似私語。
回到敦煌街頭。在輝煌的夜色中徘徊,經不起《敦煌神女》劇照的引誘,我闖入九色鹿的王國,結識了鹿王美麗的女兒,被她英勇救國的事跡感動一夜。
劇終了。人散了。
我在劇院門口發現劇中的美女,沖我微笑。我的心,咔嚓一聲。朋友的相機,咔嚓一聲。
就這樣,敦煌的美女,陪我回家,她劇中的美德,劇外的微笑,一直照耀我發霉的愛情。
詩意青海湖
青海湖,是青色的海。
青海湖,是詩歌的海。
王昌齡、高適、李商隱,李白、杜甫、李賀,唐朝的大詩人,他們不懂青海湖的美,亂用戰爭、離別、殺戮、荒蕪抒寫,把青海湖的浩瀚寫成空寂,把青海湖的澄澈寫成黯淡。攪亂一池青海!
千年匆匆而過,青海湖的詩意,越釀越濃。
一個姑娘叫卓瑪。她那粉紅的笑臉,像草原。她那動人的眼睛,似湖泊。她那油亮的辮子,如牧鞭。西部歌王王洛賓,把她追到金銀灘,做了一只溫柔的小羊。
一個詩人叫海子,在德令哈的夜色籠罩之中,想念親愛的姐姐。他用溫暖的抒情,驅趕青海湖一樣遼闊的孤獨和寂寞。
來了,來了!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倉央嘉措、艾青、徐志摩,聶魯達、泰戈爾、雨果,惠特曼、紀伯倫、里爾克……古今中外的偉大詩人,都到青海湖來了,趕一場詩歌的集。來了,來了!格薩爾王傳、江格爾,荷馬史詩、羅摩衍那,吉爾伽美什、松迪亞塔……全世界的不朽史詩,都到青海湖來了,安一個詩歌的家。青海湖,是詩人心中流動的詩。詩人們,是青海湖畔凝固的歌。
在青海湖國際詩歌廣場,我沒有看到海子的身影。
我知道:這個詩人小海子,早已融入青海湖那個大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