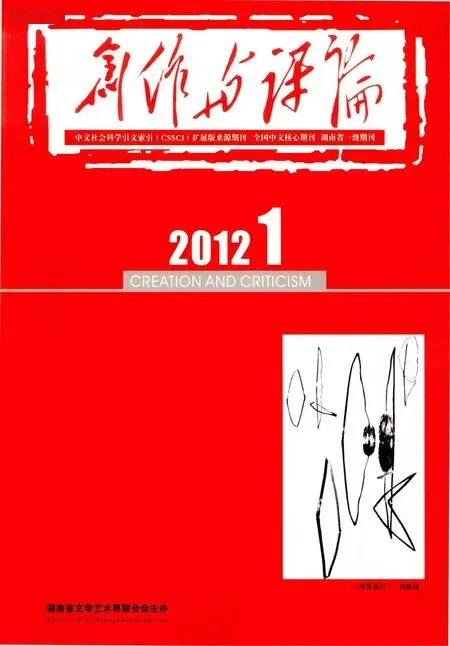再談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使命——評劉奇葉《紅豆生南國》
■ 張先軍
當人們還沉迷于“網絡文學”的玫瑰色夢幻小資情調的宣泄時,當國內一些作家還在以街頭小流氓、江湖黑社會的代言人自居而對社會表示所謂的“憤怒”時,湖南武岡籍青年作家劉奇葉卻把他的創作關懷投向了那片生養他的湘西南熱土,歷時五年創作出了一部旨在表現“當代農村社會傳統與變革、文明與愚昧的沖撞所帶來的陣痛和沉思、奮進與觀望、希望與茫然”的長篇小說《紅豆生南國》,以寄寓作者對湘西南這片熱土的人和事深深的熱愛和眷戀之情。小說始終以湘西南為地域背景,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湘西南獨有的風韻和湘西南人民的性情和性格,具有濃厚的湖湘文化特色。同時,作品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原有的鄉村風情,又涵蓋了正在向城市化發展的小城鎮及城鄉結合的趨勢和背景,具有“新”的鄉土文學特色。作品以一曲愛與恨、恩與怨、美與丑、真與假的情歌解讀改革開放這一時代背景下的鄉村男女的情色掌紋,透視人物冷酷與激情的表象,直擊現實生活背后的各色人生。故事發生在富有“神奇的土地”之稱的湘西南云山腳下,妙齡少女嫣紅長得風姿綽約,美麗迷人,性格開朗,純情可愛。出于和初戀情人龔一彬、丈夫笑云兩個男人的感情糾葛,嫣紅離家出走打工,后追隨龔一彬在南國都市深圳打拼創業。嫣紅盡管在事業上有所收獲,但她的愛情卻在滾滾紅塵中被無情地剝落得支離破碎,尤其當她看到自己無暇顧及的女兒茵茵漸漸墮落時,更是悲痛和憂郁不堪,方才猛然覺醒,反省自我,重梳思緒,回歸理性。無疑嫣紅這一形象是中國當代文學表現改革開放農民形象這一題材中一個嶄新的形象。因為無論是在表現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形象的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還是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這一形象都是以男性為主人公,而在劉奇葉這里卻出現了可喜的變化,是首次以女性為主人公形象。
嫣紅這一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不僅體現在她渴望擺脫貧困落后、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足這一時代主題上,同時也表現在她對原始情欲的合理欲求上和對自我價值的苦苦追尋與確證上。
貧困的農村姑娘嫣紅,十七八歲年齡,出于一種原始情欲的沖動,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于湘西南云山腳下那片原始、古樸、封閉的山野里與有婦之夫身為民辦教師的龔一彬相遇,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并進而產生錯覺把這種關系看作是愛情了。他們一次次地在原始山野里偷情,構成了一幅幅生動的原始風情畫。終于這種關系被龔一彬的老婆發覺,嫣紅在鄉里人們守舊的輿論中成了“不要臉的婊子”,不得不被迫離家出走,走上了南下打工之路。可以說嫣紅的出走并非出于一種自覺的行為,在她身上殘留的小農經濟意識也還很濃重,在她的意識里,用賣掉自己頭發換來的錢美餐一頓就很滿足,她并不幻想大富大貴,對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商品意識不斷向社會各個層面縱深滲透的外部世界也毫無覺察。如果不是偷情事件,她的思想觀念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侍奉男人為男人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生命軌跡是天經地義的,她并不是要有意識地去改變這些,也就是說,作為傳統女性的因襲,她的自我意識并沒有覺醒。她只是追求一些生命的本能欲求的滿足。很顯然,在這里嫣紅與以前文學作品中塑造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農民形象比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她并不是一個自覺的形象,只是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被動地卷入到這一時代的洪流中的,是她在深圳龍崗打工過程中目睹各種社會丑惡現象,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經受各種被利用和被背叛,出于生存的需要,才不自覺地從一個農村姑娘而變成了一個“漂亮,會說話的嫣紅小姐”,學會了推銷自己,利用自己的姿色籠絡客戶,把她的“紅豆房地產公司”一步步壯大起來的。
這一形象的塑造寄寓了劉奇葉對改革開放這一時代主題的新的理解。從嫣紅這一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到,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建設新農村是時代的要求,但是發家致富追求物質上的富足并不是這一主題的全部,也并不是所有農村人的自覺追求。劉奇葉提出的是一個更高更深刻的命題:農村人如何才能獲得自我的解放,那些生命的合理欲求如何才能得到實現,在生命的欲求實現上有否層次的高低。正如嫣紅在商業上的成功,卻換來了個人情感的失落,對女兒茵茵教育的失敗,以及衣錦還鄉卻遭到鄉親們的排斥所帶來的個人身份的無法確證,個人靈魂的無所歸依等等。
劉奇葉通過《紅豆生南國》這部小說試圖把握時代命脈、對時代主題作出縱深的理解詮釋,卻選擇了一個女性主人公的形象來承載,是有深刻用意的。我們知道,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封建男權傳統的國度,女性的命運總是令人深深嘆惋,因為女性在現實的泥淖中背負著過多的因襲的重擔,難有自我解放的可能,尤其是普通的勞動婦女,她們在生理上心理上不自覺地充當了男性的附庸。因此,任何一次時代的洪流都是首先把男性推向前臺,在男性的巨大陰影下她們難以有突破自身局限的可能。這就不難理解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那種種的封建落后現象沉渣泛起,諸如“包二奶”、賣淫等等。
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建設新農村,實現人的價值和解放,這正是時代的使命所在。正如嫣紅最終還是回到了故鄉,決心以自己的資產為故鄉修“一座紅豆新公寓城,讓廣大貧困居民住上廉價的公寓”并投資成立“紅豆教育救助基金會,幫助那些貧困線上掙扎的學子們”。從這樣的結局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嫣紅經過“傳統與變革、文明與愚昧的沖撞所帶來的陣痛和沉思、奮進與觀望、希望與茫然”而終于確證了自己的價值。顯然這是一個內涵豐富而又富有時代意義的形象。
無疑地,劉奇葉的小說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使命是什么”這一問題上是給我們交了一個很好的答卷的。他的小說不僅深深地植根于生養他的這片湘西南熱土,對這片熱土上的勞動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以博大的人文關懷關注著他們的生存命運并滿腔熱情地充當他們的代言人,傳布他們的憂喜悲歡,為他們指出出路和希望所在。“表達自己對那種浪漫和幻想的禮贊,表達那種對真愛和純美的歌頌”,“用愛與美作為理想主義的最后一道壕塹,向著日益世俗化、平庸化的社會現實做完全地抗爭”。
德國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國際社會主義婦女運動領袖之一蔡特金在分析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藝術時指出,“在這樣的時代里,由于人們只看到藝術的一個方面——明顯的頹廢沒落的特征。就忽視了它的另一方面——蓬勃向上的新生活的征兆。這種生活既可以把藝術從頹廢沒落中拯救出來,又可以給予它廣闊發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內容。”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正是“蓬勃向上的新生活”,可以給予藝術以“廣闊發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內容”。這就需要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同志“自由的寫作,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只有這樣,我們的藝術才能無愧于時代和人民,才能煥發永恒的藝術魅力。
可喜的是劉奇葉這樣做了,在創作實踐上體現了可喜的創作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