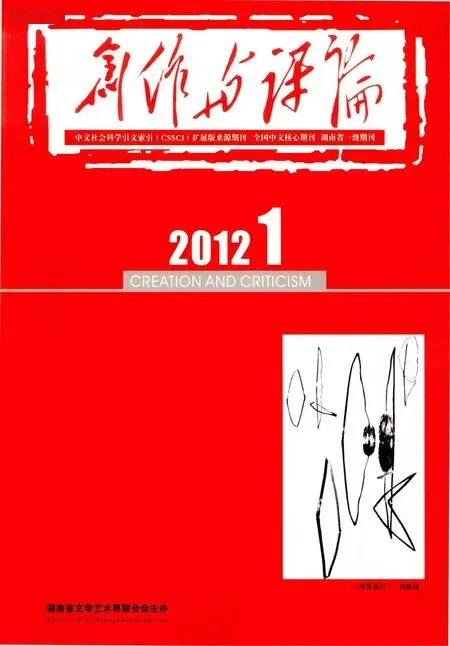紅色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轉換
■ 傅書華
近年來,從表面看,紅色革命文化再成文化大潮、主潮,紅色歌曲天天唱,紅色革命經典電視劇、紅色革命老電影頻頻出現于各地熒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這其中,除了情感的抒發,情緒的激昂,生命的懷舊,對昔日的懷念,對現實潛在的批判,是不是還有一些深層的學理需要我們認真地給以思考、梳理呢?我覺得,是需要的,并且是急需的。這其中,紅色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就是其中應該予以特別重視的問題之一。
所謂現代性,是一個內涵復雜歧義頗多的概念,學界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紅色革命文化也是一種具有中國自身特點的現代性文化。為了避免在概念上作不必要的糾纏,我在這里指的現代性轉換,是指紅色革命文化如何在當今具有現實意義。
紅色革命文化中最為直觀、醒目的也是最為公眾所歡迎的,是對底層民眾利益的代言。在這其中,在今天,最為重要的兩點是:第一,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人為代價,評價歷史進步的尺度,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程度,更重要的是人的解放程度。第二,人,生而平等,底層民眾不因其經濟的弱勢而失去人應有的尊嚴及社會對其的尊重,請注意,是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同情或憐憫。
就第一點而言,資本經濟在其自身發展中,是以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實現目標的,在這其中,是以無視底層民眾經濟利益為代價的。1930年代全球性的紅色革命運動,正是對這一無視的抵抗并迫使資本經濟在經濟發展中,增加社會公眾福利,縮小貧富差距。與之相應的,是對歷史進步的重新評價,歷史進步的尺度,絕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而是將人作為歷史的主體,將人的解放、幸福程度視為其根本性的評價標準。在當今中國的經濟騰飛的過程中,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使紅色革命文化與現代性文化在這一點上,形成了直接地對接與承繼。但對底層民眾經濟利益的維護,并不意味著回到計劃經濟,回到“大鍋飯”,并不意味著取消競爭,取消差距,更不意味著無視經濟規律、取消市場經濟,不意味著“仇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對底層民眾經濟利益的維護,二者之間不可缺一而形成的關系的“張力”“緊張”,二者之間關系“張力”“緊張”的復雜性與微妙性,或許是紅色革命文化現代性轉換中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這一問題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在山西的地方性的煤炭生產中,顯得尤為突出。
就第二點而言,資本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經濟實力的大小作為人的自身價值大小的核心價值觀,由此,形成了底層人與上層人在個人價值認可上的不平等,使底層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感不能得以體現。紅色革命文化在過去的革命歷史中,在政治文化層面,給了底層人以個體自我價值實現的滿足。馬斯洛的人的存在需求層次說認為,人的自我實現是人的最高層次的實現。在這一點上,紅色革命文化與五四“人的文化”不是如學界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斷裂”而是另一種形態的承繼,與現代性文化中人的價值本位,也是有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但在這一致之外,是否也有著諸多不一致之處呢?我想,是有許多不一致之處的。諸如,如果我們不是刻板地局囿于馬斯洛的原意的話,馬斯洛的人的存在需求層次說中的人的自我實現,是在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實現之后的更高的人的需求層次,這與馬克思在其《手稿》中所表述的,人的自我解放、實現的程度,要看其在何等程度上,不再為物質的需求而從事真正的創造性活動可謂是有著某種程度的一致之處的。要而言之,雖然我們對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之間的關系,對馬克思所說的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的關系,不能作簡單的線性對應理解,但人的真正的自我實現,是需要著一定的前提條件,包括物質的解放,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層次的滿足等等,這樣的判斷還是應該能夠成立的。如是,我們在承認底層民眾的自我實現的價值需求時,才會不因此而否認五四時代所重視的對底層民眾的啟蒙要求,才會不忽視物質貧困所帶來的精神貧困給底層民眾所帶來的在自我實現中的虛幻性、扭曲性,以及在這種虛幻性、扭曲性中所帶來的對底層民眾真正的自我實現的“遮蔽”,才不會讓底層民眾在這種“遮蔽”中“迷失”自我。如是,我們也才不會讓“文革”中所謂“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舞臺”“貧下中農領導高等院校”之類的鬧劇重演,也才不會給這些鬧劇的各種變異形式以學理性的依據。既不在資本經濟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中,失去對底層民眾自我價值的肯定,又不重復讓底層民眾在自我價值實現的虛幻性、扭曲性中迷失自我的悲劇,這也應是紅色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轉換中所需要正視與研究的問題之一。
紅色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轉換中,還有三個問題是需要給以認真研討的:個人與整體;物質與精神;過去與現在。
首先,個人與整體。紅色革命文化強調整體利益至上,為了整體利益要以犧牲個人利益為榮。但現代的經濟生產形態卻又是以個體利益為其驅動力的。常常遇到的問題是:當今社會還要不要強調對個體利益的犧牲精神?個體利益是否應該有價值形態上的合法性認可?在個人與整體的關系中,馬克思認為:以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是否認可和成全為價值標準,整體被相機判為“真實的整體”與“虛幻的整體”這兩種整體分別配稱于以之為存在對象的兩種個人,即“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我覺得,在今天,我們應該更深刻地以此為價值尺度,更加具體地明確整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在對個體利益價值形態上的合法性認可的基礎上,強調個人對同樣作為個人的“他人”及整體的責任感及負責精神。這樣的一種個人/整體關系的觀念,無論是對作為整體的代表者的權力者,還是對每一個個人來說,都還是比較陌生的。
其次,物質與精神。紅色革命文化偏重于強調在貧困的物質生活中精神的力量,現代經濟生活則刺激人的物質生活的欲望。二者之間的不平衡,常常給人以這樣的感受與判斷:今天物欲橫流,精神喪失。我覺得,在這其中,有這么兩個問題需要我們作理性的認真辨析:
第一個問題,紅色革命文化不但注重在政治文化層面給底層人以自我價值實現的自豪感并在這同時強調其中的精神的力量,究其根本,其實紅色革命文化首要注重的,倒是強調物質上的翻身與解放,是在物質上特別是在近期的可以具體實現、體現的物質生活中,給人以希望與滿足,如農村中的分田地,城市中的平物價、保供給等等。所以,當今社會對物質生活的重視與認可,與紅色革命文化的這一承傳,在深層上,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個問題,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底層民眾物質生活的長期的普遍貧困,由于紅色革命是在經濟貧困的地區與階層首先得以發動的,所以,相對說來,缺乏建立在豐裕物質生活基礎上的精神資源,而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形成的速度又是不一致的,相對說來,前者較快,后者較慢,如是,當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物質生活初步豐裕起來之后,與之相應的精神世界卻未能同步形成,由此,給人以精神喪失的感受與判斷。但也正因此,如果我們還記得馬克思的基本原理: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那么,形成建立在豐裕的物質生活基礎上的新的精神形態與精神力量,建立與豐裕的物質生活相適應的新的精神形態與精神力量,正是紅色革命文化在今天的當務之急,正是紅色革命文化的現代性轉換的當務之急。
再次,過去與現在。目下紅色革命文化的盛行形態,更多地是以一種過去形態出現的,革命歷史歌曲、紅色革命的老電影及對其的電視劇改編等等,在這其中,潛在地體現著對今天諸多社會問題的不滿、困惑及相應的情感性補償。在這樣的一種過去與現在的關系中,我想,也還是有兩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給以深思的:
第一個問題,歷史記憶、歷史認知與生命記憶、生命活力的關系。紅色革命文化在今天得以盛行,與兩部分人密切相關:中老年人、青年人。中老年人的青少年時代,是汲取著紅色文化資源長大的,當他們在今天普遍地過了“知天命”之年時,伴隨著人的生命活力的漸次衰退,對生命活力、人生往事的憶念,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生命現象、生命需求了,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以充滿生命激情作為其主要價值特征的紅色革命文化,就成為了他們實現生命記憶的最好的對象。與中老年人不同,青年一代是因為紅色革命文化中的生命激情與自己生命中的青春激情的相一致而對紅色革命文化給以認同的。但在這其中,中老年人與青年人,都面對著一個將生命記憶、生命活力與歷史記憶相混同的誤區并在這一誤區中喪失了對歷史的認知能力——既不能認知紅色歷史真正的輝煌所在也忘記了我們對紅色歷史應有的反思。
第二個問題,在對過去的情感性宣泄中,形成了理性應對現在的缺失。如前所述,紅色革命文化潛在地體現著對今天諸多社會問題的不滿與困惑,但這種不滿與困惑,卻因了在對過去的生命記憶或今天的生命活力的情感的宣泄性滿足中而得以釋放。然而,在這種釋放中,對今天諸多社會問題的困惑與不滿卻沒有得到理性的進一步的深入認識,也因此,無助于今天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我們習慣于激情的滿足,習慣于在運動性的社會活動中,獲得激情的滿足,而時時忘記,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冷靜的科學與理性。我們習慣于以現實問題刺激激情,卻對通過激情來促進理性認識還十分地陌生。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對紅色革命文化的這一現代性轉換的意義,我們對之至今也還缺乏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