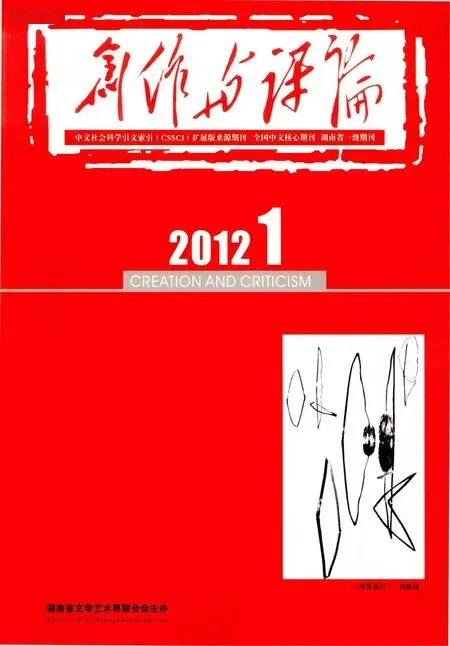看上去很美
■ 杰克船長
花了大概四個小時看了《巖石上的夢想》這本書,封上這本書之后,隨即蹦出來的是一個詞語,石頭。我記得有些人小時候也被叫做石頭,長輩們說這樣的話,好養活一些。
貝勒有一篇文章,說的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塊石頭。雖然他本人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他也沒有石頭。即便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有1000本外國小說,300張爵士樂唱片,800張DVD,但對于石頭,一塊也沒有。
雷宜鋅大師有很多的石頭,與此不同的是,他給那些石頭起了一個供人記住的名字。比如說,出自《絕望之山》的《希望之石》。他深知,人只有在最絕望的地方,才能看到最美麗的風景。
夢想記
關于馬丁·路德·金的記憶源自于《I haveadream》,那個時候練習瘋狂英語,出口的第一句話就是,I have a dream。然后身邊不知內情的人就問,你有什么夢想?我說,我在練習口語。
我記得有一次因為一時興起,就在豆瓣里發了一個帖,帖的名字叫,閑著沒事,來談談理想……里邊的內文引用了村上的一段話,生活時間一長,連趣味恐怕都將變得相似。如果有人問:幸福嗎?我只能回答:或許。因為所謂理想到頭來也就這么回事。剛一發,立馬就有人回復了,他說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不勞而獲。
緊接著又有人跟了一句,別跟我談理想,戒了。
后面的人逐漸多了起來,當然也有人回復的詳細一些,比如有一個說到,小時候想當科學家,小學了想畫漫畫,初中了想當偵探,高中了想超越希特勒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大學了想一邊畫漫畫,一邊周游世界,一邊綁架個面點師,每天都給自己做各種糕點,等到沒有雜志連載自己的漫畫了,或者沒有資金旅游了,或者面包吃膩了,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后他又加了一句,是不是很沒出息……
看后竟然不自覺的笑了,說實話,人在夢想面前總是會顯得微不足道。偶爾走在某條小巷上聽到許巍唱著,曾經夢想仗劍走天涯……你說,都好久沒唱這歌了,趕明兒,去練練嗓子。
回到1963年8月28日,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國家廣場林肯紀念堂的臺階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當時22歲的鮑勃迪倫在演講結束之后,就用口琴和木吉他唱出了這首夢想的民謠《答案在風中飄》。人們因為他而開始變得瘋狂起來,因為歌里唱到了那句“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然而,正是因為這首歌,他一路走紅。而這首最初只是為了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的歌曲,最終卻成了那個時代年輕人的圣經。
那是一個最好的年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這是狄更斯說的。年代相差一百多年,但是在那個時候卻也是一樣的適用。你難以置信,幾千年來,青年人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打贏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么?他們供你吃供你喝,又為你安排了一個妥妥貼貼的前程,你怎能不當他們的乖寶貝?但是,兒子覺得,父母的愛已經窒息了他們的每一個毛孔。他們不得不大聲自問: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真實而獨立的自我?
更讓人無法想象的是,那該是一個怎樣的年代。他們開著破車沖上美國的每一條大路,并且一上車就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他們聽鮑勃迪倫的歌,聽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的歌,他們大聲朗誦金斯堡的詩句,他們隨處野營,盡情享受最狂熱的愛情,同時他們也用空空如也的腦袋去琢磨最根本的哲學問題。當然,他們也遇到了馬丁·路德·金博士,那個時候,他正領著黑人兄弟向華盛頓進軍。他一遍又一遍地對他 們大聲說:“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讓你覺得血在燒。
至于這個夢想是什么,答案在風中飄。
遐想記
《遐想》是雷大師的一個作品名。雕像是一位優雅的東方女性,一只手托著下巴,一只手扶著腦袋。眼睛和頭發的線條類似于飄起的柳葉。關于雕像的原名曾考慮過用《沉思》,不過有人提議說,這個名字會讓人立刻就想起羅丹的名作《思考者》,而這個東方的女性就應該有一個更飄逸更富于想象力的名字,然后他問,《遐想》如何?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大家都說好,就這樣,名字就敲定了下來。
為此,我特意去查了一下,遐想在百度百科里的解釋是,超越現實做高遠的想象。沙汀在《困獸記》里說:“正如一個凄涼美麗的夢境一樣,好是好的,既然是夢醒了,你就只能閉目遐想而已。”遐想是一個很美好的詞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可以變為可能。
提到遐想,當然就不能忘了生活在別處。開玩笑的說法是,蘭波創造了這句話,隨即被寫在了巴黎大學的墻壁上,只不過,后來米蘭·昆德拉卻把這句話弄得世人皆知了。王小波說的極是,“一個人僅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還應該擁有一個詩意的世界。”踏上遐想這葉扁舟,即刻便可抵達。
然而正是因為有了《遐想》,才有了后面馬丁·路德·金的《絕望之山》、《希望之石》。一塊“瑕紅”的花崗巖是很平常的,但是當人給它賦予了某種涵義的時候,它開始變得與眾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活了。
馬丁·路德·金像活了,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當雕像展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會看到了很多雕像以外的東西,比如說,馬丁路德金專注的目光以及對夢想的執著。這并不是人人能及的,但是,雷大師做到了。你也許會立刻就把杰克遜那句話帶出來,“你我可以都算是平常人吧,但如果你把雷大師也稱作普通人,我可不同意。”然后大家各自開懷大笑,坦言這個世界因為有了雷大師而變得如此不同。因為《遐想》,有了夢想。
雕像記
書里說雷大師從十歲起就知道馬丁·路德·金的鼎鼎大名,但從未想過有機會會為這位著名的美國領袖做雕像。與此不同的是,三年前的我就在步行街的《百年長沙》系列下留了影,而今卻在為這本書寫讀后感。這說到底,算是一種緣分。
當然,除了目睹了《百年長沙》的銅雕之外,雷大師另外的作品也見過很多,比如說湘江風光帶的《怪神射箭》、《怪神奇獸》、《天上人間地下馬王堆圖騰柱》,另外的就是芙蓉廣場的《瀏陽河》、賀龍體育館邊上的《沙水汩汩》。當來自望城的同學看到《雷鋒和我們在一起》是雷大師所作時,他說了一句,沒想到他這么牛逼。
牛逼的人,干的大都是一些牛逼的事。而之所以稱他牛逼,那是因為別人做不了,或者是別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做了,于是我們說他牛逼。但一個人絕不可能只是因為做了一件牛逼的事情才牛逼起來的,他需要的更多的是個人的積累,畢竟,完成一件藝術創造并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有名的雕像有很多,比如說米開朗基羅的大衛、羅丹的思想者、亞歷山大德羅斯的維納斯、米隆的擲鐵餅者、巴托爾迪的自由女神像……它們都是那樣的牛逼閃閃,但一個人能夠記住的也就那么幾個。
執著記
雕刻石頭是一件很花費時間的事情,除了日以繼夜的工作之外,就是一往無前的執著了。一個人選擇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但是能夠一直堅持下去卻很難。
從雷大師年輕時上山下鄉去芷江縣,到后來去廣美學習雕塑,最后到長沙開始雕塑工作,這漫長的過程中就一直與雕塑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如果我們能夠為我們所承認的偉大目標去奮斗,而不是一個狂熱的、自私的肉體在不斷地抱怨為什么這個世界不使自己愉快的話,那么這才是一種真正的樂趣。也許雕刻就是雷大師的真正樂趣所在。
執著,它還讓我想起了許巍的歌。
大學開始的時候,知道了許巍、搖滾、《在別處》。聽完《執著》之后,第一反應是,怎么到現在才知道許巍,頓時覺得虧欠了他太多。
后來陸續的知道了《曾經的你》、《藍蓮花》、《完美生活》、《那一年》、《時光》……
于是,手機上、電腦上、KTV里都是他的歌,認識的人說,你很許巍。
我不知道這是褒義還是貶義,因為一聽到許巍兩個字,夢想、滄桑之類的詞語就會隨即蹦出來。你知道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象征著一些什么。
然而聽許巍的歌,你就會感覺像是去見一位久違的老友,聽他娓娓道來最近的人生感悟。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愿意講給我們聽。
所以,每到不開心的時候,就放一下許巍,頓時一身輕快,感覺像是打了雞血。那略帶沙啞的歌聲,仿佛成為某種能量,只要你一聽到,你就會不自覺的振奮起來。而當你發現他已經是踏入四十不惑的年紀的時候,笑的還是那樣的恬靜溫暖,就像一朵緩緩綻放的藍蓮花。你說,想不到經歷了人生百態世間的冷暖,這笑容卻是依舊溫暖純真。可是,這一切都止于屏幕之上。
那還是一年之前,在經歷了有汪峰的那場橘洲音樂節之后,就開始期盼著一些什么。曾經有消息稱許巍有可能作為特邀嘉賓,頓時激動不已。可是直至后來才搞清楚,許巍不能來了,不過崔健來了。也是一樣的很搖滾、很執著、很熱血。那個時候跟自己說,雖然人不在,但歌依舊還在。其實活在音樂里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一群人。
與許巍能牽扯上的總是很多,比如說,每次我用拼音打xuwei,虛偽總是在前面,而寫完這篇文章,許巍領先了。他讓我明白,這個世界上不僅有虛偽,同時也有許巍,說到底,還不錯。
那歌里不是說么:“青春的歲月,我們身不由己。只因這胸中,燃燒的夢想。”
夢想照進現實
從2006年5月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舉行國際石雕研討會,馬丁·路德·金紀念園基金會中杰克遜等人看中了雷大師的作品,到2011年10月16日馬丁·路德·金紀念園揭幕,用了近五年的時間打造了《絕望之山》和《希望之石》。這讓我不得不想起姜文的那個廣告,“有人說,拿那么多時間做這么一點東西,是不是有點傻?但是時間是為了干什么的?時間……就是為了做一個好東西。你先知道什么是不好,把不好去掉……”雕塑也一樣。
就雷大師的《巖石上的夢想》而言,總是能有一些東西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就牽動你內心的某根心弦。因為他的作品早已被人所接受,這其中就包含了我,雖然那個時候的我對于這些東西出自于他還渾然不知。可是當你某天在不知不覺中發現這些東西的來由的時候,你就會驚嘆,原來是他啊!頓時對他肅然起敬。同樣,之于國際友邦人士的杰克遜給雷大師的評價是,這位藝術家能夠抓住人物或對象的靈魂,以一種無可名狀的表現力,使之躍然紙上,或者讓石塊栩栩如生。換句話來說,就是活了。你會感覺到這東西已經被他賦予了一種靈魂。當你走進的時候,你就會慢慢的被他吸引,然后,當你在它的面前停留下來,仔細端詳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無論是從線條還是神情,凡是你能夠想到的,到這里最終都凝結為一個點,然后圍繞這個點,慢慢的延伸下去。于是,一個新的世界就在這里默不作聲地誕生了,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這本書里講的是一個石頭的世界,如果深入了,你就會發現這里面無奇不有。而當你帶著這塊精心挑選的石頭,從里面快步走出來,重新踏入那熟悉的街道,你就會發現夢想總是那么的遙不可及。你說,有那么一個瞬間,想起了《老男孩》。即使是如此不把他當做一回事,但偶爾聽著歌聲,還會淚流滿面,只不過聽完之后,生活的本質依然未變,我們只是越來越懂得想哭的時候跟自己說,哭是沒有用的,連眼淚都是禁忌,但我們依然還要在張牙舞爪的社會中和所有人一起爭奪有限資源,并且渴望有那么一天,夢想能夠照進現實。
曾經聽人說,如果一個人30歲之后還讀《格瓦拉》,那他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我聽到了這句話,我準備開始讀它。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