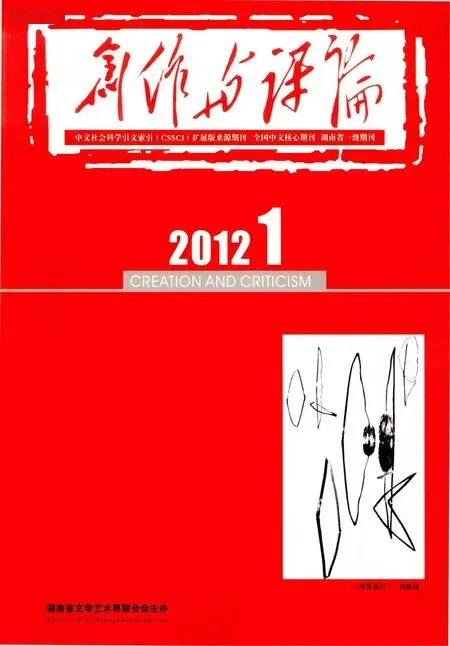大灣村:一個(gè)人的詩(shī)意故事及靈魂
■ 李小雨
這是一組凝結(jié)了一個(gè)人三十多年回憶的詩(shī)。仿佛是人生的階段性總結(jié),全部詩(shī)作均起始和沉落于中國(guó)西南角的一個(gè)偏僻而又無名的低矮村莊,它是作者夢(mèng)繞魂?duì)康囊黄恋兀橇钭髡邿釔邸⑿耐础⒘鳒I和吟唱的故鄉(xiāng)。我相信它的小:“天井中漏進(jìn)的光照著那只木桶”(《舊屋》),但它又是多么的大啊,無邊無際:“我見證了它由一滴而化為一片汪洋”(《一個(gè)村莊的性格》),它是詩(shī)人心中的整個(gè)世界。
近四十年了,作者奔走于湖南永州故鄉(xiāng)和北京之間,這漫長(zhǎng)而又短暫的時(shí)間跨度,使這組詩(shī)凝結(jié)在同樣的瞬間,并在此展開了一個(gè)人的心靈史。在想象中訴說,用這片扎根的貧瘠土地建構(gòu)自己的精神家園,承載那無休無止的思念,撫平那些人生旅途上的坎坷創(chuàng)傷,填補(bǔ)著心靈中的大愛和游子的心聲……遠(yuǎn)離,仿佛只有遠(yuǎn)離,才能更深地?zé)釔叟c體驗(yàn);才能讓村莊長(zhǎng)出翅膀,“多么難得的翅膀,一個(gè)國(guó)家的翅膀/三十年,攜著風(fēng)雨、雕花窗子和麻雀蒼翠的鳴叫”(《珍藏》)。詩(shī)人此時(shí)的感情已經(jīng)熟透了,像一壇三十年的陳酒,芳香而甘洌。詩(shī)歌之杯中,情感的壺口是多么的惜酒如金呵,自如的節(jié)制,使詩(shī)人的歌喉處于清爽狀態(tài),鋤去滿地的亂草臃果,故鄉(xiāng)大灣村的風(fēng)景如一幅素描,洗練、干凈、簡(jiǎn)潔,而靈魂的部分得以凸現(xiàn)。
因此,講述一個(gè)村莊的故事,就成為一個(gè)有責(zé)任感的詩(shī)人用回憶構(gòu)筑的想象的天堂,它包含著一個(gè)人的命運(yùn)、內(nèi)心的蒼茫,它是他通向現(xiàn)實(shí)的唯一的路。
他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通往個(gè)人的獨(dú)自存在的荒村小土路。一如鄉(xiāng)村詩(shī)人弗羅斯特在其詩(shī)中所說:“黃色的樹林里有兩條岔開的路/可惜我不能在同一時(shí)間走兩條路/我選擇了人少行走的那條/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異。”因?yàn)檫@種差異,田人的詩(shī)歌給我?guī)砹碎喿x的欣慰。他寫詩(shī)的時(shí)間很長(zhǎng)了,寄給我的那些詩(shī)稿里好像總有一只田鼠或什么風(fēng)車的影子之類的細(xì)微地一鳴,讓人眼睛一跳。
他以弱者的身份出現(xiàn),他在風(fēng)景里言說,像一株稗子開言。誰能注意到一株稗子的愛情呢?它是壞人,它是該剪除者,短暫易逝。但它細(xì)小的感情一經(jīng)詩(shī)人的表露,就令人難以忘懷。“它有了一次愛情,它深深地愛著一株稻子”、“它想起曾經(jīng)要謀害稻子的歲月/它現(xiàn)在不想了”(《一株稗子的愛情故事》)。害草也是草,壞人也是人。博愛超越所謂好壞的簡(jiǎn)單劃分,它的意義不言而喻。他的另一首詩(shī)也寫到野豬,以同樣方式,我們體察到了野豬的心靈。誰能說這世界原本沒有野豬的一份呢?人占有野豬林,是文明還是野蠻,這可能不是田人詩(shī)歌的關(guān)注點(diǎn),但這是一種新鮮的詩(shī)歌觸覺。
讀這些詩(shī),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對(duì)故鄉(xiāng)的愛,這種愛,可以是溫暖的、明亮的,甚至是一切貧窮、苦難掩蓋不住的熾烈:“它不再懼怕風(fēng)/不再懼怕饑餓的光在它的上空盤旋/和四壁的明鏡將它的翅膀撕裂/它飛翔,將通過太陽的炙烤//我仿佛看見一切輝煌都是虛假的/和我的抱吻。惟有螢火蟲/這大灣村的精靈,它閃動(dòng)的光/多么熱愛這里”(《螢火蟲》),這是螢火蟲,也是田人自己的寫照和獨(dú)白。他的許多詩(shī),在直面痛苦、凄涼的同時(shí),都依然充滿著人性的美,充滿著人與自然融合時(shí)的令人心醉的自如與純凈,連一棵白菜都會(huì)說:“世界多美好啊!”(《一棵大白菜》),連一片云都會(huì)說:“走過農(nóng)田和鏡子/把金子從天空中撒下來 /像撒下花瓣”(《際遇》)。愛是純粹的、無條件的,愛小村的普通:“那些長(zhǎng)長(zhǎng)的草,散亂地長(zhǎng)在路邊/那些花,我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它們都是這樣,干凈”(《一盞馬燈》);愛小村的孤獨(dú):“這低低的山岡……/這人類的地獄”、“我的故鄉(xiāng),我的聲名的馬車/把我的孤獨(dú)一件一件/放在我的灰燼安放的地方”(《歸途》);這是刻骨銘心的愛:“寬闊的石頭和倒懸的青碧的水/是我的骨頭和血液”(《夢(mèng)》)。因此,他的愛使他的詩(shī)帶有一種難以舍棄的疼痛感,帶有生命成長(zhǎng)的不安和涌動(dòng):“我需要像大海一樣地翻滾”(《器皿》)。在短小輕盈的篇幅下,他寫親身經(jīng)歷過的親人的死亡,在這條返回大灣村的路上,有多少淚滴又有多少鮮花遠(yuǎn)去:“這條孤零零的路上/沒有一個(gè)車夫/我走著/沒有人看得見//那邊的塵土/裹住我全心/仍然孤零零的路上/聽不見一個(gè)人的咳嗽聲”(《在這條路上》),孤獨(dú)乃至終老至死的氣息彌漫著歸鄉(xiāng)之路。
詩(shī)人的山岡是低低的,就像一只低飛的鳥,低向深淵。故鄉(xiāng)也許是唯一的一塊埋人的地方。田人是經(jīng)歷過親人的猝然離去的,這種打擊令其終生難忘。但是,“在亂墳遍布的山岡/我走來的路邊的那些花草和樹木/仍在蓬勃地生長(zhǎng)”(《山岡》),這是詩(shī)人自己說的,故鄉(xiāng)是生也是埋葬,埋葬一如大地的珍藏,那也是一種幸福。當(dāng)讀到這樣的句子,讀者已確信跟隨著詩(shī)人回到他真實(shí)的大灣村,而不是一次虛無縹緲的遐想。最終精神纏繞著灰土,他的詩(shī)中,便也有著深長(zhǎng)厚重的內(nèi)涵和回味。
《三十年后·大灣村》,從各個(gè)角度和片斷講述一個(gè)村莊的故事,質(zhì)樸、平靜、簡(jiǎn)約、節(jié)制與敏感、細(xì)致、小巧、精致并存。作者不是寫實(shí)主義地?cái)⑹拢羌庸ぬ釤捄蟮那楦械纳A。他有意識(shí)地控制著敘述的節(jié)奏,節(jié)制著語速的鋪排,內(nèi)中留下了看似平淡中的大量空白:“鐵樹是那個(gè)很老的老人栽的/一百年之后鐵樹開花了/開完花之后鐵樹就死了”(《大灣村》)。一個(gè)人的一生在兩句詩(shī)中平靜地結(jié)束,沒有感嘆、沒有渲染,白描的手法背后,留下關(guān)于人生和時(shí)間的懷念。他的詩(shī),是村莊情感的記事,而不是對(duì)具體事物過程的客觀描述,他不展示技巧而崇尚樸素,我們往往被詩(shī)人緩慢的敘述方式吸引,在不知不覺中將閱讀的速度放慢,讓詩(shī)歌內(nèi)在的情感漸漸彌漫。這樣的敘述首先要詩(shī)人創(chuàng)作時(shí)的沉靜心態(tài),他用紙包住火,用泥土裹住種子,他有意識(shí)地讓自己不說出一切,而在這樣的遲緩中暗藏著多少心事:“它們雖然有些不情愿/但是它們沒有太多的話說”(《黃陽司鎮(zhèn)的魚蝦》),“人們對(duì)它視若無睹了/乃至它的枝上發(fā)出的那幾片新芽”(《花兒漸漸遠(yuǎn)去》),這些心事只有魚知道,新葉知道。詩(shī)人帶著坦誠(chéng)的率真,將這壓抑下痛苦變得如此安靜,甚至如啞然和失語:“你經(jīng)歷的這些風(fēng)險(xiǎn),我很擔(dān)心”(《廊坊》),這簡(jiǎn)單的直白,使人感到土地的樸拙和冥想中生命狀態(tài)的真實(shí),那些仿佛是大地上蘊(yùn)含的原始的生命力,在風(fēng)平浪靜的底下,起伏著波瀾。
田人這組詩(shī),讓我們看到了鄉(xiāng)土本身呈現(xiàn)的價(jià)值。鄉(xiāng)村生活里綿延著中國(guó)人的行為方式和精神方式,在城市里的嘈雜改變和斷裂著我們的生活時(shí),在這個(gè)物質(zhì)主導(dǎo)、精神匱乏的時(shí)代,堅(jiān)守著自己腳下那一塊扎根的土地,不斷地在這內(nèi)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接壤處耕耘播種,仿佛一個(gè)質(zhì)樸的在詩(shī)歌田間勞作的人,誰能說他不是這土地的主人呢?他讓我們共享他珍藏于內(nèi)心的糧倉(c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