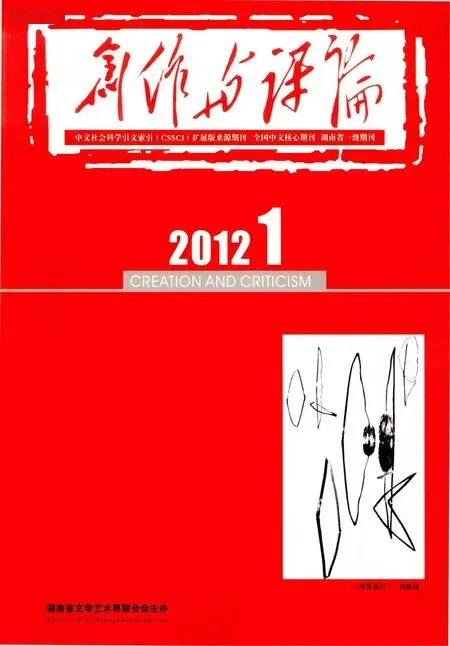好人徐則臣
■張楚
我有個小學同學,叫小靜。此人有種非凡的能力,那就是:輕易就能把自己貌似庸常、幸福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糕甚至慘不忍睹。每次見他,我都有種心驚肉跳的感覺。有一次同學聚會,他喝了三杯白酒后問我:聽說你也寫小說,那你知道有個叫徐則臣的嗎?我說知道。他瞥了我一眼說,我最近看了他的《跑步穿過中關村》,寫得真他媽棒啊!我使勁點頭。他又瞥了我一眼,說:你該向人家學習,小說就要寫到人的心里去!他說話的聲音很大,大到把自己的眼淚都驚了出來。我知道這個人的生活一向匪夷所思,只不過,我搞不懂他的眼淚是為自己而流,還是為《跑步穿過中關村》里的敦煌而流。
那是2006年冬天的事。我記得當時給則臣打了電話,歡迎他來找小靜同學喝酒。
其實2002年就認識則臣了。那時有個“新小說論壇”,是浙江作家黃立宇辦的純文學網站,駐站作家有李修文、艾偉、廖增湖、夏季風。“新小說論壇”每個禮拜都就某一文學主題進行熱烈討論,當時非常之火,一時無兩,很多青年作家都跑到那里貼小說。則臣的名字就是那時慢慢熟起來的。如果沒有記錯,他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尚未畢業。第一次在北京見面,他還特意帶我到北大的未名湖轉了一圈。中午吃飯,他只陪我喝了一杯扎啤,讓我很是失望。不過,他倒是非常能吃,而且吃相頗為莊嚴。那之后,偶爾去北京,都忍不住給他打個電話,一起吃頓飯,聊聊小說,聊聊生活。他總是爽快地應允,不管倒幾次地鐵,都會背著一個黃色帆布書包風塵仆仆趕過來。我貌似喜歡喧鬧,喜歡酒桌上大塊吃肉大口喝酒的快慰,其實與人真正交往起來,反倒是收斂、自閉的。好在則臣長了張忠直無欺的臉,你只能從他的臉上看到真誠、樸素、從容等一干詞匯,并讓你內心分泌出無端的信賴感。
再幾年,則臣發表了大量的中篇小說,形成了自己的“京漂”、“花街”系列,名聲大噪,獎拿到手軟。則臣雖年少,卻沒有年少得意者慣有的蠻傲,人還是那個人,依舊實誠的一張臉,依舊樸實燦爛的笑容。他不會拒絕別人。有一次,一幫朋友喝酒后去錢柜唱歌。中間我去洗手間,見他正在走廊里徘徊——肯定是不想唱歌,又礙于情面不好早走。于是我們靠著玻璃幕墻聊起來。那是我們談得最久的一次。我提到《蒼聲》和《傘兵與賣油郎》,我覺得這兩部小說雖是他小說里的異類,卻有著獨特的、豐富的、狂野的美。它們有著潮濕的、腥甜的氣味,而這種氣味,在他的小說里比較少見……他也提到我小說里的諸多問題,譬如敘述、譬如語言……不斷有人從我們身邊走過去又走過來,也不斷有朋友端著酒杯過來招呼我們,而我們只是在那里靠著墻壁,深一腳淺一腳地聊著文學……其實于我而言,生活在小鎮,極少有這樣暢談的機會。更多時日,我慣于沉默并惰于思考。而則臣不同,他科班出身,名師之徒,有著深厚的理論素養,又有文字實踐,對文學最本質的東西有著獨立的、自由的思考。與他交流,時常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
當然,他不只是單純的老好人,對朋友,有什么話他也不藏著掖著。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學》發了一篇小說,是他校對的。見面時他說,張楚啊,我給你提個意見,以后你的小說在投稿之前,能不能先把錯別字好好改一改?我說,好啊。從那兒以后,無論給哪里寫稿子,我都是把小說先打印出來,拿著鉛筆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拿不準的就去查字典,校兩遍后,再讓我的一個中文系畢業的同事幫忙看一遍。
則臣雖厚道,卻不是個中庸主義者。他敢于說話,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有思想、有氣魄的年輕作家走向成熟、走向“大家”的標志。譬如關于卡佛。我從來沒有覺得卡佛寫得有多好,當然,也沒有覺得他寫得有多壞,只是個有特點的作家而已。看到別人對他的溢美之辭,我時常感到困惑:是不是我自己的審美出了問題?后來我看到他寫了篇文章,叫《如果我說,卡佛沒那么好》。他說:“節制是寫作的美德,但準確是更大的美德,如果為節制而損害準確,吾未見其明也。節制過了頭可能就是矯情和做作。我讀卡佛,常覺得這是個技術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斧劈帶了點表演的成分……小說該有的枝蔓和豐沛,該有的模糊性,文字該有的毛邊和藝術感,以及在更高精確度上需要呈現的小說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殘酷的刪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過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說簡化為單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細節,那樣不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閉合的結構,死死地封住了意蘊的出路。”我覺得他說的真是字字珠璣且一針見血!還譬如關于197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的寫作問題,他寫了篇《別用假嗓子說話》,提到問題所在:這一代作家中有眾多保有才華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謂的“通約”的、“少長咸宜”的文學款式,在從事一種跟自己無關、跟這一代人無關、甚至跟當下的這個世界無關的寫作。這樣的寫作里沒有“我”,沒有“我”的切膚的情感、思想和藝術的參與。此類拼貼和組裝他人經驗、思想和藝術的作品,的確可以更有效地獲取鮮花與掌聲,但卻與文學的真義、與一個人眼中的時代南轅北轍。我把這樣的寫作稱為假聲寫作。我只能說,則臣長了一雙火眼金睛,透過紛繁蕪雜的表象,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假菩薩誰是真羅漢;我只能說,則臣生了一顆正直的心,在事關文學的問題上,從來不會裝“老好人”,從而維持面子上的一團和氣。對這個在文學道路上一路狂奔并時刻腦子清醒的人,我保持著一種真誠而且必要的敬意。
2011年春天到夏天,我跟則臣都在魯迅文學院進修,成了同學。按理說,漫長的四個多月,我起碼能把他的酒量訓練出一點。可是除了上課,我極少見到他。他比我想象中的忙多了:要去農展館南里10號樓上班,還要到芍藥居文學館路上課;要去國內國外參加文學交流、活動,還要牽著大腹便便的老婆的手去散步;要自己寫小說,還要閱讀別人的小說。我只能說,這孩子真是太皮實了。有一次上課,他聽得格外認真,頭都沒舍得抬一下。等中午吃飯時,他瞪著我說,今天上午,我校對了一個十來萬字的長篇呢。然后他垂下頭,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來。
說實話,到了今天,我早就不指望則臣當個好酒友了。不過也無所謂了,鄭小驢、馮嘯然他們都練到白啤不忌葷素不忌的份了。只要則臣能繼續寫出好小說,只要則臣能當好那個叫“巴頓”的孩子的爹,只要則臣能保持一名無關風月、無關左右的獨立知識分子應有的風度,那么,作為哥們的我們,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我們只會為他感到驕傲,猶如阿赫瑪托娃在《在哪里總會有一種普通的生活》里所言:這座光榮與苦難交織、花崗巖建造的華麗之城……繆斯的聲音,隱約可以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