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戰時云南文教圖景
○段福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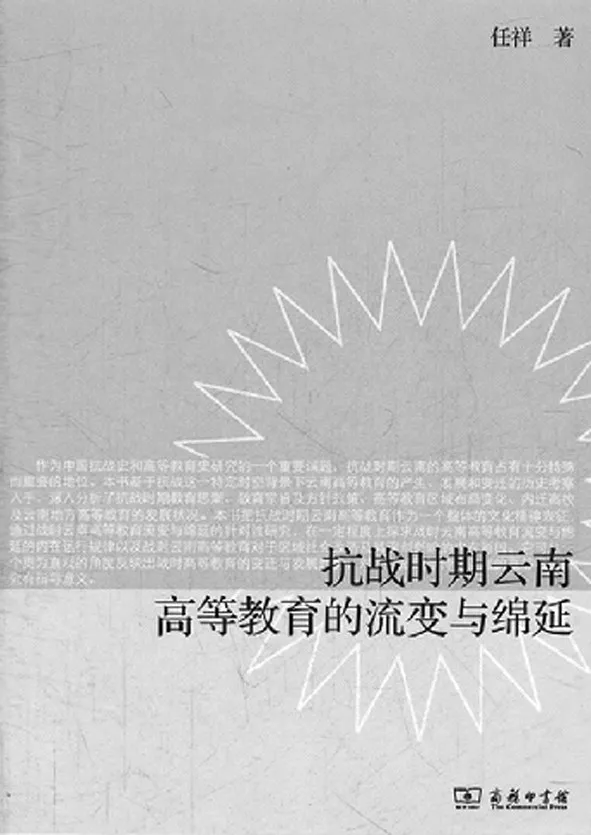
《抗戰時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變與綿延》,任祥著,商務印書館2012年5月版,36.00元。
云南雖有170萬年前“元謀猿人”這一人類先祖,有秦漢時期的“古滇國”文明,有唐宋盛世時的拱衛疆土的妙香國“大理”,也有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的學術重鎮、文化要地、民主堡壘”,亦有今天的“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然而,“交通閉塞、民智未開,荒蠻邊夷”仍是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的“云南標簽”。在這些與事實有所出入的外界認識中,折射的是云南本土文化,尤其是文教事業被淹沒、被掩埋的現實。
今天,提起云南的文教事業,浮入人們腦海的更多是戰時的內遷高校,尤其是國立西南聯大,而很少有人會想到早在晚清便創立的“云南蠶桑學堂”,以及一度與“黃埔軍校”齊名的“陸軍講武堂”,也很少會想到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收錄的中國15所著名大學里的東陸大學(云南大學),更很少會想到國立藝專、國立中山大學、私立武昌華昌大學、私立中法大學等其他內遷高校。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內遷高校的光輝掩蓋了云南文教的輝煌,而西南聯大的光輝又籠罩了內遷高校的輝煌。
人們常說,歷史是屬于過去,然而梳理和評述歷史的人,是屬于現在,屬于未來的,因為他們能撥開歷史的云霧,為我們再現曾經的歷史,因為他們可因循史料的經驗得失,啟示未來的發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云南師范大學任祥所著的《抗戰時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變與綿延》一書,以詳實的史料和嚴密的邏輯推論將內遷高校的風采從西南聯大的光環籠罩中透射出來,將云南本土文教事業的本真面貌從內遷高校的光環中離析出來,以知識的理性為我們再現云南文教事業的歷史圖景。它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作為邊陲的云南,不僅有長期偏安一隅的處世姿態,還有著歷久彌堅且璀璨多姿的地域文明,更有從未間斷的中華文化延續和中華文明傳承;它使我們知道,“學校教育”并非域外文明的獨有產物,“睜眼看世界”的近代風潮也曾席卷云南這片廣袤的土地;它使我們意識到,抗戰后方的民主堡壘并非僅有西南聯大的支撐,其后還有無數內遷高校的身影;助推民主的“一二·一運動”,不僅有諸如聞一多的斗士身影,有聯大學子的風采,還有南箐中學不屈的脊梁。它使我們關注到,與西南聯大一道進步不僅是內遷高校,還有云南本土高等學校生生不息向上的內生發展。
戰時云南高等教育的歷史,是一部內遷高校與云南本土高校、云南本土文明以及云南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史。正如云南省商會聯合會、昆明商會《公送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歸復校序》中所述:“自聯合大學南來,集諸科多數之專家,得悠長之歲月,或以修志躬蒞其地,或受委精研其事,其已結集成書者既不少成書,其待編行者層出不窮。凡茲所為,均可謂之類通方,開物成務,有關國計民生大者。于是滇之為滇,始一掃陰霾,以真面顯示于天下,后者有董事開發之者,其必以為是借鏡矣。”可以說,從內遷高校逐步融入云南經濟社會開始,就使云南高等教育呈現出接納性、嵌入性的發展態勢,從中小學的師資養成,到高校間的協作發展,云南文教事業的發展無不深深地烙上內遷高校的印記。客觀而言,一方面,勤勞的云南人民以自己的無私哺育著內遷高校;另一方面,內遷高校也以知識的教化無聲地浸潤著云南人民質樸的心靈。與此同時,內遷高校既在競爭中擠占了云南本土文教事業的資源,同時也在協作中促動了本土文教事業的飛躍。戰時云南的高等教育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精神表征,從某種角度看是一種抽象的存在,然而它對云南開發這一歷史功績,實際上已深刻地體現于中國20世紀戰時大學遷變所引發的促進西部落后地區發展的總體特征之中。
“夫然后教育事業之神圣,學術思想之尊嚴,乃有所麗,而可久維而不蔽。如是熏習而楷模焉,久與俱化,他日士氣民風,奐然丕變,溯厥從來,知必有所由矣”。回顧歷史,我們很難給戰時云南高等教育的那段流金歲月下一個完整的結論。究竟是內遷高校助推了云南的文明進程,還是云南的固有文明成就了內遷高校的輝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因為內遷高校的到來,云南得以成為戰時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民主堡壘,自由、民主、科學的思想得以在此開枝散葉,云南的經濟社會、民智民風、社會風尚都得到了更新與進步。在內遷高校的促動和本土文化的自覺下,云南有識之士或奔走于“教育救國、保存民族精神文化血脈”的最前線,或遠走異國他鄉尋求智識增進,以獻身國家和區域事業改造。這期間,云南的高等學校數、中小學校數以及相應各類學校的受教育者人數明顯、持續增長;各種進修班、講習班、培訓班、掃盲班、婦女先修班遍地開花;云南籍旅美、旅日、旅法留學生人數急速增長;鄉紳宦士捐資助學、出資辦學的漸次升溫。從龍云統轄的云南省政府到龔自知執掌的教育廳,從登大雅之堂的顧映秋(龍云夫人)到籍籍無名的鄉里市儈,從文化學人濟濟一堂的昆明到民智初開的大山深處,一股“尊師重道、興文教化”的風氣悄然刮起并持續回蕩。據作者任祥統計:聯大在昆明八年,所培養的8000余名學生近半數留在后方工作,成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支撐;華中大學在大理八年,共培養了300多名滇籍學生,為邊疆開發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和技術保證;受內遷高校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1944年初,昆明市工業從業婦女達6296人,占是年婦女總人數的17%,商業婦女從業者達4858人,占是年婦女總人數的13%,交通運輸婦女從業者3129人,占是年婦女總人數的9%,公務員婦女從業者2698人,占是年婦女總人數的7%。婦女就業面的擴大、就業率的上升,反映了云南社會對婦女的歧視現象有所改變,也說明婦女擺脫家庭依附關系、要求掌握自己命運的主體性意識正在覺醒;從1935—1945年10年間,昆明的公立中學由戰前9校63班增加至10校85班,私立中學由2校6班增至19校98班,總體增長近10倍;僅1942年一年,云南籍高等教育受教育在校學生1113人,而從1911—1938年的27年時間里,云南籍畢業生僅為2575人,直接反映出云南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劇增……如上種種,既是云南文教事業發展的縮影,更是戰時云南高等教育流變綿延的真實寫照。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更不能忘記在歷史中的不斷自我省思。在內遷高校復員7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的文教事業雖然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但很難說其還保有曾經的輝煌與榮耀。個中原由,值得我們深思!內遷高校對云南文教事業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但透過歷史,我們更希望在這種深遠的影響中,有一批本土的高等學校,能夠支撐起云南經濟社會的發展,能夠為云南建成中國西南面向東南亞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提供更為豐富的智力支持,為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社會文化的繁榮而不懈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