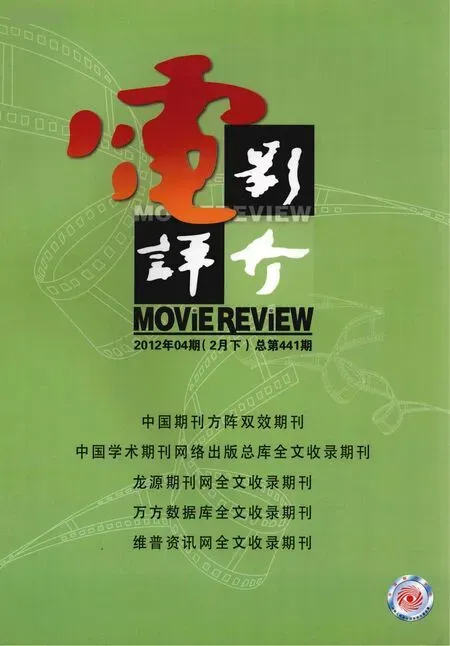影像作為存在:簡評姜文導演的電影
一、《陽光燦爛的日子》:叛逆的內容與歷史語境的誤讀
從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起,由于姜文對角色的準確理解與感悟,使得人物形象生動鮮明,自此,姜文躋身于中國優秀演員的行列,在成功地演繹了眾多銀幕形象之后,他執導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自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影片表現了在軍隊大院中的孩子們在“文革”的個人經歷。姜文和王朔都成長于軍隊大院,姜文原名叫姜小軍,而影片中男主角的名字叫馬小軍,可見姜文自己對于影片中的生活也是認同的,由此這部電影和大多數導演一樣,處女作以自傳體的形式開始,《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帶有姜文自傳體性質的影片。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姜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真實的展現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中青春的騷動和叛逆。姜文把情感經驗和內心對于生活、生命的體驗和想象的空間融合在一起,把題材的選擇、主題的呈現、人物性格、敘事技巧的運用和時空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敘事是成功的,然而,這種成功得益于影像敘事的邏輯服從了《動物兇猛》的敘事邏輯,服從了王朔,姜文少年時代的真實生活的展開邏輯。
影片故事所呈現的歷史語境文革時期,是一個畸形的時代,軍隊大院是那個畸形年代中的畸形敘事環境。作為軍人特權子弟的馬小軍們放蕩不羈、肆意妄為。他們打架斗毆,酗酒滋事,玩弄女性,重傷無辜,危及生命,甚至游走在社會個人生活的刑事底線。馬小軍們在特權餐廳(莫斯科餐廳)中歡呼打架斗毆勝利的時候,共和國的元帥彭德懷,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正在監獄中痛苦地呻吟,與馬小軍同齡的蕓蕓眾生正在上山下鄉的凄風苦雨中掙扎。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十年動亂已經是根植于中華民族集體記憶中的深深的黑暗痛苦,馬小軍們是一群在畸形年代中,在畸形環境中生長起來的畸形青春。然而,在文革結束16年之后(1994年),姜文對文革那段特殊黑暗時期的畸形青春的結論是: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簡言之,姜文的處女作具有兩大特征:影像敘事的客觀真實,對敘事語境的主觀誤讀。
二、《太陽照常升起》——敘事結構的叛逆與代價
《太陽照常升起》倒果為因的敘事結構,顯現出一種對傳統敘事模式和敘事結構的顛覆,這種顛覆跌破了電影藝術敘事結構的底線。如圖表所示,故事的總體邏輯應該是1,2,3,4,而姜文把敘事邏輯鏈條打亂成為2,3,4,1的組合結構。這不僅僅顛覆了電影的敘事結構,同時導致在一般現實邏輯層面受眾無法理解故事的整體性走向。

影片呈現順序影片內容2 瘋 1 瘋媽、唐妻尋愛,瘋媽產子3 戀 2 瘋媽因丟失了一雙鞋而瘋了4 槍 3 唐老師、梁老師、林大夫之間的情感1 夢 4 小隊長因與唐妻偷情被殺影片內容故事順序
這部電影的題材又涉及文革時期,一些時代化的影像符號依舊不斷出現在影片之中,這些影像符號的風格是調侃的,不合邏輯的,略帶有一點點荒誕,或浪漫色彩。它或許負載著導演內心主觀世界對于世人的審視與體驗,情感與意向的雙重體驗,遺憾的是:在混亂的敘事結構中,這些影像符號破碎成為受眾理解的障礙。
《太陽照常升起》中把姜文叛逆的性格和思想再次顯露無疑,按照自己個人邏輯去建構整個影片的敘事結構,姜文的叛逆精神從《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內容上的叛逆發展到了《太陽照常升起》中對于敘事機制、敘事結構的叛逆,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變化。而在電影中,敘事過程的合理性是極其重要的,電影敘事規律應該在總體上遵循因果聯系。
三、《讓子彈飛》——影像敘事規律的把握與回歸
《讓子彈飛》的題材視點對準民國時期動蕩不安的歲月,影片合理的解釋了張麻子的行為動機,張麻子原名牧之,是曾追隨蔡鍔將軍的手槍隊長,這就使得影片的敘事動機具有了合理性,辛亥革命失敗后,社會動蕩不安,但曾作為革命分子的張麻子依舊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因素,內心的英雄主義情懷使他決心留在鵝城殺富濟貧,除暴安良,在黃四郎、張麻子和馬邦德三人關系的層層遞進中,準確無誤的將民國時期1920年的景象濃縮在人物中,同時以小人物在時代大背景下的人和事去闡釋導演的理想抱負,以眾生相的自為的存在去做出自由的選擇并承擔責任,盡力依靠張麻子他們自己選擇的行為及有密切關聯的可能性做出決定,以一種存在者的身份與視角去審視民國那混亂年代下人類的內心經驗,更是審視張麻子這種從蕩寇到英雄的內心理想的覺醒,他那“存在先于本質”的精神被重新點燃,孤獨的前行。
《讓子彈飛》在敘事動機合理的情況下,民國作為一種亂世亂象的社會歷史語境的讀解,對《讓子彈飛》某些荒誕的敘事元素的植入,以及某種魔幻意義上的影像風格的建構,提供了敘事語境的支持。影像的總體風格是合理的。從之前的叛逆到現在的合情合理,姜文在朝著符合電影敘事規律的道路上行走,在進行一種必要性的回歸。
四、姜文電影中的潛意識文本顯現
姜文導演的電影作品中幾乎都有現實與想象的交叉影像,而在想象的影像呈現中,觀眾能夠明確的看到主人公想象內心世界的一種主觀情感的客觀呈現。而這種精神層面的想象世界的呈現其實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對于潛意識的一種解讀。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精神存在的基本結構是由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三部分組成的,它們分別處于人的心理層面的深層、中層和表層,三部分之間是一種彼此共存的狀態。
潛意識是人類深層心理活動的驅動力,人的行為也會受到潛意識的制約與影響,并且這種行為具有非理性的特點。這種潛意識文本在姜文的電影中都有所展現。
《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在自己的頭腦中多次主觀能動性的想象他和米蘭的種種際遇,隨之感情迅速升華,但隨后馬小軍真實的內心獨白否認了事件的真實性,一切不過是馬小軍通過想象來完成的一種敘事和表達,是他人格類型中“本我”狀態的外顯。電影展現的是在文革背景下一群青年恣意的青春,馬小軍們潛意識中的“唯樂原則”讓他們一味的追求快樂,放縱自己。影片中所展現的內容,究竟哪個是真實的回憶,哪個是虛構的回憶,導演并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答案,而這樣一種空間建構方式可以稱之為影片的自適性空間。
《鬼子來了》中村民們一輩子都生活在被壓抑的狀態中,直到最后看到全村村民被日本人殺害時,終于激發了馬大三潛意識中的反抗精神,他不顧一切為村民復仇。當馬大三人頭落地時,他看到了一個紅色的世界,此時他依靠的并不是自己雙眼的視力,而是一種超人的視力,是主觀心理醒悟的彰顯。
《太陽照常升起》中瘋媽夢到了一雙鞋,而夢醒了后她買到了那雙鞋,夢的愿望得以滿足,“夢的愿望屬于另一種潛意識”[1],但同時瘋媽也因為丟失這雙鞋而瘋了。小隊長因潛意識中的性沖動而不顧后果的與唐嬸發生了性行為,這是小隊長性本能的表現。影片以四個貌合神離的故事按照非邏輯的順序組合在一起,由此產生的空間自在存在給觀眾更多的想象和解構,這種空間的設置顛覆了受眾群體在一般現實邏輯層面上的接受習慣。
《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在與黃四郎作對的過程中,激發了他潛意識中的英雄豪情,開始運籌帷幄與黃四郎對決,打敗地方惡霸以換取鵝城太平。成功擊敗黃四郎使張麻子的革命理想開始燃燒,但他手下的兄弟們卻選擇了離開,去過自在的生活,最后只剩下張麻子獨自一人黯然傷神。
五、存在主義觀照下的姜氏電影
存在主義強調“人的存在”,是以人為核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選擇。薩特認為“存在先于本質”,人的本質是通過自我意識的形成而逐漸建立起來的。當薩特的存在主義把人放在第一位去尊重時,人自由選擇的權利自然而然也就躍居于上,人存在的本質在于自由,人通過自由選擇來實現個人意愿,但同時人也要為自己的個人行為后果負責。
在姜文導演的電影作品中,存在主義潛移默化的存在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之中。姜文的電影中通過自在的存在與自為的存在的結合,將世界荒謬,人性孤獨與自由選擇,很好地展現了出來。存在主義的核心問題貫穿影片始終,對于人的生存以及生存的根本問題用影像去闡釋,去構建,諸如人的自我選擇、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孤獨等都在他的影片中有所呈現。
薩特認為,人的存在是一種自由的存在,個人的意志可以自主進行選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當現實時空中的馬小軍在回憶他的青春時光時,他在回憶中按自己的自由意志進行選擇,他在潛意識中期望自己成為英雄一般勇敢的人物,因此在劉憶苦和馬小軍的生日會上,馬小軍因為嫉妒劉憶苦,也因為對米蘭的感情沒有得到回報而致使他與劉憶苦發生爭執,并拿起酒瓶對劉憶苦大打出手。“否定是對存在的拒絕。一個存在(或一種存在方式)通過否定被提出來,然后被拋向虛無。”[2]馬小軍的這種自由選擇只是一種虛無的存在,因為隨之馬小軍就否認了這件事情的真實存在性。畫面定格在馬小軍痛打劉憶苦時,伴隨著畫外音畫面開始閃回,那天的生日會很和諧,大家聚在一起很開心。“非存在永遠在我們之中和我們之外出現,就是虛無糾纏著存在”[3],影片通過主人公對回憶的否定和畫面的閃回,暗示了一種虛無與存在的關系。
這種存在與虛無的思想在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中也有所揭示,姜文在這部影片中顛覆了傳統的敘事結構,四個貌合神離的故事按照非邏輯的順序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真實與想象的混合,造成了觀眾觀看本片時理解上的困難,影片從結構上來講就是一種存在與虛無的展現。
存在主義指出,當在生存過程中理想與現實發生沖突時,人應該進行自我選擇、勇于行動。《鬼子來了》中,馬大三一直生活在自己天真的想象中,他希望把花屋小三郎和翻譯官送回去后,可以給全村人帶回幾車糧食,結果卻造成了全村人慘死。馬大三一生都在與現實妥協,他的這種自我存在是一種痛苦與焦慮,但當他看到全村人死在日本人手下時,他的主體意識得以激發,他做出了重要選擇——復仇,這是主體人的自為存在。
存在主義是講給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普通個人,它是普通個人用來尋求精神慰藉的良藥。《讓子彈飛》中小六子為了表明自己和張麻子一伙人的清白,不惜剖腹來證明。這種自殺式的行為,實質上也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尋找一種希望,一種解脫,他的行為是自己內心的言說,在他的心中只有這種行為能帶來證明自己清白的希望,作為民國中的一個普通小人物,他的存在在某種層面上就形成了抱有希望的存在者,而存在主義的意念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小六子身上。《讓子彈飛》在展現了張麻子的英雄主義情結之后卻以一種悵然若失的孤獨結尾,人在得到了一切之后卻反而更加空虛,這也符合我們現代人的精神困惑,正如薩特所謂的:人是孤獨的,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質的一種產物。
薩特認為,人在自由選擇之后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因逞一時英雄而把別人打成重傷,這是他的自由選擇,而面對的結果就是引發了兩個幫派打群架;《鬼子來了》中馬大三在自由選擇復仇之后,他所面對的后果是被砍頭,當他的頭顱落地之后,他看到了一個紅色的世界,而這個世界是一種原始的人性和生命的世界,這個責任不僅僅是馬大三去承擔的,也是導演警惕所有的觀眾去承擔的,我們應清晰的審視歷史;《太陽照常升起》小隊長迷戀上了唐嬸,并在不顧一切的自由選擇下和唐嬸偷情,結果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讓子彈飛》中黃四郎以一方霸主的身份與張麻子處處作對,企圖把張麻子趕出鵝城,但最后,黃四郎為此犧牲了五代家業,也毀掉了自己。
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薩特認為“他人就是地獄”,薩特在他的《存在與虛無》中提到:“一旦我存在著,事實上我就給他人的自由設置了一個界限,我是這個界限。”[4]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在幻想中拿酒瓶對劉憶苦大打出手的原因就是米蘭,在馬小軍眼中劉憶苦是他的情敵,對他構成了威脅,而他把自己從他人的地獄中解救出來的辦法就是將他打敗。由此可以看到我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就對他人——劉憶苦產生了界限與限定,同樣劉憶苦的存在對我也產生了限定與界限,這是存在主義中的“他人就是地獄”在影片中較為明顯的顯現。
《鬼子來了》中我與他人的身份顯而易見,但“我”作為愚昧、樸實的村民,并沒有對侵入我的界限的“他人”提高警惕,反而抱著一種天真的態度與想法,直到村民們因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才激起了內心的自為存在意識,開始反抗。影片以他人的存在致使村民死亡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關系,把存在主義中他人就是地獄的內在引申含義拋出,引發觀眾的警惕心理,而這種警惕不僅僅是針對日本人,更是針對我們自身,警惕我們自身的僥幸心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影片的讀解產生更多層次的意蘊,并使得影片具有哲學意蘊。
《讓子彈飛》中,黃四郎、張麻子和馬邦德三人在鵝城各自有自己的主體意識,他們有各自的追求,這時的他們是“面對別人在場時的自為與自在的關系”,由于對方對自己自為存在的影響和制約,致使這種自為存在的存在需求就有了一定的內心恐懼,于是他們通過自由的選擇,在人與人的存在中轉換主客體關系,“我們”與他人生活在同一世界里,擁有相對意義的他人,讓異于自己的人進入自己的世界,“他人”亦以同樣的方式把“我”化入他的世界。沖突是存在主義中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義,這也是張麻子與黃四郎之間的關系,他們都企圖作用于對方,這種“占有”性導致了二人之間矛盾的步步上升。同時在這種個人與他人的矛盾沖突中,還蘊含著對自我身份的尋找,張麻子對付黃四郎的過程就是對自己身份的尋找與認同過程,他在這一過程中找到了自己內心維護正義的人道主義思想。
姜文通過影像傳達了存在主義的觀念,以主人公們自我選擇、勇于行動,在行動中塑造自己,從而實現理想的行為展現了存在主義的價值。通過用存在主義的哲學觀解讀姜文導演的作品,使得他的電影不僅透過影像給受眾傳達了一個獨特的空間世界,更加提升了影片的內在張力與引申義。把存在主義的觀點運用到電影中,將自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滲透進人物設置中,同時把“人的自由選擇”以及“他人就是地獄”的存在主義價值體系融入影片的情節結構中,使影像具有濃厚的思辨精神,提升了電影的哲學內涵。
結語
姜文作為導演,從之前的叛逆到現在的逐漸性回歸,在一部部電影中真正認知了電影敘事的規律,開始尊重一般現實邏輯的存在,他從內容叛逆到敘事結構叛逆、敘事規律顛覆,再到現在符合敘事規律創作的回歸,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進步。姜文的這種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姜文人格類型的不斷完善與成長,他的思想意識開始從叛逆的心態中走出來,并逐步成熟。人格類型的健全,思想認知的成熟,情感體驗的豐富,普世價值的領悟都在一步步的影響姜文電影藝術的創作,對他今后的創作將有深遠積極的影響。
注釋
[1]【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學》九州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419頁
[2][3][4]【法】薩特《存在與虛無》,三聯書店,2007年11月第3版,第37頁、第38頁、第500頁
【1】【法】薩特《存在與虛無》,三聯書店,2007年11月第3版
【2】《姜文:我一直說我是個業余導演》,《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
【3】【法】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4】《姜文:它是我心中的太陽》,《大眾電影》,2007年第18期
【5】【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學》九州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6】【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人生哲學》九州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