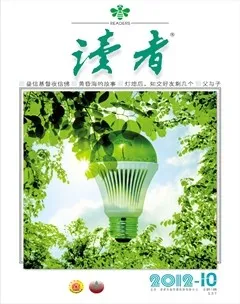不悲戚的凋零
琴臺

終于看了那部電影《桃姐》。提前備了紙巾,等著淚如泉涌,可是,直到片尾曲響起,眼睛還是干干的。沒有眼淚,只有無盡的悲涼。
當桃姐在老人院逼仄的小房間中窸窸窣窣地收拾衣物時,當桃姐艱難地拄著拐杖在骯臟的洗手間外徘徊不前時,某個瞬間,我看到了更多衰老的和即將衰老的背影在桃姐身上疊加,一層又一層,滿是負累和沉重。
60歲的葉德嫻說,她在桃姐身上找到了自己。
這話,乍一聽有點匪夷所思。一個是衣食無憂的女演員,一個是寄人籬下的老女傭,她們怎么會有交集?在柴靜的訪談《看見》中,我看到春華不再的葉德嫻一個人在空曠的房間中,寂寞地同一只貓咪說話,間或定定地翻開兒子幼年時的相冊,輕輕感喟:“一生人只一個,血脈跳得那樣近,而相處如同陌生,闊別卻又覺得親……”那一刻,你又會無比清晰地感知到,熒幕上下的這兩個相距千里的老女人,分明有著同樣的靈魂——孤獨、寂寥、無傍無依。
而這樣的靈魂,在我們身邊俯拾皆是。
樓下過道里曾寄居著一個阿姨,無兒無女無積蓄,60歲的時候老伴去世,經人撮合嫁給了另外一個老頭。誰都知道,阿姨的再嫁是為了重新找一個飯碗,新老伴無疑是有這個能力的——離休干部,兒女俱在外地。而他遇到樸素勤勞的阿姨,無疑是遇到一個再合適不過的保姆。阿姨也的確恪盡職守,10年中,不顧體弱年高,盡心竭力地操持家務,伺候老頭。后來老頭癱了,將近70歲的阿姨,一個人竟然可以將他從輪椅上抱上抱下。老頭無疑是感動的,多次表示要對阿姨負責到底。怎奈世事無常,最終,老頭還是先走了。久不出現的兒女們從天而降,極利索地辦理了父親的喪事,然后,房門落鎖,將70歲的阿姨趕出了家門。
無處可去的阿姨,只能在樓下的過道里簡單地用布簾圍出一方小天地,艱難度日。因為自知給樓上的居民添了麻煩,她很少出現在眾人的視野中,除了偶爾晴朗的天日。那樣的時候她總會穿著黑黢黢的外套寂然坐在角落里,面無表情,木雕泥塑一般。白花花的頭發和傴僂的后背上,寫著碩大的兩個字:絕望。
面對這可憐的暮年,眾人皆感慨欷歔卻又無可奈何。令人欣慰的是,小區物業公司做了一件頂人道的好事,經過多方斡旋,最終將阿姨送進一家老人院。
我們去老人院看阿姨。她的房間狹窄,響晴的春日里,阿姨坐在一室陰冷中,但滿臉都是滿足的笑意:“這里很好了,很好了,吃得飽,睡得暖,實在是托了大伙兒的福氣。”
看著阿姨顫巍巍的笑,心頭的悲涼再次席卷而來。只不過,如今的悲涼不再關乎老無所依的凄清,而是瞬間體味到生之寂寥,讓人無法不悚然震驚。
老去,實在是人生中最最殘酷的事情。不止是芳華凋零、青春不再,更是面對偌大的世界,你忽然成了赤手空拳的俯首就擒者。老人的無助和幼兒極其相似,可他們的境遇卻有天壤之別。幼兒因為承載著眾多殷切的愛和希望而備受呵護,老人承受的更多不過是行將就木的絕望。
沒有未來,只有近在咫尺的終點,活著的唯一瑰麗,不過是回憶中那些燦爛的過往。更可怕的還有疾病、孤獨……正如所有人都喜歡新生兒的笑臉,幾乎所有人看到老去的親人,心頭多多少少都是悵然。而這又是誰都無法逃脫的現實。
紙媒上有組數據:北京老年人口比率已近15%,上海20年后老年人口預計超過500萬。中國目前正處于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階段進入老齡化”的階段。
社會進入老齡化,銀發晚年的生命狀態幾乎成為每個家庭都必然面臨的問題。
就如同所有幼兒都喜歡媽媽的懷抱,這世上怕也沒有哪個老人不渴望子女承歡膝下的圓滿。然而,現實的拘囿同樣不容忽視:兩代人之間頻發的糾葛和矛盾、生活習慣的不兼容和個性差異,終究造成了孝心和“圍城”的沖突,以及親情對愛情的圍剿。
人類的規律,向來是自上而下的垂愛毫無保留,由下而上的盡孝則淺嘗輒止。所以,羔羊跪乳、烏鴉反哺,更多時候不過是廟堂之上的說辭。將年老的幸福筑建在孩子身上,這本身就有著緣木求魚的危險。
《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報告記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狀況:中國有近半老人處于獨居狀態,其中3000萬需長期護理而不得。
子女不恭之外,那些年老的生命亦有著讓人不堪承受的重負:工作退了,奮斗停了,老胳膊老腿的世界里,除了兒女,再也找不到別的著眼點。所以,難免有一哄而上的熱情,難免有鋪天蓋地的癡纏。可兒女們正當盛年,有事業要忙,有房子要掙,有愛情要經營,有兒女要教育……面對觀念不同、狀態不佳的父母,他們難免不勝其累。
不勝其累后,大多數人的選擇是逃離。
獨居,或者入老人院,便成為衰老的最終窠臼。
于是,我們輕易便可看到,更多的桃姐和葉德嫻。
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孤獨對于老人,是天生的痼疾,無藥可醫。
當子女無法成為衰老的救贖時,怎么辦?
影星李亞鵬媽媽的經歷或許值得更多老人借鑒。
李爸過世后,李媽將兒子當成唯一的支柱。盛名之下的李亞鵬卻沒有那么多時間來陪護母親,不得已,他只能用失望一次次讓媽媽自我清醒。對于一般老太太而言,指定要大罵兒子不孝,可李媽的選擇是,失望過后另辟蹊徑,尋找自己的幸福——她用了一年時間跳街舞、練瑜伽、寫書法,生生讓已經癟下去的日子再次充實起來,自己容光煥發,也重新贏得了兒子的尊重。
重生的幸福里依然有孤獨的影子,但烏云卻再也籠罩不了生命的蒼穹。
其實仔細想想,無論哪個階段,人都不可能逃離孤獨的如影隨形。無論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還是羈旅異鄉的中年,孤獨的宿命都像追逐花香的蜂蝶那樣追逐著每一個人的靈魂。年輕時,我們用充實的忙碌來對抗與抵擋,當年已垂垂,雙手空空時,何以對峙!
世上有這樣一些老人,用自己的行動,給出了答案。
畢加索85歲那年激情飛揚,一年之內就創作了165幅畫作;巴甫洛夫80歲時提出了大腦皮質反射學說;陸游85歲時寫出的《示兒》流傳千古;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理論時,已經70多歲。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是太多暮年英雄的自問。對于庸常大眾來說,這種詰問或許過于高蹈。但老而有為,哪怕只是強弩之末的掙扎,卻亦有著以一當十、雖敗猶榮的豪情。
動物界有一個傳說,所有大象都會在辭世之前的15天內,去一個神秘的地方,就是大象的公共墓地。哪怕它從沒有到過那個地方,但當最后15天來臨的時候,它還是會很準確地找到自己的歸宿。
人類沒有這15天的幸運與從容,但縱然不知歸期為何期,卻亦不妨礙我們從內心深處真正接受那份坦然——坦然的孤寂,坦然的宿命,坦然的清冷。就如桃姐執拗地選擇在老人院終老,又如葉德嫻所堅持的滿目寂寥的一個人的生活。這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女人,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證明了一個真理——老而無力是無奈,但只要保住尊嚴,躑躅獨行的寂寥中,亦可有仰望星空的驕傲與從容。
生如春花之爛漫,死如秋葉之靜美,乃人生兩大極致。而在生與死的旅程末梢,我想所有人都更愿意看到,所有的凋零不悲戚、不絕望,哪怕遺世獨立,滿目洪荒。正因為認清了靈魂的本質,所以,不卑微,不乞憐,亦不苛求,只向隅微笑,看一朵朵落花化為春泥,溫暖根下那小小的一方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