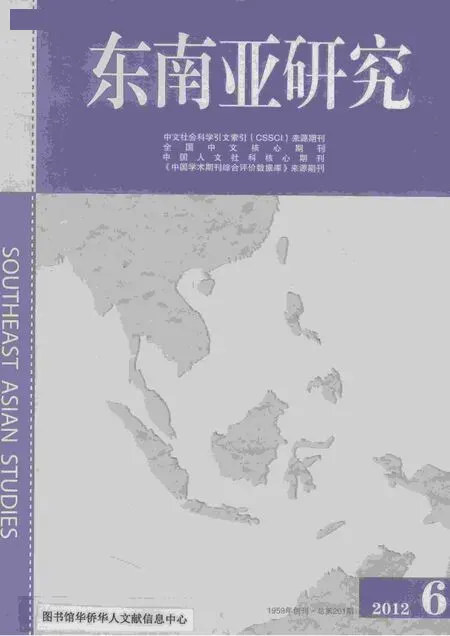認識大國:中國與日本在東南亞的軟實力比較研究
周玉淵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北京100871)
前言
在20世紀80年代末軟實力的概念提出后至今的20幾年間,軟實力的指涉對象、時代背景和工具性,以及相應的理論和研究范式都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冷戰結束后,國際多邊力量格局以及多層次國際權力分工的形成為軟權力概念的普及推廣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軟實力不再僅僅是美國維護霸權的工具,更多的國家開始借鑒并將軟實力視為是拓展地區或國際影響力的戰略工具。軟實力的戰略轉向構成了當前國際行為體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更強調軟實力的戰略功能和工具性,更期待通過軟實力的建設來吸引乃至影響其他行為體的行為。從這種意義上理解,軟實力以及軟實力戰略實際上是對國家或其他國際行為體非強制性權力的一個概括性界定,它本身并沒有改變國際政治的現實,相反,對軟實力的重視是新的國際政治環境的產物。在后軍權時代,文化的向心力、價值觀認同力、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觀念和創新能力成為國家間軟實力競爭的主要內容。
中國與日本兩國的國力競爭一直以來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和學術課題,在軟實力的話語體系下,中日兩國的軟實力比較和競爭也逐漸受到政策制定部門和研究人員的重視。在目前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地區權力結構體系中,感召力和吸引力更強的一方無疑會具有更大的優勢。當前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結構中的地位本質上是由其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實力決定的,而軟實力則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視為或者被學界解讀為中日雙方鞏固和提高各自結構性權力的重要手段[1]。事實上,軟實力戰略所指涉的內容一直是中日雙方東亞戰略的重要內容,例如在反殖民獨立戰爭時期,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三世界的政策概念,以及后來的睦鄰友好政策,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援助以及在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共同體等上的政策倡議和觀念輸出。然而,當軟實力成為一個時髦詞匯后,學術界對軟實力的研究出現泛化和濫用的現象[2]。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這導致對軟實力的研究缺乏說服力;第二個問題則是重視軟實力施動者的戰略研究,而相當程度忽視了軟實力受眾的研究。
當前的中日軟實力研究中仍存在這樣的問題:受眾國如何認識中日兩國的軟實力?中日兩國的軟實力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影響著受眾國的認識和行為?本質上,軟實力的強弱是由受眾國決定的。一國即使制定了非常詳細和宏大的軟實力戰略,如果其他國家并不認可也不愿進行有效回應的話,那么其軟實力或者感召力仍是非常小的。為此,本研究將以東南亞國家為案例來比較分析中日兩國的軟實力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通過對軟實力的要素分類進行可操作性指標設定來分析中日兩國在軟實力建設上的比較優勢。
一 檢驗軟實力:受力國的認識和回應
20世紀80年代末,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自此,軟實力開始成為學術界新的研究話題。根據奈的界定,軟實力指通過吸引而非強迫他人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國家軟實力的主要來源有: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3]。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一是軟實力本身到底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如沃爾茲和保羅·肯尼迪等對軟實力影響力和有效性的質疑[4];二是軟實力的來源,即到底哪些資源可以被界定為軟實力的來源,這本質上又決定了軟實力的概念界定問題。在中國,軟實力不僅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時髦話語,而且也開始成為中國政府的官方詞匯[5]。
(一)中國軟實力研究現狀
軟實力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僅中國學術期刊網收錄的文章就高達700多篇。國內學者對軟實力的概念、內涵、重要性、建設路徑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和界定,在研究范式上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閻學通認為,國家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內部和外部的政治動員能力,是一個國家對物質實力資源的使用能力,而不是物質資源本身[6]。蘇長和認為,國家軟實力是指在國家交往中因為知識、溝通、信息等因素而產生的彼此關系中的影響與被影響、支配與依附的狀態[7]。其他學者也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進行了相應的界定,這里不一一列舉①具體可參見胡鍵:《軟實力新論:構成、功能和發展規律》,《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黃金輝、丁忠毅:《中國國家軟實力研究述評》,《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閻學通、徐進:《中美軟實力》,《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期。。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軟實力來源的模糊性,雖然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被認為是軟實力的主要來源,但是其本質上又依附于國家的硬實力,即使奈也認為,能夠產生吸引力的資源,包括軍事、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等,都可以視為是軟實力的來源。也就是說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硬實力的軟化處理可以發展成為軟實力。
當前國內學術界對中國軟實力的研究主要在軟實力的建設路徑上,力求為中國軟實力水平的快速提升提供理論資源[8]。中國軟實力的研究更多的是一個政策命題,軟實力建設被視為是服務中國對外戰略、國家和平發展,以及樹立國際形象、構建和諧世界等方面的一項重要內容①如李杰:《軟實力建設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1期;俞新天:《軟實力建設與中國對外戰略》,《國際問題研究》2008年第2期;郭樹勇:《新國際主義與中國軟實力外交》,《國際觀察》2007年第2期;宋效峰:《試析中國和平崛起中的軟權力因素》,《求是》2005年8月;李捷:《提升軟權力對實現我國和平崛起戰略的作用》,《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12期;劉杰:《中國軟力量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時事出版社,2006年,第101-115頁。。在這種研究傾向的影響下,對中國軟實力的研究開始細化,具體到對中國軟實力重要性、軟實力的來源和要素、軟實力評估、軟實力外交和戰略、國際軟實力比較等問題的研究②如王逸舟:《中國外交的思考與前瞻》,《國際經濟評論》2008年第4期;王軍榮:《中國軟實力要素研究》,《經濟管理》2011年第Z1期;〈美〉貝茨·吉爾等著,陳正良、羅維譯《中國軟實力資源及其局限》,《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11期;〈韓〉《中國的軟實《力:討論、資源與前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4期;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下),《國際觀察》2007年第3、4期;20中07國觀念變革的戰略路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方長平:《中美軟實力比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年第7期;張永年、張弛:《國際政治中的軟力量以及對中國軟力量的觀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王京濱:《中日軟實力實證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在這些研究中,對中國軟實力要素的研究應該是最基礎但卻是最重要的研究內容,因為只有最大可能地理清中國軟實力的來源并能夠最大可能地進行要素和指標界定,才能更科學地對其進行評估,并提出相應的軟實力戰略,同時以此為基礎進行的軟實力比較才有說服力。大部分關于中國軟實力的著述基本上都對中國軟實力的來源和要素進行了界定,這些界定大同小異。如張永年等將中國軟實力要素界定為“中國模式”、多邊主義、經濟外交與睦鄰政策;閻學通等將其界定為國際吸引力、國際動員力和國內動員力[9];門洪華將其界定為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國際制度和國家形象[10];還有其他一些界定如意識形態影響力、制度安排上的影響力、外交事務中的影響力、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影響力、基本路線和發展戰略的執行力、國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創造力、文化的感召力等[11]。也有學者從系統和層次的角度將軟實力的要素界定為:主體、關系、資源、知識、目標、管理、能力和影響力[12]。
當前的研究相當程度上忽視了中國軟實力的實踐,更多的是一種單向的理解和闡釋,即中國應該怎么做,而缺乏受眾國認知的研究。一個基本的假定是,中國的軟實力在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程度大小是不一樣的,而且軟實力不同要素也存在著不均衡的現象。因此,缺乏對受眾國的差別化研究,而單純從中國自身角度對軟實力進行界定和評估難免會導致籠統和不清晰的結果。而從某種層面理解,一國的軟實力是否存在以及程度大小取決于受眾國的認知和反應,即軟權力來自于主體間關系的過程,“當受力者主動、自愿去尋求和接受某種力量時,這個力量往往體現出軟權力特征”[13]。
(二)主觀構建與他者認知:軟實力建設的兩種路徑
軟實力強調受力國的自愿行為,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一國軟實力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受力國的主動性。如果他國認同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等軟實力要素,并且這些要素在影響他國行為上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那么可以判定這一國家具有較大的軟實力;相反,雖然一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足夠強大,但是也有可能對他國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非常弱。與硬實力手段相比,通過運用軟實力,獲得他國認同,影響乃至改變他國行為可以降低成本。然而這畢竟是一種理想化的預期,在現實政治中,軟實力并不能獨立影響他國行為的改變,他國認知和行為的改變往往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軟實力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一國對外交往和為硬實力的應用提供文化、心理和政策互動的環境。而這一環境的優劣則取決于軟實力在受力國的社會化程度,受力國在軟實力認知和接受上的優先次序和程度差異則可以為一國軟實力的建設和改善提供相應的領域和方向。因此,他者認知可以作為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參考。
中國目前的軟實力建設主要是通過挖掘和開發現有的資源,包括文化、發展經驗、模式、外交思想和國際主張等。大多數研究和討論更強調軟實力的主觀構建性,認為國家的軟實力可以通過文化交流傳播、政策設計、項目或工程建設、公共產品供給等舉措來實現和提高。需要說明的是,軟實力與軟實力建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軟實力本身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軟實力建設或戰略則屬于政策范疇,具有明顯的主觀性。軟實力建設并不一定導致軟實力的提高,在一些情況下,脫離實際的軟實力建設可能會起到反作用。就此而言,中國的軟實力建設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充分考慮受力國的實際。
中國和日本是當今重要的地區性和國際性國家,在東亞地區都發揮著積極重要的作用。在東南亞國家,中日兩國軟實力的來源、產生影響的領域、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通過兩者的比較研究,可以更加明確中國軟實力建設存在的問題。通過東南亞國家對中日兩國軟實力認知的研究,可以發現中日兩國的軟實力影響該地區的優勢領域和欠缺之處。閻學通和徐進曾經提出一個衡量中美軟實力的模型,大致包括國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友好關系、國際國內動員力等六種指標。這一模型分析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例如事實上,很難將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同質性或相似性視為是中美兩國軟實力影響的表現,因為西歐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早于美國建立的,而且一些國家的民主制度是通過軍事干預后建立的,而與中國政治體制類似的國家確實是被中國所吸引還是迫于國際環境壓力不得不與中國建立“友誼”?很難說這是軟實力影響的結果[14]。但是,這一研究還是給軟實力的衡量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方法。鑒于這一研究對主體間關系的忽視,在本研究中,為了更好地理解東南亞國家對中日軟實力的認知,本研究將立足于受力國自身的需求和偏好,界定最能引起東南亞國家關注和興趣的領域:第一,對外政策。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對與軟實力受力國雙邊關系和發展方向的直接闡述,受力國能夠從對外政策中直接感受、認識并據此做出反應。第二,國家治理。國家治理涉及政治人權價值觀、發展模式、環境保護、民族政策以及社會管理等內容,主要是指政府在國家和社會建設上的作用和有效性。國家往往愿意向他國學習和借鑒適合自身實際的先進治理經驗,如中國向新加坡等國學習促進政府廉潔的經驗。這一過程包括獲取信息、國內形成共識或方向性意見、學習和借鑒等較長期的階段,因此對先進國家軟實力的認知并沒有那么直接。第三,文化。相比之下,文化的吸引力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各種文化要素的累積,但同時其影響力則會更加持久。
二 中日對外政策軟實力比較
冷戰結束后,中國和日本積極調整各自的東南亞政策,這對兩國在東南亞地區軟實力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是中國外交思想變化的重要動力。20世紀90年代,為應對“中國威脅論”,中國提出了“睦鄰政策”,“新安全觀”,以及后來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并最終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理念。在東南亞地區,中國積極踐行這一外交思想,中國是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國家,恪守《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首先提出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先于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制定了《全方位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在二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東南亞政策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賠償外交”、援助、貿易和投資加強與東南亞的聯系,但最初并沒有很大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反而由于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加劇了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反感。20世紀70年代末,福田主義的出臺正是為了緩和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反感情緒。20世紀90年代,日本在地區事務上的熱情開始提高,不斷提出新的倡議和設想,例如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東南亞時提出的“東亞發展倡議”、“全方位經濟伙伴”、“東亞共同體”等。近二十幾年來,中國的多邊主義參與使曾經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加深和政治安全互信的增強提高了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和國際形象,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東亞經濟快速發展中的領頭雁作用以及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承擔的國際責任使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地區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兩國的東南亞政策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相似性,例如重視多邊主義、參與而非取代東盟主導的地區合作框架、自由貿易區建設、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全面合作伙伴關系框架的建設等。然而,中日兩國的東南亞政策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例如在對東南亞的援助上,日本比中國更有經驗、援助體制更加合理先進。在經濟合作上,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互補性更強,在優化產業分布格局、促進技術轉移、帶動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差異構成了中日兩國在東南亞軟實力對比的重要依據。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CCGA)“亞洲軟實力”研究團隊從以下幾個問題對中日兩國對外政策的軟實力進行了對比:外交在解決問題上的有效性、對主權的尊重、建立互信和合作、人道主義援助、國際機制中的領導地位、推廣觀念和政策等。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都認為在亞洲外交軟實力最強的國家是日本,在印尼,中國與美國的軟實力指數持平,并列第二;而在越南,中國的軟實力則低于美國,在中、美、日、韓等四個國家中排名第三。印尼認為中日兩國的亞洲外交政策比美國更有效,而且更尊重他國的主權[15](參見表1)。另外,其他一些研究也基本得出類似的結論[16]。這類問卷統計主要是從民眾態度的角度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能完全反映兩國外交政策軟實力的對比,因為一方面,受訪民眾的樣本數量有限,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了解外交政策的途徑和程度受不同因素的制約,而且外交政策處于不斷變化中,這會導致民眾的態度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表1 中日等國外交軟實力對比
在政府層面,對外政策的軟實力主要體現在政策倡議以及對政策倡議的回應度上。從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就積極在地區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上提出倡議,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的建立與日本的倡議有著密切的關系①雖然東南亞國家一開始對這些倡議存在不同程度的懷疑和抵制,但結果是日本的倡議最終還是轉化為地區政策,盡管與日本的預期有所出入,但這表明日本在影響地區政策構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中國在地區事務上的倡議能力開始增強,中國首先提出與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倡議,這促使日本開始著手建立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湄公河區域是中日兩國軟實力競爭的一個代表性區域。1992年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倡議下,中國、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瀾滄江—湄公河沿岸6國共同發起次區域經濟合作 (GMS)機制,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以項目為主導。經過10多年的發展,大湄公河次區域已經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和東亞一體化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超過6%[17]。截至2010年底,大湄公河次區域成員國在交通、能源、電信、環境、農業、人力資源開發、旅游、貿易便利化與投資九大重點合作領域開展了227個合作項目,投入資金約140億美元[18]。2011年12月22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四次領導人會議通過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十年 (2012—2022)戰略框架》,為未來十年合作制定了三大戰略目標,即:推動次區域一體化進程,促進繁榮、公平的發展;在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上,為跨境貿易、投資、旅游等合作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關注自然環境和社會因素,促進次區域可持續發展[19]。2009年,日本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召開了第一次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與日本峰會 (Mekong-Japan Summit),之后每年舉行一次。2012年4月21日,第四次峰會在日本東京舉行,制定了《2012年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日本合作東京戰略》,取代了第一次峰會通過的《東京宣言》,并決定制定新的行動計劃,取代第一次峰會通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與日本63項行動計劃》。
通過這些機制和舉措,中日兩國分別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建立了全面的戰略合作框架,然而,兩國在合作倡議、形式、重點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也反映了兩國外交政策軟實力的差異。比較重要的四點差異是:第一,作為大湄公河次區域重要一員的中國大部分情況下扮演的是參與者的角色,主動倡議較少。而日本則在次區域開發上積極提供新倡議,如湄公河區域—日本經濟與產業合作倡議 (MJ-CI)、東盟—日本災害管理網絡倡議 (ASEAN Disaster Management Network)、綠色湄公河區域十年倡議(“A Decade toward the Green Mekong”Initiative)等。第二,中國重視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而日本則是硬件和軟件并重。中國與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的合作主要以工程和項目為依托,而日本則積極為區域國家提供新的發展理念和戰略支持,如根據《2012年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日本合作東京戰略》,日本支持該區域國家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結構,在每個國家以及整個次區域制定產業發展戰略。第三,中國重視官方合作,而日本在官方合作外,更重視人的尊嚴、安全和發展。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與日本峰會將人的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發展作為雙方合作的重要支柱之一,具體的舉措包括:與相關組織和機構進行合作,提高水資源管理、水電項目影響評估等方面的能力,分享低碳經濟增長經驗等。在人的安全上,雙方已經合作挽救了14.2萬兒童和1.2萬母親的生命,避免2萬人因為艾滋病、1.6萬人由于結核病以及5.5萬人由于瘧疾而死亡。第四,中國重視公有部門間的合作,而日本則大力推動公私之間的合作。私有企業被視為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與中國不同,日本大力支持和推動次區域私有行業的發展,通過培育和發展公私伙伴項目,完善公私部門合作框架、人力資源培訓等形式,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日本的這些舉措能夠較大程度地惠及更多民眾,這無疑會增強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感謝日本自2009年第一次峰會以來對行動計劃承諾的有力執行,我們堅信日本是一個長久的、可以信賴的而且必不可少的伙伴。我們期望日本能夠在地區發展繁榮的協調合作上發揮領導作用,我們歡迎日本維持其在該地區的重大利益。”[20]
三 中日國家治理軟實力比較
國家治理包括政治體制、發展模式、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內容,是一國內源性吸引力和軟實力的集合。這些內容之間相輔相成,或許用短板理論理解,國家治理的軟實力本質上是由其中最弱的一環決定的。在實際操作中,拋開較弱的一環而空談其他軟實力顯得毫無意義。中日兩國國家治理的發展階段不同,有各自的優勢,更有各自的劣勢,提升國家治理軟實力的過程就是修復弱勢環節的過程。

表2 中日國家治理軟實力對比
當前關于中國國家治理軟實力的討論主要集中于發展模式,即所謂的“北京共識”。發展模式被視為是衡量中國軟實力的主要標準,然而,“北京共識”的吸引力到底如何?學界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且更多的討論仍集中于“北京共識”本身①在此,筆者并無意繼續探討“北京共識”的本質,而是借用這一已被格式化的界定來代指中國的 (政治)經濟發展模式。。CCGA對中美日韓四國的經濟軟實力、政治軟實力和人力資本軟實力進行了問卷統計,根據其分析結果,在不同國家,中國經濟的軟實力排名第三到第二位,而在越南和印尼,排名第一的都是日本;中國政治軟實力的排名則全部是第三,而美國和印尼認為亞洲政治軟實力最強的是日本;在人力資本軟實力上,中國排名從第二到第四位不等,而日本則是第一、二位。政治、經濟和人力資本都可歸為國家治理的范疇,因此,根據這一結果,我們簡單地判定日本在國家治理上的軟實力是高于中國的。那么中國近年來快速的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有研究人員通過問卷調查對中國發展模式進行了研究,這一研究也得出了與CCGA類似的結果。該研究認為,盡管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獲得了巨大的提升,但是中國模式對亞洲國家并沒有產生很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說影響力的提高與軟實力的提升并不具有必然聯系,而且和中國關系密切與偏好中國模式之間也并不存在必然聯系。同時在美國、日本、中國以及本國模式的對比上,傾向于美國和日本發展模式的比例遠遠高于中國[21]。
上述研究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發展模式并不能單獨促進軟實力的提高,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國家內源性軟實力是由多領域構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現有的問卷研究總體都認為,民主和人權價值觀是中國國家治理軟實力落后于日本的重要原因。而事實上,這又與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等問題密切相關,共同構成了國家治理軟實力和合理性的基礎,這也是中國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如果發展能夠兼顧社會的和諧、公平、公正,能夠兼顧環境保護和發展的可持續性,這種發展模式將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相反,其中任何一個出現問題的話,都將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的軟實力,甚至帶來致命的后果。具體而言,其一,政治制度是根本,它決定著政府的社會與環境政策、管理效能以及發展模式的形成,決定著國家軟實力的廣度;其二,社會管理是關鍵,它需要合理協調發展與人之間的關系,發展最終是人的發展,如果與此違背,其吸引力注定有限;其三,環境保護是標尺,它關系到發展的可持續性、人的生存乃至發展模式的合法性。由此可見,國家治理軟實力的比拼不是某一優勢領域上的比拼,如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在克服劣勢領域上的比拼。這恰恰是中國國家治理軟實力落后于日本的重要原因。
四 中日文化軟實力比較
中國是文明古國,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使中國在當今的國際聯系中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代表性國家,其現代化的文化產業和文化理念在東亞地區乃至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國文化的延續是自然累積和提煉的過程,但是,文化上升到軟實力的高度更多地又是一個政策問題,文化軟實力反映了國家在利用自身文化增強外部認同和促進對外交往上的能力。中日兩國的這種能力存在著較大差異,也存在可以相互借鑒的空間。
歷史上,中國文化從物質、制度和精神等不同方面對東南亞國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2],而這又對當今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產生持續的影響[23]。CCGA的研究也證明了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巨大影響力。研究發現,所有受訪國家 (不僅包括越南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大部分民眾認為中國具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對應指標從7.8到8.6不等 (最高值為10)。然而,這一豐富的文化遺產并沒有有效地轉化為中國的軟實力,或者即常說的中國是文化大國,但不是文化強國。具體表現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吸引力相對很小,一個重要指標是中國文化產品,如影視、書籍等的輸出情況,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國家對應指標為5.5到6.4(除了越南為8.2)[24]。從這一結果可以看出,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文化影響的看法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以越南為代表的陸地東南亞國家相對于以印尼為代表的海洋東南亞國家更認可中國文化。然而,盡管存在差異,在相關的各種指標上,包括流行文化的吸引力、文化遺產豐富程度、國際旅游目的地等,越南和印尼兩國對中國文化的正面認識都高于對日本的認識。也就是說,至少在東南亞國家看來,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是高于日本的。

表3 中日等國文化軟實力對比
上述研究主要是對中國與日本文化吸引力的評估,并沒有對將文化遺產轉化為軟實力的能力進行評估,因此,這并不能呈現中日兩國文化軟實力的全貌。將文化遺產轉化為軟實力的其中一個方面是文化外交或文化政策的范疇,如中國在其他國家建立孔子學院、舉辦中國文化年活動等,日本提出的以日本動漫等流行文化為主題的文化外交戰略等。中日兩國都將文化外交上升到國家整體外交戰略的高度,文化外交在促進國家間關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日兩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在文化外交上的比較優勢決定了兩國文化外交形式和內容的不同。比較而言,當前的中日文化外交有以下幾點差異:第一,中國的文化外交主要由政府主導和包辦,項目鋪得很大,民眾真正自發參與的很少,而日本則是政府主要扮演政策設計者、引導者和資助者的角色,具體項目由企業、民間組織或半官方組織等去操作。第二,中國文化外交的形式相對單一,人們談起中國的文化外交,往往指的是孔子學院、教育合作、中國文化年、文藝匯演交流等基本形式,而日本則將在文化上做出國際貢獻及傳播文化作為日本文化外交的總體戰略目標,致力于構建多層次的文化外交體系[25]。第三,中國的文化產業輸出相對落后,而日本的文化產業輸出在東亞乃至世界范圍內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是文化硬件和器材的生產大國,但是在軟件尤其是凝聚中華文化的產品生產上仍然落后,一些研究將中國電影、戲曲等文化產業輸出落后的原因歸因于語言問題[26]。第四,中國在國際聯合學術研究,尤其是在國外進行長期調研和研究上的重視程度不夠,而日本已經將此作為文化戰略的重要內容。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海外研究隊伍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精英能夠將本國先進的理念、技術和精神帶給所在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知識精英能夠扮演“文化傳教士”的角色。在遙遠的非洲大陸,經常能夠看到日本研究者的身影,他們一呆就是數年甚至更久①中國學者在非洲國家進行調研時多次遇到過長期駐扎在非洲的日本研究人員,他們從事人類學、農學、地理學等不同的研究。。中國近些年來已經開始對此有所重視,如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提出的中非聯合研究交流計劃,開始為學者海外研究提供資助,然而,在實踐中,這還需要不斷地完善,從而能夠形成長期的機制。
相對于日本,中國在文化軟實力上具有更大的優勢,然而如何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國家的軟實力是中日兩國面臨的共同問題。中日兩國在文化外交的實踐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經驗上可以彼此借鑒和分享。同時,兩國的文化外交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問題,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文化外交的目的與結果之間的差距。在很多情況下,文化外交所預期的結果與目的之間會存在著時間差,而且結果并不僅僅只是來自文化外交的作用,而是涉及政治、經濟和國際形勢變化等多種因素②如有學者通過日本在菲律賓文化外交的案例發現,日本在20 世紀70 年代制定的以消除菲律賓國家對日本不滿情緒為目的的文化外交戰略并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到了80 年代,當日本流行文化如漫畫、動漫、卡拉OK 等開始傳播時,越來越多的菲律賓人開始了解并羨慕日本的成就和文化,菲律賓民眾對日本的態度也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參見Lydia N. Yu Jose,“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An Assessment”,G - SEC Working Paper,No. 11,December,2006.。這就需要國家在開展文化外交時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制定相應的文化策略。
結論
一國軟實力的大小是由受力國的態度和反應決定的。當前的研究并沒有就軟實力的概念和要素形成有說服力的定論和模型,根據研究需要,筆者將軟實力的來源界定為:對外政策、國家治理和文化。對外政策軟實力來自于對外政策的有效性,國家治理軟實力來自于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等綜合治理能力,文化軟實力來自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和文化外交的合理性。
根據這一界定,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水平是不均衡的,通過借用已有的統計數據,并結合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國家的軟實力案例,本研究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在東南亞地區,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強于日本,然而,中國對外政策和國家治理的軟實力則不如日本。具體而言,東南亞國家認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有效性和地區發展合作上的領導能力不如日本;在國家治理上,中國的發展模式并沒有引起東南亞國家多大的興趣,相反國家治理中的弱勢環節,如政治制度和環境保護及發展可持續性等往往成為決定中國國家治理軟實力的短板;在文化軟實力上,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獨特優勢,然而,中國將文化轉化為軟實力上的能力還存在不足,日本在這方面的一些成功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總體而言,很難明確界定軟實力影響他國行為的程度,相比之下,對比國家間的軟實力大小則相對容易。軟實力可以視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通過中日兩國之間軟實力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軟實力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而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將最終決定著中國軟實力乃至整體實力的發展水平。
【注 釋】
[1]H.H.Michael Hsiao and Alan Yang,“Soft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Chinese and Japanese Quests for Regional Leadership”,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8-2-09,February 17,2009.
[2]萬君寶:《論軟實力的基本理論模型與中國軟實力的最新發展態勢——基于國外學者的研究視角》,《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黃金輝、丁忠毅:《中國國家軟實力研究述評》,《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3]可參見〈美〉約瑟夫·奈著,吳曉輝、錢城譯《軟力量:世界政壇政工之道》,東方出版社,2005年;約瑟夫·奈、王緝思:《中國軟實力的興起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6期;Joseph S.Nye JR.,“Think Again: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ebruary 23,2006,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
[4]Paul.Kennedy,“Soft Power is on the up.But it can Always be outmuscled”,The Guardian,November 18,2008,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nov/18/usa-obama-economy-military.
[5]約瑟夫·奈、王緝思:《中國軟實力的興起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6期。
[6][14]閻學通:《中國的軟實力有待提高》,《中國與世界觀察》2006年第1期。
[7]蘇長和:《中國的軟權力——以國際制度與中國的關系為例》,《國際觀察》2007年第2期。
[8]黃金輝、丁忠毅: 《中國國家軟實力研究述評》,《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9]閻學通、徐進:《中美軟實力比較》,《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期。
[10]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國際觀察》2007年第3期。
[11]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軟實力在中國的實踐之二——國家軟實力》,中國軟實力研究院網站,http://civiledu.cn/yj/ShowArticle.asp?ArticleID=898,2012年6月4日。
[12]王軍榮:《中國軟實力要素研究》,《經濟管理》2011年第Z1期。
[13]張永年、張弛:《國際政治中的軟力量以及對中國軟力量的觀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
[15]Christopher B.Whitney,David Shambaugh,Soft Power in Asia:Resut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9,p.35.
[16]Zhengxu Wang,Ying Zhang,“Is China's Soft Power Dominating Southeast Asia?Views From the Citizens”,Briefing Series-Issue 44,China Policy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008;Jiakun Jack Zhang,“See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Asia:An Empirical Test of Soft Power”,Duke University,2011,http://dukespace.lib.duke.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16 1/5383/Duke%20Honors%20Thesis.pdf?sequence=1
[17]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國使館經濟通商處:《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簡況》,2011/11/17,http://th.mofcom.gov.cn/aarticle/haiguan/201111/20111107835380.html
[18]《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04/content_617370.htm
[19]中國在該區域合作的參與可參閱《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j/t419061.htm
[20]“Mekong-Japan Action Plan 63”,November 7,2009,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911/action.html;“Action Plan for‘A Decade toward the Green Mekong’Initiative”,October 29,2010,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2/gm10_iap_en.html;“Tokyo Strategy 2012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April 21,2012,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4/joint_statement_en.html
[21]具體數據參見Jiakun Jack Zhang,See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Asia:An Empirical Test of Soft Power,Duke U-niversity,2011,p.65。
[22]可參見賀圣達《中國古代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思想戰線》1992年第5期。
[23]有學者認為當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系受到了歷史和文化的深刻影響,表現在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可能給予中國想要的東西——適當尊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認可中國的利益——來換取中國不干涉它們的內政和建立公平的貿易關系。可參見〈澳〉馬丁·斯圖爾特·福克斯《東南亞和中國:歷史和文化對形成未來關系所起的作用》,《南洋資料譯叢》2005年第1期。
[24]Christopher B.Whitney,David Shambaugh,Soft Power in Asia:Resut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9,pp.15-17.
[25]具體內容可參見朱威烈主編《國際文化戰略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2-174頁。
[26]Christopher B.Whitney,David Shambaugh,Soft Power in Asia:Resut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9,pp.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