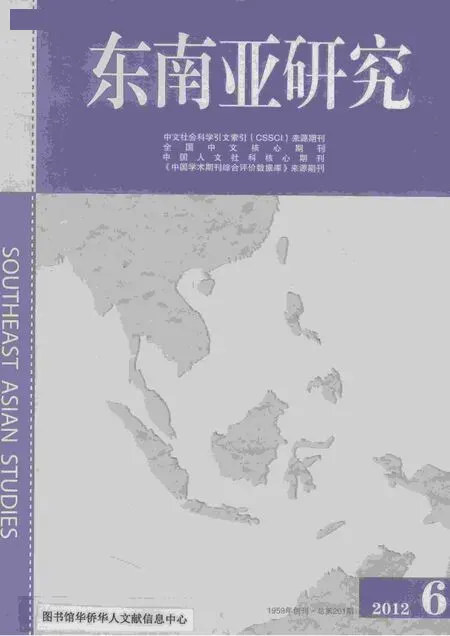想象的地方性神圣歷史*——菲律賓阿拉安人的神話觀
史 陽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語言文化系 北京100871)
對于“非西方”式傳統社會的“異文化”的關注,一直是兩百年來現代民俗學和人類學流行的學術主題,東南亞地區的原住民族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長期吸引著民俗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目光。21世紀的今天,在菲律賓僻遠山區和海島上,還有一些與現代社會文化交流有限、秉承傳統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土著居民,本文所涉及的阿拉安芒揚人(Alangan-Mangyan)就是其中之一。阿拉安人是菲律賓民都洛島山區中的原住民,筆者于2004年7月、2006年4月、2007年1-2月、2009年2月和2010年8月跋山涉水深入熱帶叢林,五次在該原住民中從事田野工作。在阿拉安人的諸多村社中,筆者搜集洪水神話、創世神話的異文①民俗學術語,“異文”指的是某一個具體的文本。,考察神話在原住民中的流傳形態和信仰方式,調查原住民關于神靈的各種信仰,以及與神話密切相關的占卜、神判、神諭和巫術等儀式。
一 阿拉安人的創世神話
阿拉安芒揚人在當今菲律賓官方民族劃分中是隸屬于芒揚 (Mangyan)民族的阿拉安部族,一般稱作阿拉安芒揚人或阿拉安人。芒揚人是世代居住在菲律賓中部民都洛島的原住民族,現有的民族劃分將其分為八個部族,阿拉安人是其中之一②為方便起見,下文討論田野資料時,出現的“芒揚 (洪水)神話”指稱的都是阿拉安人的神話,“芒揚人”也是指阿拉安人。這是因為阿拉安人通常自稱是“芒揚人”,“mangyan”一詞在阿拉安語中正是“人”的意思;而“阿拉安”是外界和民族學者對他們的稱呼,源自于該民族聚居地的阿拉安河,而阿拉安原住民并不用它作為對自己的稱呼。。阿拉安人是無文字民族,世代生活在民都洛島中北部的全島最高峰——哈爾空山 (Halcon)周圍廣袤的山地上,人口約一萬多人③關于阿拉安人詳細人口,各種機構提供的統計數據差別不小,沒有定說。這可能是因為阿拉安人的村社富有流動性,且散布在大片山區中,以及不同機構對于阿拉安族群的劃分、調查的細致程度上也有差異。有很多山地村社分布在非常偏僻、艱險的山區內陸,調查人員根本無法到達;有些村社的人因為害怕外來調查人員,在人口普查時逃離了村社,便沒有統計在內。所以綜合多方數據,參考當地教會組織的經驗數據,并結合筆者自己的田野經驗,估計現在阿拉安人的人口約有一萬多,不超過1.5萬人。。筆者在近20個阿拉安村社中,搜集了70多則洪水神話和創世神話的異文,這些異文在細節上雖有一些出入,但敘事的情節主線大都一致。為了便于討論,筆者選取卡里羅社報告人的文本并適當簡化和整理,作為阿拉安創世和洪水神話的代表文本:
在遙遠的過去,創世神靈安布奧 (Ambuao)創造了天空、大地、人類和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大地就像一個藤盤子,安布奧用手托舉著大地,地震、臺風、下雨、打雷、閃電等等自然現象都是他身體的動作造成的。世界有一個出水口,叫布魯旦(Bulutan),河流海洋里的水都會流到那里,再流到地下世界杜由安 (Tuyungan)當中。那時人們沒有生殖器官馬莫 (mamo),也不知道如何兩性交合,懷孕生育的方式是兩腿交叉相碰,小腿肚便不斷脹大,最后生出人來。那時的人們擁有神奇而強大的特殊能力——“命令能力”,可以命令各種工具自動勞作,所以人們不用自己干活就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天上和地上都有人,天空與大地的距離很近,在布卡亞干山 (Bukayagan)的山巔上,一個叫拉拉亞萬 (Laylayawan)的地方,那里有個竹質的天梯供人們上下。后來來了一個叫巴利亞溫(Balyawon)的人,他給人們裝上了馬莫,主動教人們怎樣使用馬莫進行兩性交合。有一對父女,去天上參加為豐收而舉行的阿格巴馬果 (agpamago)慶典,從天梯上下來在拉拉亞萬休息。女兒睡著了,父親則在一邊磨刀,女兒身下的馬莫就露了出來,父親受到了誘惑,于是他們兩性交合。這時突然電閃雷鳴,大地陷了下去,水從地下涌出,陷下的土地變成了一個湖,就是今天的卡迪布里用(Katibliyon)湖。天不斷往上升,天梯崩裂了,陷入湖水之中,今天湖水里還有根梯子樣子的竹子,正好露出水面一點點,有時能看見有時又看不見。父女倆變成了湖中的兩種魚,一種在胸部有白色的紋路,就像是女兒穿的抹胸,另一種在腰部有白色的紋路,就像父親穿的短褲。大水涌出后,河水不斷上漲,但是布魯旦被沖下來的大木頭堵住了,水流不出去,于是全世界都發起了大水,這場大水名叫布瑞瑞斯 (Pureres)。人和動物都往山上跑,有一對同胞兄妹爬上了布卡亞干山,幸存了下來。后來各來了一個青蛙、鰻魚和大蝦,它們到布魯旦把洞口里的木頭清理走了,洪水才退去。兄妹倆便結婚生子,這時人再也不能命令各種東西自己運作,必須下地干活了。而且人有了馬莫,全都開始兩性交合、在肚子里懷孕生孩子。這對兄妹倆生下來的幾個孩子分別成為了阿拉安人和其他民族的最早的祖先,還有的孩子成為幫助人的善靈,也有的成為危害人的惡靈④阿拉安—芒揚人是無文字民族,本文中出現的阿拉安詞匯系筆者根據菲律賓語語音規則和當地傳教士的習慣轉寫而成。。
上述文本首先是講萬事萬物的起源,然后發生了大洪水災難,最后是幸存者成為人類始祖,各民族、精靈分別起源。洪水是故事的核心,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神靈創世的那個時代充滿了各種神奇的事物,后來經歷了大洪水,很多事物都發生了變化,世界才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樣子。阿拉安人自己并不會把這段故事叫做“神話”,在當地這種故事有個特定稱謂——Pangisudēn。Pangisudēn 這個名詞來自于動詞gisud,gisud在阿拉安語中意為“回頭看”,pangisudēn即為“往回看到的東西”,比如某件過去發生的事情、某人以前的經歷,所以說Pangisudēn指的是“通過口頭講述的、具有歷史性質的、真實的故事”,它是阿拉安人民間敘事自然分類系統中的一個文類 (genre),體現了原住民在敘事時采取的心理態度和信實程度[1]。對于阿拉安人而言,這些故事講述了從世界的創生、經歷洪水災難再到現實世界的整個“歷史”,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是本民族關于遠古時代歷史記憶的“地方性知識”。
二 神話觀的理論問題
本文探討的是阿拉安人在洪水神話、創世神話中展現出的神話觀,即阿拉安人看待神話的心理和態度。神話研究不僅關注其文本內容本身,神話被信仰者講述的方式、神話所存在的語境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些文本之外的信息對于理解神話以及信仰神話的民族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早在馬林諾夫斯基對特羅布里恩德島的美拉尼西亞土著進行調查并發表經典論文《原始人的神話》(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時,學術界的研究就已從單純的內容分析走向在語境中進行解析,原住民的神話觀成為民俗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采集神話文本時,一方面要關注原住民信仰的具體內容——即神話傳說本身的情節,一方面也要重視這些信仰的形式——即原住民對這些神話的信實程度以及對各種信仰的看法和態度,也就是原住民的神話觀或信仰觀。馬氏提出,在土著自己的觀念中,神話被視為是真實、“崇敬而神圣”的,它給土著的各種儀式、禮數、巫術、魔法、道德、社會規則提供了“具體而有前例可援的故事”作為理論依據和歷史權威,解釋了它們從何而來、為何而來,于是人們崇敬和尊重這些古老故事揭示的準則,以其為標準在現實生活中施行這些儀式習俗和倫理道德[2]。
在馬氏所謂的科學、系統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式的田野作業方法的影響之下,原住民族信仰體系的多樣形式和豐富形態,與信仰的具體內容一樣,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民俗學者、人類學者的關注、重視和詳盡記錄,這反映在各種民族志材料中。今天,原住民族的神話和神話觀都被作為一種重要的“地方性知識”。不難理解,正如現代社會是用“科學知識”去思考、解釋和理解世界的,土著居民是使用“神話”去解釋和理解他們的世界的。“神話”對原住民族既是思考方式又是“知識”,但神話不是一般性的知識,而是一種特定的“地方性”知識。在文化研究領域,“地方性”是一個獨特的術語和概念,它源于60年代國際學術界興起并成為當今學界主導之一的解釋人類學,克利福德·格爾茨等人側重于符號、心理等層面,提出用“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一概念來描寫原住民族的文化形態。格爾茨強調,文化研究應該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的眼界”,去“創設一種與文化持有者文化狀況相吻合的確切的詮釋”;不僅要了解異文化中種種詞匯的具體意思——即對異文化進行語義上的一般性解釋,還要去理解異文化持有者的心靈——即文化持有者本人對于所持文化的認知和理解,文化研究是“解釋解釋的解釋”[3]。所以,研究和分析神話時,應該力圖還原神話在原住民中的本來面貌,而非學者去主觀想象;學者不僅要對神話的內容進行介紹和分析,還須對原住民自己對于神話的認知進行詮釋。在原住民諸多的地方性知識中,神話是極其核心的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原住民信仰體系的奠基與核心,因為它講述的是萬事萬物的起源和初始時期的變化。神話是“地方性”的,它包含了該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心理特質、具有民族特色的符號和特定的象征內涵,是該民族特定的文化認知,要想真正理解神話,就必須采取“地方性”的辦法,深入到原住民中觀察和思考,從原住民的心靈出發去理解這種“地方性”的知識,這正是本文采用的思路。
三 樸素而神圣的口頭歷史敘事——阿拉安人如何講述和看待神話
對于阿拉安人而言,神話是當地的一套關于神圣信仰的歷史敘事,原住民們用樸素的方式,通過口頭講述而世代相傳。筆者在訪談中,詢問報告人關于創世、洪水故事具體情節的同時,還會詢問報告人自己對于這些故事的看法。常見的回答包括:“這些是非常古老的故事”、“這全都是我們芒揚人的歷史”、“都是千真萬確的”、“不僅是我知道,這里村上的所有人全都知道,村里面每個人都可以講”。事實上,關于洪水的敘事被阿拉安人視為是民族歷史的一個片斷。阿拉安人的觀念中存在著一個穩固的關于歷史的觀念或集體記憶,人們相信自己的民族有著這么一段從古至今、連續未斷的歷史,這段歷史始于創世神靈創造了天地萬物,后來發生了大洪水,接著阿拉安人的祖先出現了,然后又經過一代代的發展變化直到現在,阿拉安人成為今天的樣子。本族中人與人的差異在于,各人對這段歷史記憶的清晰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人說起來頭頭是道,有的人稀里糊涂。
可見,在阿拉安人的觀念中,其實并不存在我們所謂的“神話”,更不用說洪水神話、創世神話等現代民俗學學術分類中的具體文類,存在的乃是“關于大洪水的一段真實歷史”。阿拉安人對于自己的“歷史”信以為真,并且代代口耳相傳,而大洪水正是這個“歷史”中的一個片斷,阿拉安人對于上古大洪水的信實基于他們對本民族“歷史”的信任。馬林諾夫斯基亦曾提出,在土著的社會中神話的地位非常獨特,神話“不是說一說的故事”,絕非“我們在近代小說中所見到的虛構”,而是被原住民認為是“在荒古的時候發生過的實事,而在那以后便繼續影響世界影響人類命運的”,它“活在土著們的道德中,制裁著他們的行為、支配著他們的信仰”[4]。阿拉安人關于安布奧神創世和布瑞瑞斯洪水災難的敘事對他們自己而言絕不是隨意的,他們相信正是這段歷史決定了今天的世界和自己民族的命運,即使這段歷史已經非常久遠,阿拉安人也絕不會忘記。而且,阿拉安人認為這種歷史不僅是被信實,還不可被挑戰。因為神話包含了眾多起源事件,解釋了當地的現實生活是如何變化而來的,所以人們必須相信。對神話的信實是對歷史的信實、對現實的肯定;反之,不相信神話,就是否定現實生活。于是,神話為現實生活提供了歷史和道德的權威,雖然這是一種想象出來的、帶有虛幻色彩的權威。
1.神話中的時間觀念
阿拉安人的時間與神話密切相關,阿拉安人關于時間的觀念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問題。阿拉安人的時間不是數字式的,而是事件式的,于是在這個基礎上,神話成為了阿拉安人的歷史,神話就是時間的開始,阿拉安人在神話的基礎之上構建了自己的時間觀念。阿拉安人衡量歷史所用的時間觀念,和我們現代社會中常見的以數字度量為基礎的時間觀念不一樣,阿拉安人的時間觀念是以事件為核心的。時間能夠成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概念,完全取決于存在著這些事件。因為這些事件的發生有先有后,于是才有了時間;這些事件按發生的先后順序形成了一個自古至今的序列,于是就有了歷史。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要從年月日的角度來確定報告人講述中的時間是一件很難的事。在阿拉安人眼中并沒有類似于現代社會中用數字所標定的時間,在他們的記憶中,只有一連串的事件,每當需要表述時間時,都使用所發生的事件來表示時間。比如阿拉安人會說,大洪水“布瑞瑞斯”發生的時候,安布奧神創造世界的時候,日本人來的時候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至1945年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民都洛島,原住民的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紛紛跑到深山中躲避戰亂,眾多阿拉安長1者95對4此都有深刻的記憶。,斯邦神父在巴伊旦做第一次彌撒的時候②年左右,天主教神父馬丁·斯邦來到阿拉安人領地傳教,從此部分阿拉安人逐漸開始皈依天主教、新教。等等。正如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哥特所指出的,在任何口述歷史中,日期是同事件聯系在一起的,他在馬來西亞吉蘭丹州進行田野調查時常遇到“日本人占領時期”、“我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這樣的時間表述[5]。在阿拉安社會中,中年以上的人通常既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無法說清自己年紀多大,更重要的是,具體而數字化的生日、年齡這些觀念對他們而言無關緊要。在我們現代社會中人們會說,“他已經60了,該退休了”,“他到3月就滿65,可以辦老年證免票了”,“90歲以上的老人醫療全部報銷”。在這些表述中,“年老”這個概念顯然是用一連串表示年齡的數字標定的。而阿拉安人如果要表示某個人是位老者,會說“他下面的牙都已經松了”,“他腿腳開始不好,不能再去旱田干活了,已經老了”,“年輕人可以爬上青檸檬樹采高處的果子,但他只能在樹底下采低處的或者撿掉下來的,因為他老了”,“吃飯時他第一個吃,因為他是這些人中最老的”。在阿拉安人的表述中,“年老”這個概念顯然與身體狀況發生變化的事件有關,而不是與抽象的數字有關。如果一個人牙齒仍沒有變松,還能在旱田里干活,也能敏捷地爬樹采青檸檬,吃飯的時候也輪不到他吃第一口,那么對阿拉安而言,并不能說明這個人是個老人。
筆者參考了波斯特馬對于哈努努沃芒揚人的時間表定法的總結[6],阿拉安人的時間表定法與之相似。阿拉安人用來界定時間的標志大致包括如下四類:(1)自然和歷史事件,比如地震、臺風、日食月食、日本人的戰爭、摩洛人侵襲。阿拉安人口中經常出現的時間界定詞就是“(日本人的)戰爭時我剛結婚”、“(民都洛島)大地震的時候我住在山上”、“第二次日食的時候我已經出生了”等等。(2)天文氣象,比如日出日落、月相圓缺、刮風等與天相、氣象有關的內容,這些在阿拉安人中通常用來表示每年周而復始舉行各種儀式、發生事件的時間,諸如“滿月的時候舉行 (某儀式)”。(3)人體的狀況,尤其是用來衡量童年和青少年時候的時間,比如身體發生的變化、學會走路、長了多高。阿拉安人會說“那時候我才剛會爬”、“那時候我已經有欄桿那么高,可以自己拿砍刀了”等。類似的,雷納多·羅薩爾多在研究菲律賓北部山地民族伊隆哥特人時發現,伊隆哥特人對于自己的年齡也是模糊的,最終報告人的年齡只能通過估計而得出。伊隆哥特人會說:“在日本人來的時候,我還太小都不能走路,都是我父親把我背在背上。”[7](4)自然界的變化,比如動物的行為、植物作物的長勢。阿拉安人會說“這時候旱田里長得正好”、“那頭豬下第二次仔的時候”等等。總之,原住民的時間“是以觀察自己身邊的自然界為基礎”,“單一或復合使用”各種標志時間的事物[8]。不同于很多少數民族直接擁有或者可以根據各種傳說構建出較為完整的祖先世系,很多阿拉安人只能追溯到自己的曾祖父,有些可以追溯到高祖父,而哈努努沃芒揚人也僅可以上溯五代[9]。從曾祖父、高祖父再往上,阿拉安人追溯的時間就是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口頭流傳中的各個事件。可見,阿拉安人的時間觀念是以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為基礎,然后一件件事情按發生的順序展開,從過去延伸至今,就是阿拉安人心目中所謂的歷史,而且這些能夠被阿拉安人記住的事件常會是有重要意義、影響很大的事情。所以在前文對阿拉安神話進行分析時,筆者發現他們的神話其實只是一個又一個事件按照一定順序先后排列,有很多事件前后沒有邏輯性,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也連在了一起,如果仔細追問,連報告人也無法解釋清楚,要是去深究其中某一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報告人往往給不出明確的答案,只是泛泛地說是“過去”、“很久以前”。比如筆者非常想問清楚巴利亞溫創造了兩性并教會人類性交到底是在什么時候——洪水之前還是之后,這件事與洪水有什么關系。結果詢問了多人,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到底是之前還是之后,“就是布瑞瑞斯發生的時候”,而且“無所謂是在布瑞瑞斯前還是后,不知道那具體是什么時候,反正就發生了,有布瑞瑞斯的時候,人就有了馬莫,布瑞瑞斯之后人已經在肚子里生孩子”,甚至還有報告人反問筆者:“你真奇怪,為什么問這個問題?(我們)其他人都沒有在意(這個),我被你問住說不出來了。”可見,在阿拉安人的記憶中,只是記住了事件,并不會去深究這些事情之間的邏輯關系或前后關系,也不會去追究事情的具體時間,因為時間、事情的邏輯對于他們是個很抽象的概念,并沒有特別的意義;他們只要記住以前發生過的那些重大事件本身是什么就已經足夠,這是因為他們認可這些事件是有特殊意義的,這些遠古時代的事件影響到了今天人們的生活,決定了現實人類的命運。
所以如果想問阿拉安人是否有時間的概念,答案是阿拉安人只擁有一個由事件構成的時間。阿拉安人關于時間的觀念是在神話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神話中的各個事件就構成了遠古時代的時間,大致包括了:首先發生的是安布奧創世,然后是大洪水災難,接下來是兄妹倆繁衍出各民族的人類和精靈,再往下是關于人類祖先兄弟姐妹的故事,繼續發展過來就是某某人的祖父旅行、歷險的事情,民都洛島大地震時的事,出現日食時村社里發生的事,日本人來時的事情,前些年在旱田里的事情,最近發生的事情。這一連串事件在每個阿拉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完整的、按順序發展的序列,事情一件接一件發生一直延續到今天,今天的現實生活可以按照這個序列毫無差錯地一直追溯到神靈創世的時候。在阿拉安人眼中,即使是非常奇幻的情節,即使有自相矛盾和缺乏邏輯的地方,這些事件環環相扣、連成一串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因為他們就是把自己記憶中本人、長輩、先祖、傳說中的人物和神靈經歷的各種有趣的、重要的或特別的事件連接在一起,就成了自古至今的歷史,這個由一連串事件構成的序列就是阿拉安人眼中的時間。這個時間始于神話,而且神話決定了這個時間發展的方向和趨勢,因為最初時發生的事情決定了世界后來發展的秩序,決定了后面的一連串的事件。就神話本身而言,阿拉安神話中的時間也是由發生的事件決定的,在阿拉安神話中從沒有出現過任何具體的時間,只有具體的事件,是事件賦予了神話以時間的意義,同時也是神話和其他事件賦予了阿拉安人以時間的觀念。
2.神話是樸素的地方性知識
在阿拉安人的認知中,關于洪水的種種敘事是具有神圣性的,而且這一神圣性具體表現為,神圣的內容蘊含在看似簡單和樸素的敘事表演形式中。阿拉安人講述神話的整個過程都處于稀松平常的、生活化的狀態。講述神話時,對于講述人的性別絕無要求,婦女、兒童都可以在場,婦女也可以參與到敘述中來。對于神話的講述者和聽眾,阿拉安人也并沒有特別的要求和禁忌。在采錄時,筆者常常是和一家人或者好幾位老人在一起,他們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相互核對一下記憶中的信息;有時會有一個人主說,不過旁邊的人也會時不時地插嘴。神話的講述完全可以在日常的環境中進行,不一定需要與某種儀式或特別的表演相配合,或者尊重某種特定的講述規則。只是阿拉安人一致公認,講述人應該是上了一定年紀、見多識廣的長輩,這樣說出來的才比較權威、準確。這些敘事被講述人嚴肅而認真地當作真實事件來講述,沒有任何主觀上的戲謔或編造。這些阿拉安報告人在講述時,都是以平實樸素的語言平鋪直敘,使用普通的話語、詞匯、語氣和聲調。報告人的講述通常缺乏修飾的成分和對具體細節的精細描述,講述中主要關注的是各主要事件一步步按時間序列依次發生,而非其中的種種細節。即使是一些奇幻、難以理解的情節,報告人也不會展開或深入講述,或者主動給出原因以解釋,如果回頭再詢問“為什么”,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事情就是這樣,沒有什么原因”、“聽說時具體情況就沒有說”。因為神話信仰者與現代人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對于土著而言,并不需要知道為什么在歷史上要發生那些奇幻的事件,那些事件是不是太神奇了,這種問題是并不信仰神話的現代人心存好奇才會想到的;作為信仰者的土著并不關心為什么發生那些神話,他們關注的是那些奇幻的事件對于今天的現實生活導致了怎樣的結果,神話和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系才是他們所關注的,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才是對自己有意義的。
講述神話是阿拉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落之后、睡覺之前,人們在一天勞作之后歇了下來,常常會以家庭或幾個家庭為單位聚集在一起,伴隨著年輕一輩的發問,長輩會講述包括大洪水在內的各種故事,并且這種講述既被當作是與別人一起分享這些傳統知識,又被作為是對年輕一代進行教育。在阿拉安人看來,神話中的確充滿了各種神靈魔怪和靈異事件,但是神話并不會因此就成了遠離現實生活的神秘詭異的事情。那些故事都是很現實的事情,只不過發生的時間是很久以前、地點是與今天不同的世界,所以不必覺得那些故事有太多的特別之處。阿拉安人把神話視為是神圣的,它的內容是無比的真實,不可以隨意篡改;但又決不是神秘的,它亦是本民族中大眾共同分享的一些基礎觀念和知識,并且也可以非常平常地告訴外來者。若與我們現代社會中的學校教育、科學文化知識相比,在原住民的社會中,神話正是他們的“知識”,不過是僅存在于當地的“地方性”的“知識”。
不過,上述這些神話敘事形式上的樸素性質,并不會遮蓋其敘事內容的神圣性本質,更不會妨礙原住民講述者及聽眾把這些神奇的故事當作真實的事件。因為在原住民眼里,這些敘事的內容一直被視為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由于它們非常真實,原住民們早就習以為常地接受了,所以無須再額外添加種種修飾和奇幻色彩,從而去刻意夸張這種神圣性。阿拉安人洪水敘事的神圣性恰恰表現為一種平凡和純粹的真實,“神圣”以一種自然的、簡單的、生活化的狀態出現。
在阿拉安語中,知識叫做“katawan”,傳統叫做“ugali”。對于這些神話,他們并不是作為某種極其特別、讓人畏懼的信仰來看待,而是作為阿拉安人的“知識”中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神話被作為當地的一種非常“日常”的“知識”,被視為是一些關于自己民族祖先歷史的“知識”,被視為每個阿拉安人都應該知曉的基礎“知識”。另一方面,阿拉安人視掌握神話內容如同于掌握砍樹、取火、捕獵等各種基本生活技能,阿拉安人的“ugali”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掌握好這些“知識”。如果一個阿拉安人不知道這些,絕不是光彩的事情,會被視為是不了解本民族的傳統,人們會說這個人“沒有katawan”或“缺乏katawan”,甚至會說“這個人是笨蛋”,“不尊重我們的ugali”。與之相反,阿拉安語中還有一個形容詞katawanēn,意為“有智慧的、有知識的”,原住民會說“對Pangisudēn非常熟悉的人是katawanēn的”,也就是說,通曉神話的人會被認為是有“知識”(katawan)的人。阿拉安人中有一套眾人公認的“katawan”和“ugali”,包括的內容既有各種生活技能、倫理道德,又有這些神話傳說,此外還有各種儀式和信仰,這些合在一起正是一套完整的、成體系的“地方性知識”。這套地方性知識正是在神話基礎上構建的,而且是本民族中人人都應該掌握、每天都要操作實踐的。
3.神話與身份認同
更為深遠的是,這些神話既然被認為是阿拉安人的文化傳統,那么它同時也成為一種重要的身份認同,給整個民族、村社提供了一個想象的歷史歸屬觀念。長期以來,人類學家“一直習慣于將族別范疇 (被命名的并自我認同的社會體系及其文化)在原則上認作是近乎原生的實體”,即把族性作為原住民們的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然而以《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漸表明,所謂的族性可以被想象作為“社群社會政治關系的一個函數”,其實是相對的,而非絕對、固定或單一的[10]。對于阿拉安人而言,“我是阿拉安芒揚人”這一族性認同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這個概念需要通過神話敘事、儀式實踐來維系,如果神話、儀式等該民族特有的地方性知識不存在了,族性的認同就會喪失。阿拉安人的領地很大,地廣人稀,崇山峻嶺間交通非常不便,各村社都形成自治,需要有一種力量把這些散居各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這個力量就是對本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同一村社內部、不同村社的人們信仰著同樣的歷史,而且他們對這段歷史的信仰又不同于鄰近的其他芒揚人和平地民族,再加上彼此操同樣的語言、采取同樣的儀式和習俗、有著或遠或近的親屬關系,于是土著彼此之間才會相互認同:對方和自己一樣都是阿拉安民族的成員。
筆者在田野調查中遇到一些阿拉安人與其他族的芒揚人或平地民族通婚而組建的家庭,比如報告人胡安尼多是阿拉安人,但她妻子蒂娜是他加祿人,嫁到阿拉安村社中生活了近30年之后,蒂娜能說一口很好的阿拉安語,交了很多阿拉安朋友,很多阿拉安村社中都有人認識她,外表看起來與阿拉安人已然無異,但實際上還是有一些細節展現出了差異。比如蒂娜在稱呼丈夫或其他同輩人時用阿拉安語詞kalē,但她會經常說成kalo。這是因為他加祿語中沒有中舌位展唇央元音“ē”(發/?/音),即使是說了近30年,她依然習慣性地將“ē”音變為他加祿語中最接近的/o/音。而且蒂娜不太清楚阿拉安人的神話、儀式習慣,更不會參與這些儀式。每次我和胡安尼多聊阿拉安人的故事和習慣時,蒂娜并沒有多少興趣來聽,但他們的孩子,甚至是周圍的鄰居,或者是路過的阿拉安人,卻頗有興趣參與,大家會一起津津有味地聊起來。蒂娜最積極的事是去教堂做彌撒——這是他加祿人中極為流行的宗教,胡安尼特和他們的幾個孩子雖然也皈依了天主教,但是和其他大多數皈依的阿拉安人一樣,遠沒有她那么熱心。而在其他阿拉安人看來,即使蒂娜嫁給了阿拉安人,可以滿口流利地說阿拉安語,她還是他加祿人,還是“外人”,不會和他們坐在一起閑聊、嚼檳榔、講故事——因為她講不出他們講的故事,對此也不感興趣。筆者調查過的克斯路言社 (Kisluyan)位于阿拉安芒揚人領地的南緣,旁邊就是塔加萬芒揚人的領地,在那里兩族之間的交往很多,很多阿拉安人會說塔加萬語,而且不少塔加萬人也會說阿拉安語。一次,筆者跟著幾個阿拉安人在小路上行走,遇到了一個背著筐的芒揚人,他們幾個就用阿拉安語聊了起來,這讓筆者以為他也是一個本地的阿拉安人,結果后來他們告訴筆者,那是鄰近村社的塔加萬人。對于筆者,根本無法分辨這位路遇的芒揚人到底是阿拉安芒揚人還是塔加萬芒揚人,于是筆者詢問道,語言一樣,衣著也差不多,嚼檳榔等習慣也一樣,如果你又不認識他,怎么能分得出來?同行的阿拉安人說:“光是說話沒有什么區別,但一起生活時就知道,我們的 (神)叫安布奧,有事要 (舉行)班素拉 (儀式),他們的習慣 (和我們)不一樣。”
4.神話中“神奇”的歷史觀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阿拉安原住民僅僅是神話的傳承者,對于這些先民們所創造的神話,他們的理解也是有限度的。一方面,他們和我們一樣,也認為這些古老的故事里有很多光怪陸離、不可思議的情節,今天看來,這些“神奇”的東西的確不合常理。他們對此也是迷惑的,并不明白這些關于祖先的神奇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內涵。這正類似于我們現代人面對神話時所具有的疑惑。所以如果我們在研究中探索神話的真正涵義時,是不可能通過在田野調查中詢問原住民就可以直接得到的。雖然他們人人都相信神話是真的,雖然神話對于他們而言是重要的、地方性的“知識”,但神話決不是“常識”。因為原住民認為,這些神話絕不是日常隨意就可以了解和運用的,而是需要用信仰和儀式來不斷地驗證才能夠真正認識和掌握到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們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會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去思考,覺得這些神話非常荒謬,而他們雖然也會對神話中的神奇事件疑惑不解,但仍然篤信這些祖先的故事真實無疑。他們認為,這些故事說的是很久以前,那時候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并不一樣,那些神奇的情節在過去完全可能、一點都不荒誕,完全符合那個時代的“常理”,說它們“神奇”只是“不合”今天人們所認為的“常理”而已。
這其中有一個有趣的問題,雖然神話所構筑的歷史觀是想象的,神話中描述的那個古老的理想世界與今天的現實世界千差萬別,但是原住民卻能夠運用一條“非常合理”的邏輯,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證據,來驗證神話所講述的理想世界以及發生的神奇事件都是“千真萬確”的。即原住民會用今天的“常理”來證實歷史上的“神奇”,從而維護自己想象的歷史觀。原住民認為,就是因為發生了神話中所說的神奇事件,今天的世界才變成了這個樣子,于是今天世界的樣子和神話中所說的神奇事件不一樣恰恰是對的,發生了那么多神奇事件,兩者自然應該不一樣。原住民堅信神話暗含著這樣一個思想,即神話解釋了理想世界變化發展成現實世界的過程,神話正是講述這個過程的歷史敘事,所以那些歷史上的“神奇”與今天的“常理”迥然不同,正好證明了神話是無比真實的。這樣就不難理解,神話傳承至今,阿拉安原住民為什么仍然相信這些光怪陸離的神話,甚至越是“神奇”越是相信。
結語
綜而觀之,阿拉安人神話在原住民自己看來是一段標準的口述史,所講述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歷史過程。阿拉安人的神話觀是樸素而神圣、自然而真實的,作為現實的民族認同歸屬和想象的歷史觀念,神話又構成了阿拉安“地方性知識”中核心的內容。阿拉安人的神話是由一連串的闡述各種事物起源、產生、出現的起源事件組成的,包括了世界的起源、天空大地等的產生、人類的起源、天與地的分離、性別的出現、生育方式的改變和起源、現代人類或各民族的起源、一些具體地貌的起源等。在土著居民看來,祖先流傳下來的這一切關于洪水的種種說法,是一整段連貫的非常古老的故事,其內容都是祖先們當初親身經歷的,是在遠古時代確實發生過的真實歷史。這段歷史是連續的,是以一個又一個事件為核心串連在一起而成,這些事件彼此間不僅有著時間序列上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還有著生活常理上的因果、承接、轉折等密切的邏輯關系。神話被原住民視作為一段完整的、前后關聯的、客觀存在的歷史,阿拉安人就生活在這些事件構成的歷史時空之中。所以說,阿拉安民族的神話觀亦是歷史觀和世界觀,在原住民看來,這些神話是一段標準的口述歷史,整個神話的敘述給阿拉安人構建出了一整套想象出來的歷史記憶,講述的是他們周圍的世界由奇幻走向真實、由理想狀態走向現實形態的宏大歷史。這些神話承載了對于原住民最為核心和重要的一些觀念,原住民自然會非常重視它們,千百年來世代相傳并始終成為阿拉安民族所珍視的“地方性知識”。這套阿拉安人的地方性知識,是以非常樸素和平常的形式存在著并且被原住民講述,但樸素的形式并沒有遮蓋其神圣性的內核。這些口承敘事成了阿拉安人民族傳統的構成部分,是不容挑戰的。
【注 釋】
[1]關于阿拉安人的民間敘事自然分類,參見拙作《地方性的神話觀:菲律賓阿拉安—芒揚原住民的民間敘事自然分類》,《東南亞研究》2009年第3期。
[2]〈英〉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132頁。
[3]〈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王海龍、張家瑄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72、73、90頁。
[4]同 [2],第131-135頁。
[5]〈美〉詹姆斯·斯哥特著,鄭廣懷等譯《弱者的武器》,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222頁。
[6]Antoon Postma,“The Concept of Time among the Mangyans”,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44 No.2,1985,pp.232-233.
[7]Renato Ignacio Rosaldo,Jr,Ilongot Society: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Non-christian Group in Northern Luzon,Philippines,Ph.D thesis in the subject of Anthrop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70,pp.164-165,note 5.
[8]Antoon Postma,op.cit.,p.233.
[9]根據 Masaru Miyamoto在 Kilapnit社的田野調查,轉引自Antoon Postma,op.cit.,p.233.
[10]〈英〉埃德蒙·利奇著,楊春宇等譯《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對克欽社會結構的一項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代譯序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