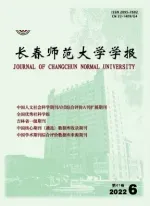明清文言小說中夢會神女故事的文化解析
張桂琴
(大連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遼寧大連 116021)
明清文言小說中夢會神女故事的文化解析
張桂琴
(大連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遼寧大連 116021)
夢會神女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常見的母題之一。與此前的夢會神女母題相比,明清文言小說中夢會神女的故事借鑒了神女故事的原型,卻脫離了情欲的窠臼,顯得更為清新純情。這與作者的儒生身份、陽明心學的影響以及“至情”學說的影響有很大關系。
明清小說;文言小說;夢會神女
自《高唐賦》揭開夢會神女的朦朧面紗之后,夢會神女便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最為常見的主題之一,其后的一系列作品大多衍生于此。明清時期,封建社會進入歷史的轉折期。政治生活的窳敗,使越來越多的文人不得不被動地疏離了政治中心。儒家傳統的“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教育,使得他們產生了極大的挫折感、失落感。于是,沉寂許久的神女幻夢原型逐漸破冰而出。夢會神女原型是遠古的祖先留給我們的無意識的記憶,具有特殊的恒定性;同時,它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準確地破析其文化內核,對理解由夢會神女結構而衍生出來的文藝作品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明清小說,尤其是明清文言小說中存在著大量的夢會神女的故事:明代徐熥的《十八娘外傳》①敘萬歷年間東海生出游東郊,小憩于報國寺,“晝長假寐,夢至一所,朱戶紅樓,丹檻紫閣,極其壯麗”。小丫鬟引導東海生會見十八娘,細說天寶遺事,與其他三女同席賦詩。臨行之前又以紅繡鞋、麝囊、珍珠、紫瓊等相贈。華玉溟《銀河織女傳》中武陵少子夢到一“駕鶴纏云”之美姝引領其前往天境,被帝君認為“佳婿”,游歷仙境故地。此后二人經常夢中相見,詩詞唱和,“嗣是則恒夢同游勝地,而不復入銀河”,經年之后,美姝方留書別去。《聊齋志異》中有許多夢幻故事都與遇仙有關,如《絳妃》(卷六),作者用第一人稱寫自己夢見兩個華衣女子來請,后來得知是花神絳不滿風神對花木的摧殘,請自己去寫一篇討伐風的檄文。文中記敘花神前來請求自己幫忙,將自己亦置于神的地位,且從某種角度而言更高于普通神靈。作品中僅檄文就占了大量篇幅,而且這檄文寫得文采風流,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對自己文章的沾沾自喜,這其實是作者在現實中對自己才能不被社會所接受而發表的激憤之詞。
清代文言小說家樂均《耳食錄》中也有夢會神女的故事:《宓妃》(卷五)敘寫家住洛水旁的好義任俠的某書生,一日夢到宓妃前來請求他幫助借兵以消除外辱,某生慷慨允諾,“遂藉已歿軍士,得若干,牒送洛水”,并親自派兵遣將,伏兵云集,轉戰夾擊,“賊師披靡,斬首數萬……大索其巢,余黨盡獲,露布馳聞”,大獲全勝。宓妃感念,贈以珍器、珠寶,生均卻之。驚窹后,家人來報,“東軒有寶物無數,耀目充庭,視之,即妃向所贈”。此文與《絳妃》異曲同工,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注重通過細節的描畫來刻畫人物,宓妃的出場時的委屈愁怨,戰勝之后的笑靨歡顏,懲處俘虜時的內心不忍,慶功酒宴上的愉悅舒心,臨別之際的徘徊眷戀,在作者筆下漸行漸近,一個百態千姿的女神形象栩栩如生地走進讀者的視野。《紺霞》(卷六)中博學多才的吳姓公子,十五歲時“夢行溪上,春水揉藍,落花如繡”,不覺沉醉其間,欲窮其源。朦朧間仿佛隱隱有墮釵之聲,又覺有“搴簾微笑者”,聞有人來,始驚去,吳生悵然若失。他日又夢至此處,遙聞女子笑語,俄見跟隨著丫鬟的幾個麗人逶迤而來,女子對自己的丫鬟說:“人間劉阮再來矣,盍歸乎?”吳生尾隨而去,但女子已經失去了蹤影,只遺留下詞箋一幅,署名“紺霞”。故事中雖然沒有言及吳生所遇女子的身份,但是我們從其語言中可以推測出,她稱吳生為“人間劉阮”,那么其自身所處自然為“非人間”了。
林鴻《夢游仙記》中作者酒酣醉臥莎草,夢到“瑤華洞天”,遇瑤華洞主的三女兒蕓香。蕓香對作者訴說了對其才華的傾慕之情,并向求詩詞一首,作者慨然允諾,揮毫立就。蕓香亦一蹴而就,不假構思而和詩一首。兩人談性正濃,卻被突然回府的真君驚擾而夢醒。《夢花記摘略》 (《小豆棚》卷五)中先生史小峰夢游一山,抵山腰,一院落“朱扉洞開,仰視額書懸云際,為‘碧落九層天源’”,循中迤邐而行,遍遇延陵花史吳慕娥、冰夫人梅素仙、仙姝椒青、侍常謝妙香等佳麗,相互歌詩酬唱,自得其樂,于“狂喜大叫”中“灑然而寤”。
夢會神女故事多屬于文人士子的自慰式幻想。這些故事中的神女往往聰穎智慧、機敏過人、身份非凡,實現了現實生活中文人的人生缺憾的補償。從文本結構來看,故事中女強男弱,女性對于男性承擔著提攜、救濟的功能;從文本意義來看,則是“對男尊女卑傳統性別文化的一次顛倒思維”[1],具有明顯的時代進步性。
二
現代科學認為,男性夜夢異性是正常生理現象的表現,即使是科學不大發達的封建社會,對于這樣的現象也是能夠接受的,“宵寐”一詞即反映了此意。但是,何以在月明星稀、燈火闌珊的夜晚,走入尋常男性書生夢幻中的女子不是普通的民間女子,而是溫婉靚麗、知書達理、身份特殊的神女?從表層時代角度而言,明清時期正是禮教思想最為濃郁之時,禮教不但束縛了女性,也同時束縛了男性,使他們放棄了自主爭取情愛的念頭。神女“聞君游高唐,愿薦枕席”的自由宣言,男性打心眼兒里是渴望的,希望自己也碰見一個,因而行諸夢幻。從深層心理學角度而言,夢會神女故事也是男性作家以守為攻、以退為進,顯示男性權威的心理產物。神女的地位越高貴,她們之俯就男性就更能體現出男性的重要與尊貴。這正好印證了榮格的話:“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傾向,特有的偏見與心理病癥,一個時代就像一個人,它的意識觀有自己的局限,所以需補償性的調整。”[2]葉舒憲先生指出:“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敘述功能——現實與幻想——的人格化。在這里,男子大都代表著孤苦、貧困的現實存在,女子則代表著使現實存在得到改變和拯救的幻想功能。”[3]
夢會神女故事中神女的身份與地位往往都非比尋常,這與道教的女性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道教自產生時期起,對女性的尊重程度就相對較高。聞一多曾說過:“我常疑心這哲學或玄學的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種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體點講,一種巫教。這種宗教,在基本性質上恐怕與后來的道教無太差別,雖則在形式上與組織上盡可截然不同。這個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們可暫稱為古道教。”[4]中國原始巫教里女神崇拜的案例數不勝數,如女媧、西王母、九天玄女等等,這顯示了原始氏族社會中女性占主導地位的殘余影響。在明清文言夢幻小說中,這些神女出現在尋常男性的夢幻中,對男性,尤其是對書生青眼相睞,使得現實生活中不甚如意的書生們找到了一種對自己才華和自我價值的肯定感和確認感。作者意將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女引為自己的知己,通過幻想與虛構情境實現自我確證、自我肯定,落魄文人的個體生命價值受到社會的貶抑或冷落,卻得到神女的贊賞和肯定,以達到心靈上的自我療救,也使得創作者在寫作中得到內心苦悶的舒解和精神創痛的撫慰。這樣,文學創作便發揮了它“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的社會功能。
三
明清文言小說中夢會神女故事與此前時代的同型故事相較最為典型的情節,即男性書生與所遇合之仙女往往先是志趣相投,進而情投意合,但是卻鮮有纏綿悱惻的情欲景象的發生。在道教文化的系統中,男女間的性愛并沒有受到禁忌,相反,在道家文化的早期甚至還一度倡導房中之術。明代中后期,資本主義思潮漸漸萌生,個性解放思潮漸漸浸潤于傳統的禮教思想中。描寫男女情事的白話小說一度流行以至于泛濫而被朝廷禁毀。然而,在明清文言夢幻小說中卻鮮有赤裸裸的情欲的描寫。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創作者儒生身份的影響。文言夢幻小說的創作者多為儒生,他們飽讀儒家經典,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發乎情,止乎禮”是他們所恪守的道德尺度。同時,這些儒生在現實中雖然生活相對窘迫,但是他們大多可以憑借自己的知識賴以謀生,所以基本的家庭生活還是有所保障的。但他們的精神生活還是存在一定的缺失。封建社會對于女性的要求是“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這些夢幻小說的創作者們的妻子往往只是普通的女性,于琴棋詩書精通者相對較少。因此,小說的創作者們所需要的是精神的伴侶,是能夠與其有共同語言的精神伴侶。作者以濃筆重彩表現神女美貌多情、富有才學的共性,以及風趣幽默、落落大方或矜持優雅、嬌媚可人的個性特征。這些都是現實世界里才子心目中理想佳人的生動寫照,是文人士子在世俗社會中的審美趣味和情愛理想的產物。
第二,“心學”的影響。明代中后期,“心學”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思潮。王陽明提出的“致良知”,羅汝芳提出的“赤子之心”以及李贄的“童心”說在當時的文壇掀起了弘揚個性解放、抒寫真情、表現性靈的風潮。這樣的思潮要求情感是真、善、美的統一。文言小說的創作者正是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從而在小說中著力強調女性主人公曼妙的身姿、溫婉的性格、廣博的才學以及自己與女主人公之間情感的純真、美好,而摒棄了情欲的描寫。
第三,“至情”說的影響。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具體闡述了“至情”說:“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說的“至情”,指的是一種真摯的感情。這種感情,能使活人死去,也能使死人再生。這種“至情”體現著一種反對封建主義的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情可以超越有限的肉體而不死,比之道德更具有永恒的意義。“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5]人因情而生死,情卻并不依賴于人的生死,它具有獨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這樣的一種情感價值觀,極易為多情善感的文人所接受,故而在文言小說中所描寫的情感除去了白話小說中大量的色情成分,而顯得相對單純、潔凈。
四
日本學者窪德忠所說:“自公元前四世紀至今,中國人一直無限向往神仙。……神仙能實現凡人可望而不可得的一切愿望;神仙能永遠享受現世的快樂等等。正因為神仙能即刻實現人類的一切夢想,所以在人們心目中神仙成了實現人類夢想的偶像。”[6]中國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積極達觀,勇于擔當,“致君行道”是中國文人的終極價值取向。然而在封建社會,真正能夠實現文人“致君堯舜上”的政治理想的機率少之又少,于是文人往往在入世與出世的夾縫中輾轉。所以,每當他們想要表現自己的美好愿望,表達自己對理想生活的追求的時候,夢幻小說便成為展示他們精神世界的常用方式。而神女作為中國原始的美神,早已在漢民族集體無意識中積淀為一個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原型。明清時期是一個封建秩序斷裂重建的時代,以禁欲主義為特色的儒家道德開始發生了動搖,受到了質疑,長期的封閉和壓抑需要補償,因而一個沉睡多年的話題又變得熱鬧起來。當男性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的欲望難以通過社會允許的正常途徑得以實現之時,便以虛構的幻夢情境,假借神女意象來宣泄被抑制的人性基本欲求,使主人公(更確切地說是作者和讀者)得以恢復或重建人欲與天理之間的平衡。文人對夢會神女故事的記敘與關注,實際上是在對現實生活產生了失落感以后找到的一種彌補方式,通過對神女意象的描繪來達到對人生的新悟。
[注 釋]
①曾衍東《小豆棚》卷五稱此文引作幔亭羽客撰。徐桲《榕陰新檢》卷十五題作《荔枝假夢》,出《幔亭集》。陳毅中《明代小說鈔》(明代卷)考證,《幔亭集》為明徐熥所著,但今所見《四庫全書》本《幔亭集》不載此傳及詞,蓋已刪去。《十八娘外傳》收入《廣艷異編》卷十二,題作《扶離佳會錄》。三本互有短長,《小豆棚》所載文字最詳。
[1]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中國小說史稿》編輯委員會.中國小說史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356.
[2][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馮川,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54.
[3]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467.
[4]聞一多.道教的精神[M]//聞一多全集:第九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448.
[5]馮夢龍.情史[M].長沙:岳麓書社,1986:340-341.
[6][日]窪德忠.道教史[M].蕭坤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52.
A Culture Analysis on the Stories of Meeting-Goddess-in-Dream in the Classical Novels of Ming&Qing Dynasties
ZHANGGui-qin
(School ofLiterature and Law,Dalian Radio&TVUniversity,Dalian 116021,China)
Meeting-goddess-in-dream is a common motif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Different with other times,the meeting-goddess-in-dream motif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cended the mode of lust and became simpler and fresher.The form of this phenomenon has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riter’s identity,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scholars and human nature ofearnest feelings.
novels in Mingand Qingdynasties;classical novels;meeting-goddess-in-dream
I206.2
A
1008-178X(2012) 04-0074-04
2011-11-03
張桂琴(1971-),女,河北黃驊人,大連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博士,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