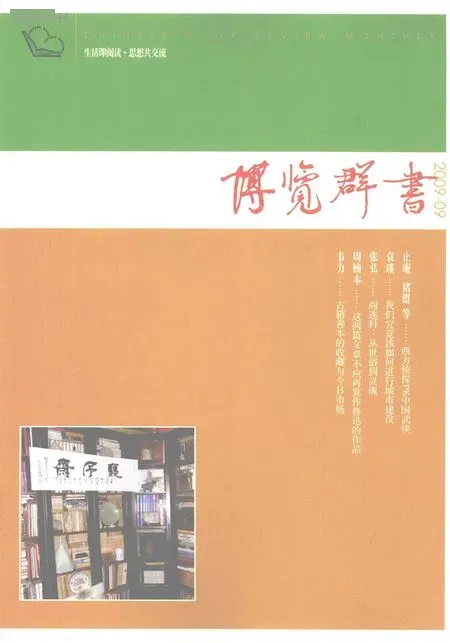七個(gè)日本漂流民的故事
○顧鈞
○周楞伽(周允中整理)
七個(gè)日本漂流民的故事
○顧鈞
在19世紀(jì)中期美國迫使日本門戶開放之前,日本一直維持著只與中國和荷蘭在長崎一口通商的體制,從18世紀(jì)末開始,美國和英國就試圖打破這種體制,建立正常的貿(mào)易關(guān)系,但屢遭拒絕。在這半個(gè)多世紀(jì)的艱難交涉中,出現(xiàn)了不少今天看來非常有趣而當(dāng)時(shí)卻相當(dāng)無奈的故事,七個(gè)普通日本水手有家不能回的經(jīng)歷是其中之一。
1831年11月,一艘運(yùn)糧船從愛知縣小野浦駛往江戶(今東京)的途中遭遇風(fēng)暴,17名水手中14人遇難,只有三人幸運(yùn)地躲過了這一劫,他們的名字是巖吉、久吉、音吉,均來自愛知縣的尾張。這三個(gè)水手雖然保住了性命,船卻嚴(yán)重地偏離了航向,他們只好隨風(fēng)漂流,在茫茫太平洋上熬過了14個(gè)月(一說17個(gè)月)后在美國西部上岸,地點(diǎn)是俄勒岡的哥倫比亞河口,他們上岸后立刻被當(dāng)?shù)赜〉诎踩俗カ@,從此開始了一年的奴役生活。1834年5月,一位好心的美國商人解救了他們,并讓自己的一位合伙人將他們經(jīng)英國送往中國。三人所乘的“老鷹”號(hào)于1835年夏到達(dá)倫敦泰晤士河口,十天后另一艘船“帕爾瑪將軍”號(hào)又帶著他們?cè)俣绕鸷健T谶@十天當(dāng)中,他們只被允許下船一次去逛倫敦市區(qū)。在當(dāng)時(shí)日本人被嚴(yán)禁出國的情況下,他們很可能是踏上英國國土最早的幾個(gè)日本人。“帕爾瑪將軍”號(hào)從倫敦出發(fā),經(jīng)好望角,于1835年12月到達(dá)澳門。三名日本水手被交給當(dāng)?shù)赜虅?wù)監(jiān)督的秘書郭實(shí)獵(Karl Gutzlaff)照管。郭實(shí)獵是德國人,在為英國政府效力之前曾在東南亞傳教多年,在傳教過程中學(xué)會(huì)了漢語、泰語、柬埔寨語等多種語言,是個(gè)對(duì)語言十分敏感的人。三個(gè)日本人的到來為他學(xué)習(xí)日語提供了契機(jī),一年多以后另外四個(gè)日本人的到來使他的老師增加到了七人。
稍后來到澳門的這四個(gè)日本人的名字分別是莊藏、壽三郎、熊太郎、力松,都來自九州。1835年12月他們從天草駕一小船前往長崎,途中大風(fēng)將桅桿吹折,小船隨風(fēng)漂流,35天后在離馬尼拉不遠(yuǎn)的一個(gè)小村莊附近上岸,很快被當(dāng)?shù)厝俗カ@并解送到馬尼拉。1837年3月他們被一艘西班牙船只送到了澳門,并被安排和早先來到澳門的三位同胞住在一起。
對(duì)于這七個(gè)日本人來說,在澳門生活倒也無憂,但梁園雖好,畢竟不是家鄉(xiāng)。于是在美國商人金(C.W.King)的提議下,一個(gè)將他們送回日本,并借此大好機(jī)會(huì)與日本建立貿(mào)易關(guān)系的方案被確定了下來。1837年7月4日,載著這七名漂流民的“馬禮遜”號(hào)離開澳門,向日本進(jìn)發(fā)。為了向德川幕府顯示誠意,金卸下了“馬禮遜”號(hào)上的武器裝備,并特別安排自己的夫人同行,其他成員包括美國傳教士衛(wèi)三畏(S.W.Williams)和伯駕(Peter Parker),他們沒有帶《圣經(jīng)》和任何傳教的小冊(cè)子,而是帶了大量的藥品和科學(xué)儀器,目的同樣是為了取悅?cè)毡井?dāng)局。郭實(shí)獵沒有和他們一起出發(fā),他當(dāng)時(shí)正在英國戰(zhàn)船“拉雷”號(hào)上執(zhí)行任務(wù)。在“馬禮遜”號(hào)到達(dá)琉球首府那霸的第三天(7月15日),他被“拉雷”號(hào)送到了那里,開始為此次日本之行充當(dāng)翻譯。
經(jīng)過半個(gè)月的航行,“馬禮遜”號(hào)于7月30日到達(dá)了江戶灣口的浦賀,在靠近陸地的過程中突然遭到了來自平根山炮臺(tái)的炮火襲擊,于是駛離岸邊,停在自以為安全的水域。沒想到夜里有四門重炮被拖上了炮臺(tái),它們?cè)诘诙彀l(fā)揮了威力,一炮就擊中“馬禮遜”號(hào)的甲板,盡管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但也足以讓“馬禮遜”號(hào)放棄了前往江戶的計(jì)劃。在打道回府時(shí),金老板等人仍不死心,又嘗試在鹿兒島登陸,結(jié)果又一次遭到炮擊。“馬禮遜”號(hào)不得不徹底放棄希望,于8月29日返回澳門。這次歷時(shí)兩個(gè)月,耗資兩千美元的行動(dòng)最終以完全的失敗告終。
將日本的漂流民遣送回國,這在美國人看來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行為,卻遭到日本幕府政權(quán)如此野蠻的對(duì)待,不能不使他們義憤填膺,也更加堅(jiān)定了他們用武力打開日本大門的信念。同時(shí)他們也意識(shí)到有關(guān)日本信息的貧乏,這從不得不在那霸等待郭實(shí)獵的大駕光臨可以看出。衛(wèi)三畏回到澳門后立刻開始學(xué)習(xí)日語,并著手收集各種有關(guān)日本的信息。其實(shí),德川幕府早在1825年就發(fā)布過“驅(qū)逐令”,驅(qū)逐所有靠近日本海岸的非中國和荷蘭船只。如果金老板、衛(wèi)三畏他們?cè)缫稽c(diǎn)知道這個(gè)信息,也許就不會(huì)冒冒失失、一廂情愿地前往日本了。也正是由于這個(gè)“驅(qū)逐令”,致使浦賀和鹿兒島的地方官員不問青紅皂白就對(duì)“馬禮遜”號(hào)實(shí)行炮擊。至于“馬禮遜”號(hào)來日本的真正目的,德川幕府直到一年后才從荷蘭駐長崎的貿(mào)易官員那里得知。有趣的是,荷蘭人的報(bào)告中將“馬禮遜”號(hào)誤說成是一艘英國船,造成這一誤解的原因可能是因?yàn)轳R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英國人,作為最早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不僅得到了英國商人的尊敬,也同樣受到美國商人的尊敬。幕府高層最終知道“馬禮遜”號(hào)是一艘美國船是在1842年,這一年荷蘭駐長崎的貿(mào)易官員將兩位漂流民——莊藏、壽三郎——給家人的書信帶到了江戶。在信中,兩人描述了他們漂流和被“馬禮遜”號(hào)送回國的經(jīng)歷。
七位漂流民在重返澳門后,人員進(jìn)行了重新的分配,音吉、力松繼續(xù)跟著郭實(shí)獵,其余五人則由衛(wèi)三畏管理。他們此后的情況由于資料缺乏而比較模糊,可以肯定的是音吉、力松作為英國船只的翻譯在十多年后有機(jī)會(huì)去過長崎和函館,至于其他人是否在有生之年回過日本則不能確定。
關(guān)于這七位漂流民的情況,最早的記錄見于衛(wèi)三畏的《“馬禮遜”號(hào)的琉球與日本之行》(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一文,這是衛(wèi)三畏回到澳門后立馬完成的,該文刊載于《中國叢報(bào)》(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6卷第5期(1837年9月)。《中國叢報(bào)》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在廣州創(chuàng)辦的近代中國第一份英文刊物,每月一期,開始于1832年5月,停辦于1851年12月,共20卷。既然名為“中國”叢報(bào),絕大部分內(nèi)容自然都與中國有關(guān),但也有一小部分內(nèi)容涉及中國周邊的國家,其中之一便是琉球,它是當(dāng)時(shí)從中國去日本的必經(jīng)之地。《中國叢報(bào)》上有關(guān)琉球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裨治文寫的,他在這篇文章中簡要介紹了《琉球國志略》一書(凡16卷)的主要內(nèi)容。《琉球國志略》為清朝人周煌所著,主要記載琉球國的歷史和地理概況。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周煌同翰林院侍講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冊(cè)封尚穆為琉球國中山王,于次年正月回國。在出使途中,周煌留意當(dāng)?shù)卣乒剩S手記錄。回國后又參閱大量史籍,整理編輯,手寫成書后進(jìn)呈皇帝御覽,以便把握琉球國的歷史、地理、風(fēng)俗和人情等方面的情況從而確定相應(yīng)的國策,具有很高的文獻(xiàn)價(jià)值。裨治文這篇題為《琉球小史》(Brief History of Lewchew)的文章刊登在《叢報(bào)》1837年7月號(hào)(第6卷第3期)上,可以說是非常及時(shí),因?yàn)?月4日“馬禮遜”號(hào)離開澳門開始了送七名日本水手回國的航程,所以他希望將“馬禮遜”號(hào)即將經(jīng)過的這個(gè)地區(qū)的信息提供給讀者,估計(jì)同時(shí)也希望以這篇文章來彌補(bǔ)自己無法參加此次航行的遺憾吧。
交代我寫黑文放毒的罪行
編者按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為羅織罪狀,往往勒令被迫害者以文字的形式交代“罪行”。造反者意欲從字里行間找尋到蛛絲馬跡,以便捕風(fēng)捉影,栽贓罪名;而寫作者則希冀通過文字表述來逃脫這種捉捕,以致文字不免誠惶誠恐,避重就輕。今天看來,這種荒謬的“貓鼠游戲”著實(shí)令人哭笑不得。
本文是已故作家周楞伽(1911—1992)于“文革”期間寫就的自我檢舉文章。文中記述了自己解放后寫作“黑文”的經(jīng)歷,列舉了自己發(fā)表在各類刊物上的所謂“毒草”。誠如這篇文章的整理者周允中所言,“在‘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huì)里,閱讀這份檢查交代,難免不令人怵目驚心。為了彌合這種罕見的時(shí)代鴻溝,發(fā)表這份交代自然有相當(dāng)?shù)纳鐣?huì)意義,這不啻是一份認(rèn)識(shí)時(shí)代悲劇的極佳教材”。鑒于此,作為周楞伽之子,周允中不避繁冗,將這份自父親舊信中偶然翻檢到的文史資料略加整理發(fā)表。
交代我寫黑文放毒的罪行
○周楞伽(周允中整理)
我于1956年5月底被安排分配到上海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當(dāng)編輯。當(dāng)時(shí)的古典是新文藝出版社的一個(gè)組,但和新文藝隔開,分處兩個(gè)編輯室,出版物也用古典的名義,不用新文藝出版社的名義。我和劉金(整理者按:當(dāng)時(shí)是新文藝出版社小說組編輯,“文革”以后,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文革”初期因?yàn)樨?zé)編長篇小說《戰(zhàn)斗中的青春》,最早被上海出版界揪了出來。)素不相識(shí),到古典后經(jīng)錢伯城(按:時(shí)任古典文藝編輯室組長,“文革”以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獲國務(wù)院特殊津貼,現(xiàn)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介紹才認(rèn)識(shí)的。但他因我耳朵聽不見,也無話可說,并未和我交談。這時(shí)新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俊民。
有一天,劉金叫我到新文藝編輯室,說李俊民要我修改一部稿子,就是茅珵的《監(jiān)獄里的斗爭(zhēng)》。我說我對(duì)新文藝作品已經(jīng)拋荒多年,改不來了。他說,拿去看了再說,把稿子交給我,就沒再說別的話。后來,他派新文藝的編輯江鶩、鄭嘉治來和我談話,我剛看了稿子,覺得文筆生硬,結(jié)構(gòu)散漫,形象不突出,對(duì)他們說要改寫,他們沒有表示,好像懷疑我沒有修改的能力。不久,我患肺結(jié)核病,在家休養(yǎng),花了約一個(gè)月時(shí)間,修改重寫了開頭一部分,約三萬字,交給鄭嘉治。他看后對(duì)李俊民說我修改得不好,主要是沒有監(jiān)獄生活的經(jīng)驗(yàn),李俊民就來信,叫我停止修改,把作者原稿退還新文藝編輯室。但因我已花費(fèi)了相當(dāng)?shù)膭趧?dòng),補(bǔ)償我修改費(fèi)每千字五元,共計(jì)150元。我因修改未成,不好意思接受,退了回去。后來,錢伯城對(duì)我說,會(huì)計(jì)科已發(fā)出,退回?zé)o法銷賬,我原有唯利是圖的思想,也就老實(shí)不客氣地收了下來,不久,古典脫離新文藝,獨(dú)立出版,搬到永嘉路,我就沒有再見過劉金的面。
我在1957年用周夷的筆名替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注釋的《剪燈新話》和補(bǔ)校的《綠窗新話》,都是提倡神鬼迷信,宣揚(yáng)色情戀愛的封建糟粕。除此以外,我還用柳文英的筆名,在《山西師范學(xué)院院報(bào)》1957年第四期上,發(fā)表過一篇《崔懷寶月下聞箏考》。在《光明日?qǐng)?bào)》副刊《文學(xué)遺產(chǎn)》上發(fā)表過《談裴铏的〈傳奇〉》(1957年12月15日)、《明代的傳奇小說》(1958年2月23日)、《談關(guān)漢卿的雜劇》(1958年6月29日),都是美化古人,宣揚(yáng)封建毒素的毒草,但均系投稿被采用,和編者并不相識(shí),也無信件往來。此后該刊有四年多,沒有發(fā)表過我的黑文,直到1963年2月3日才發(fā)表了我的一篇《評(píng)〈聊齋志異〉會(huì)校會(huì)注會(huì)評(píng)本》,但并非我自動(dòng)投稿,而是舊中華上編(按: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文革”以后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組(按:即第一編輯室)組長受該刊特約,叫我寫了送去發(fā)表的。
1961秋天起至1962年年底止,我又開始在報(bào)刊上放毒,1961年在《江海學(xué)刊》九月號(hào)上發(fā)表《〈典論論文〉齊氣辨》,1962年在《學(xué)術(shù)月刊》七月號(hào)上發(fā)表了《談李商隱的風(fēng)貌》,也都是投稿關(guān)系,連編者是誰都不知道。1961的秋天,我寫了兩篇有關(guān)《文心雕龍》的黑文,由反革命分子陳向平(按:時(shí)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副所長兼副總編輯)介紹送到《文匯報(bào)》去發(fā)表。第一篇《說镕裁》原來的署名是華嚴(yán),但陳向平送去時(shí),竟把我做漢奸文人用過的已經(jīng)臭了的“周楞伽”的筆名告訴了《文匯報(bào)》編者鄭心永,編者在打完小樣送來時(shí),竟改上了這臭名,我當(dāng)時(shí)沒有反對(duì)的表示,這說明我有替自己漢奸文人的臭名翻案,想繼續(xù)在新社會(huì)里使用的意圖,于是,這篇黑文在8月11日的《文匯報(bào)》上發(fā)表了。然而這名字畢竟太臭,因而引起社會(huì)輿論的不滿,編者只好在9月14日發(fā)表第二篇《談情采》時(shí),改用了柳文英的筆名。后來,我又自動(dòng)寄去了一篇《論修辭》,發(fā)表于11月12日,用的署名是周華嚴(yán)。我和《文匯報(bào)》的編者鄭心永并不認(rèn)識(shí),他雖然先后發(fā)表了我的三篇黑文,卻從未和我通過信。1962年《文匯報(bào)》第三版開辟《說林》一欄,專載數(shù)百字的短文,他忽然來信向我征稿,我一共替他寫了11篇黑文,因有索引,所以并不難查,茲將篇名、署名、發(fā)表日期列表如下:

篇名 署名 發(fā)表日期能短還是寫短些爭(zhēng)鳴與態(tài)度新風(fēng)與舊框訓(xùn)詁也不可偏廢談工具書引用經(jīng)典著作熱愛新苗資料與輯佚說比喻輯佚的標(biāo)準(zhǔn)眉批旁批及其他周夷劍周周夷司馬驊柳枝文英周夷周夷文英周夷文英1962年6月5日1962年6月14日1962年6月23日1962年7月1日1962年7月5日1962年7月8日1962年7月12日1962年8月16日1962年9月2日1962年9月21日1962年10月11日
另外在1962年10月24日,還發(fā)表了一篇較長的黑文《蒲松齡的聊齋俚曲集》,是為推薦《蒲松齡集》寫的,也是一棵美化封建僵尸的毒草。

年輕時(shí)的周楞伽
在1961—1962年內(nèi),我還用蕭劍周的筆名在《羊城晚報(bào)》副刊《晚會(huì)》上放毒,所寫的都是宣揚(yáng)封、資的黑貨,也都是投稿被采用的,不知道編者是誰。他們發(fā)表后寄來剪報(bào),我未保留,所以究竟發(fā)表了多少篇,以及具體篇名、發(fā)表日期都記不起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資料室查《羊城晚報(bào)》,預(yù)備開張清單交前工作組(按:指市委宣傳部派來的工作組),以便查考批判,但在查報(bào)時(shí),工作組通知資料室,不許我查,所以并未查全,這張單子在抄家時(shí)被抄走,現(xiàn)在只記得有如下的幾篇:1.《談〈江湖奇?zhèn)b傳〉》,2.《陳夢(mèng)雷的冤案》,3.《〈中山狼〉雜劇的幕后》,4.《蒲松齡與聊齋》,5.《最初的畫報(bào)》,6.《邵飄萍與林白水之死》,7.《林譯小說的辯證》,8.《左翼作家與影評(píng)》。好在資料室有《羊城晚報(bào)》可以查,凡是1961—62年內(nèi)用蕭劍周署名的黑文,都是我寫的。此外在1962年3月初的該報(bào)另一副刊《花地》上,我還發(fā)表了一篇解釋魯迅舊詩《秋夜有感》的黑文章,具體篇名也記憶不起來了(按:篇名為《魯迅〈秋夜有感〉新探》)。
1962年初,《少年文藝》忽然來信,向我征稿,要我寫些歷史故事,我在唐人裴铏作的《傳奇》里面選了一篇《韋自東》翻成白話寄給他們,發(fā)表在二月號(hào)上,題名下編者加了“降妖記”三字,其實(shí)內(nèi)容并不切合。不久該刊就派了個(gè)名叫劉遠(yuǎn)東的編輯來和我聯(lián)系,除了提出稿件內(nèi)容要求之外,沒談別的什么,也無話可談。后來該刊因我的文筆帶鴛蝴派舊小說氣息,不合新文藝體裁,叫他把我寫的四篇稿子統(tǒng)統(tǒng)帶來,退回給我,見我態(tài)度冷淡,從此絕跡不來,以后《少年文藝》上,就沒有我寫的黑文了。
1963年,我又用柳文英的筆名給香港《大公報(bào)》副刊《藝林》,寫了兩篇無聊的封建考據(jù)文章:《西施的下落問題》和《錦瑟詩辨》(按:是《錦瑟詩發(fā)微》)。該報(bào)遠(yuǎn)在海外,我從未想到為他們寫稿,因劉拜山(時(shí)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副總編輯,系原上海市委書記劉述周的兄長)、富壽蓀(時(shí)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后為上海師范大學(xué)、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特約教授,上海文史館館員)在該刊上搞《唐人絕句選講》,常有報(bào)紙和稿費(fèi)寄來,我見了眼紅,也想撈點(diǎn)稿費(fèi),就自動(dòng)寄了稿子去,很快就被采用了。編者陳凡來了兩封信,第二封信上竟說“此地有人說你的真名是周楞伽”,我也不知道是誰告訴他的,又覺得香港是個(gè)國際關(guān)系復(fù)雜的地方,既然已經(jīng)有人知道,還是不寫為妙,就不再寄稿去了。他給我的兩封信和報(bào)紙都已交前工作組。
此外,我在1961年,還替舊中華上編的大毒草《中華活頁文選》注釋了兩號(hào),一是47號(hào)唐人王昌齡的《從軍行》七首、盧綸的《塞下曲》六首和宋人陸游的詞《訴衷情》;一是60號(hào)秋瑾詩五首和林覺民的《絕筆書》。同年,又應(yīng)舊中華書局海外組的要求,翻譯了兩本唐人傳奇和兩本聊齋故事,后來有沒有出書也不知道。1964年還替大毒草之一的工農(nóng)通俗文庫寫了一本《文學(xué)家的故事》,后來停止出版,但拿了退稿費(fèi)50元。
我從古典到舊中華上編,十年來為劉鄧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服務(wù),負(fù)責(zé)編輯加工了不少封建糟粕,自己又在報(bào)刊上放毒,先后泡制了三十多篇長短黑文,毒害人民思想健康,罪行非常嚴(yán)重。
至于解放前發(fā)表的反動(dòng)黃色的文藝作品,因?yàn)闀r(shí)隔二三十年,具體篇名已難記憶,有的已經(jīng)輯成小說集出版過的,和替私營出版商編的壞書,以及解放后替人編的和自編自出的投機(jī)書,當(dāng)另作交代,這里僅僅交代我在解放后所寫的黑文。
(選自《芳草地》2012年第2期,本刊略有刪改。)
(實(shí)習(xí)編輯 朱琳)
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海外漢學(xué)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