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國際觀的內政鏡像
孫興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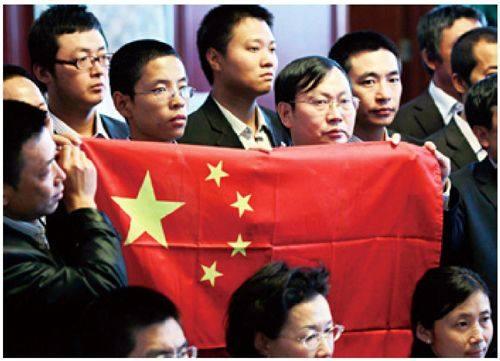
從南海風波到中東變局,從湄公河船員遇難到蘇丹人質事件,國際問題越來越受到普通中國人的關注。中國民眾,尤其是網民,雖然不能直接影響中國外交決策,但卻是中國外交轉型的推動力量。民眾對國際問題的認識,遠遠超出了學術界所討論的“三個主義”或者幾種范式的界限,民眾國際觀的多元化是中國社會思潮多元化的表征,也是中國內政困境的鏡像。
國際觀多元化折射中國社會復雜性
從網絡上紛繁復雜的爭論中,大體可以歸納出以下五種中國民眾國際觀的思想譜系:
第一種,革命浪漫主義。這種觀點將西方尤其是美國視為中國的敵人,動輒以陰謀論來分析中國外交面對的困境。這種觀點與長期以來“革命”的思維訓練息息相關,階級斗爭的理論在“文革”時期泛濫成災,流毒至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文革”的浪漫化粉飾越來越嚴重,對民眾認識國際問題蒙上了一層“血色浪漫”。浪漫主義,忽視或者淡漠規則,而是以個人的意愿或者臆想來猜度世界運行的規律,最典型的是將當代世界的諸種危機歸結為少數精英或者某些神秘組織的操控。陳志武教授將陰謀論比作精神鴉片,可謂一語中的。在一個革命被神化的社會中,需要對革命浪漫主義祛魅,但是智識上的怠惰卻構成了無形的障礙。
第二種,孤立主義。其核心特征在于外交要服務于內政,外交只是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工具。去年中國校車事故頻發,而中國向馬其頓捐助校車一事引發國內輿情反彈;歐債危機重重,中國不能拿本國人的血汗錢去援助歐洲的“笨豬”國家。從這種觀點出發,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只有把自己發展起來,老百姓安居樂業之后,才有可能參與國際事務,承擔國際責任。中國的孤立主義不是源于本國遠離外部喧囂的自信與安全感,而是源于資源有限而弊病叢生的現實的焦慮。這種焦慮或者不滿一方面來自中國與世界橫向比較產生的反差,走出國門的中國人發現,歐美國家的物價更低、福利更多、社會更寬松與平和,相形之下,中國需要把更多的精力與資源用于國內社會建設,有些人更是將一些援助活動比作“寧與友邦,不與家奴”之舉;另一方面,則源于中國歷史上“防御型外交”的傳統,長城便是這種外交文化的反映,文化傳統的慣性使中國容易陷入被動的“救火式”外交。
第三種,實用主義。其精髓是“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國的外交就是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現實主義者也如是說。但是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所說的國家利益不僅包括有形的資本、資源,也包括國家形象、威望這樣無形的資源;而后者所理解的國家利益主要是物質層面。實用主義外交失去了道德規范與倫理的約束,最終的結果是“失道寡助”,在國際舞臺上沒有朋友。中國國內社會道德失范、信仰缺失,實用主義外交便是這種國內境況在外交上的投射。
第四種,自由主義。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使得中國民眾中的自由主義觀點凸現出來。在這些人看來,無論是卡扎菲還是巴沙爾都不值得中國同情,中國應該在安理會投贊成票制裁這些獨裁者。這種觀點以為,推翻獨裁者便可以改變政治秩序,但事實并非如此。網絡上譴責巴沙爾而褒揚哈維爾的觀點比比皆是,從深層來講,這些觀點與其是對國際事件的評點,莫不如說是對國內現狀不滿的宣泄。
第五種,國際主義。這更多地源于中國歷史的經驗與記憶。筆者在整理一次問卷調查時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問及“如果可以穿越時空,你愿意回到哪個時代”時,多數人都選擇了漢唐盛世,而那個文化自由、貿易發達的宋朝卻沒有得到人們的青睞。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漢唐時代的煌煌帝國才是未來中國可以追求或者模仿的典范,而宋朝割地賠款則是一種屈辱。有位學者稱,中國的歷史決定了中國必須做大國,否則老百姓是無法接受的。
大國、大國民與大外交
法國大革命打破了秘密外交的傳統,公共輿論在媒體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當下中國也是如此。雖然民眾無法參與外交決策,但是外交決策機構卻不得不傾聽民眾的聲音。只有大國民才能支撐起一個真正的大國,只有一個大國才有真正的大外交,當然這三者并非單線的決定關系,而是形成一個循環的三角。
中國民眾的國際觀并非單色調的,而是具有流變性和偶然性,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會有不同的態度與表達。終其一點,國際觀更多地源于國內的經驗,培養理性、客觀的國際觀還要從國內入手。
首先,擁有幸福感的國民才能寬容、理性地看待國際問題。一個充斥“官二代”、“富二代”的社會是難以形成開放、多元的言論空間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崇洋媚外,要么以陰謀論抗拒所有的反對者;失勢者帶有難以抹去的受害者情結,要么自怨自艾,要么仇視財富或者權力。如果國內社會是一種維穩的邏輯,那么外交必然是一種救火式的。大外交的視野和戰略需要夯實有力的國內基礎,和諧外交的信心應該源于和諧社會的構建。當中國社會的和諧不再是口號的時候,大外交的民意基礎就會慢慢匯聚。
其次,理性、客觀、人道的媒體是大國民心態的“培養基”。新聞審查、商業利潤制造了大量的信息泡沫,模糊了事實的原貌。沒有建立起媒體自律的社會,必然充滿著夸張、獵奇,以及無謂的炒作。娛樂是一個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潤滑劑,但是如果政治、外交也被娛樂化,那會造成一種可悲的“犬儒主義”盛行。中國逐漸在世界舞臺上“入戲”,世界需要一個有擔當、負責任的中國。娛樂化、炒作帶來的不僅是無效信息的泛濫,更是國民心態的泡沫。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走向世界,媒體也需要與國際接軌,以新聞的專業主義去觸摸世界政治的脈動,以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去感動世界,進而引導中國民眾與世界的“共振”。
再次,持續推進的改革開放為國民提供一個良好的預期。國家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不進行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其中的道理也適用于國民的心態。經濟高歌猛進容易形成暴發戶的心態,但是政治經濟改革一旦陷入停滯甚至倒退則會滋生恐懼、悲觀的情緒。上個世紀大危機時期,羅斯福在就職演講中說了一句鼓舞民心的話:唯一恐懼的是恐懼本身。當國內矛盾叢生的時候,需要以一種改革的決心和意志來穩定民心,用改革的行動塑造國民穩定、良性的預期。唯其如此,才能培育大國民心態和視野。
復次,摒除歷史教育中的“受害者”情結,鍛造國民直面歷史與現實的勇氣,培養大歷史的胸懷。誠然,近代中國是充滿著種種不幸,但是也應該看到,100多年的近代史也是中國社會轉型、國家重構的過程,也是中國學習與模仿世界規則,融入世界的過程。當歷史教科書把跨國公司僅僅視為殖民擴張的幫兇,當下走向世界的中國企業就會面臨一種歷史經驗空白的困境。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選擇性遺忘,便是對未來的褻瀆。
最后,大外交不僅需要民意的支撐,也需要制度的設計。美國國務院被稱為世界的外交部,而美國國務卿的權勢僅次于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專職外交與國防事務,俄羅斯也是如此。羸弱的制度是難以支撐起大國大外交的,更無法培育大國民的心態與風范。在未來,設立國家級外交與安全委員會已經勢在必行,集中統一的外交決策機構與多元外交渠道并不矛盾,前者負責研判、制定國家大戰略,后者是靈活有效的實現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