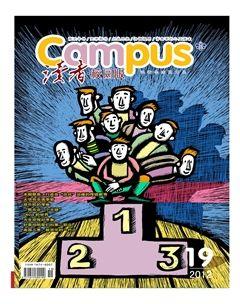救孩子與救教材
徐迅雷

幾位中國(guó)教育界的思想者,做了一件功德無(wú)量的事,他們拿一把輕巧的柳葉刀,對(duì)準(zhǔn)小學(xué)語(yǔ)文課本這個(gè)重要的部位,動(dòng)了一次手術(shù)。他們聯(lián)合組成研究團(tuán)隊(duì),以課題組的方式,認(rèn)真披閱教材文本,深入分析思考,得出20萬(wàn)字的研究成果,此事一度引起強(qiáng)烈反響,如今成就了一本書(shū)《救救孩子:小學(xué)語(yǔ)文教材批判》(郭初陽(yáng)、蔡朝陽(yáng)、呂棟等著,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這件事情恐怕是要被寫(xiě)進(jìn)當(dāng)代中國(guó)教育史的。感謝以郭初陽(yáng)、蔡朝陽(yáng)、呂棟這三位為主的作者們,他們都是中學(xué)語(yǔ)文老師,都是有獨(dú)立思想的年輕人。
生于1973年、著有《言說(shuō)抵抗沉默》的郭初陽(yáng),書(shū)中自我簡(jiǎn)介為“獨(dú)立語(yǔ)文教師”,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gè)稱謂。從杭州著名的外國(guó)語(yǔ)學(xué)校辭職出來(lái)后,他成了語(yǔ)文教育的“獨(dú)立”者。獨(dú)立是一種姿態(tài),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品格。一個(gè)人,無(wú)論是學(xué)生還是先生,無(wú)論是學(xué)者還是作者,無(wú)論是領(lǐng)導(dǎo)者還是被領(lǐng)導(dǎo)者,都應(yīng)該有自己獨(dú)立思考的能力,否則這就是一個(g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世界。
沒(méi)有獨(dú)立的精神,缺乏獨(dú)立的思考,后果將是什么?我剛剛看了里芬斯塔爾制作于1934年的紀(jì)錄片《意志的勝利》,那是“法西斯美學(xué)”的大制作。這位深得希特勒欣賞的德國(guó)女藝術(shù)家,是電影史上最具爭(zhēng)議的導(dǎo)演之一。她通過(guò)電影語(yǔ)言,描寫(xiě)了1934年在紐倫堡舉行的德國(guó)納粹黨第六屆代表大會(huì)以及相關(guān)的各種大規(guī)模集會(huì)。“君臨天下”的希特勒,一次次“激情澎湃”的演講,頂禮膜拜的公眾,旗海、人海,萬(wàn)眾一心禮贊希特勒,萬(wàn)臂指向同一個(gè)方向……那真是一個(gè)國(guó)家、一個(gè)民族,一個(gè)黨、一個(gè)主義,一個(gè)領(lǐng)袖、一個(gè)元首,總而言之是“一個(gè)思想”。這就是可怕的大集會(huì)思想場(chǎng)景,盲目崇拜、盲目忠誠(chéng)—在那樣的場(chǎng)景中,人是沒(méi)有獨(dú)立思考能力的,每個(gè)人都成了其中的“一分子”,只明白整齊劃一,只曉得個(gè)人崇拜。這就是思想被整齊化、統(tǒng)一化、格式化的結(jié)果。這多么危險(xiǎn)、多么可怕,其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一個(gè)人獨(dú)立思考的能力,離不開(kāi)教育的熏陶培養(yǎng)。但現(xiàn)今的中國(guó)教育,一個(gè)大綱,一種課本,一張?jiān)嚲恚粋€(gè)課堂,一個(gè)模式—應(yīng)試教育的模式,幻想著播下素質(zhì)教育的龍種,收獲的卻是應(yīng)試教育的跳蚤。而諸多教師本身就是應(yīng)試教育的產(chǎn)物,“教材云教師亦云”,教師們都在同一個(gè)模子里打轉(zhuǎn),最稀缺的是獨(dú)立思考的精神與能力。
應(yīng)試教育愈演愈烈的中國(guó)教育,確實(shí)病得不輕,而教材就是重要的病灶之一。要救孩子,得先救教材。好在現(xiàn)在有一批勇于獨(dú)立思考的教育者,對(duì)教材中存在的種種問(wèn)題予以揭露。他們著重從研究“母親、母愛(ài)”的課文入手,揭示那些虛構(gòu)的、虛假的、虛偽的、專制的、扭曲的、夸大的、殘缺的、濫情的母親和母愛(ài)形象,先破后立,推薦閱讀學(xué)習(xí)真正的母愛(ài)經(jīng)典佳作。通過(guò)該書(shū),作者告訴我們:許多語(yǔ)文課文存在著種種價(jià)值觀的問(wèn)題,這可是最直接、最嚴(yán)重而且也是最本質(zhì)的問(wèn)題。
教育與每個(gè)人息息相關(guān),如果教材錯(cuò)誤了,教育就不可能好。語(yǔ)文教材,是給一個(gè)人乃至一個(gè)民族奠定人文底蘊(yùn)的。錯(cuò)誤、失誤的課本,就是讓孩子們吃錯(cuò)藥—很清楚,吃錯(cuò)的藥大抵就是毒藥,盡管可能不是急性中毒而是慢性中毒。在世界教育已經(jīng)發(fā)展到現(xiàn)代化的階段,在美國(guó)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拿諾貝爾獎(jiǎng)拿到手軟的今天,我們?nèi)绻€是拿一些錯(cuò)誤的教材忽悠、誤導(dǎo)、“催眠”下一代,這是無(wú)論如何都說(shuō)不過(guò)去的。
我們的孩子當(dāng)中,并不是缺少獨(dú)立思考的種子與嫩芽,可怕的是被格式化的教育扼殺了。很多年前,我看過(guò)一個(gè)報(bào)道,是說(shuō)一位小學(xué)女生在學(xué)習(xí)《小馬過(guò)河》時(shí),大膽向老師提出:“寸步不離老馬媽媽的小馬,不可能一直被關(guān)在馬棚里,否則它不僅不知道小河的深淺,也不會(huì)知道磨坊在哪里,那怎么馱半口袋麥子去磨坊?它既然知道磨坊在河的那邊,那么一定是曾經(jīng)跟著老馬媽媽去過(guò)的。既然它曾經(jīng)去過(guò),那么它一定也曉得小河的深淺……”你瞧,孩子的思想是多么厲害!《小馬過(guò)河》是一篇讓人學(xué)過(guò)就不會(huì)忘記的好寓言,而且老馬媽媽就是鼓勵(lì)小馬獨(dú)立思考、勇于實(shí)踐的。在《救救孩子:小學(xué)語(yǔ)文教材批判》一書(shū)中,對(duì)這篇課文所評(píng)的星級(jí)是最高的五星級(jí),這個(gè)我也贊同。但是有獨(dú)立思考能力的孩子,仍然可以對(duì)它提出自己的“質(zhì)疑”。教材是用來(lái)學(xué)習(xí)的,但也是可以用來(lái)研究、探討的;教材不是圣經(jīng),不是膜拜的對(duì)象。編寫(xiě)教材也好,審視教材也罷,都需要“獨(dú)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課文的選取、教材的修編,完全可以向百年前學(xué)習(xí)。最近我在《深圳商報(bào)》上看到一篇報(bào)道說(shuō),人文社科系列讀物《讀庫(kù)》的主編張立憲先生,正在進(jìn)行一個(gè)龐大的工程—整理出版民國(guó)老課本,已篩選確定了8套,總共有三四百本。有人曾看到過(guò)這套課本,感嘆了一句:“‘錢(qián)學(xué)森之問(wèn)的答案就在這里!”而《讀庫(kù)1001》的第一篇就是《老課本》(作者鄧康延),開(kāi)頭那句話概況得非常到位:“民國(guó)年間,兵荒馬亂,但教育未廢止。上有信念,下有常識(shí),小學(xué)課本集二者于一身。”那是商務(wù)印書(shū)館印制的課本,其中“新國(guó)文”第一冊(cè)第8課是“天地日月”4個(gè)字。是啊,“天地日月”是永恒的,“萬(wàn)歲”才是速朽的。這是常識(shí)啊!幾年前,我曾買(mǎi)到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文獻(xiàn)出版社重新出版的《開(kāi)明國(guó)語(yǔ)課本》(上、下冊(cè)),那是葉圣陶先生寫(xiě)的課文,豐子愷先生繪的插圖,1932年由上海開(kāi)明書(shū)店出版。讀它,那種親切、溫暖的感覺(jué)自然而然地彌漫開(kāi)來(lái)……
《救救孩子:小學(xué)語(yǔ)文教材批判》一書(shū)的扉頁(yè),記錄了康德的一句名言:“父母在教育孩子時(shí),通常只是讓他們適應(yīng)當(dāng)前的世界—即使它是個(gè)墮落的世界。”確實(shí),“適應(yīng)”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現(xiàn)實(shí),但好的老師要告訴孩子這個(gè)世界的“墮落”,何處墮落、為何墮落,否則就是自欺欺人。只有告訴孩子這個(gè)世界的“墮落”,才能在孩子身上種下改變這個(gè)世界的種子。那么,到了一定的時(shí)候,長(zhǎng)大的孩子中總會(huì)有人著力去改變這個(gè)世界,一點(diǎn)點(diǎn)、一步步的改變都是寶貴的,從而促使這個(gè)世界發(fā)展、進(jìn)步,就像這幾位對(duì)小學(xué)語(yǔ)文教材進(jìn)行批判、既破又立的年輕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