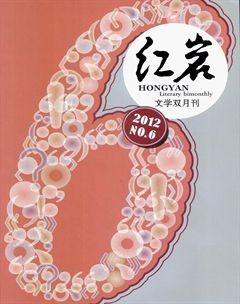從記憶里駛出來的汽車
2012-05-08 03:40:12李海洲
紅巖
2012年6期
李海洲
1
在我淺灰色的記憶里,九十年代初期的重慶就像一個微型的火柴盒。城市暫時還沒有迎來它大規模的開發時代,火柴盒的周圍,是一些綠油油的樹木和積滿淺水的稻田,而火柴盒的內部,矮小的建筑隨著山勢起伏,略顯孤單的街道上,總是奔跑著趾高氣揚的汽車。在我的記憶里,那時候的汽車全都開得像風一樣快,一百米之外,喇叭就開始鳴叫,亢奮的聲音由遠及近,一直會近距離地追進你的耳朵,追到你不由自主地向它行注目禮為止。那時候,汽車司機是高檔職業,幾乎每個人都是一副金領的派頭,即使談戀愛,好像也隨時可以把任何一位姑娘塞進后備廂里帶走。
我的父親是一位資深警察,他除了喜歡用皮帶和棍棒問候頑劣的我之外,就是喜歡駕駛一輛捷達警車在城市里縱橫捭闔。重慶的道路蜿蜒曲折,那時的路面大多由碎石子鋪成,捷達警車帶上我,快樂地顛簸著,快樂地行駛在有些凹凸不平的路面。在我少年時代的記憶深處,一個比較詩意的鏡頭就是:制服閃亮的父親,一邊哼著“駿馬奔馳在遼闊的草原”,一邊駕車帶著他頑劣的兒子沖向陽光燦爛的街頭。
那些年,每到春節,這輛車就會載著父親和我奔赴老家守歲。我那愁腸百結的老家,離遙遠的主城大約有200多公里距離,其間還隔著兩座后來被隧道直接貫穿的大山。當時的盤山公路,曲折陡峭,彎道密布,應該不弱于后來我做旅游雜志時多次經過的川藏線。……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環球人文地理(2022年8期)2022-09-21 03:49:42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11期)2019-12-30 06:08:38
汽車與安全(2019年9期)2019-11-22 09:48:03
重慶行政(公共人物)(2018年5期)2018-11-06 07:42:18
今日重慶(2017年5期)2017-07-05 12:52:25
作文大王·低年級(2016年4期)2016-04-18 00:24:37
決策探索(2014年21期)2014-11-25 12:29:50
漢語世界(2012年2期)2012-03-25 13:01:27